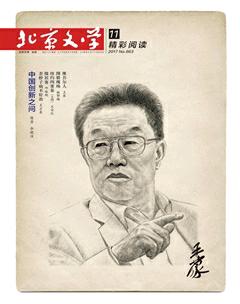叶骑小小说两篇
张二爷
张二爷有些饿了,去桥头买了一碗肉丝粉。
碗很大,是人们常说的海碗,但里面只有半碗米粉。
过了一会儿,二爷对面来了一个年轻后生,点了一碗猪脚粉,还有一碗煎饺。
二爷望着煎饺有些发愣,猛然觉得喉咙里痒得难受,对着煎饺打了一个喷嚏,一张嘴差点喷进别人碗里。
年轻后生满脸通红,脖子鼓得像粉店的烟筒。
后生闷着头,吃了米粉,转身走出店门。
二爷见桌上还剩一碗煎饺,就问,后生,这煎饺不要了?
年轻后生头也不回地说,留着喂狗。
二爷轻蔑一笑,心里骂着,狗日的,还嘴硬。一碗煎饺下了肚。
晚上,张二爷吃了晚饭,喜欢坐在桥头的杂货店歇凉,杂货店卖油、卖盐,也卖酒。
二爷点了半斤苞谷烧,跟村里另外两个光棍老五、生华醉成一个麻花,互相说起狠劲来。
老五说,我年轻的时候,在城里打工,挣了足足十万块钱,结果坐车回来的时候被人顺走了,我日死他妈,你们这辈子见过这么多钱?
生华说,我在城里的时候,睡了不知道多少女人,晚上县里播“晚间新闻”的那婆娘,我都睡过,你们睡过没有?
两人说完看着二爷。二爷抿了一口酒,问,张权你们认不认识?
两人说,县委书记哪个不认识。
二爷突然从地上跳起来,说,我日死你先人,我在他办公室拉过一泡屎,你们两个狗日的谁拉过?
说完,二爷摇摇晃晃回家了。
二爷曾经在县城当过农民工,县委大院就是他们修的,至于他有没有在县委书记办公室拉过屎,那就真没人知道了。
七月,葡萄上市。张二爷说,葡萄就像女人胸前的那啥,看着醉人。刚开始,葡萄摆在路边,要十五块钱一斤,后来成了十块钱一斤,再后来成了五块。
二爷走到一家小摊,问,葡萄怎么卖?
生意人说,十块钱两斤。
二爷把葡萄拿在手上掂量了一阵,说,现在还不是吃葡萄的时候,等卖到十块钱三斤,那时辰正好。
二爷说完,从村尾刘寡妇的门前走过。
刘寡妇的门是关着的,五年前,刘寡妇就不在了。
刘寡妇还住在屋里的时候,是寨子的一大祸害,那几年,全村的男人都成了土狗,追着屋里的骚气跑。
后来,劉寡妇怀孕了,生下孩子狗仔,寨子里一夜炸了锅。有的人说,这刘寡妇败坏门风,应该拉去沉潭;有的人说,这一村男人贱得无法,也该阉了喂狗。不过,说归说,日子跟往常还是没什么两样。
刘寡妇就这样一个人带着孩子过活,孩子他爹一直没有出现。第二年冬天,狗仔夭折了,刘寡妇家徒四壁,孩子活活病死在穷冬的炕头上。那段日子,没有一个男人敢去敲刘寡妇的门,光棍们说,刘寡妇见人就咬,刘寡妇发了疯。
寨子里有个算命的,给刘寡妇算了一卦,说她可以撑到开春。但没几天,刘寡妇也僵在那床穿孔的棉絮里,算命先生就此丢了饭碗。
刘寡妇死了,寨子里关于她的流言也就慢慢散了。有些女人嘴如茅厕,但都不敢明说,“死者为大”这个道理,她们还是懂得。
天麻麻黑,二爷又在村头跟寨里的几个光棍喝酒。
那狗日的女人,天天在外面跟人睡觉。
那狗日的女人,连个孩子也养不活。
那狗日的女人,还把自己养死了。
那狗日的女人,……她就是个狗日的。
二爷一喝酒,就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周围的人见他犯了忌,一起把他架回了家。
二爷在家里躺了三天三夜没见出门,大伙知道出事了。第四天,几个村干部破门而入,二爷躺在床上,嘴巴里只剩最后一口气。
村干部凑过去,二爷的声息若有若无。
我有两个心事。
二爷,你说。
我想吃串葡萄。
村干部风风火火赶到村头买来葡萄。
二爷闭着眼睛,尝了尝,问,葡萄怎么卖?
村干部说,十块钱两斤。
二爷奄奄一笑,狗日的,十块钱两斤的葡萄到底比三斤的好吃。
过了老久,村干部又问,另外一件事呢?
二爷油尽灯枯,暗淡的眼睛亮了一下,说,把我跟刘寡妇葬在一起吧,我对不住她娘儿俩。
二爷说完,一颗豆大的眼泪落在冰冷的枕头上。
最后的猎人
我睁开眼,雪花漫天,像一场缤纷的葬礼。
我静静望着灰茫的天空,大片的雪花迎风飘散,落在我的额头,彻骨的冰寒,几乎将我冻结在地。
我微微仰起头颅,打量四周,狼藉的地面,逼仄的土墙,我想挣扎着站起身来,但钻心的疼痛让我瘫软在地,我的双腿已被尖锐的木桩刺穿。
这是一个陷阱。
一个我们曾经为捕获猎物而设下的陷阱,若不是时间久远,坑底大多削尖的木桩已经腐烂,或许它们中的一根,早已穿过我的心脏。
我挣扎挪动身躯,倚着坑底的墙壁坐起身子。
土墙高耸过人,我的双腿早已血肉模糊。曾经,我们设下的陷阱,今日已然成为了自己的坟墓。
“这个陷阱会是我布下的吗?”
我有些荒诞地问自己。
春去秋来,我们穿行在这片熟悉的土地,知道哪里有一座小山,哪里有一条浅河,我们了解她,就像了解自己的母亲。我们在山高林茂的地方设下陷阱,等着猎物自投罗网,但谁又曾想到,有一天,时光终将把我们打败,让一个苍老的猎人成为自己的猎物。
我从四周摭拾了一些枯枝败叶,掏出火柴,生了一堆火。火苗很微弱,在风雪中苟延残喘,我又加了些枝叶,火堆明亮起来,在雪地里画出一个昏黄的圈。
“兴许,会有一个老伙计恰巧从这里路过。”
我安慰自己。
但片刻,又陷入了深深的绝望,在这寥廓的山林里,我已是最后的猎人。
我不由得想起身边的这群老伙计。
那时,我们黄毛乳臭,壮志萦怀,冬天的风雪,不是寒冷、阒寂的悲歌,而是铿锵、激昂的号角,我们骑上骏马,呼鹰逐兔,驱马游猎,尽情驰骋在这片土地上。但如今,岁月啃噬了他们的身躯,流光腐蚀了他们的枪膛,他们颤抖的双手再也无力举起猎枪,枯竭的躯干也终将交还给这片挚爱的土地。
我们已经老了,是放下猎枪的时候了。
三天前,我收到儿子的来信,在信里,儿子一再告诫我放弃今年初冬的狩猎,他说,他在城里打拼得不错,可以接我过去居住,也能很好地解决我常年食用兽肉而带来的高血脂、高血压问题,狩猎不是唯一的生存方式,我应该接受新的生活。
然而,我却是一个猎人,一个以山林为家的乡巴佬。我的身体开始枯槁,视线变得模糊,但我还能行走,还能辨出雪地上的足迹,我必须接受这片土地发出的邀请,一个没有猎枪的猎人,只是一个稻草人,一个剥去了灵魂的可怜虫。
天色愈加灰暗了,黑夜终将来临。周围能够捡拾的枯枝,已经燃烧殆尽,火堆绝望地发出最后一丝光亮。
我闭上双眼,抚着手中的猎枪,等待这最后时刻的到来。
黑暗、死寂……我孤独对抗着这寒夜的侵袭,隐约感到身边缺少了什么。
哦,我的老伙伴,乌托。
清晨,我们一起走出家门,步入山林,尽管你已如我一样老去,但步伐仍旧矫健,双耳依然聪敏。悲剧发生那一刻,你一定耳闻目睹,但现在,陷阱里既没有你的尸骨,四周也没有你的吠叫,你又会身在何处呢?
我的伙伴,你一定朝家的方向飞奔而去了吧。这崇山峻岭,万千沟壑,你能否安然跨过?这雪域千里,冰寒彻骨,你能否安好到家?
风雪愈大了,我紧紧蜷曲在墙角,雪花几乎将我掩埋。我亲爱的老伙伴啊,这片土地亦是你出生、成长的地方,外面风再大,雪再深,我知道,你总能找到回家的路。
(标题书法:熊尉东)
责任编辑 张 哲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