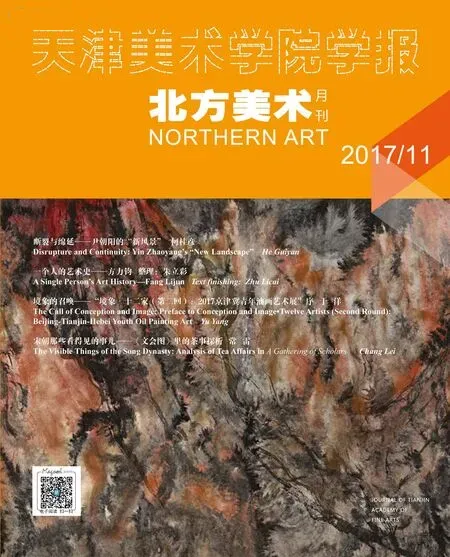典型论与左江花山岩画人形图像研究
梁穆穆 陈 锋 Liang Mumu and Chen Feng
传统的对于左江花山岩画的研究,都在努力研究图像所代表的事物,不管是人物图像,动物图像,还是器物图像,并且在这个方面已经取得了较大的研究成果。根据左江流域考古研究,已经发现了较多的武器(长剑、环首刀、匕首等)、乐器(羊角钮钟)等和花山崖壁画上的图像非常相似。这些图像和现实的物之间可以确立为一一对应的关系。如图1所示。很多研究者尝试将其他图像与现实中的事物一一对应起来,如,梁庭望认为崖画上投影式的形象是壮族祖先供奉的神,那些蛙形舞姿的形象是古代壮族祖先所崇敬的民族守护神——蛙神。[1]他将人形图像对应为蛙神,这有一定的根据。在壮族民间神话传说中,在农业经济时代,蛙被认为是雷神之子,被作为民族的守护神。但也有很多专家把花山岩画人形图像当成人物造型。总的来说,对于人物图像、动物图像和圆形图像的具体所指目前还有较大的争议。人们对于这些图像所指的东西有不同的理解,花山岩画的研究也到了一个瓶颈阶段。
本文试图从绘画者的角度研究图像与现实所指事物之间的关系,如图2所示。实际情况是现实事物与图像之间不是一种直接的关联(所以用虚线来表示),而必须通过绘画者的艺术加工。绘画者在对现实事物进行理解、加工、记忆等过程之后,在一定的条件下,基于自身的绘画技术和绘画条件,经过一定的艺术加工将图像画在崖壁之上。在整个过程中,绘画者发挥了积极能动的作用。
绘画者是如何处理现实事物的?一般来说,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对现实的临摹;一种是绘画者的表现(这也是西方文艺界关于艺术创作的两个重要观点:模仿说和表现说)。模仿是现实事物的反映,而表现则体现了绘画者的主观能动性。尤其是每组图像中所要表达的主题,绘画者通过一系列的图像、图像组合的形态等来记叙一个个事件,讲述一个个故事等。可以肯定这些事件和故事等在当时是人人熟知的事情。所以这些绘画创作才能够持续进行。也就是说绘画者受到了整个部落或者首领的持续供给,才具备创作绘画的前提条件。这样图像所要表现的内容既是绘画者的一种创造性活动,也体现了骆越先民的集体诉求。这就必然要求绘画者在创作的过程中要抓住典型形象,这个形象可以反映现实,也可以是多种形象的结合。对于绘画行为本身而言,在创作上也是要表现创作对象一刹那的典型情景。这些形象为骆越先民集体接受、喜爱。在整个创作过程中,骆越先民发挥了极大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描绘了骆越先民典型的艺术文化生活,这也赋予了岩画本身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极大的艺术价值。

图1

图2
一、典型论与左江花山岩画人形图像
(一)典型论
典型论是一种西方文论,其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从亚里士多德开创到17世纪前,典型论的主要观点是类型说,强调典型的普遍性和类型性。18世纪后,以个性典型理论为主导。19世纪8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发展了典型论,对典型的共性、个性的关系作了辩证统一的总结。[2]
蔡仪认为艺术美的根源在于客观现实本身,艺术作品能够达到艺术美,就在于它反映了美的规律、典型的规律。艺术典型的塑造主要是通过艺术家的主观精神的分析和综合、抽象和具象的能力,对现实生活中的事物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改造,集中概括,最后创造出以突出、鲜明的现象或个别性充分地表现其本质或普遍性的艺术形象,即艺术典型形象,也即美的形象。典型化的过程是艺术家所进行的剔除事物的偶然的现象,突出它的本质,剥开假象、显露真象的过程。[3]
典型论主要指的是典型环境下典型人物的塑造和典型事件的记述。这些典型人物或者事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特征,从典型论出发去研究花山岩画人形图像有重要的意义。
(二)典型论与左江花山岩画人形图像
花山岩画的人物图像分为正身人像和侧身人像。图像的形象比较程式化,都是双腿向外下蹲、双手向两边弯肘上举的形象。这种形象类似于青蛙的造型,也可能是人们在狂欢时刻的一种舞蹈动作。作为舞蹈来说,很具有表现力和视觉冲击力。对于蛙的造型来说,这种造型具有统一性。但是一群青蛙跳舞,缺乏生活的原型,不具有典型性特征。对于舞蹈动作来说,这种造型具有共性特征。在表现方法上虽然可能有一定的夸张,但考虑到乐器的使用对于人们舞蹈动作的整齐有一定的约束、引导作用,那么舞蹈造型的可能性也是不可忽视的。可能性较大的是绘画者将两个形象融合在了一起,这样可以使图像具有更大的阐释空间和意义张力。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到绘画者的主观能动性。由于绘画者的参与,图像与现实事物之间已经不能直接对等(虽然在当时图像的意义可以说是确定的)。这使绘画的内容和意义对于后来者有一定的阐释空间。
在国内外其他区域虽然发现有类似的蹲踞式人形形象,但整体上与花山岩画还是有很大的差异。花山岩画在创作上采用的是“影子画法”,省略了较多的细节刻画。这样就使图像具有了一定的共性特征,具有了类的普遍性,但影子是真人的投射,所以具有真人的动态、特征,具有真人的神韵。这又使图像具有了个性特征。在花山岩画图像的创作上这种共性特征和个性特征很好地融合了起来,塑造了千古典型形象——花山岩画图像。
花山岩画的圆形图像,有单环形图像、双环形图像、三环形图像、实心圆形图像和空心圆形图像。对于这些图像,有的人认为是铜鼓鼓面图像,有的人认为可能是日月星辰等天体的图像。有的人认为是盾牌、铜锣或车轮。从这些猜测可以看到,后人也是通过生活中的典型形象来认识花山岩画的内容的。
二、花山岩画的主题内容
花山岩画的图像造型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绘画者抓住了当时社会的主要活动场景,用典型的形象栩栩如生地表现了古骆越先民丰富的社会画面。这些图像对于了解骆越先民的艺术文化生活有极大的价值。左江花山岩画究竟要表现什么内容,覃圣敏总结了下几种说法:“战争”说、“语言符号”说、“祭神”说和“巫术”说。[4]张利群认为花山岩画的影像造型是先民生命意识的表现,是一种原始宗教意识,体现为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和灵魂崇拜。[5]通过典型论的视角对其图像进行分析,作者认为其主题内容可能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战争主题
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在原始社会末期,阶级社会初期,生产发展,人口增加,部落或大家庭为了争夺私有财产,包括土地、财物等,或者因为其他矛盾和冲突,相互之间经常发生械斗。从历史记载结合花山岩画上的图像来看,每组图像中大都有一个高大正身人像,腰挎环首刀或者铜剑,有的手拿匕首,四周是一些小的图像环绕,高举双手在舞蹈。这些图像具有一定的典型性。那么花山岩画是否与战争有关呢?答案是可能的。在花山岩画主题内容中可能有表达对战争胜利的期望,保佑部落战士平安回家的祝愿。但这种功能可能是附带的。根据典型论,战争的主题一般的表现手段是战争场面。但整个左江的花山岩画没有战争场面的描写,如果当时的艺术家要反映战争主题,却不进行战争场面的描写,这也是难以想象的。其次画面上刀剑的出现并不多。拥有刀剑的人主要是一些居于画面中心的正身人像,刀剑的功能可能是象征性的,主要象征刀剑持有者的权力和地位。
2)神灵崇拜、祖先崇拜
骆越先民最初对自然、人的生死问题认识是有限的,他们面对无法控制的事情及其相伴而来的恐惧时,将自身的生死、生存与发展等寄托于外在事物。人们通过祭祀活动,希望自己的祖先,或者部落信奉的神灵,或者自己的祖先能与神灵相通,来帮助自己实现愿望,或者使自己得到心灵的安慰。从很多组完整的图像组合可以得到这个结论。在每组图像中,居于每组图像中心的,大多有一个高大正身人像,大多都是腰挎环首刀,高大勇猛。周围的人像围着他,或者正面或者侧面在欢舞。高大正身人像的身份是谁?是领舞的巫师?是骆越先民的祖先?是部落首领?还是他们所崇拜的神?这从图像上很难推测,但在先民的心目中一定有着神一样的地位,或者是客体或者是主体。一般说来,远古神灵的能力是同时代的人所无法达到和超越的,这样更容易让人虔诚地崇拜,所以是远古神灵或者祖先的可能性更大。这里可以结合骆越先民的神话传说来分析。壮族先民英雄为了民族福利,有很多神迹,做了很多牺牲,甚至是生命。壮族始祖布洛陀神,是壮族人民的创始神、始祖神和道德神,为了人类的福祉,与各种邪恶进行着不断的斗争。壮族地区的神话故事《布伯》,描述了布伯为了人类与管水的雷王斗争的故事等。在布伯之后,另一位民族英雄岑逊应运而生,他用神牛劈山犁河,就是现在广西境内的左右江和红水河。还有射下11个太阳的侯野等。[6][7]他们都为骆越人民的生存发展做出了贡献,或者与自然灾害做斗争或者与外敌做斗争。这些都体现了骆越先民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顽强的生命意识。在一些画面中为什么会有裸身图像或者生殖活动图像呢?这也印证了花山岩画更可能是一种祭祀活动和巫术活动,可能和种族的延续有关,祭祀祖先活动希望得到祖先保佑,子孙绵延。希望祖先能够投胎转世,为子孙后代造福。潘其旭认为花山岩画是一幅幅原始歌舞祭祀图,是一种多职能的繁复的混融性结构,表现了他们萌芽状态的宗教观念,体现为一种图腾祖先崇拜仪式,又体现了先民的超自然信仰。通过影响自然界的虚幻手段来为现实需要服务的巫术仪式,担负多种社会职能,用以满足人们的求知、教育、抒情和审美等方面的需要。[8]
花山岩画所绘制的人形图像反映了壮族先民重要的生活场景,真实地再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这些生动的人物形象,使花山岩画的真实性达到了时代和历史真实的高度。这些所塑造的形象都具有深广的概括性,同时又具有自己的个性特征。这种时代的典型性形象使其具有了极大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三、花山岩画的艺术价值
蓝直荣在1985年花山岩画考察日记中提到了当时考察团对于花山岩画的评价:“左江崖壁画以其作画条件之艰险,画面规模之宏大,图像之高大密集,风格之古朴独特,在国内外都是罕见的。”[9]花山岩画规模宏大,图像众多,有的图像高达3米多,作画条件艰难,画风古朴。这些都使花山岩画不同于国内外的其他类岩画。法国考古学家让•克劳兹教授认为花山岩画非常独特,而独特性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列条件中是排第一位的。这种独特性包括选址地点、善用自然景观、岩画元素系统等。[10]花山岩画的独特性使它在国内外岩画领域成为一种独特的岩画类型,具有典型性特征。这也使花山岩画具有了重要的艺术价值。
花山岩画的典型性图像是先民生活的凝练,体现了骆越先民共性的艺术文化生活,这使图像具有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也使花山岩画具有了极高的艺术价值。恩格斯说:“一切观念都来自经验,都是现实的反映——正确的或歪曲的反映。反映是对客观事物的复写、摄影、镜像。”[11]反映的对象来自于生活的原型,左江花山岩画反映了骆越先民的集体生活。左江花山岩画的绘制是骆越先民集体创作的产品,体现了他们的集体意识。这种意识应该是来自于生活经验的积累,和对生活长久的思考,是现实在艺术家头脑中的反映。从花山岩画可以看到骆越先民广阔的社会艺术文化生活,一个个图像符号向后来的读者传递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岩画主要分布于沿河两岸,这说明骆越先民逐水而居的生活,岩画上的船造型,说明了当时的交通工具,也体现了骆越先民有了一定的造船技术。岩画上的动物图像,可能是狗和鸟类,反映了骆越先民有了畜牧业养殖活动。岩画上,正身人的头上大多都有头饰,种类繁多。从头饰文化上可以看出先民的精神追求,对美的热爱,他们通过各种头饰装饰自己,提高个人的魅力。花山岩画上的很多圆形图像,有些内带芒星、芒线,与铜鼓鼓面图形非常相似,可能是铜鼓。还有一些钟铃图像与广西境内考古出土的战国时期的钟铃非常相似。这些图像可能反映了骆越先民在绘画之前已经有了丰富的音乐生活,进行了大量的音乐创作实践。这样才会在祭祀时,选择正确的音乐去激发人们的舞蹈冲动,让人们忘情狂欢,以达到娱人娱神的目的。这些乐器及其正身人物图像所佩带的环首刀、铜剑与考古发现在造型上是一致的,或者说非常接近。这反映了当时人们有了一定的工业技术——青铜铸造技术,或者表明骆越先民和中原地区有了一定的交往。在每组岩画图像中,图像大小、主次、装饰等的差异,可能反映了参与祭祀活动的人群在身份地位上的差别。从壁画上我们还可以看到骆越先民对生活的渴望,渴望人丁兴旺,丰衣足食。
花山岩画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活动。画师在绘画的过程中,将现实的祭祀场景以镜像的模式记录在头脑中,在观察祭祀场景时,一个个人像、物象都是立体的,画师需要将这些图像重新排列在一个平面上,涉及一个复杂的艺术加工过程。如何在平面上去表现一个立体的图像,图像之间的位置关系如何排列,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从花山岩画上可以看到有很多组图像都有正身人像和侧身人像,人像用上下左右的排列来表明位置关系。在图像处理和颜料使用上都体现了一种创造的激情。花山岩画图像,所有的正身人像和侧身人像都是双手高举,曲蹲双腿,似蛙状,给人一种欢腾、跳跃、非常愉快的感受。这种画面应该是画师采用了一种夸张的手法来表现当时祭祀的场面,这是一种创造性的表现方法。
四、结语
花山岩画的图像和所体现的内容对于后来者都有极大的艺术价值,它是骆越先民生活、信仰、艺术、文化等的反映。岩画图像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器物、动物图像。这些图像对于后人了解骆越先民的历史文化生活、对于现代绘画创作都有极大的价值。张玉能认为典型是具有极高历史价值的艺术形象。[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