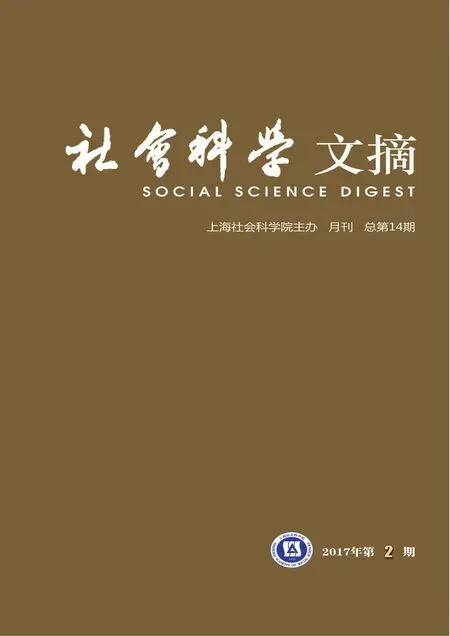情感结构视野下的城乡关系史书写
文/徐德林
情感结构视野下的城乡关系史书写
文/徐德林
传统乡村与城市关系发微
1973年,雷蒙·威廉斯出版了旨在考察和探讨“如何阅读英国乡村宅第诗歌”的理论著作《乡村与城市》。为了挑战半是想象,半是观察得来的缩减惯例,威廉斯研读了多部以乡村和城市为主题的英国文学作品,发现了一种定型化的、二元对立式的乡村与城市关系:
关于乡村,人们已得出那是一种自然生活方式的观念:宁静、纯洁和质朴的美德。关于城市,人们已然得出那是一个如愿以偿的中心的观念:知识、交流和光明。人们也已然形成强烈的对立性联想:城市是喧嚣、俗气和充满野心的地方,而乡村则是落后、愚昧和处处受限的地方。
这样的“对立性联想”不但很有传统,而且早在城市开始显影为一种独立的机体存在时就被固定了下来,引发了“从维吉尔时代一直延续到我们这一代的一种生活方式突然中止了”之类观点,催生了以“消失的农村经济”“过去的好日子”“黄金时代”为能指的怀旧情绪,其结果是文人把情感投向了代表“宁静、纯洁和质朴的美德”的乡村。乡村与城市的对比见诸文人所挪用的意象的截然不同:“乡村的一般意象是一个关乎过去的意象,城市的一般意象是一个关乎未来的意象”;在“一个未被定义的现在”、在“一个被体验为一种张力的”现在,乡村与城市的对比被“自然地”用于证实关乎“一种关乎冲动的尚未解决的分裂和冲突”。所以,华兹华斯等人的作品中存在一种情感结构,就是“关于乡村的观念即关于童年的观念”,它“常常被转化为关乎乡村往昔的幻觉:接连不断的、不停地回溯的‘童年时代的快乐英格兰’”。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未被定义”“被体验为一种张力”的现状导致了学人们的著述中不乏英格兰农村“现在正在消失”之类观点,但他们眼中的“现在”却始终像自动扶梯一样向前移动。比如,在利维斯和汤普森看来,“旧英格兰”的“有机社会”消失于他们出版《文化与环境:批评意识的培养》的1933年的“最近”;艾略特坚信,古老的乡村英格兰终结于1820年代和1830年代初。所以,向后追溯可谓是文人的一种情感结构,不但导致了上述二元对立的乡村与城市及其关系认知的定型化,而且引发了一种“田园符咒”——文人对乡村的喜爱引发对城市的憎恶,而他们对城市的憎恶又引发对乡村的喜爱。在基于这一情感结构的乡村与城市叙述中,乡村与城市真实的历史被遮蔽、乡村与城市关系被错位也就在所难免。既然“真正的历史历来都是令人吃惊地形形色色的”,任何人但凡旨在考察乡村与城市的真实图景,都必须质疑、打破定型化的乡村与城市叙述,必须把城市与乡村的关系视作“一个社会、文学和思想史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威廉斯指出,“对这些叙述,我们必须探究的并不是历史错误,而是历史视角”;视角的选择导致了“证人”——观察者——在面对复杂的历史状况时的选择性叙述,以理想化为前提选择支配其特定“情感结构”的意象,建构出以“在异之同”为特征的定型化的乡村与城市及其相互关系。所以,一旦我们转换视角,我们就会在通往“过去的好日子”的自动扶梯上,“看到回溯所支持的依次出现的批评阶段:宗教的、人文的、政治的、文化的。这些阶段每一个就其本身而言都是值得考察的。而且这些问题中每一个都关注不同,但它们最终把我们引向了一个难以回答却又根本性的问题”。
为了回答这个“难以回答却又根本性的问题”,威廉斯考察了田园诗的发展和演变。威廉斯指出,最早关注乡村生活的重要文学作品是赫西俄德的教谕诗篇《工作与时日》,虽然忒奥克里托斯时代对乡村土地肥沃、牛羊成群、享受春夏的宜人时光的歌颂,才宣告了真正意义上的田园诗的出现。古典时期田园诗人延续了前辈的传统,在理想化田园生活描述、对田园生活进行文学加工的同时保留了田园诗与真实乡村生活的联系,于是便有了日后常见的种种对比抑或张力:“夏季和冬季之间、愉悦和丧失之间、收获和劳作之间、歌唱和旅行之间、过去或未来和现在之间。”在文艺复兴期间的新田园诗中,原本见诸古典时期田园诗的这些张力被一步步消除了,唯有精心挑选的快乐、安宁的乡村意象存在,以致在16至18世纪的英国田园诗或“乡村隐退”诗歌中,“我们绝对不能……以乡村的本来面目看待乡村”。随着“学术雕饰”成为新传统,“诗中不再有真相”;英国新古典主义田园诗“已变成一种高度造作和抽象的形式”,一方面是自然已经从劳作中的乡下人眼中的自然,变为了科学家或旅行者眼中的自然,另一方面是它通过严格的戏剧化和浪漫化,刺激了僵化的“人造”牧歌和田园诗的发展。
一如以《致潘舍斯特》为代表的乡村宅邸诗歌所证明的,人造田园诗在呈现一种基于快乐往昔和纯真等概念的情感结构的同时,刺激了“乡村与城市以及宫廷之间的对比:这边是自然,那边是俗世”。虽然这样的田园诗中并不存在历史回溯价值,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
对封建与紧随其后的后封建价值的理想化:对一种基于显然是一个整体的固定的、互惠性的社会和经济关系秩序的理想化。因此,非常重要的是,这些诗歌在时间上与这样一个时期的吻合,于其间另一种秩序——资本主义农业秩序——正在被成功开拓。
鉴于吻合背后是至今依然重要的价值冲突,这些诗歌承载着巨大的意识形态功能。首先,美好纯真的乡村叙述传统之所以得以潜在地留存下来,是因为作为观察者的诗人采取了与乡村统治阶级合谋的选择性叙述策略,因而维护了乡村统治阶级的利益。其次,“在稀松平常的回溯性激进主义脉络中,对责任、慈善和向邻居敞开大门的强调与资本主义动力形成了对比,后者将一切社会关系都功利性地化约为赤裸裸的金钱秩序”。因此,威廉斯不但道明了那个“难以回答却又根本性的问题”即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所带来的生产和生活危机,而且暗示了这个问题的另一面,即乡村与城市的真实关系。
比如,在19世纪英国农村,随着资本主义秩序的确立,无论是全面地区隔工业阶级与地主阶级,还是简单地对立乡村英国与工业英国,都已不再可能。所以,19世纪英国文学作品中不乏这一反复出现的意象:“鲜花与特权;工厂浓烟与民主。”然而,一如联系着科贝特等人的另一传统所暗示的,隐匿在这一意象背后的是乡村的颓势、乡村劳工的饱受剥削与屈辱:“1815年之后,乡村中劳工和穷人所遭遇的一切一如漫长的剥削和屈辱中的任何东西那样糟糕。”维多利亚时代以降,英国乡村进一步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乡村与城市的关系因此从过去的相互依存关系变为了支配与被支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一如他在讨论作为当下主要工业社会隐喻的“大都市”的乡村与城市关系时所言:
发生在“城市”“大都市”经济中的一切决定、取决于被设定发生在“乡村”的一切,首先是本国的边远地区,然后是之外的广大地区、其他民族的国土。从那时起,在英格兰发生过的一切一直在越来越广泛地发生,通过所有工业国家和所有其它“欠发达的”但经济上重要的国家之间的新依附关系。
大都市已在主要工业社会居于支配地位,但这并非是工业社会内部发展的必然结果;从本质上讲,它是19世纪国家内部的功能划分在当下的延伸。西欧和北美的“大都市”社会是“先进的”“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是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力的中心,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欠发达的”农业或“欠工业化”国家。“大都市”国家通过贸易体系以及经济和政治联合管控,从占据地球大部分地区、容纳地球绝大部分人口的边远地区获取食物,尤其是原材料。其结果是“通过经济和政治关系,一种乡村与城市模式已超越民族国家的边界,不但被视为一种世界模式,而且以此受到挑战”。
乡村与城市关系重构
威廉斯对英国文学传统中的乡村与城市叙述的探幽发微,不但打开了其间的褶皱,让人看到了以旨在理想化的选择性叙述为前提的情感结构的遮蔽,而且暗示了他自己的一种新的情感结构,其基础是他的个人经验、对话文化精英主义和反思马克思主义。比如,威廉斯本人虽然并不认同“时代在变好”,但时常借助“我”“我的祖父”的乡村经验,说明“时代在变得越来越好:过去的日子是糟糕的日子”,拒斥田园诗人的“过去美好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之类历史遗憾。另外,威廉斯对“打谷诗人”达克的评价也可以证明,在他看来,文化并不像阿诺德等文化精英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相反,文化即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和共有经验。
值得注意的是,威廉斯不但通过反思经典马克思主义建构了自己的情感结构,而且正是基于自己的情感结构重构了乡村与城市的关系。受家庭与社会情势的影响,威廉斯在青年时代无疑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二战之后,尤其是在苏联出兵匈牙利之后,他一度疏离了马克思主义,但吕西安·戈德曼却让他再次拥抱和启用了马克思主义。虽然威廉斯并不认同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拒绝简单地把文化活动视作经济活动的反映和回声,但他始终坚持文化必须用一定的生产方式加以解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威廉斯力主修订、校正正统马克思主义,一如他对情感结构的建构那样。威廉斯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指出,马克思主义著述中大致存在三种意识形态观:代表某个特定阶级或集团的一种信仰体系、很可能与真实或科学知识相对立的一种虚假信仰体系、意义和观念生产的一般过程,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仅仅聚焦第一种和第二种意识形态观,忽略、无视意义和观念生产的物质性的社会过程,完全排除了意义和观念生产的社会维度。鉴于“意识”始终是这一“被遮蔽”过程的一部分,威廉斯决意启用范围比意识形态更广、要素比意识形态更丰富的情感结构,以期强调其“与‘世界观’或‘意识形态’等更为正式的概念的区隔”,凸显其“现时在场的、处于活跃的、彼此关联的连续性之中的实践意识”。
所以,威廉斯的思想重心虽然发生了从前期的左派利维斯主义到后期的文化唯物主义的演变,但他的思想从一开始便是以利维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为特征的;《乡村与城市》是“威廉斯正不断重建与马克思主义的友好关系”的标志,代表了威廉斯思想的走向成熟。第一,威廉斯拒绝了城市/当下混乱无序而乡村/往昔快乐有序的对比,摒弃了作为一种历史神话的有机社会概念。在威廉斯看来,19和20世纪英国作家对有机社会的描述暗示了一种回归封建社会关系的欲求,一如他在谈论上层农民对大地主的道德抗议时所言:
于是,道德抗议是以一种暂时的稳定为基础,就像在后来的乡村抗议史上一再发生的那样。它是有根有据且令人感动的,但它在其它一些方面却是不真实的。其理想是地方性的家长式关心与全国性的立法,以保护某些新近出现的所有权和劳工形式,这一理想似乎差不多均等地基于拒绝封建主义专制、深切厌恶新的金钱专制,以及试图稳定一种过渡性秩序,借助这种秩序,小人物们将被保护不但免遭圈地运动之苦,而且免遭其劳工懒散之苦。
威廉斯不仅批评了有机社会思想是对往昔的理想化,而且指出了它是一种旨在遮蔽和逃离当下危机的真实性的神话。“有机社会概念让人念念不忘如下错觉:我们的问题的根源并非是资本主义,而是都市工业主义这一更为显在、更易分辨的制度。”
第二,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向往鼓励了威廉斯对资本主义危机的揭示,但这未必意味着他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全盘接受。威廉斯指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无疑是资本主义的敌人,但在乡村与城市的问题上,社会主义“却逐一而且经常原则上继续,甚至加剧一些相同的基本进程”。所以,威廉斯虽然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历史的如下论述,即“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但同时指出,“正是在这种对现代化和文明的单一价值观信心之上,共产主义历史上的一个重大歪曲产生了”。鉴于“中国革命在城市中遭遇了失败,它转移到了乡村并最终发展壮大。古巴革命从城市来到了乡村,在那里它的力量逐渐成形”,威廉斯指出,首先,由于“城市无法拯救乡村,乡村也拯救不了城市”,“我们不应将自己局限于它们的对比,而是要进一步看到它们的相互关系,并透过这些关系看到潜在危机的真实形态”。其次,在城市进步主义进一步战胜田园主义的未来,乡村建设可谓是抵抗资本主义抑或与资本主义决裂的重要举措之一。
第三,受启发于乡村与城市的差异“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发挥到了极致”这一观点,威廉斯批评了制造乡村与城市之分裂、人与人之间的疏离的工业主义:
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虽然并不是始于资本主义制度,但却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发展到了一个令人吃惊、行将变革的程度。这一基本分隔的其它形式包括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隔、管理与操作的分隔、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分隔。
威廉斯认为,消灭劳动分工、实现新形式的合作即解决社会危机的出路之所在,一如他在《乡村与城市》的结尾处所言:“唯有拒绝被分工,我们才能克服分裂。这是一种个人决定,但也是一种社会行为。”威廉斯因此一方面从一个侧面呼应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分工论述,另一方面凸显了我们生活于其间的诸多乡村与城市,因而帮助我们获取现在与未来。
结语
《乡村与城市》是一部尚未受到足够重视的威廉斯著作,于其间他不但揭示了见诸英国文学传统的乡村与城市叙述的情感结构,而且基于自己的情感结构重构了乡村与城市关系,因而把情感结构这一概念的运用从文学艺术拓展到了社会变迁。正是在方法论的意义上,随着近年来“乡愁叙述”“乡愁热”再度流行于中国,中国学人纷纷把目光投向了《乡村与城市》,希望从中获取洞见与启发。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剧的情势下,当下中国的乡愁叙述无疑是多维的,“接合”了农二代、城市中产、资本精英等视角。所以,我们不妨以《乡村与城市》为方法,拒绝对“乡愁叙述”进行简单的是非判断,认识到其背后复杂的城乡历史和社会经济现状。比如,在城市化浪潮面前,“进城”“去农”正在或已然成为当下中国的一种支配性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趋势,一方面是乡村日渐凋敝甚至逝去,另一方面是城市因改造扩建面目全非,结果“乡下人”和“城市人”毫无差别地患上了“乡愁病”,纠缠于其间的既有“回不去的乡村”,也有“留不下的城市”。然而,我们在看到《乡村与城市》的启示意义的同时,还必须当心威廉斯曾勉力避免的陷阱,即把乡愁叙述建构为“另一首唱给乡村的挽歌或一种愤世嫉俗的宿命论”,尤其是在城市中产享有乡村话语支配权的情势下。对他们而言,浪漫的田园梦与其说是对不合理城乡关系的质疑和挑战,毋宁说是以乡村之名寻求安全而不失优雅的抚慰;从这个意义上讲,看似浪漫的田园梦可能不仅含有更加隐蔽的偏见,而且隐匿着把乡村抽象为无人的风景和新的欲望空间的危险。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摘自《外国文学评论》2016年第4期;原题为《乡村与城市关系史书写:以情感结构为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