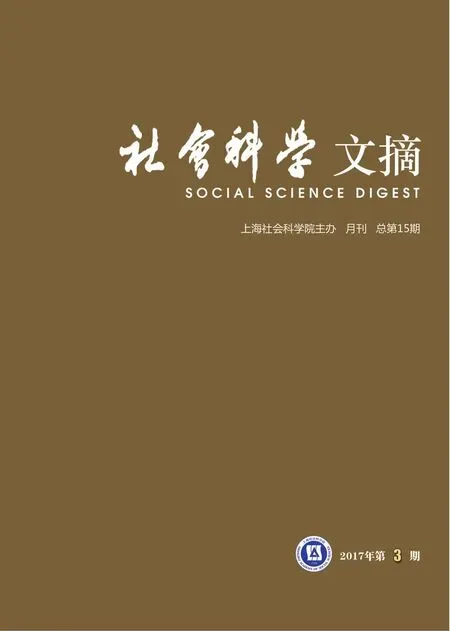女性意识、宏大叙事与性别建构
文/郭冰茹
女性意识、宏大叙事与性别建构
文/郭冰茹
性别视角遮蔽了女性写作的丰富性
在20世纪中国小说史的框架中讨论女性写作问题,自然离不开女性主义理论对女性意识的开掘、推动和梳理。乐黛云从三方面来定义女性意识:“从社会阶级结构看女性所受的压迫及其反抗压迫的觉醒;以女性生理特点研究女性自我,如周期、生育、受孕等特殊经验;以男性为参照,了解女性在精神文化方面的独特处境,从女性角度探讨以男性为中心的主流文化以外的女性创造的‘边缘文化’及其所包含的非主流的世界观,感觉方式和叙事方法。”因此,在“女性意识”的观照下,“女人”被发现、被解读、被重视;也正是在“女性意识”的观照下,女性文本独立于现代文学史的价值和意义得以凸显。
冰心、庐隐、丁玲、萧红是较早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女作家。文学史家看重的是冰心的“问题小说”对“五四”时期家庭、教育乃至社会人生等诸多问题的思考;庐隐对一面背负着几千年的传统负荷,一面渴望追求人生意义和“自我发展”的“五四”青年们的生动写照;丁玲对“五四”退潮后小资阶级内心幻灭的刻画以及这一代知识分子从个人主义走向集体主义的过程;萧红笔下“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等等。然而,有了“女性意识”的参照,冰心借助男性口吻对女性的描述“显而易见地包含着某种屈服于秩序的意味”;庐隐小说中女学生们徘徊在父亲的门与丈夫的门之间饱受“情智激战”的煎熬,永远都只是“娜拉的瞬间”;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被视为追求个性解放,肯定女性自身欲望的女性主义经典文本;萧红的《生死场》从女性的种种身体经验去透视生、死以及民族存亡的宏大主题;至于张爱玲,则是在“重写文学史”的学术清理工作中“浮出历史地表”,并受到了持续的关注。她杂糅古典白话的语言形式、细腻的心理描写、对世事人情的体察和揭示以及从女性主义角度来解读她对女性命运的关注都成为常论常新的话题。与此同时,在“女性意识”的烛照中,越来越多的女作家开始“浮出历史地表”,成为我们现在熟知的女作家,比如石评梅、苏雪林、袁昌英、凌淑华、白薇、苏青,等等。“女性意识”主导下的性别视角因此成为一种洞见,昭示出被民族解放、国家独立、阶级革命等宏大叙事所遮蔽的性别经验。
借助“女性意识”,研究者们一方面清理了文学史,一方面也介入当下具体的文学书写,总结其成果和经验,并力图将部分作品经典化。在这种功利性地解读中,张洁的小说《方舟》被认为是新时期初年具有明确女性意识的女性宣言。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我在哪儿错过了你》展示了新时期初年两性关系的紧张和社会结构的不稳定。王安忆的“三恋”、《逐鹿中街》《香港的情与爱》《长恨歌》等作品则是在承认并肯定性别差异之后,对女性“主内”角色的多向度探讨。至于20世纪90年代闪耀文坛的林白和陈染,更是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文本实践者。在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实践中,谌容、张抗抗、王安忆、铁凝、毕淑敏、迟子建、徐小斌、卫慧、棉棉等女作家分别构成了新时期不同阶段女性文学的研究点。而被归入其他文学现象的代表作家,比如“朦胧诗”中的舒婷、“先锋小说”中的残雪、“新写实小说”里的池莉,还有惯以讽刺笔法写教授学者小世界的徐坤等,都被纳入女性主义批评的体系和框架中进行了解读。一时间众多的女作家构成了一部蔚为壮观的当代女性写作图景。
当我们把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将女性写作作为女性主义理论的实践工具时,为了达到既定的叙述目的,对20世纪女性文学进行归纳总结,去除枝蔓,突出女性意识的觉醒和表达不仅是有效的而且也是必要的,这也是以往的女性主义批评实践所作的重要工作。但是这种做法的代价便是遮蔽了女性写作自身的丰富性,无疑也将女作家的作品价值窄化了。换言之,仅仅依赖性别视角,关于女作家作品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便难以解答,比如被目为“五四之女”的冰心为什么从未在作品中表达出“五四”一代的叛逆精神,反而始终强调“贤妻良母”的女性观?《莎菲女士的日记》被女性主义者视为书写女性个体欲望的经典之作,然而为什么丁玲在一次访谈中否认这篇小说写的是女人的情欲?“五四”时期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女作家都写过同性情谊,这是否如一些女性主义研究者认为的那样与礼教制约下的性压抑有关?张爱玲、苏青这些在沦陷区盛极一时的女作家为什么很长时间没能进入现代文学史?如果不仅仅局限于“女性意识”,而是将这些文学书写放置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这些问题也许不难解决。
此外,在一些女作家的文学书写中,文本的内容、价值或意义并非与“女性意识”的阐释珠联璧合。比如铁凝的《哦,香雪》《没有纽扣的红衬衫》《麦秸垛》《遭遇礼拜八》《甜蜜的拍打》《对面》等作品,常被批评家认为其性别特征并不显著,甚至还刻意回避了单一的性别视角。比如迟子建的《北极村童话》《白雪的墓园》《雾月牛栏》《清水洗尘》等作品,都着力在重写文学与故乡、童年和大自然的关系,与性别视角的关系并不是特别紧密。方方的《风景》被誉为新写实小说的开山之作,那个一家9口拥挤在13平米的窝棚里,没有尊严,几近动物般的物质生存与女性主义批评的性别诉求相差太远。对于这些女性书写,女性主义批评又该如何阐释呢?
与此相关的是,虽然女性主义理论着力于阐发女性写作的价值和意义,但很多女作家并不愿意被冠以性别的标识,比如张洁,她始终强调自己是一个“炽热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坚信妇女真正的解放有赖于人类社会的全面进步,因此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一个“女权主义者”的封号。还有王安忆,她虽然强调性别,但同样拒绝“女性主义者”的标签,她主张在“男女平等”的主流宣传中重新检视性别差异,并将女性归位于传统的“主内”角色,进而探讨女性在“份内”实现个人价值的可能性。女性主义理论在解读女性文本时遇到的问题,以及女作家不愿意接受“女性主义者”的封号,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女性意识”或者“性别”视角处理中国问题时的局限。
女性写作参与了现代化这一宏大叙事
检视女性写作的发生史,我们不难发现,晚清以来,由于现代文学始终参与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女性写作的历史脉络也始终是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相关联的。换言之,女性写作的起承转合,都深刻地打上了这一元叙事的烙印。
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写作探讨的是女性如何成为“女性”,成为怎样的“女性”的问题,或者说是女性写作是女性性别建构的过程和体现。波伏娃说:“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换言之,性别问题总是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相勾连的。因此对女性写作的研究也不能仅仅局限于“女性意识”或性别视角,而应在其中加入一些与性别相关或无关的参照系,比如官方宣导的意识形态与民间私人生活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不同阶级、阶层、经济水平、地域、社会/生活圈、年龄、受教育程度、生活经历等所造成的个体差异,等等。此外如前所述,女性写作作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宏大叙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性别建构的考察也必须与同一历史时期宏大叙事相参照。
现代女作家的出现,意味着女性有了自由言说的可能。“五四”之女们着力描画“新女性”走入社会后如何面对婚姻、家庭、职业、爱情、革命等问题,借此来思考“新女性”的性别建构问题。这正是从晚清到“五四”的历史变动过程中知识界塑造女性的必然结果。换言之,如果没有现代民族国家叙事的兴起,也就没有“现代女性”的出现。在这个意义上,女性的觉醒和社会化,始终是在“他者”的影响下进行的。历史首先是一个巨大的“他者”,它总是以大势规定女性解放在现代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的位置和顺序,因此女性解放始终是这一元叙事的一部分。知识界则是另外一个“他者”,它在参与宏大叙事的过程中塑造女性。正因为有了这些“他者”,冰心始终坚持女性在家庭中以奉献和自我牺牲为主调的贤妻良母观;苏雪林宁愿做个“养家男人”,不愿成为“司家的主妇”;庐隐追问那些受过高等教育,却既不善持家,又无力兼顾社会事业的“新女性”们“何处是归程”;也正是有了这些“他者”, 丁玲将个体情欲的表达视为追求自我的体现而非情欲本身;凌叔华对新女性在家庭中精神和情感空间的探索有了新的维度。虽然历史的规定和知识界的塑造,也使女性的性别建构带有了宿命性的困境;但是,当女性能够以文字的方式介入社会、国家时,当女性参与宏大叙事的建构同时也表达自己对性别问题的思考时,女性写作之于文学史的独特意义也就显示出来。
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是中国战争频仍的阶段。乱世弃绝了传统的性别规范,也中断了“新女性”基于婚姻、爱情、家庭等方面对性别的建构探索。这其中有人放弃觉醒了的“自我”而投身革命,从而与革命构成了同构关系,此时的革命不再是“他者”,而成为“主体”的一部分。或许正因如此,丁玲才能彻底放弃她早期小说中的那些忧郁、苦闷、颓废且执着于个体情愫的modern girl,转而去书写她不怎么熟悉的工农兵;杨沫才能将《青春之歌》中一个女人对个人情感的选择讲述成知识分子对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这其中也有人既介入革命又疏离于革命,此时的革命作为“他者”,始终“在场”。比如萧红,她的《生死场》《马伯乐》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相吻合,可她进入这一宏大叙事的角度和方式却极为个人化,她始终自觉地从生存的角度来观照她的写作对象。这些不同的路径,不仅是革命战争年代错综复杂关系的折射,也呈现出这一复杂语境中探索性别建构的多样性。
社会主义革命对日常生活的改造对女性的意义非比寻常,这一阶段的女性写作对性别建构的探索呈现出与宏大叙事高度的同质性。草明、茹志鹃虽然也写婚姻家庭和爱情,但文本的主旨是:只有把一己之爱升华为对国家、对社会主义的爱,只有走出自己的小家庭,献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能使女性收获真正的幸福。文本中的女主人公也首先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翁,她们首先对社会主义事业负责,与之相比,小家庭和一己之爱都是微不足道的。这样的表达方式是当时意识形态宣传的一部分,也是婚姻、家庭、爱情等现代女性写作的核心主题淡出建国后女性文本的原因。
新时期与“五四”时期一样,都是要求打破思想禁锢,要求拨乱反正。胡适那篇《敬告青年》同样也适用于20世纪80年代的“人的觉醒”。不过,在80年代的具体语境中,胡适所说的“他人”已经不是“五四”时期的伦理道德和婚姻家庭,而是极“左”思潮、迷信权威。这些与性别问题无关,而这些问题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启蒙运动,讨论的也不是女性的解放,而是人的解放。因此,80年代初的知识分子,包括女性知识分子首先考虑的都不是女性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描述重工业部改革的艰辛;谌容的《人到中年》表达了对知识分子生存的关注和呼唤;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描述了当期待已久的机会来临时,人与人之间残酷的竞争;而戴厚英的《人,啊人》的后记则鲜明地彰显出了那个大写的“人”。张辛欣、戴厚英的作品发表之后引发诸多争议甚至是批判都与女性问题无关,虽然这些文本后来得到了女性主义的解读。显然,在80年代的语境中,精英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文化立场才是思想解放潮流中的最强音。
当然,不能否认的是,性别问题在彼时虽然不是知识分子首先考虑的问题,甚至该问题也没能像晚清和“五四”时期那样,构成知识分子思考民族国家宏大叙事的切入点,但“思想解放”运动所带来的观念解放和思想变革以及世俗生活的合法化都为性别意识的生长提供了土壤。在参与宏大叙事的写作中,女作家既突出了时代主题,也发现了现代化进程中的角色冲突,新时期女性的性别建构由此展开。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时期的性别建构过程是由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介入推进的,因为所有能够被纳入女性主义批评阐释系统的文本都得到了认真而严肃的意义阐发。但几乎与此同时,女作家们却试图在女性主义理论之外,探索性别建构的中国方式,比如王安忆的《逐鹿中街》《弟兄们》、铁凝的《棉花垛》《玫瑰门》质疑了女性主义理论赋予女性参与性别重塑或历史建构的主体性。显然,新时期的女作家们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所标举的“女性意识”持怀疑态度,同时也将自己对性别问题的思考融化在她们书写社会生活的宏大叙事中,这未尝不是新时期女性性别建构的独特所在。
与新时期女性淡化“女性意识”的性别建构相对应的是20世纪90年代强化个人经验的性别建构。强调性别身份,注重个体的心理和生理经验在90年代的文学书写中蔚然成风,这是新时期思想文化背景重构的一个衍生结果。80年代中期以后,“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等文学现象纷纷重新设计了“个人”进入历史的方式,“个人”不再是英雄抑或精英,也不再是集体中的一员,叙述的主旨开始回归日常生活,回归“原生态”,宏大叙事逐渐被解构。这一写作潮流原本与性别建构没有必然联系,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尤其是关于“身体写作”的理论在这一潮流中找到了切入点,相应的,迎合这一潮流的“个人化写作”也为女性主义理论提供了可操作的文本和范例。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等文本将女性身体经验的展露视为性别建构的途径;陈染的《私人生活》等文本也以私密性的女性经验来呈现性别建构的困境,只是这种私密性的经验不仅表现为身体和欲望的表达,更体现为敏感、脆弱、碎裂、隔膜的内心生活。她最终在《破开》中将女性的性别建构指向五四前辈们的“同性情谊”,但她赋予了姐妹们更强烈、更自觉的主体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百年,女性的性别建构又回到了起点,但显然,此起点已非彼起点。
结语
回顾百余年女性书写的历史,当我们将女性视为一个性别群体,将女性写作视为“女性意识”的觉醒和表达时,一部去除枝蔓、线索清晰的女性文学史得以呈现。对文学研究而言,这一学术工作不仅是有效的而且也是必要的。然而这种目标明确的批评梳理将女性写作与20世纪中国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相剥离,剔除了所谓的“旁枝末节”,也遮蔽了女性写作自身的丰富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女性书写的历史也是女性自身进行性别建构的历史,而性别建构与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密切相关,当我们撇开既定的规则和目标,重新进入故事讲述的年代,触摸那些文本,并将其与当时的思想文化问题相关联时,枝蔓丛生、枝节凸起、纷繁驳杂的女性文学史才因此得以绘就。
【作者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摘自《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