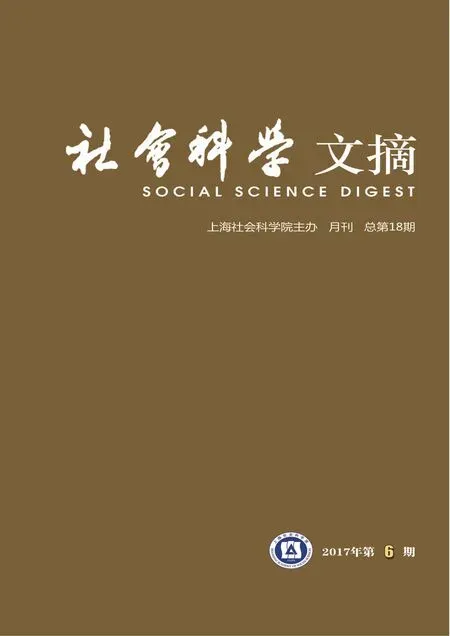中国现代诗学中的性灵派
——论徐志摩的诗学思想与诗论风格
文/龚刚
中国现代诗学中的性灵派
——论徐志摩的诗学思想与诗论风格
文/龚刚
引言
文学批评是否应该科学化?以诗话词话及小说评点为代表的更重兴会与妙悟的传统文学批评形态是否应当传承发扬?性灵化的文学批评在当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总体格局中是否应有一席之地?这三个问题是关乎中国文学研究前途和中国现代文论话语建构的重要问题,值得关注和深思。著名现代诗人徐志摩主张诗歌是性灵的抒发,并以“活泼无碍”的创作境界作为自己的理想。与此相呼应,在文学批评与鉴赏层面,他高度推崇个性化的“整体领悟”,而不是科学化的机械分析。
虽然徐志摩自称“我素性的落拓始终不容我追随一多他们在诗的理论方面下过任何细密的功夫”,但他所留下的总量不大的诗论文字,如《汤麦司哈代的诗》《济慈的夜莺歌》《拜伦》《白朗宁夫人的情诗》《波特莱的散文诗》等篇,却是中国现代文学领域的宝贵财富。 他的诗论恰是其诗风和人格的延续,自由不羁,才气外露,充满激情和想象,既不乏深邃灵思,又有激动人心的力量。如果说,他的诗歌是性灵的迸发,他的短暂一生是性灵自由的恣意挥洒;那么,他的诗论则是来自性灵深处的激情之思。概而言之,徐志摩是新性灵派的代表,其散文体诗论与郭沫若、郁达夫、李健吾等人的印象主义、唯美主义批评交相辉映,有其不容忽视的价值,对于深思文学批评的科学化问题以及如何建构现代人文学的“中国话语”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本文拟在探讨徐志摩崇尚“性灵”的诗歌创作观、反对教科书式机械分析的文学批评观的基础上,解析其代表性诗论及风格,以期有助于深入认识徐志摩诗论文论的特质及其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独特地位。
以“性灵”为宗的诗歌创作观
徐志摩曾留学英国,受到雪莱、拜伦、华兹华斯和印度田园诗人泰戈尔的影响,但他获得的不仅是艺术上的滋养,更是他们诗中所蕴含的“性灵深处的妙悟”。徐志摩认为,有性灵才有真诗,写诗就是性灵的自然流露,而性灵得之自然,需要培养和保全。
不过,他并未对“性灵”一词的具体含义加以说明。《志摩全集》的编者赵家璧指出,“他常用这个词,意指inspiration”。赵家璧又说徐氏常鼓励他的学生去参观美术展览和听音乐演奏,因为这两者“同样是触动着性灵而发的”。综合考察徐志摩在各种语境下使用的“性灵”一词可以推断出,他所谓“性灵”,兼有灵感、灵性、性情等义,也可以是灵感与性情的结合。
由于徐志摩所谓“性灵”,兼有“性情”之义,因此,他的“性灵”说就可以说是明清“性灵派”诗论的现代延伸。明代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清代性灵派主将袁枚所谓“性灵”,均以人之情为内核。袁宏道在揄扬“独标性灵,不拘格套”的诗风的同时,对“情与境会,顷刻千言”的激情写作格外赞赏。袁枚则更是明诏大号地主张“性情之外本无诗”。徐志摩虽然不曾直接提及明清“性灵派”的诗论,但他的“性灵”说显然与袁宏道、袁枚的观点相契合,同时又融入了西方浪漫主义诗学崇尚情感、崇尚创作自由与自我表现的内在精神。
徐志摩多次以“野马”自况,如他说,“我的笔本来是一匹最不受羁勒的野马,看到了一多的谨严作品我方才憬悟到我自己的野性;但我素性的落拓始终不容我追随一多他们在诗的理论方面下过任何细密的功夫”。“野马”是现实秩序之外的存在,无拘无束,任性驰骋,既不像战马一样供人驱驰,更不愿成为乖顺的家畜,由人饲养,任人驭使。这一意象就像徐志摩所喜爱的风和云雀一样,都是自由的象征。而自由,正是徐志摩“单纯信仰”的核心内涵。纵观他的言论和生平可见,他对自由的追求,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创作的自由,一是灵魂的自由。所谓创作的自由,这是指不受成规与教条的羁绊,尽情地抒发性灵,尽情地表现自我。他明确表示,“要使我们的心灵,不但消极的不受万物的拘束与压迫,并且永远在继续的自动,趋向创作,活泼无碍的境界”是他的理想。这样的理想既彰显了西方浪漫主义所推崇的创作上的绝对自由,也和明清“性灵”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诗学精神相契合。
对“教科书式文学批评”的质疑
作为一个诗人,徐志摩崇尚的是性灵之歌,作为一个批评家,徐志摩崇尚的是性灵之悟。在他看来,艺术的欣赏和批评应以性灵的感应为前提,不能满足于以主义和流派来区分、标签作者,也不能以科学的分析替代整体的感悟。他在《汤麦司哈代的诗》一文中指出:“艺术不是科学,精采不在他的结论,或是证明什么;艺术不是逻辑。在艺术里,题材也许有限,但运用的方法各各的不同;不论表现方法是什么,不问‘主义’是什么,艺术作品成功的秘密就在能够满足他那特定形式本体所要求满足的条件,产生一个整个的完全的,独一的审美印象。”
徐志摩的上述观点是针对学界关于哈代的评价而提出的。当时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将哈代定性为“悲观主义者”“厌世主义者”“定命论者”。徐志摩认为,这是拿“主义”和“派别”来标签作者的方法,犹如旅行指南、舟车一览,虽然能予人便利,却不够亲切。对一个真诚的读者来说,即使哈代真是悲观的、勃朗宁真是乐观的,也得通过亲口尝味去寻出一个“所以然”,而不是随便吞咽旁人嚼过的糟粕;对一个批评家来说,如果贸然以“悲观”“浪漫”等“抽象的形容词”涵盖文艺家对生命或艺术的基本态度,就会失之浮泛。例如,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意大利诗人莱奥帕尔迪(Leopardi,徐氏译为“理巴第”)也同样被视为悲观主义者,但他们的悲观思想却与哈代不尽相同。以莱奥帕尔迪为例,在他最深的悲观中也有对于美好价值的刹那彻悟,如果泛泛地冠之以“悲观”“厌世”的标签,就不能更深刻地理解这位诗人的内在精神。
此外,以“主义”“派别”标签作者还有一重危险,它会使读者误以为作家都是带着某种“成心”——“主义”或“派别”的成见——去创作。徐志摩认为,“成心是艺术的死仇,也是思想大障”。在他看来,“哈代不曾写裘德来证明他的悲观主义,犹之雪莱与华茨华士不曾自觉的提倡‘浪漫主义’,或‘自然主义’”。他进而指出,哈代并不是一般人所谓悲观主义者,而是人生的探险者,其思想是对于人生的“倔强的疑问”(Obstinate Questionings)。
在徐志摩看来,习惯以“主义”“派别”来标签作者乃是“教科书式的文学批评”的一大特点,这种批评方式实际上是把文学艺术降格为了观念的附庸,或是将一首诗、一部小说当成了合乎逻辑地证明某个结论的过程。因此,当学院派批评家发现了作品的结论(悲观的或乐观的),他们就自以为准确地揭示了作者的精神和所属派别。与此相反,徐志摩既不认同以抽象的概念将作家笼统归类,也反对将艺术等同于科学和逻辑。在他看来,艺术作品成功的秘密在于产生“独一的审美印象”,这种“审美印象”需要读者亲自去感知,而不能由批评家代劳,也不能被先入为主的“主义”所框限。因此,他说:“在现在教科书式的文学批评盛行的时代,我们如其真有爱好文艺的热诚,除了耐心去直接研究各大家的作品,为自己立定一个‘口味’(taste)的标准,再没有别的速成的路径了。”
徐志摩是在1924年提出上述观点的,当时,西方“科学主义”思潮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影响,以及西方各种主义、流派的涌入,正处于方兴未艾之势。徐志摩对“教科书式的文学批评”的质疑,既是对文学批评科学化的反思,也是对“主义”先行的跟风现象的讥刺。如上节所述,徐志摩主张诗歌是性灵的抒发,并以“活泼无碍”的创作境界作为自己的理想。与此相呼应,在文学批评与鉴赏层面,他高度推崇个性化的“整体领悟”,而不是科学化的机械分析。他认为:“能完全领略一首诗或是一篇戏曲,是一个精神的快乐,一个不期然的发现。”他又认为:“领略艺术与看山景一样,只要你地位站得恰当,你这一望一眼便吸收了全景的精神;要你‘远视’的看,不是近视的看;如其你捧住了树才能见树,那时即使你不惜工夫一株一株的审查过去,你还是看不到全林的景子。所以分析的看艺术,多少是杀风景的:综合的看法才对。”
徐志摩的批评观显然与发端于他那个时代的崇尚客观分析与文本细读的英美新批评大相径庭。新批评派的燕卜逊自居为“分析性批评家”,反对“欣赏性批评家”,并声称“无法解释的美让我恼怒”。与新批评的科学化倾向相对立,徐志摩所崇尚的“整体领悟”式的文学批评,类似于传统的印象式批评,突出了读者和作品的精神契合和心灵感应,表现出极强的主观化和个性化色彩,甚至还有一点神秘感。例如他说,要完全领略一首小诗,“一半得靠你的缘分”,并自嘲说,在艺术鉴赏方面,“我真有点儿迷信”。 迷信正是科学所要破除的,徐志摩自称“迷信”,显然是要和“分析性批评家” 与科学化批评划清界限。对他来说,为“无法解释的美”而恼怒无疑是可笑的,因为文学批评本来就是对文艺作品的“不期然的发现”。
正因为徐志摩高度推崇心灵的自由、灵魂的自由,并将文学艺术视为人类性灵活动的成绩,所以他明确表示“不很喜欢”德国人的文艺批评。他讽刺说,德国派批评的分类题签是“各式各样的‘悒死木死’(‘-isms’),古典悒死木死,浪漫悒死木死,自然悒死木死……”徐志摩之所以将“主义”的复数译为“悒死木死”,显然是反对以各种“主义”的标签来区分、框限个性不一的作家,也反对带着“主义”的成心从事创作。所谓“悒死木死”,就是“愁死僵死”的意思。在他看来,概念化的批评与理论图解式的写作,都会束缚心灵的自由,从而令性灵僵死,最好的批评方式不是解剖和分析,而是“了解与会悟”。
从文学批评类型学的角度来看,徐志摩所反对的“教科书式批评”或德国式文艺批评,类似于当代学界所谓“学院批评”。他所推崇的“会悟”式批评,则类似于当代学界所谓“作家批评”。有学者指出,“学院批评”和“作家批评”这两种模式各有弊端,“学院批评”过分地依赖理论从而导致批评与创作实际脱节,“作家批评”则欠缺理论从而导致批评的现象化而缺乏深度。徐志摩是诗人、散文家,在西方文学文论研究上也有一定造诣,他的富有浓郁诗人气质的诗论文评,不仅展现出“作家批评”的灵气和敏锐的艺术感觉,也颇具“学院批评”的思辨深度,值得深入探讨。
徐志摩的诗论及其风格特征
在徐志摩为数不多的诗论中,篇幅较长也较具代表性的主要是探讨19世纪至20世纪初英国诗人与诗作的《汤麦司哈代的诗》(1924)、《拜伦》(1924)、《济慈的夜莺歌》(1925年)、《白朗宁夫人的情诗》(1928年)等文章。
虽然卞之琳认为徐志摩的诗思、诗艺“几乎没有越出过19世纪英国浪漫派雷池一步”,但作为一名批评者和译者,徐志摩在引介哈代的诗艺与人生哲学方面的建树,却不亚于他对英国浪漫派的译介和评述。除了译有20余首哈代的诗作之外,他还撰写了《汤麦司哈代的诗》《汤麦士哈代》等评论文章,以及记录其拜访哈代经历的散文《谒见哈代的一个下午》。
其中《汤麦司哈代的诗》一文不仅是中国学界较早系统介绍哈代诗思与诗艺的专文,也是国内哈代研究中的经典之作。这篇诗论共有6节,第一节对东方诗人与西欧作家的创造力、生命力进行比较,热烈颂扬了西欧“文坛老将”如法国佛朗士、德国霍卜曼、英国萧伯纳等人老当益壮的矍铄精神和磅礴气概,痛心疾首地抨击了东方诗人和东方民族的精神颓唐、心灵贫乏和缺乏活力,表现出浪漫派诗人试图激发古老民族青春活力的热情。从结构上来看,这篇万余字的诗论条理、逻辑较分明,初具西式论文的形态,但从行文风格上来看,更像一篇随兴而作的散文,文中涌动着不可抑勒的激情,闪耀着灼灼逼人的灵光,散布着启人深思的妙悟、妙喻,展现了一个新文化运动孕育的才子对英国维多利亚传统反叛者的深邃洞见,堪称哈代研究的思想指南。
除了哈代研究之外,徐志摩对19世纪英国浪漫派和维多利亚时代传奇诗侣白朗宁夫妇也有一定研究,代表性的成果为《济慈的夜莺歌》《拜伦》《白朗宁夫人的情诗》。与以上3篇诗论相比,发表于1924年的《拜伦》一文,更为别出心裁。这是一篇梦话拜伦的奇文,采用了现代派小说的白日梦形式,率性纵情,随心所欲,完全无视正统的批评章法,突出体现了性灵化诗论的不羁风格。
拜伦生于1788年,卒于1824年,与济慈、雪莱同为代表积极浪漫主义精神的英国撒旦派诗人。徐志摩的这篇诗论是为纪念拜伦逝世一百周年而作,刊发于《小说月报》纪念拜伦专号。诗论的主体部分正是作者的白日梦。这个白日梦包含着多个画面。第一个画面是迷雾退去后的拜伦头像。 第二个画面是拜伦在阿尔帕斯山(阿尔卑斯山)漫游。第三个画面是拜伦与雪莱在梨梦湖(莱蒙湖)遭遇风浪(1816年),而此处是卢梭的故乡。在最后一个画面中,拜伦站在希腊西海岸梅锁朗奇(Mesolonghi)的滩边(1824年)。这篇神奇的诗论通过梦境演绎了拜伦的诗境、身世和功业,也通过梦境刻画了拜伦的人格特质、澎湃激情和叛逆精神,勾勒出一个融伟大的诗魂、光荣的叛儿与美丽的恶魔于一体的撒旦派诗人形象,有力地回应了拜伦是否值得纪念、其诗作与精神能否不朽的质疑,堪称拜伦评论中最光彩夺目的篇章之一。
杨振声在《与志摩最后的一别》中评价徐志摩的散文艺术说,他那 “跑野马”的散文,用字生动活泼,联想富丽,生趣充溢,“像夏云的层涌,春泉的潺湲”。梁实秋也认为,徐志摩的散文确如他本人所说的“跑野马”,但是“跑得好”,其因有三:一是“永远保持着一个亲热的态度”,“像和知心的朋友谈话”;二是“随他写去,永远有风趣”;三是“他的文章永远是用心写的”。其实,徐志摩的代表性诗论都是散文体的文学批评,也都体现出“跑野马”的风格特征,乘兴而发,率性而作,恣意驰骋想象,快意抒发胸臆,大量运用比喻、象征、拟人、夸张等修辞手法,迥异于严肃的教科书式批评,也迥异于排斥比喻、想象的纯粹理性思辨,与传统的妙悟式批评与西方的唯美印象主义批评交相辉映,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一道奇观。
(作者系澳门大学中文系教授;摘自《现代中文学刊》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