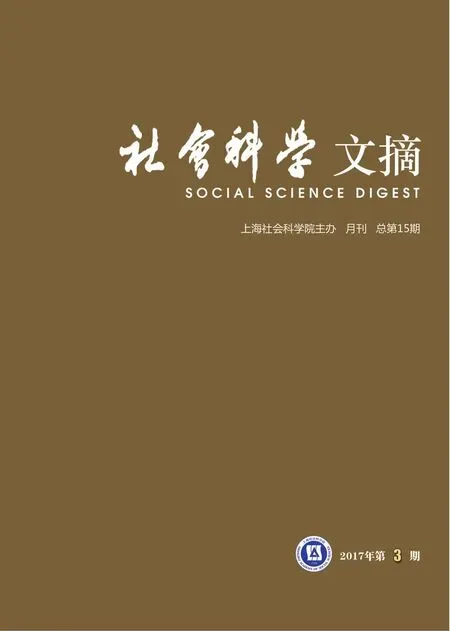舆论与外交
—— 晚清政府“媚外”形象的形成
文/杨雄威
舆论与外交
—— 晚清政府“媚外”形象的形成
文/杨雄威
“媚外”是在清末庚子国变后出现的一个流行语。梁启超认为以义和团运动为分水岭,“排外的反动一变为媚外,将国民自尊、自重的元气斫丧殆尽,此为心理上所得最大之恶影响”。此处的批评显然指向了整个国人。但在清末的舆论界,“媚外”的恶名主要集中在朝廷内外官员群体身上,并成为政府的整体形象。但诚如清末报人汪康年观察到的:“今之诟外交官,动曰媚外。此语未圆足也。实则吾国关涉外交之人员,并未尝以此为事,且视为极可憎厌之事。遇有事,意绪纷乱,惟以推出为第一要着,至于不能,则惟有坐听外人吩咐而已。至于平时,隔绝殊甚,同在一处之官,相见亦且不相识,何况言融洽乎?”汪康年关注外交多年,对庚子后外交与舆论的关系多有反思,此语不可等闲视之。近年来学界已能够抱着理解之同情的态度考察晚清国人的外交活动,由此产生的大量具体深入的个案研究为重新审视清政府的“媚外”形象提供了参考。
在晚清从“天下”观念向“民族国家”观念转变过程中,国人就如何与世界交往这一时代课题进行过复杂的心理和行动调适。自甲午特别是庚子以降,伴随着外交环境的急剧恶化,清政府在外交上的软弱退让,以及大量官员面对外人时自重自尊的丧失,成为尽人皆知的事实。但政府“媚外”形象的形成毕竟与时人的主观认知相关联。因此,本文从“媚外”这一流行语入手,考察在晚清朝野复杂多歧的外交心态变迁中,社会舆论如何审视和评判中外权力失衡格局下的政府外交行为。
形象与事实
在义和团运动后,“媚外”以固定短语形式出现并迅速流行,但在鸦片战争后到20世纪之前的晚清文献中则常见“媚夷”的说法。“夷”的用法虽遭西人的外交抗议,但同治初“媚夷”之语在中兴名臣群体圈子的书信中经常使用。李鸿章便曾指责他人“媚夷”,后来则饱受“媚夷”的批评。庚子后“媚外”便取代了“媚夷”。但二者各自背后的历史语境有巨大差异,“媚夷”之说多指向特定官员和特定举措,从未用来描述官场和政府的整体形象。“媚外”一词的出现和流行是一个包含了重要历史议题的历史过程。
“媚外”于庚子年底开始出现在报端,并从1902年开始流行。梁启超在日本所办的《新民丛报》和天主徒英敛之开办于天津的《大公报》,都开始使用“媚外”的说法。二者同《中外日报》在基本政治主张上相一致,特别是均扬光绪而抑慈禧。“媚外”之说,矛头直指戊戌变法期间与维新派敌对的守旧势力。“媚外”的含义,也与维新人士在戊戌之后极好提及的“奴隶”一词相关联。如《大公报》主笔评论说“媚外则确系发自服从之劣根性而甘心为外人之奴隶也”。
借助庚子和辛丑舆论界的一再提起,“媚外”很快成为一个重要政治话题。1902年8月底上海《新闻报》发表《论媚外之祸》一文,承袭此前《中外日报》和《大公报》的论调,将“媚外”视为庚子以来外交的重大转向。这一看法随后被舆论普遍接受,使之成为清末描述和定义官员与政府外交行为的核心概念。其影响力无所不至,以至于不仅舆论界操之为武器,对政府的批评不绝于书,连官场内部也借用此概念观察和衡量同事的行为。
这一流行语直接参与了政府整体形象的塑造。1907年有论者写道:“人之名政府者多矣。一则曰媚外之政府,再则曰贼民之政府,三则曰割地赠礼之政府,四则曰制造盗贼纵民非行之政府。”清王朝在其末年身负多重负面形象,“媚外”即其一。这种整体形象与中西交涉个案往往相辅相成,在清末最后近十年发生的诸多涉外公共事件中,具体涉案官员和整个官场同时遭受舆论界的“媚外”之讥已成常态。
“媚外”形象与史实之间的微妙关系,需要放在具体的案例中去考察。《大公报》在论述当今官场“媚外之术”时提到一个源头:“自皇太后迭次召见公使夫人,而王公士夫莫不以多识外国人为荣矣。”慈禧此举后来成为其“媚外”的最有力证据。但军机王文韶视角却大不相同,在日记中誉之为“千古未有之创举,可谓躬逢其盛矣”。慈禧太后获此骂名,跟她的声望在庚子后的急剧下降有直接关系,其所行新政常被视为有“媚外”目的。
自1905年后路权成为困扰清政府的极大问题,路权的不断丧失和保路意识的不断增强使得经办官员极易遭受“媚外”骂名。在此之前胡燏棻即因参与索路被讥媚外,但其是“谦让礼貌”还是“一味谄媚”,当非局外人所易知。路事当中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1907年集中爆发的苏杭甬铁路风潮。汪大燮提到办理此事的唐绍仪“于外人则名之曰排外,而中国人则谓之媚外”。随后汪本人也因参与苏杭甬路对英借款谈判而转瞬间成为“媚外”典型。在其他各种类型的涉外公共事件中,1906年初发生的南昌教案是观察“媚外”形象与事实出入的绝佳案例。报纸在报道中不断使用“媚外”二字来定性各级官员在此案中的相关行为,一向被西方人看作“排外之城”的南昌此时似乎一变而为“媚外”之城。但揆诸史实,朝廷上下皆曾强硬对待,外界的诟病往往无的放矢。
排外与“媚外”
当“媚外”作为一种语言事实在清末最初出现时,其使用者便开始认为,以庚子国变为分水岭,清政府发生了从排外到“媚外”的急剧转变。但应注意,最初报界在叙述排外到“媚外”的转变时,大都以戊戌为排外的起始。但后来人们通常认为排外是清王朝乃至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悠久传统。起初一般认为“媚外”始于庚子后,但其后却时常推及整部晚清史。这些不同判断的存在,提示我们这种转变本身是个复杂多歧的历史过程。
以教案为例。基督教在晚清借助列强的坚船利炮进入中国后,士大夫们一度视之为足以“动摇邦本”的心腹大患,因此做出种种抵制的尝试。但甲午战争后官员对教士的态度明显好转。因为朝廷开始严谴保护教堂不力的“地方官”。1897年巨野教案后,朝廷在教案问题上对地方官员的词气更加严厉,明言罪及将军督抚等封疆大吏。朝廷的态度促使督抚转变,继而影响到地方官的态度。
实际上面对攻守之势不利的时局,官员对付传教士本就不能一味直接用强而需要讲究策略。江西官场便长期流行阳奉阴违之术。广而言之,在晚清官员群体中长期而普遍地采用“阳奉阴违”的驭夷术。1844年耆英上奏称要对英国人“驭之以术”,其诀窍便不出阴阳二字。随着中西之间攻守平衡的日益倾斜,耍弄阴阳之术需要支付的政治成本越来越难以承受。由此势必导致整个官场特别是“不肖”与“懦弱”官吏的阴违日少和阳奉日多,但阴阳之间的反差可能更大。严复曾用“宗法社会”概念来解释外表愈媚外则内心愈排外的现象。阴阳表里之间的张力造就了庚子前后从排外到“媚外”表象上的剧变。有论者就辰州教案讥讽俞廉三“忽焉肯宴西客,忽焉肯办洋务,与此前杀教士时演剧称贺,另换一副面孔”,前后差异之大“竟成两人”。
这一现象对清末士人来说不难理解。《大公报》论官场“媚外派”时便揭示出排外与“媚外”在心理层面上的同根同源。1908年《申报》一篇文章提到,“责备政府之持媚外主义者有之,赠礼主义者有之。然于政府心理上观察之,亦未始不引为大敌。惟引为大敌,而对付此大敌者,一味出之以调停,加之以柔顺,而别无所以对付之良法。”这一心理观察可谓一针见血。其实,在“媚外”刚刚作为名词问世之时,其对应的行为曾得到过充分的体谅:“此日之媚外,未始非臣妾侍吴卧薪尝胆之成规也。”
总之,清末官员的“媚外”表象背后不乏排外心理。二者统一于鸦片战争以来外交实践中的“术”的泛滥。这一切当然是时人基于对西人侵略者身份的认知。敌强我弱之势愈明朗,外交回旋空间愈小。陈虬即认为“一切权谋诈术”,在今日局面下已“举无所用”,徒然见轻于人。1902年《新闻报》鉴于“中外启衅,在彼此失信”而鼓吹中外交谊。作者特以荣禄宴请西方外交官为例,称“荣中堂宴会西人,极从丰盛,技俩尤为狡猾”,实属“面交西人者,非心交西人”。问题是面对凭借炮舰登堂入室的侵略者,“心交”谈何容易!像荣禄此类行为很快被舆论视为“媚外”的凭据,而如作者所见之“言不由衷”与“并无真意”,却在暗示其排外之心不死。
交际与交涉
民国时期学者蒋廷黻评价说,“耆英所谓‘驭之以术’,就是肯与外以交际。这没有什么了不得。但清议骂他‘媚外’,因为清议要死守‘人臣无私交’的古训。”蒋氏此论道出了术、交际与“媚外”之间的逻辑关联,不过尚未触及相应观念的历史发生过程。下文便讨论蒋氏所说之“交际”为何物,并展示其与“媚外”的关系。
在晚清官教关系中还普遍存在另一种现象,即官员囿于华夷之辨,刻意回避与洋人的接触。而一旦接触,又会秉持平日“情意相通”,办事就能“通融”的传统思维。与中国官员颇有交往经验的新教传教士李佳白发现,中国官员办事喜欢将私事与公事、个人与官方合为一体。
与在中西文化比较视野中凸显出来的公私之分相关联的,是“交涉”与“交际”这对外交概念。薛福成在其1879年出版的《筹洋刍议》中指出:“西人以交际与交涉判为两途,中国使臣之在外洋,彼皆礼貌隆洽,及谈公事,则截然不稍通融。”交涉与交际的分野原本是不存在的,这一提法对后世影响极大。
在薛福成所提倡的交际中,酒宴是重要内容之一。中国早有“折冲樽俎”的典故,晚清亦常以此指代外交活动。但有意思的是晚清士大夫长时间内以与西人同席为耻,因此开通较早的国人不得不去营造新的观念和常识。1885年王韬为其友蔡钧《出使须知》一书作跋,内称:“夫两国交际,燕享雍容,原古者之不废。泰西列国之风犹近乎古。会盟聘问,皆以酒礼笙簧为欢聚好合之具。情至而文自生焉。”几年后薛福成在其《出使四国日记》的跋中也专门列举交际事。
此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交际在外交中的作用。1906年有论者指出:“盖公私既明,则平时接之以情(所谓交际也),临时裁之以法(所谓交涉也),外人虽横亦当帖耳以就我衔勒。”交际的作用也获得了一些实际例证,外交官蔡钧在其《出洋琐记》中便曾列举。曾手抄过总理衙门历年档案的何刚德也发现,“咸同年间外国所来照会,肆意谩骂,毫无平等地位,与近日之来往文字,迥不相同。”何氏将其归因于交际的娴熟。
尽管趋势如此,但转变过程绝难一蹴而就。1902年春出使日本的蔡钧给荣禄的信写道:“欣悉宫太保中堂于京中设筵款洽各国公使,颇称欢惬。盖此等胜举,在各国本属应有之例,特中国未经举行,今自我宫太保中堂首先提倡,即可渐次推行,尊俎联欢,干戈永靖,固有左券可操者。”蔡对一个“应有之例”如此称道,盖缘于其为当时中国稀见所以可贵。实际上20世纪之交的报界在报道此类交际活动新闻时,常有“中西交际之礼宜然”之类的后缀,亦暗示这一时期的“正常”交际仍需要向读者作说明才不致有疑义。
然而,官员的交际观念尚未转变到位,便已迎来质疑之声。1905年有文章对政府的“媚外之伎俩”如此描摹道:“甲日台宴于宫庭,乙日馈礼于使馆,丙日则恭邀听戏,丁日则敦请赏花。极意逢迎,极意结纳,极意趋承。”上述场景并非凭空想象,在那桐任职外务部时期的日记里便可以得到清晰印证。酒宴这一常见交际手段,后经常受到抨击,被视为“媚外”。
政府与民间
庚子后国民外交开始成为士人观察和评判政府外交的一个重要维度。从清末的大量表述可知,国民外交的神奇之处在于其中的“民气”。其实晚清士大夫有利用民气对抗外人的传统,但在后来的表述中,却认为“我政府向不知外交策略关系民气”。这实际上是对民气的再发现和再解读。
在某些人看来,民气与国民外交已经在近来的外交中发挥了功效。1908年某士人奏请开国会折即称:“近年以来如粤汉铁路之废约,苏杭甬津镇铁路之改约,皆以我民气渐伸可为政府之助,外人因是之故亦稍稍就我范围。”他乐观地认为人民与外交可以“影形响应,相与为援”。参与苏杭甬路事交涉的汪大燮虽认为“国民正可为政府后援”,但发现英方并不轻易就范。人民与政府二者的“相与为援”力量实则有限。
虽然晚清士大夫对民气实际效用的质疑从未断绝,但经过清末的再解读后,“民气”与“国民”建立关联,成为救亡图存的希望所在。此后它时常外化为“舆论”,使得“舆论”突破传统“清议”在官僚体制内的反对派角色,成为与政府相颉颃的民间的代言人,自然亦成为中国政治的一股新势力,在内政外交中扮演关键角色。1906年预备立宪诏有著名的“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之语,实际承认其与朝廷的对位。
对政府来说,糟糕的是这种对位实际上已在庚子后演变为一种对抗。双方形成此消彼长的关系,一面是政府权威的急剧流失,另一面是舆论愈加强势。时人常将舆论的强势称为“舆论专制”。强势崛起的舆论在外交方面延续了清议的强硬立场。熊希龄向瞿鸿禨上书阐述政府与舆论在外交上的天然对立:“大抵一国政府策略,与民间理想相去悬殊,政府知世界之大势,迟回顾虑,不敢以国家为孤注之一掷,故可行则行,可止则止,有不能明喻于众者。民间则抱其孤愤之志,一意直行,遂至离于政府所行之轨道。”这种基于朝野角色差异而形成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对立冲突在清末体现得尤为清晰。
由“外交”转成“内变”而累及“大局”,政府的隐忍与民间的孤愤对清末外交的推动作用还未清晰显现,其冲突却已暴露无遗。结果在政府一方则以为“我国薄弱无能之外交官,从前但须对付外人者,今又须对付舆论”;在民间一方则以为“我国民实立于两敌之间:外人挟政府以制我国民,政府复挟外人以制我国民”。这种局面对政府的执政权威无疑是极大的冲击。
晚清政府“媚外”形象的形成,与其公信力的丧失正是一对相因并至的伴生物。其实清末“媚外”之名本非由政府独享,但其后不断有声音将官与民区分开来,制造官员媚外而国民排外的印象。《神州日报》主笔杨毓麟说:“政府诸人必欲实行媚外政策,在国民应别有最后之武器以待之。”“最后之武器”无疑是指革命。
清末民间对官方的“媚外”指责,是以民族主义和主权意识的觉醒为背景的。但官员一方,亦非一味独自酣睡。只不过在现实政治面前,单纯的“孤愤之志”不足以解当下的危机困厄,内心的愤怒不得不与行动上的“隐忍将就”相伴随。
(作者系上海大学历史系讲师;摘自《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