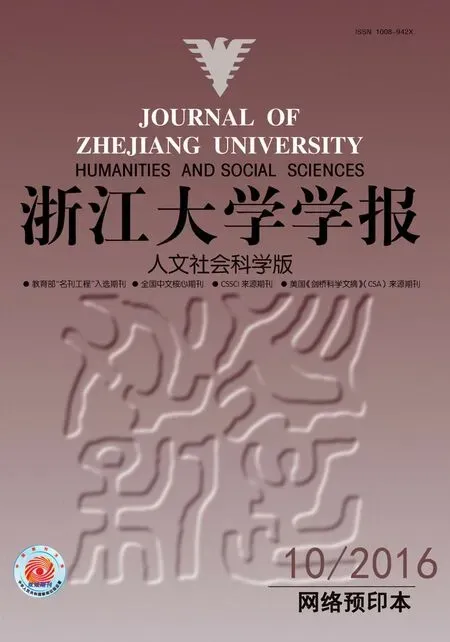论中国式协商民主发展的四种形态
段治文 杨 光
(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8)
主题栏目:协商民主研究
【编者按】 协商民主(又译为“审议民主”“商议民主”)是一种20世纪90年代兴起于西方的民主理论,随后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西方进入了协商民主的政治试验阶段,目前该理论又进入系统阶段。21世纪初,协商民主理论进入中国,有少数学者尝试以此来分析中国地方民主的一些经验现象。浙江大学率先与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合作,于2004年11月在杭州举办了国内第一次有关协商民主的国际研讨会,随后《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也率先开设“协商民主研究”栏目,选择研讨会的若干论文发表,所发表的论文在学术界引起持续关注。需要指出的是,协商民主理论虽然兴起于西方,但协商民主的思想与实践在中国却有着长期的探索,并且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实践的全部过程之中,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特别是当前,中国协商民主的发展已经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期。从比较的视角来看,无论较之亚洲还是北欧、美国,中国协商民主的建构与进展都可以用“神速”一词来形容,每年在基层有上百万次协商实践;2005年,地方政府颁布的关于各种听证会要求、进程、程序及其召开情况的文件全国有945个,2006年上升为1 282个,最高峰是2010年,达到1 833个,2016年仍保持了1 476个。在中共十八大后短短五年里,中国就构建出由七大协商(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和社会组织协商)所构成的全方位、多维度、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地方尤其是乡村社会的协商最为基础,也最具创新性,可以说协商民主机制和精神已经深入到地方的诸多治理实践之中。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专门做出了重要阐述。当然,这些富有特色与成果的协商民主需要我们从中国自己的语境并放在比较的维度加以理解。有鉴于此,《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将继续开设“协商民主研究”栏目,以期通过此栏目继续推进中国协商民主理论研究,推进中国协商民主经验的总结与探索,讲好中国协商民主的故事,梳理中国协商民主的传统资源,传递国内外研究的最新前沿信息。
本期推出两篇论文,段治文、杨光的《论中国式协商民主发展的四种形态》讨论的是中国式协商民主四种形态(党际协商民主、党内协商民主、社会协商民主、公共协商民主)的历史演进及其背后的逻辑线索;郎友兴、张品的《中国协商民主的新进展及对西方经验的超越——北京市朝阳区协商民主实践之分析》检讨了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的局限,并通过北京市朝阳区协商民主实践案例的分析,展示了中国协商民主对西方经验的超越性。希望《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的“协商民主研究”栏目能够成为全球研究协商民主的重要学术交流平台,并期待海内外学者惠赐大作,共同推进协商民主研究。
本栏目特约主持人:朗友兴何包钢教授
论中国式协商民主发展的四种形态
段治文 杨 光
(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8)
中国式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的伟大创造。在从统一战线到多党合作、从群众路线到人民民主的历史进程中,在处理和协调不同利益矛盾以及借鉴和创新等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通过独特的制度设计,推动了党际协商民主、党内协商民主、社会协商民主和公共协商民主四种形态的形成。前两者是领域的横向展开,更多体现的是政治协商民主;而从政治协商民主到社会协商民主、公共协商民主的演进则是层次上的纵向深入,展现的是协商民主从国家政治层面发展到国家—社会互动层面,再到国家—社会—公民互动层面的逻辑递进。中国式协商民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之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制度形式,也是对人类民主政治文明的独特贡献。
党际协商民主; 党内协商民主; 社会协商民主; 公共协商民主
民主的形式不是唯一的,而是多样的,协商民主也是如此。中国式协商民主不是西方的舶来品,而是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与国情的土壤中,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实现的伟大创造。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形成呈现出党际协商民主、党内协商民主、社会协商民主、公共协商民主四种形态的历史演进,其中的逻辑线索深刻地蕴含在从统一战线到多党合作、从群众路线到人民民主的历史进程中,蕴含在处理和协调不同利益矛盾以及借鉴与创新的历史实践中,体现了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是对人类民主政治文明具有独特贡献的成果。
一、 从统一战线到多党合作: 党际协商民主形态的形成
中国式协商民主最早形成的形态是党际协商民主。党际协商民主形成的逻辑线索深刻地蕴含在中国共产党从统一战线到多党合作的理论和实践中。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深刻地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统一战线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加强无产者自身的团结。因为全世界的无产者“有共同的利益,有共同的敌人,面临着同样的斗争;所有的无产者生来就没有民族的偏见”[1]666。其次,要求无产阶级在革命进程中要与可以团结的阶级结成同盟,强调“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2]66。再次,强调在与其他阶级结成同盟时要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指出:“共产主义者同盟不应再度降低自己的地位,去充当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随声附和的合唱队,而应该谋求在正式的民主派旁边建立一个秘密的和公开的独立工人政党组织,并且应该使自己的每一个支部都成为工人协会的中心和核心,在这种工人协会中,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利益问题应该能够进行独立讨论而不受资产阶级影响。”[2]193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直接受到了列宁统一战线思想的指导。列宁在斗争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统一战线思想。列宁强调,不仅要加强无产阶级内部的团结,形成无产阶级统一战线,而且要尽最大的努力联合同盟军,要“对工人和小业主的各种政党采取机动、通融、妥协的办法”[3]183,把“优秀的工人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优秀分子,都转入我们的阵营”[3]184,强调无产阶级政党肩负着“把全国一切民主分子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进行顽强的斗争,彻底战胜万恶的制度,完成历史先人的未竟之业”[3]318的历史任务。同时,列宁要求不仅要在联盟中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而且要在联盟中掌握领导权,强调“无论与其他革命派别订立什么样的实际联盟,都不能而且不应当在理论上、纲领上、旗帜上实行妥协或让步”[4]434,要“保持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阶级独立性”[5]345。
在中国民主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全面实践了统一战线理论。早在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提出,无产阶级“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6]97。中共二大面对国际形势,决定“召集中国工人们加入世界工人的联合战线”[6]136;面对国内形势,提出“中国的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要建立一条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7]63,进一步通过协商,推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抗日战争时期,面临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国共产党明确指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8]152,并通过努力最终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放战争时期,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出“五一”号召要求:“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9]283-284“五一口号”得到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召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形成。
从统一战线到多党合作,其内在精神是在承认多元主体平等地位的基础上追求共识,在沟通协商的基础上力争共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协商理念和民主思想,由此推动了党际协商民主形态的形成。
首先,各主体之间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是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形成的基础,也是党际协商民主的基础。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封建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打倒列强,铲除军阀,争取中国独立,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虽然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政党,但反帝反封建的使命是一致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了抗日救国成为一致的要求。解放战争期间,推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共同的政治目标。总之,各主体之间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使不同阶级、不同政治组织之间有了对话的可能性,为各方的合作提供了空间。在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的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在纷繁复杂的矛盾与斗争之中寻求不同主体间的共同利益,把握共通之处,建构双方的统一性基础,这也成了党际协商民主运行和发展的基础。
其次,承认多样性和平等地位是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的核心,也是党际协商民主的核心。周恩来曾指出:“每个党派都有自己的历史,都代表着各自方面的群众。有人要求各民主党派都和共产党一样,如果都一样了,则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又何必联合呢?正因为有所不同,才需要联合。”[10]163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是以承认党派之间的多样性和平等地位为出发点和立足点的。在民主革命时期,正是基于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全面科学的分析,中国共产党人要求“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8]3,提出建立民主主义联合战线。在统一战线的不断实践中,进一步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确保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进而实现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切都体现了党际政治协商民主的核心是在承认各主体的差异性、多样性和平等地位的基础上的协商合作。
再次,重视沟通协商的工作方式是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的重要表现,也是党际协商民主的重要形式。整合利益追求共识的关键在于沟通和协商。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的基本工作方式是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各方灵活地进行沟通、协商。这种灵活性主要表现在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各方在组织上是独立的,行动上是自主的,平时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需要讨论时各方聚在一起进行平等的沟通与讨论。在革命战争年代,各个时期的统一战线都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各民主党派等在共同目标的基础上,经过广泛的讨论、协商以及相互妥协,最终达成的共识。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更是在共同的政治基础上相互合作,在强调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大团结、大联合的同时,也承认党派间差异的存在,并为因差异而产生的不同利益诉求提供正常的表达渠道,通过沟通和协商达成共识,实现各方利益均衡的最大化。
总之,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发展统一战线并实行多党合作,构建了党际协商民主的前提和基础,也推动了党际协商民主的具体实践。从统一战线到多党合作的历史进程蕴含了党际协商民主形态的形成逻辑。
二、 从群众路线到人民民主: 党内协商民主形态的形成
与党际协商民主相对应的是党内协商民主。党内协商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民主道路过程中形成的重要协商民主形态。以往讲到政治协商,通常主要指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间的党际协商,其实,在中国共产党党内也有广泛的政治协商,这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发展的重要体现,而这一党内协商民主形成的逻辑线索就蕴含在从群众路线到人民民主的历史演进之中。
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深刻地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群众史观。首先,马克思、恩格斯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强调“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1]104,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现实的人及其活动是社会历史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其次,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民群众不仅是认识的主体,而且是实践的主体。认识的主体不是天才人物或英雄豪杰,而是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世界的任务主要是由人民群众完成的,人民群众是人类认识不断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再次,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因此,无产阶级必须要敢于放手发动群众,“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42。
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直接受到了列宁群众观的深刻影响。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和建设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首先,列宁肯定人民群众的重要性,强调“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机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11]53。“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生机勃勃的人民创造力泉源中去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11]57其次,强调无产阶级政党要与人民群众保持真正的联系。列宁指出:“我们党的一切组织和团体每天经常进行的全部工作,即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都是为了加强和扩大同群众的联系。这种工作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12]2而对于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就是先锋队往前跑得太远,没有‘保持排面整齐’,没有同全体劳动大军即同大多数工农群众保持牢固的联系”[13]304。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全面实践了群众路线。早在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明确指出自身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6]162,因此,“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6]162。中共三大宣言指出:“拥护工人农民的自身利益,是我们不能一刻疏忽的;对于工人农民之宣传与组织,是我们特殊的责任;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6]277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要求贯彻民主集中制,了解群众的意见,真正使群众参与到问题的讨论中,使群众得到政治训练。1934年,毛泽东指出:“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8]136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强调,共产党要与人民群众保持紧密联系,“它(共产党)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14]809。1943年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从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工作方法、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基本领导方法、统筹全局的领导艺术等几个方面系统阐述了党的群众路线思想。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14]1094-1095群众路线由此成为人民民主政权建立的重要基础。
从群众路线到人民民主,是以实现人民当家做主为价值取向,以人民为主体,以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为基础,在多方面构成了党内协商民主形态形成的基础。
第一,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是群众路线与人民民主的基础和保障,也是党内协商民主的基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的无限信任和拥护是无产阶级克服一切困难并取得胜利的根源。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人民当家做主。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始终是人民民主得以存在的基础和保障,党内政治协商民主正是在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中形成的,目的就是促进人民当家做主。
第二,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贯穿于群众路线和人民民主的全过程,也是党内协商民主的核心。群众路线强调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也就是要以人民为主体,正如毛泽东所说,“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一定要在革命斗争中显出它的效力,使群众了解它是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利于斗争的,方能普遍地真实地应用于群众组织”[8]72。陕甘宁边区推行政权组织上的“三三制”,就是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的表现,通过各种渠道倾听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真正意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确立后,一方面强调人民民主的实际担当主体是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另一方面强调国家权力不仅来自于人民,而且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这蕴含着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民主精神。而政治协商民主的目的就是实现人民的主体地位,落实群众路线和人民民主。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15]
第三,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群众路线和人民民主的出发点,也是党内协商民主的落脚点。毛泽东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14]1094-1095要求“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4]1096。人民民主的真谛是要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必然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根本实践路径就是协商,通过协商倾听群众的呼声,使决策和工作更好地顺乎民意、合乎实际。
第四,倾听民意、协商沟通的工作方式是群众路线和人民民主的具体表现形式,也是党内协商民主的工作方式。群众路线推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式。从群众中来,就是要倾听民意,将群众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到群众中去,就是要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在“去”和“变”的过程中,必然要求党注重与群众的协商沟通。人民民主国家的要求是要把人民的意志作为国家的最高意志,把人民的利益作为国家的根本利益,倾听民意、协商沟通的工作方式也就内含于人民民主的生命之中。而党内政治协商民主的运行机制正是通过参与、对话、倾听的方式整合各群体的利益、要求和愿望,听取不同的声音,又通过协商、沟通的方式协调各种利益关系,最终达成共识。
总之,倾听民意,了解民情,既尊重多数人的意愿,又照顾少数人的合理要求,以人民群众意志为行动指南,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党内协商民主的实质和精髓。从群众路线到人民民主的历史实践蕴含了党内协商民主形态的形成逻辑。
三、 处理和协调不同利益矛盾: 社会协商民主形态的形成
新中国成立实现了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革命转向国家建设。为了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就需要通过进一步巩固政权,并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在此社会转型中,虽然在新中国内部有不同的阶级、不同的党派,但它们同属于新中国的建设者,因此,其最终的政治身份和政治利益具有内在一致性。这种内在一致性为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可能,也要求要用非对抗性的方式来协调和解决可能出现的矛盾与冲突。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协商民主实践调和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矛盾,维护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地位,最大限度地巩固了新生政权,实现了新中国社会各阶层的高度融合,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为创新中国式协商民主模式提供了重要经验。可以说,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社会协商民主形态开始初步形成。
社会协商民主形态初步形成有以下表现:首先,协商民主开始关注的不仅仅是国家,更多的是关注社会。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从领导人民进行革命转向国家建设,这就要求必须承担起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重任,要求整合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调动各界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在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必然要求协商民主不仅关注国家政治层面,更要关注社会层面。中国式协商民主也就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更多表现为政治层面的党际协商和党内协商,开始慢慢渗透到社会层面。其次,协商民主的形式发生了重要变化。为了调和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矛盾,坚持与不同的利益主体进行对话协商,充分维护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地位,成为社会协商民主的重要形式。比如在1950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实行全国土地改革,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实现了从革命型协商民主到执政型协商民主的转变。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过程中,坚持和平过渡的方针,用咨询、讨论、协商的方式调整公私关系,实现了从决策式协商民主到咨询式协商民主的转变。特别是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通过与资本家直接的平等对话和开展多种形式的咨询式协商,最终决定采取和平赎买的方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把对企业的改造与对人的改造相结合,通过团结和教育,把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在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中,坚持与不同的利益主体进行对话和协商,从实际出发,采取渐进、和平的方式进行改造,避免了改造期间可能发生的剧烈的社会动荡和经济破坏。在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制定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先与各党派代表就相关细节进行协商,再就宪法草案与社会各界人士进行讨论,后开展宪法草案全国范围的协商讨论,实现了从精英型协商民主到大众型协商民主的转变。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以后,社会经济制度和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开始从封闭半封闭的社会逐步走向开放,从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在这样一种新旧结构的替代进程中,旧的利益集团被打破,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不断出现,不同区域间、城乡间、阶层间的利益矛盾不断凸显。这些发展中涌现出的社会问题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了严峻挑战,能否正确处理好这些问题至关重要,社会问题的协商解决成为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点。同时,在经济体制转轨、社会日益开放的过程中,社会管理格局也发生了新的转变:传统的“国家—单位—个人”的一元主体社会管理格局被打破,“国家—市场—社会”的三元结构格局初步形成。在社会管理和利益整合中,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成为常态。在各方社会利益矛盾的倒逼下,在各社会群众组织的呼唤下,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要求,进一步将协商民主从政治层面渗透到社会层面,其标志是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指出:“正确处理和协调各种不同的社会利益和矛盾,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个重大课题。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只有建立在倾听群众意见的基础上,才能切合实际,避免失误。领导机关的活动和面临的困难,也只有为群众所了解,才能被群众所理解。群众的要求和呼声,必须有渠道经常地顺畅地反映上来,建议有地方提,委屈有地方说。这部分群众同那部分群众之间,具体利益和具体意见不尽相同,也需要有互相沟通的机会和渠道。因此,必须使社会协商对话形成制度,及时地、畅通地、准确地做到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彼此沟通,互相理解。”[16]43社会协商民主由此走向深入。
社会协商民主进入新阶段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社会问题的协商解决成为重点,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成为常态。此时的社会协商“既不是简单在社会领域展开的协商,更不是在国家层面展开的协商,而是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围绕着建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而展开的协商。因而,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的互动是其存在的前提”[17]。第二,社会协商的内容发生了重要变化。此时的社会协商民主与中国的经济体制转轨有密切关系,“从社会建设角度看,社会协商就是国家与社会在建构与维护旨在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社会秩序中所形成的沟通、协调与合作机制。这与在国家层面展开的政治协商不同,它是在社会层面展开,其主体不是政治协商中的各政治与社会力量,它是执政党、政府与社会、民众之间形成的协调与协商”[17]。所以,社会协商是化解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之间在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矛盾,促进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之间良性互动的一种协商民主形态。社会协商民主以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为载体,以制度化的手段在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之间搭建调解矛盾的桥梁,一方面促使政府能够倾听民意、了解民情、与民众进行沟通,另一方面也为民众利益的有效表达提供渠道。第三,社会协商的形式向多样化发展。在由政府构建上通下达的利益表达渠道及处理社会矛盾冲突的社会协商民主机制基础上,形成了三种基本的社会协商形式:“党—政府—基层”互动形式,以基层群众自治为代表;“党—政府—民众”互动形式,以民主恳谈会、听证会为代表;“党—政府—社会团体”互动形式,以工会、工商联、青年联合会、妇女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等为代表。通过一系列丰富的社会协商形式,“拓展民众的利益表达空间,深化党和政府与社会民众之间的沟通,强化党和政府对民众利益的关切与关怀”[18]。
总之,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再到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中国共产党在协商民主思想方针指导下,从政权巩固和国家建设等多个方面进行了丰富的协商民主实践,创造性地将协商民主不断引向深入,继党际协商民主形态、党内协商民主形态后,在处理和协调不同利益和矛盾的过程中,推进了社会协商民主形态的形成。
四、 借鉴与创新: 公共协商民主形态的形成
进入21世纪,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社会矛盾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张力空前增大,人们的需求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转型进入新阶段,这必然要求社会协商民主向纵深发展。第一,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全面进步,对外开放日益扩大,人们不断出现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新需求。人们的需求层次不断提升,社会成员在物质需求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后,在精神文化生活方面有了新的更高层次的需求,并且更加关注基础设施、公共环境建设等公共事务。第二,随着中国的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新的深层次矛盾不断出现,社会成员的自主性不断增强,各种新的社会组织、经济组织也相继出现,多元背景下多元主体的利益需求更加纷繁复杂。由于多元文化碰撞,广大群众思想观念呈现独立性、差异性和多样性的新特点,价值取向、行为方式也日趋多样化,社会主体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要求空前增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愿望日益强烈。第三,新的社会问题不断出现,以往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带来了严峻的资源环境问题,“快速增长的多样化的公共需求与公共产品严重短缺、公共服务落后的矛盾突出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与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的矛盾加剧了”[19]31。原本主要在人民群众与政府之间搭建的处理社会矛盾冲突的社会协商民主机制已远远不够,需要进一步为广大群众就自身利益及公共事务问题提供政治参与的畅通渠道。
此时,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开始传入中国。2001年德国学者哈贝马斯来中国做的题为“民主的三种规范模式”的演讲,首次介绍了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为中国协商民主的发展带来了新的视角。“协商民主理论是20世纪末期西方政治学界兴起的一种新的民主理论范式,它主要是指:在政治共同体中,自由与平等的公民,通过公共协商而赋予立法、决策以正当性,同时经由协商民主达至理性立法、参与政治和公民自治的理想。”[20]西方协商民主是对代议制民主的完善和超越。
依照日军强大的军事实力,局部征服中国容易,但要想统治中国却万万难,日军当然深韵儒家文化博大精深,深知中华民族“得土地易,得人心难”的道理。
面对社会发展的新变化,为协调多元而复杂的利益关系,中国共产党在进一步借鉴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基础上,适应社会发展要求,于2006年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正式提出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共同构成中国的两种民主形式。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并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要求“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2015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对新形势下开展政党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等做出全面部署,创造性地将协商民主逐步拓展到公共事务领域,倡导利益主体之间的平等协商对话,实现不同利益主体的和谐共存以及多样化社会的有机统一,由此推进了中国式公共协商民主形态的形成。
新时期公共协商民主的具体表现有:第一,进一步实现了国家—社会—公民的良性互动,这是公共协商民主的基础。随着现代化进程不断深入,社会发展日渐成熟,面对矛盾和冲突,人们需要表达意愿以维护权益,更想要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理性地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实现国家—社会—公民的良性互动。这种公共协商是“共同体的公民就公共话题和集体事务通过平等讨论、理性协商达成共识的过程”[21],是利益多元共生的现代社会在尊重个体正当利益诉求的同时,又能有效协调不同群体利益矛盾的重要方式。在相互沟通中实现相互谅解,在相互协商中寻求解决方法,把无序和冲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进而使利益冲突得以缓和,有利于妥善解决问题,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第二,多元利益格局下,保障和实现公共利益成为公共协商民主的核心。一方面,发展公共事业是政府的重要任务,“理论上说,以发展公共利益为价值指向的公共事业必然会使社会成员普遍受益,因而能够赢得社会成员的理解和支持。但是,公共政策或公共项目的实施往往有可能使一部分社会成员或利益群体直接受益,而使另一部分社会成员或利益群体程度不同地蒙受直接损失”[22]。另一方面,不同利益群体的民众也会因为不同的利益需求产生矛盾冲突。不管是处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利益冲突还是不同民众之间的利益冲突,都需要进行沟通,“谋求在协商中同政府部门和其他公众达成共识,或者愿意接受依据大多数人的意愿而产生的协商结果”[22]。因此,在多元利益格局下,保障和实现公共利益成为公共协商民主的核心。第三,公民参与成为公共协商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如果说社会协商民主更多地发挥着咨询、沟通的功能,是由党和政府主导的对话协商,那么,公共协商则更多地发挥着决策的功能,是由公民主导的参与式协商。公共协商民主是对社会协商民主的进一步拓展,是国家—社会双向互动的社会协商民主向国家—社会—公民合作或共同协作的多向互动的拓展。公民参与成为公共协商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进一步体现了民主的真实性。
总之,公共协商民主基于多元利益主体的意见和需求,在多元利益格局下,最大限度地保障和实现公共利益;是在借鉴西方协商民主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在处理和协调不同群体利益矛盾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结果。从社会协商民主形态到公共协商民主形态,是一种纵向演进的过程,是协商民主在社会生活中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已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实现自我治理的重要方式。
五、 结 语
在从统一战线到多党合作、从群众路线到人民民主的历史进程中,在处理和协调不同利益矛盾以及借鉴和创新等的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通过独特的制度设计,推动了党际协商民主形态、党内协商民主形态、社会协商民主形态和公共协商民主形态的最终形成,体现出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
党际协商民主、党内协商民主、社会协商民主和公共协商民主四种形态是中国式协商民主在不同时期各个领域的表现。四种协商民主形态之间并不是相互并列和相互取代的关系,而是协商民主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体现,既有横向布局,又有纵向演进;既相互补充,又相互促进。党际协商民主形态侧重于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协商,体现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共事所开展的多层次的政治协商;党内协商民主形态是中国式协商民主的主要形态,侧重于国家建设和治理过程中更好地实现党的决策所开展的全方位的政治协商,体现人民当家做主的本质要求;社会协商民主形态是中国式协商民主的重要形态,侧重于社会发展过程中国家—市场—社会格局下的互动协商,体现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公共协商民主形态是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创新形态,侧重于公民利益的维护与实现,体现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中民众的自我教育与自我治理,进一步实现了国家—社会—公民的良性互动。
在四者的关系中,党际协商民主和党内协商民主是范围上的横向展开,更多的是展现政治协商民主层面;而从政治协商民主到社会协商民主、公共协商民主的演进则是在层次上的纵向深入,展现的是协商民主从国家政治层面进入国家—社会互动层面,再到国家—社会—公民互动层面的逻辑递进,最终实现中国式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的发展以及全方位覆盖。
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总要求下,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四种形态为中国社会转型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民主平台,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制度形式。正因如此,2014年9月2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应该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做样子的,应该是全方位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个方面的,应该是全国上上下下都要做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一级的。”这种广泛多层制度化的、“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实现了“协商民主有制可依、有规可守、有章可循、有序可遵”[15]。
总之,党际协商、党内协商、社会协商、公共协商这四种协商民主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基于中国历史、文化和国情,不断回答中国社会转型中提出的时代课题而实现的独特创造,展现了整合利益、缓解社会矛盾、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中国式优势。四种形态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完整形态,是对人类民主政治文明的独特贡献。
[1][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K.Marx & F.Engels,CompleteWorksofMarxandEngels:Vol.2,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57.]
[2][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K.Marx & F.Engels,MarxEngelsCollectedWorks:Vol.2,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3][俄]列宁: 《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Lenin,SelectedWorksofLenin:Vol.4,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2.]
[4][俄]列宁: 《列宁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Lenin,CompleteWorksofLenin:Vol.2,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3.]
[5][俄]列宁: 《列宁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Lenin,CompleteWorksofLenin:Vol.15,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8.]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Literature Research Office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 Central Archives(eds.),SelectedWorksoftheImportantLiteraturesincetheFoundingoftheCPC(1921-1949):Vol.1, Beijing: Central Committee Literature Press, 2011.]
[7]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Central Archives(ed.),SelectedWorksoftheCPCCentralCommitteeDocuments(1921-1925):Vol.1, Beijing: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Publishing House, 1989.]
[8]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Mao Zedong,SelectedWorksofMaoZedong:Vol.1,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1.]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Literature Research Office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 Central Archives(eds.),SelectedWorksoftheImportantLiteraturesincetheFoundingoftheCPC(1921-1949):Vol.25, Beijing: Central Committee Literature Press, 2011.]
[10]周恩来: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Zhou Enlai,SelectedZhouEnlai’sWorksonUnitedFront,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4.]
[11][俄]列宁: 《列宁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Lenin,CompleteWorksofLenin:Vol.33,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5.]
[12][俄]列宁: 《列宁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Lenin,CompleteWorksofLenin:Vol.11,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7.]
[13][俄]列宁: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Lenin,CollectedWorksofLenin:OnSocialis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14]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Mao Zedong,SelectedWorksofMaoZedong:Vol.3,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1.]
[15]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第2版。[Xi Jinping,″Speech on the Assembly Celebrating the 65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People’sDaily, 2014-09-22, p.2.]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Literature Research Office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ed.),SelectedWorksoftheImportantLiteraturesincethe13thNationalCongressoftheCommunistPartyofChina(Ⅰ),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1.]
[17]林尚立: 《社会协商与社会建设:以区分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为分析视角》,《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3年第7期,第135-146页。[Lin Shangli,″Social Consultation and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tinguishing Social Management from Social Governance,″SocialSciencesinChineseHigherEducationInstitution, No.7(2013), pp.135-146.]
[18]林尚立、肖存良等: 《统一战线与中国发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Lin Shangli & Xiao Cunliang et al.,UnitedFrontandChineseDevelopment,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11.]
[19]李君如: 《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李君如谈科学发展观》,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Li Junru,FromtheNewHistoricalStartingPoint:LiJunruTalksAboutScientificOutlookonDevelopment,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2.]
[20]陈家刚: 《当代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学习时报》2004年1月5日,第T00版。[Chen Jiagang,″Contemporary Western Theory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StudyTimes, 2004-01-05, p.T00.]
[21]孙存良: 《多元社会、公共协商与转型期中国的社会和谐》,《党政干部学刊》2011年第2期,第52-54页。[Sun Cunliang,″Diversified Society, Public Consultation, and Social Harmony of China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JournalforPartyandAdministrativeCadres, No.2(2011), pp.52-54.]
[22]阎孟伟: 《社会协商与社会治理》,《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第6-12页。[Yan Mengwei,″Social Consultation and Social Governance,″NankaiJournal(Philosophy,LiteratureandSocialScienceEdition), No.5(2015), pp.6-12.]
TheFourFormsofChineseDeliberativeDemocracyDevelopment
Duan Zhiwen Yang Guang
(SchoolofMarxism,ZhejiangUniversity,Hangzhou310028,China)
There is more than one form of democracy. Democracy is diversified, so is deliberative democracy. Chinese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s a great creation realiz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 the basis of its practice of leading in the country’s revolutions, constructions, and reforms.
The earliest form of Chinese deliberative democracy was the inter-party deliberative democracy, which was developed in its theory and practice from the united front to the multi-party cooperation, the inner spirit of which was to pursue consensus while recognizing the equal status of different parties and to create a win-win situation via communications and negotiations. It reflected the ideas of consultation and democracy that were consistently implement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resulted in the formation of inter-party deliberative democracy.
The inner-party deliberative democracy was practiced in correspondence to the inter-party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s the important performance of the inner party democracy of the CPC, it took shape from the practice of the policies from following the mass lines to practicing people’s democracy, in the process of which, to make the people as the masters of the country was taken as the preferred values, which in turn became the foundation of the inner-party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many perspectives.
Social deliberative democracy was started in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China and was moved forward in the seco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actualized by the socialist reform and development. Especially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when the social relations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have undergone major changes, to deal with and to coordinate the conflicts among various interest groups and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time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infiltrated deliberative democracy from the politics to society and therefore has further promoted the formation of the social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the 21st century, with the deepened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the contradictions among various sectors of the society are unprecedentedly intense. In order to coordinate the complicated and complex interest relation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reatively extends the deliberative democracy to the field of public affairs, advocating equal dialogues and negotiations for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various interest groups and for the dynamic unity of a diversified society,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public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short,in the history of its development from the united front to multi-party cooperation, from following the mass line to people’s democracy, in dealing with and coordinating the conflicts among various interest groups, in learning from history and bringing forth the new idea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realized step by step the inter-party, inner-party, social and public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mong the four forms of democracy, the first two extend horizontally, focusing on the political negotiations. While the political, social, and public deliberative democracies extend vertically and hierarchically, demonstrating a logic deepening from the nation’s political level to the nation-society interaction level, and then to the nation-society-citizen interaction level. Chinese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results of the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is a significant form of the socialist democr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is a unique contribution to the civilization of human democracy.

inter-party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ner-party deliberative democracy; social deliberative democracy; public deliberative democracy
10.3785/j.issn.1008-942X.CN33-6000/C.2017.07.034
2017-07-03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zjujournals.com/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2017-10-30网络连续型出版物号CN33-6000/C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14MLZX06YB)
1.段治文(http://orcid.org/0000-0001-7179-9698),男,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2.杨光(http://orcid.org/0000-0002-7392-2968),女,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