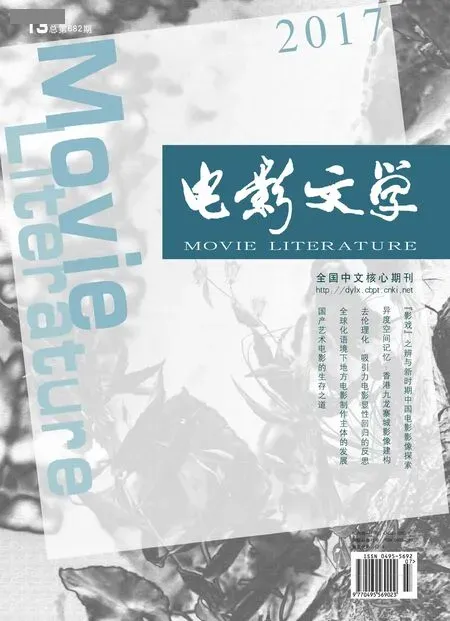异度空间记忆:香港九龙寨城影像建构
陈可唯
(广东工业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广东 广州 510000;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000)
九龙寨城曾是香港极富传奇色彩的贫民窟,既是鱼龙混杂、藏污纳垢的“罪恶之城”,又有自成体制、自给自足的“地下秩序”。九龙寨城也是一座“影像城池”,是香港黑帮片和警匪片最痴迷的原型及片场。1993年这个现代城市文明视域下的“都市疮疤”被拆除,与之相生的“寨城往事”也消散于历史烟尘,而在之后的二十余年中,“寨城记忆”依然在各种影像中持续发酵,被影视、动漫、游戏作品作为空间背景反复使用,并被构筑成集体怀旧的文化符号与末世狂欢的魔幻图景。九龙寨城作为香港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地理与文化空间,屡屡成为香港本土以及域外影像呈现的对象,它被记录、叙述、还原、重现,也被移位、变形、扭曲、重构。自20世纪80年代起至今,留存在影像中的“九龙寨城”,经过不同维度的建构,形塑了属于香港的城市空间影像与文化记忆,也投射出各个向度的身份指认与文化认同。
一、香港殖民时期的“异度空间”
(一)法外“飞地”①
在国际化都市香港,曾经有一块2.6公顷的法外“飞地”——九龙寨城,这个“异度空间”的存在几乎伴随香港整个殖民历史。寨城历史与香港近代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香港殖民历史中从未被真正殖民过的区域。
九龙寨城始建于1843年(清道光二十三年),是清廷驻军把守的海防阵地,清末香港割让给英国,砌墙封闭的九龙寨是整个香港殖民地唯一的“清朝管辖”地带。到民国初年,九龙寨城又一度成为香港人“感受旧中国”的怀旧之地,因其在法律上仍属中国领土无人管辖,开始成为通缉犯和流浪者的容身之处。日军攻占香港期间,九龙寨城的城墙被拆毁,作为扩建启德机场的建筑材料,打破了寨城原本的封闭性,引来更多无家可归的三教九流的人群。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许多内地和东南亚难民涌入香港,在寨城聚居并开始大量修建房屋,政府多次驱逐无效,从此九龙城寨成为中国政府有权管理却无力管理,英国政府和香港殖民政府想要管理却无权进入的“三不管”“无政府”地带,也是香港殖民时期特殊的“界中之界”。
从20世纪60年代起,九龙寨城已成为香港“黄赌毒”盛行之地,城内没有供电、环卫、安保、司法,聚居着赌徒、毒贩、妓女、偷渡客、瘾君子、通缉犯、无证游医、亡命之徒、黑帮势力。没有间隔的密集建筑遮蔽了阳光,幽暗狭窄的街巷宛如迷宫,无比恶劣的卫生条件不堪入目,横七竖八的室外电线盘旋交错,启德机场的飞机近在咫尺轰鸣于头顶。寨城不受港英司法管辖,以极其低廉的生活成本、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以及“不问出处”的身份包容,成为众多流亡者的落脚处。到20世纪80年代,寨城人口空前膨胀至5万人,成为当时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社区(人均居住面积0.5平方米),没有任何专业设计与工程监测的密集建筑,颇具后现代空间感。这个边缘例外的“界中之界”,因其独特的空间结构、文化生态及生存秩序,成为有世界影响的贫民窟。②
(二)寨城“生态”
九龙寨城一直都是香港殖民时期的“异度空间”,内部虽无法律却自成体制,黑帮与民间组织建立了稳固的“地下秩序”,形成一种区别于城外法治社会却又乱中有序的“寨城生态”,以“江湖道义”为中心的人际交往法则替代了现代都市规则。九龙寨城经常是来到香港的偷渡客和流浪者的第一个处所,虽然鱼目混杂、黑帮密布,却有中国民间宗族的“道义”伦理维系人情秩序,除了黑帮,还有城内居民自发组织起来的治安队、街坊福利事业促进委员会、巡逻队、九龙城寨人民代表大会(自治组织)等,这些组织和帮派势力、宗教团体、志愿组织等一起维护城寨秩序,承担寨城内的公共事务。
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毒品交易与暴力营生的整体下降,九龙寨城内居住的以“良民”居多,也在某种程度上凝聚了香港底层民众的生存希望与创业梦想。比如寨城东头有一条当时闻名香港的“牙医街”,聚集了近百家无证牙医诊所,因收费低廉吸引不少城内和城外居民,很多已搬出寨城的居民都回到牙医街诊疗。寨城还有各种地下工厂星罗棋布,进行低成本的食品加工、配件生产和手工业制造;从内地或东南亚偷渡入港的“无身份者”只要进入寨城就能找到工作维持生计,迈出立足香港的第一步;也有在城外遭遇变故和挫败的香港居民搬入寨城内暂居,用低微的生活成本渡过难关。
香港作家也斯在1993年九龙寨城拆除之时这样描述他眼里的“寨城生活”——“不管人家怎样说这是一个三不管的地带,事实上近年许多偏门的行业已没有那么猖獗了。大部分人还是过着老实的营生。鱼蛋和猪血的生意总那么好,看来那么肮脏的工作,最后做出来的产品却是全港大街小巷特别受欢迎的美味小吃。这儿也特别多牙医……从国内出来没有正式执照的医生可以在这里挂牌,这朦胧的隙缝地带容许这类暧昧的存在。当然,生存于隙缝的人,都担心这暧昧的例外地带很快就不再存在了。”③
(三)“家宅”记忆
对于流离失所、亡命天涯的香港“边缘”群体而言,九龙寨城这个“边界例外”区域,正是可以让他们产生归属感的栖息地,形成一种如同法国哲学家巴什拉所阐述的“家宅”的空间力量。巴什拉的空间理论认为“家宅”不仅仅是居住的外部空间,还能形成承载梦想和回忆的内在价值。“我们应该证明家宅是一种强大的融合力量,把人的思想、回忆和梦融合在一起。在这一融合中,联系的原则是梦想,过去、现在和未来给家宅不同的活力,这些活力常常相互干渉,有时相互对抗,有时相互刺激……在我们的梦想中,家宅总是一个巨大的摇篮。”④这种家宅情结与梦想融合,会长期寓居在群体回忆中,即使有了新的家宅,那个旧家宅里的“家神”(Lares)还是会被带走并珍藏。
无论怎样阐释九龙寨城的内在文化生态,这个存在于典范式国际大都市里的“异度空间”以及随之带来的诸多治安、市容、卫生等问题,还是让它成为港英政府眼中的疮疤。1987年,港英政府与中国政府达成清拆寨城的协议,决定在原址兴建公园。1991年,九龙寨城开始正式拆迁,经过长达三年艰难反复的协调清拆,到1994年4月,原址终于成为现在的清代园林风格的“九龙寨城公园”。从此“九龙寨城”成为历史,也因其消失不可重现,它一直成为港人的集体记忆和怀旧空间。许多在九龙寨城度过大半生的居民以及有过寨城居住经历的人,在之后的岁月里都存有某种寨城情结,这个逝去的曾经的“家宅”,成为永恒的空间记忆。如巴什拉所言:“家宅不只是历史的流逝过程中,在我们的历史叙事中日复一日地被体验着……当新的家宅中重新出现过去的家宅回忆时,我们来到了永远不变的童年国度……我们通过重新体验受保护的回忆来获得自我安慰。”⑤
二、九龙寨城“进行时”影像建构
(一)香港黑帮片发源地
香港电影的经典类型片——黑帮片、警匪片的故事原型和精神内核都可从九龙寨城找到源头,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九龙寨城经常作为港产黑帮片的实景片场,也孕育了那个年代的几部经典港产片,如今这些影片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消失的九龙寨城的影像历史资料。
1982年,蓝乃才执导的港产片《城寨出来者》是当年的热映电影,也是迄今为止最全景、最直观、最彻底展现那个时代的“犯罪天堂”九龙寨城的生活与景观的影片。全片在寨城内实景拍摄,展现一对孤儿兄弟在赌档林立、毒品肆虐、色情泛滥的城寨里的惨烈成长,片末手提摄影机拍摄的“困兽式”死亡搏斗极尽疯狂悲怆。“寨城实景”的真切可感、“法外飞地”的混乱暴戾、“江湖兄弟”的义薄云天,都极富80年代香港黑帮片的本土趣味,《城寨出来者》也成为一部永远无法重拍的电影。1984年麦当雄导演的香港警匪动作片《省港旗兵》也在九龙寨城实景拍摄,一群内地偷渡客到香港讲述了黑帮的故事,影片中“大圈帮”(内地偷渡客到香港从事黑社会犯罪活动的群体)历史的展现直观凌厉。这两部早期实景拍摄的港产片,都是九龙寨城作为“罪恶之窟”的影像记忆,它们用镜头记录了“进行时”的九龙寨城的风貌。1993年,在九龙寨城拆除之前,由黄志强执导、成龙主演的警匪片《重案组》进入寨城进行最后的实景拍摄,展现一起绑架案的始末。警匪对立、黑帮风云、功夫动作,都是那个时代经典的港产片模式,只是之后的香港黑帮片,都无缘在这个真正的“飞地”上进行摄制。
九龙寨城从空间、秩序及文化上,都可视为香港黑帮片的发源地,既有真实的“黑暗之城”的具象,又散发出暧昧的“黑色浪漫”⑥气息。一方面,九龙寨城从题材、人物、场景上给香港黑帮片提供了有据可循的延展素材,也从地理、生态、质感上为香港黑帮片奠定了无可复制的基调。另一方面,以“进行时”的九龙寨城为背景的港产片,也为“寨城记忆”提供了影像载体,对九龙寨城奇特空间的反复呈现,让它随着港产片的崛起逐渐成为香港“异度空间”的象征性符号。
(二)域外“地下香港”影像
20世纪80年代,“中国功夫”在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受到追捧,其中很大的原因是源于香港功夫电影的迅速崛起与广泛流传,美国好莱坞动作片经常以香港电影作为动作设计的范本。在当时的美国电影制作团队眼中,全世界没有什么地方比香港更适合表现“黑帮”与“功夫”,而在香港,九龙寨城又成为承载这些题材的最佳空间,于是就有西方摄制组专程远赴香港取景,1988年的美国动作片《血点》(Bloodsport)就是在九龙寨城内实景拍摄完成的。《血点》改编自美国空手道传奇人物Frank Dux的真实经历,尚格·云顿扮演的美国拳手弗兰克来参加香港九龙寨城举办的地下武斗大会,其间与各路人士、黑白两道狭路相遇,经历重重艰险,最终成为首度赢得赛事的西方人。影片颇具80年代港产动作片的趣味,用低廉的投入、摇晃的镜头、刺激的动作,呈现了一个美国英雄在香港完成的功夫梦。
九龙寨城是美国《血点》摄制组眼中“地下香港”的最佳实景,对这个空间的表现充满拉康式的“凝视”(gaze)意味,也体现了那个时代域外电影呈现九龙寨城的某种“套式”(stereotype)。英国学者彼得·伯克对这种“套式”进行过阐述,“当不同的文化相遇时,每种文化对其他文化形成的形象也有可能成为‘套式’……套式本身可能并没有错误,但它往往会夸大事实中某些特征,同时又抹杀其他一些特征,套式多多少少会有些粗糙和歪曲”⑦。作为“他者”对九龙寨城的空间影像建构,总会有先入为主的模式化定式,比如“东方黑帮”与“贼巢之地”的夸大化的预设。《血点》投入低廉,在九龙寨城中几乎都是实景实地与自然光线的无技巧摄制,片中的诸多场景,特别是其中一段用手提摄像机晃动跟拍的寨城内昏暗街道的长镜头,后来出现在大量九龙寨城的纪录片中,几乎成为城内幽暗街景最真实的动态影像记录。
(三)“实景影像”作为历史记忆
九龙寨城“进行时”电影作品,随着寨城的消失,经常作为“实景影像”的历史资料被使用,随着媒介手段的变化,将影片作为史料,已逐渐被史学界接受,但也一直伴随着质疑,美国批评家海登·怀特提出过“影视史学”(historiophoty)的主张,即“用视觉形象和影视化的话语表达的历史以及我们对它的思考”是对“史学”(historiography)的补充。⑧彼得·伯克对“作为证据的影片”⑨有过谨慎的论述,电影作为“更为流畅的叙事方法能产生更大的‘事实效应’或‘对事实的想象’”⑩。他肯定影片作为史料的潜力,也提出如何评估这类证据的价值的问题,“既要考虑到这种媒体的特征,又考虑到电影的语言”。
在九龙寨城实景拍摄电影的初衷并不属于“现实实录”性质,而是以九龙寨城为空间场景的艺术创作,充分运用故事建构、电影技巧和剪辑手段,顺理成章地将一个经过提炼、加工、想象的九龙寨城进行影像呈现,即使受众在观看过程中将注意力集中到“实景”,还是改变不了由媒体的塑造带来的“错觉”,就像彼得·伯克说的:“电影的魅力在于它会让观众产生亲眼目击事件的感受。但这也是电影这种媒体的危险之处,因为这种目击者的感受实际上只是一种错觉……用影片呈现的历史像绘画中的历史或文字写的历史一样,也属于解释行为。”但是,这也不能完全否认实景寨城影像作为历史记忆的可取性,重点在于如何进行解释。
展示九龙寨城的“实景影像”本身兼具物性与诗性、存在与意义、功能性与阐释性,如果能把空间影像的场景实录功能、影像本身的诗性特质以及影像的意义阐释系统作为一个整体纳入历史记忆的解析范畴,或可打开“影像历史记忆”的广阔空间。德国“文化记忆”理论学者扬·阿斯曼将记忆的外部维度分为四个部分:一是摹仿性记忆,二是对物的记忆,三是交往记忆(语言和交流),四是文化记忆(对意义的传承)。空间影像记忆就兼容了这四重维度,让历史展开诗与物、现实与想象、地理与文化等多重阐释的视野。彼得·伯克在《图像证史》的最后,也认可正在蓬勃崛起的“影像”的历史价值——“影片可以用画面来表现过去,也可以通过表面和空间来概括过去的时代精神,这种潜力十分明显。”
三、九龙寨城“过去时”影像建构
(一)“怀旧”空间的影像建构
九龙寨城清拆之后,关于寨城的影像作品并没有因为现实空间的消失而减少,甚至比“进行时”的寨城影像更加丰富和活跃。“怀旧空间”成为“过去时”九龙寨城影像建构的新维度,九龙寨城及其所代表的时代与精神,成为一代港人的集体记忆,也成为香港殖民时代的文化隐喻。在九龙寨城拆除之后的许多年里,展现寨城景观与历史的影片层出不穷,它变成了一个类似扬·阿斯曼所说的“被唤醒的空间”。
1993年之后,九龙寨城依然成为香港黑帮片的创作题材与影像空间。比如王晶执导的《O记三合会档案》(1999),把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九龙寨城黑帮历史进行影像复现,那个香港黑帮猖獗、治安混乱的时代,正是九龙寨城帮派势力的鼎盛期,影片展现一对江湖兄弟在寨城黑帮系统中如履薄冰、拾级而上的血泪传奇。在某种意义上,《O记三合会档案》是一部展现寨城黑帮历史的传奇影像,呈现了九龙寨城内以“三合会”(洪门)为代表的香港黑帮历史与黑道秩序,既有刀光剑影、血腥暴力、警匪勾结,也有兄弟义气、忠肝义胆、江湖风雨。而到了《龙城岁月》(又名《黑社会》,2005)的“杜氏黑帮片”,则融合了导演杜琪峰的个人情结与香港黑帮的兴衰史。杜琪峰少年时代就在九龙寨城度过,影片没有以假乱真的寨城景观复现,而是用日常感和私人化的视角展现了“龙城黑帮”的人生。《龙城岁月》一改香港黑帮片的喋血江湖与火爆场面,甚至从头至尾没有出现枪支和枪响,仅仅用层层推进的内在结构张力,以及细致丰富的人物塑造,铺陈出日常化的香港黑社会生态,收敛锋芒地呈现黑帮内部的秩序、伦理与兴衰。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在陈德森导演的合拍历史片《十月围城》(2009)中,看到被精致还原的清末民初九龙寨城的景观;可以在周星驰的《功夫》(2004)里,找到有明显九龙寨城痕迹的“猪笼城寨”,底层聚集的密集屋宇,充满香港草根人生的戏谑感与生命力;可以在日本影片《金田一少年事件簿:香港九龙财宝杀人事件》(2013)中,看到九龙寨城在域外影像中依然作为香港的文化符号存在;可以在《叶问:终极一战》(2013)中,看到逼真还原的1959年九龙寨城的景观风貌;可以在九龙寨城夷为平地之后20年,看到美国《华尔街日报》投拍的18分钟的纪录片《消失的记忆:香港九龙寨城》(CityofImagination:KowloonWalledCity, 20Year,2004),寻访那些曾长年在寨城居住的港人与移民,整合珍贵的影像图片资料,追溯这座传奇围城的历史。
(二)“魔幻”空间的影像建构
九龙寨城的空间原型和建筑特色极富“后现代”意味,毫无整体规划的楼房由居民自行搭建(最高14层),且全程没有专业建筑师与工程师的参与,楼宇之间没有空隙,摇摇欲坠又互相支撑,构成一个有凝聚感的水泥城堡,充满“反乌托邦”的奇异风格。九龙寨城的奇异建筑形态成为各种影像创作的空间原型,一贯擅长并迷恋魔幻诡谲题材的香港导演徐克,其作品《狄仁杰之通天帝国》(2010)的“鬼市”场景设计中,就能看到九龙寨城的烙印。泰港合拍的恐怖片《鬼域》(2006)里,那个亦真亦幻的灵异空间的营造,几乎全方位照搬了九龙寨城的空间格局,“被遗弃的空间”的隐喻与九龙寨城本身的空间内涵也十分吻合,九龙寨城也曾一度成为香港的“鬼域”,一个被遗弃、被孤立的“黑暗之城”。
在很多域外创作者眼中,这座消失的贫民窟,是表现魔幻现实与末世狂欢的极佳空间,西方和日本的科幻类电影、漫画、游戏中,经常出现以此为原型的空间形态。日本经典科幻动画片《攻壳机动队》(1995),“再造人”生活的未来都市“新港里”,巷深楼密,阴郁压抑,传神地借鉴了九龙寨城的另类空间美学。许多日本艺术家对九龙寨城密集奇幻的空间格局十分迷恋,日本川崎的Warehourse游乐场,以主题公园的形式细致入微地复刻了一座80年代的九龙寨城。美国科幻片《蝙蝠侠:侠影之谜》(2005),也以九龙寨城为原型,虚构出充斥着疯狂与邪恶的纳罗斯岛。
此外,九龙寨城的空间也被运用在各种经典游戏软件中,如《使命召唤之黑色行动》《街头霸王II》《生化危机6》,以及被日本评为最佳邪典游戏的《九龙风水传》等,空间创意都来自九龙寨城。在诸多域外艺术家和设计师眼里,那片不见天日、摇摇欲坠的楼宇里的霓虹灯火,破败混乱的深巷里的三教九流,不受政府管辖的“异度空间”之遗世独立,都充满末世狂欢的隐喻,也因其消逝而更显神秘。这是一座可以被高度浪漫化和未来化的“末日城池”,美国漫画家Troy Boyle甚至感叹:“我宁愿他们当年拆了埃及金字塔。”
(三)“影像重构”的变形与更新
九龙寨城是殖民时代香港的特殊地带,一段150年历史的见证,一种“第三空间”的身份隐喻,它如同一个“历史失忆症”患者,在是与非、黑与白之间暧昧存在,有挤迫环境下自力更生的顽强生命力,有“间隙”处的挤压与游弋。这与港人长期漂移的身份认同、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无根文化的母体游离,都有文化心理层面的深层应和。九龙寨城的消逝,也是一段历史的消散,它成为集体记忆缅怀的对象,也成为香港文化的怀旧隐喻。
扬·阿斯曼指出文化的记忆需要一个特定的时空来承载,“集体记忆会在具体时空中促发一些结晶点”,九龙寨城以及相关的“寨城往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港人集体记忆的“结晶点”,当时间无法重现,空间成为承载记忆的河床,被还原、建构、重现。巴什拉有过一段对“空间”重现充满诗意的阐述——“在此空间是一切,因为时间不再激活记忆……我们无法重新体验那些已经消失的绵延。我们只能思考它们,在抽象的、被剥夺了一切厚爱的单线条时间中思考它们,是凭借空间,是在空间之中,我们才找到了经过很长的时间而凝结下来的绵延所形成的美丽化石。”空间的集体记忆必然有美化与诗化,一直未从身份认同的潜在尴尬中走出来的香港人,用怀旧影像让九龙寨城在集体记忆中结成了美丽的化石,它无可避免地掺杂了“记忆”与“传奇”的双重特性。
在更深层的维度上,“文化记忆”理论学者阿莱达·阿斯曼犀利地指出文化记忆是由“媒介支撑的记忆”——“我们今天面临的不是记忆难题的自我消解,而是它的强化。其原因在于,如果不想让时代证人的记忆在未来消失,就必须把它转化成后世的文化记忆。这样,鲜活的记忆将让位于一种由媒介支撑的记忆……由于不存在文化记忆的自我生成,所以它依赖于媒介和政治。”影像即是一种媒介,在媒介承载回忆的时候,“重构”必然发生——“回忆的进行从根本上来说是重构性的;它总是从当下出发,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被回忆起的东西在它被召回的那一刻会发生移位、变形、扭曲、重新评价和更新,在潜伏的时段里,回忆并不是安歇在一个安全的保险箱里,而是面临着一个变形的过程。”文化记忆不仅指涉过去,也指涉当下,指涉未来,九龙寨城“过去时”的影像建构,既可以指向过往的集体怀旧,也可以指向未来的超现实魔幻。这个存在于香港特殊历史时代的业已消失的“异度空间”,在影像中获得重现、重构、重生,如同阿莱达·阿斯曼引用华兹华斯的诗句——“我愿为了未来的疗救,把过去的精灵涂油下葬。”
注释:
① “飞地”一词,意指一种特殊的人文地理现象,原指隶属于某一行政区管辖但不与本区毗连的土地。“飞地”具有边缘地带的特征:政府控制力相对薄弱,行政管理松弛且成本较高,社会经济相对落后,文化多样性色彩比较浓郁。
② 关于“九龙寨城”的变迁资料,源于笔者2016年5月赴香港九龙寨城遗址田野调查记录,感谢香港历史研究所邓家宙博士提供寨城历史资料与随行讲解。
③ 原载于1993年《华侨日报》,引自也斯:《也斯看香港》,花城出版社,2011年版,第42页。
⑥ 港片“黑色浪漫”阐释,见孙慰川:《当代香港电影中的黑色浪漫》,《电影创作》,200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