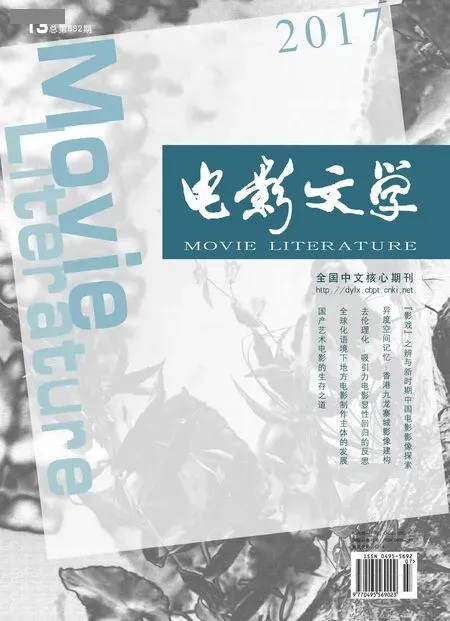“影戏”之辨与新时期中国电影影像探索
张燕菊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陕西 西安 710055)
在新时期(1979—1989)电影理论思潮中,“影戏论”是基于中国电影史而进行的一次关于电影本体问题的探讨。中国电影发展之初被称为“影戏”,在“影戏论”的语境里,“影”(影像)是电影本体元素,是电影独有的,而“戏”(叙事)则是电影与小说戏剧等叙事艺术共有的,并非电影的本体属性。
钟大丰在《论“影戏”》一文中提出“‘影戏’是中国电影的滥觞。‘影戏’是一个由‘戏’和‘影’两种因素组成的矛盾统一体”①。“影”和“戏”分别代表电影的手段和目的、形式和内容、电影本体及其外部功能,在电影发展历程中时常表现为一种此消彼长的二元关系。通常,电影思潮的活跃期也是电影影像本体探索的活跃期,如,20世纪20年代的欧洲先锋派电影运动中的纯电影和诗电影探索,40年代末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50年代末的欧洲新浪潮电影,在电影观念上都曾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叙事的弱化和对影像本体的强调。相反,相对保守的商业电影体系,电影影像探索更容易按部就班,譬如在美国好莱坞电影历程中,几乎没有出现长时段的影像实验期,其完善的电影生产体系和市场机制培育了一套关于电影叙事与影像关系的保守模式。在中国电影发展进程中,新时期是一个电影思潮的活跃期,“去戏剧化”的电影理念,使中国电影影像创作在新时期电影实践中直接或间接受益,不断获得外部形式的丰富、表意功能的增强以及对于影像真实的深入探索。但在“影戏论”的辨争中作为电影本体的“影像”与作为电影功能的“叙事”这两个维度被不恰当地对立起来,中国电影影像叙事研究的弱化也在彼时埋下了隐忧。
一、弱化叙事,以本体的名义——本体论语境下的电影影像形式探索
始于新时期之初的电影影像形式探索,源于中国电影本体意识的觉醒。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电影创新思潮首先以“电影语言现代化”“电影和戏剧离婚”“电影应该是电影”等关于电影性与戏剧性关系问题的探讨拉开帷幕。白景晟发表在1979年第1期《电影艺术参考资料》上的文章《丢掉戏剧的拐杖》,首先对电影的戏剧性传统提出质疑,认为“戏剧”或“戏剧化倾向”是当时中国电影的主要症结;同年2月,谢铁骊在答《电影创作》记者问时谈及“电影创作中舞台剧的习惯势力巨大”;6月,《电影艺术》发表张暖忻、李陀的《谈电影语言的现代》,文中用“装在铁盒子里的舞台剧”形容时下中国电影存在的问题,提出从形式上向世界电影学习、实现电影语言现代化的课题;次年3月,电影理论家钟惦棐先生在会议书面发言中提出“电影和戏剧离婚”,理由是“任何艺术形式, 只有当它足以和邻近的形式相区别的时候, 它的造型运动才算告一段落”。这些讨论的共同观点是:反对戏剧性,强调电影本体形式探索。尽管随之而来的探讨中有理论家从学理和逻辑上对“戏剧化”与“舞台化”、“戏剧化”与“虚假性”、“现代化”与“现代性”等问题进行过论证和纠偏,如邵牧君的《现代化与现代派》、谭霈生的《舞台化与戏剧性——探讨电影与戏剧的同异性》、余倩的《电影应当反映社会矛盾——关于戏剧冲突与电影语》等,但多数电影人还是本能地以更大的兴趣接受了“电影应该是电影”这一强调电影艺术本体性和纯粹性的观点。其中原因可以想见,当时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中国电影创作急于挣脱一切固有思想和艺术成规,走向了电影的本体探索和形式创新,寻求电影区别于其他叙事艺术的戏剧(舞台剧)文学(经典小说)独特之处,特别是影像形式上的独特之处。电影的本体论争使得电影创作和电影批评逐渐摆脱了原有单维度的意识形态批评,于影像创作上给予更多关注。电影创新,很大程度上被归结为影像创新,影像被认为是电影彰显其独特性的最重要元素,是其他艺术所没有的,是电影独有的。
造型意识的觉醒是新时期之初电影创作的标识性变化。最初的形式探索表现为一种形式的狂欢,电影创作者挖空心思以实现影像形式的标新立异,以至于有导演感叹“最近电影界‘创新’‘探索’的意义好像被慢动作、定格、时空跳跃等技巧所替代”②。这种狂欢式的形式探索多少有些炫技杂耍的意味,如《小花》《苦恼人的笑》等打破常规、利用过期胶片、镜头进光、单色调处理等制造视觉效果上的意外和不同,虽有创新但相对浅表,也十分短暂。反思期很快到来,比如关于形式与内容、真实与唯美、形式的内敛与外显等二元关系的思辨,后续电影中关于造型的探索始终持续,随后的阶段造型形式探索融入电影现代性探索,比如第五代电影实际是沿袭并强化了电影本体探索期的形式意识,《一个和八个》《黄土地》《红高粱》等以对造型形象的象征和表现性挖掘,充分显示了造型的力量,并以此完成了中国电影第五代的代际标识。
新时期由电影本体思考所引发的这段形式探索的另一个重要价值,在于关于电影独有表现形式的探索,以及将艺术形式先于内容进行设计的创作思维。例如,吴贻弓导演在《城南旧事》导演阐述中,探讨了影片叙事视点的问题,影片选择主人公英子主观视点的叙事,“最初只是在原作基础上的一种形式选择,但发现这一形式选择能够将人物和事件统一起来,创作者才发现形式实实在在地成了内容的一部分”。黄健中导演也探讨过意识流手法作为形式给电影影像创作带来的变化,认为“意识流影片不注重故事, 而注重含意,是因为生活中的许多哲理通过视觉和听觉的形象来反映比通过一个故事更直截了当、更生动一些”。一般而言,电影创作的出发点大约有三种情况:从思想出发、从故事出发和从形式出发。③这提出了从形式出发思考创作问题的可行性和合理性,新时期的电影创作探索了这种思维的可行性与合理性,只可惜这样的探索止步于初期阶段,而转向了象征性与符号化的形式探索。所以进入商业大片时代,形式探索仍然与炫技等同起来,至今,中国电影影像在形式维度上仍然缺少一种可以品味和把玩的形式感,一种与内容(叙事和表意)相互依附又独立于内容之外的形式魅力。
二、弱化叙事,以真实的名义——纪实主义思潮中的中国电影影像写实探索
在对西方电影理论的译介和学习中,克拉考尔和巴赞纪实主义电影理论在中国被放大和抬高。这使得中国电影摄影及时跟上了世界电影摄影纪实主义美学探索期,长镜头、自然光效、低照度等以写实主义为核心的摄影观念与技巧,进入中国电影摄影创作视野。
真实,是新时期十年创作阐述中出现频度最高的词汇。背景有二,一方面是“文革”之后,中国文艺反对虚假追求真实的艺术诉求,另外,西方写实主义电影理论的全面引入和传播,特别是巴赞关于电影摄影影像本体论的阐释,将纪录性提升为电影的本体属性。这一时期,中国电影思潮中的影戏之辨表现为电影真实性与戏剧性之辨,以及电影生活流和戏剧流的分野。叙事性的弱化,客观上导致了影像的凸显。这一时期的《沙欧》《青春祭》《邻居》《野山》等成为中国纪实主义电影摄影的优秀作品,影像真实探索从观念的更新、技术的进步,最终走向美学的成熟。
自然光效和戏剧光效概念的提出和理论总结,是新时期电影摄影探索对于写实主义电影思潮的积极呼应。电影摄影师鲍萧然在《探求摄影艺术的自然光效》一文中首次用“戏剧光效”概括经典好莱坞电影照明的观念与技巧,并将其与写实主义的“自然光效”照明理念加以区分。戏剧光效是对经典好莱坞时期因电影的商业性和明星制的需要发展起来的一整套照明体系的总结。戏剧光效的主要特点是假定性和风格化。为了获得立体感和美化画面。除了注重五种光效的匹配、直射主光的类型以及所谓交叉反测光的模式伴随人脸左右转动, 交替互为逆光和反侧光外,还要用花哨的逆光勾勒轮廓, 美化人物, 修饰画面, 用类型光弥补脸型缺陷, 用投影完成构图等。至于这些光效是从生活环境中哪里来的, 则不深究。戏剧光效强调光的戏剧表现力,忽视光线的自然规律;按照戏剧内容的要求以及人物内心活动运用光线,常用脚光、顶光、局部照明以及各种效果光来处理人物形象,来烘托气氛、增强戏剧效果或刻画人物的心理状态。而自然光效追求光线的真实感,具体表现为:(1)光质上,追求与人们日常生活状态的光线质感的接近,散射光和漫反射光,强调光源的单纯性,尽量采用现场的固有光及自然光,少用人工光;(2)光强度方面,追求日常生活常态光线照度,即低于100LUX的低照度光域;(3)光源设计(画面光源及光源方向)方面,强调画面光源的合理依据,不主张使用假定性光源,反对“五光”俱全,少用辅助光,不用修饰光。自然光效,引发了摄影照明上的一系列探索性实验,如,《大桥下面》《野山》《青春祭》的探索都深入到低照度光域,生活中的室内散光, 一旦太亮, 就会完全吃掉那种柔和的自然感,接近生活常态的低照度光线才能表现出常态生活的自然情趣和质朴美感。
写实主义电影思潮对电影叙事性的弱化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题材和故事选择上对叙事性的明显弱化,二是电影叙事手法和影像形式上的反戏剧性。电影《野山》就是后者,用鲜明的纪实风格影像将影片内在的戏剧性包装成生活流的模样,使电影看上去自然真实但又极具张力。《野山》的摄影师米家庆赢得了当年的中国电影摄影师学会奖。米家庆的《野山拍摄散记》一文开头引用巴赞的话作为题记,《摄影造型不是画》对“用光作画”的摄影观念提出了质疑和反思,在《野山》的探索中真实影像原则是用一系列“不”字建构的,“不用那些可以使观众察觉的摄影技巧,包括不用变焦距镜头、特写镜头、不正常的大俯大仰视点等”“放弃绘画性的完整构图”“放弃‘用光作画’的造型观念,不拍‘美人照’,不拍‘风光照’”“少用光和不用光”“基本只处理环境光,不加人物光”④。使用常规视角、标准焦距、常见景别、自然光效、固定机位、长镜头等拍摄手法。强调了真实,弱化了形式,将技术技巧和造型降至最低限度。
艺术的审美始终是在逼真化和陌生化的二元关系中寻找均衡。新时期摄影探索中有极致的自然主义写实派,也有所谓绘画派和唯美派,但传统意义上的戏剧光效和相应的摄影手法被摒弃或改进了。崇尚生活流的作品中,叙事维度被理所当然地淡化了。
三、弱化叙事,以表意的名义——现代性辨争中的中国电影影像表意探索
1984 至1988年,中国“影协”举办数届国际电影讲习班,尼克· 布朗将电影符号学、精神分析学、意识形态批评、解释学、叙事学等西方学院派电影理论带入中国电影语话体系,此后,这些理论经由学术刊物及各种研讨活动广泛传播。在此期间,中国电影史学研究者基于对中国早期电影的渊源研究提出“影戏”论,但这场因中国电影的影戏传统之名进行的讨论,并非为电影的叙事性寻找原初依据。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影戏说本身却携带了对影戏模式的否定意味。这一点,影戏论提出者钟大丰在若干年后发表的《是否有重谈“影戏”的必要》一文中有清晰描述:“从理论思想的渊源上,‘影戏理论’说的提出,是20世纪80年代初电影创新运动以非戏剧化为武器否定‘文革’电影经验理论的产物。因此在历史描述的措辞和理论的价值取向上都带有明显的否定性倾向。”⑤影戏论,实际是再度推进电影的非戏剧性特质。随后的1986年,因青年学者朱大可的《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一文引发的“谢晋模式”大讨论,电影的现代主义和精英主义实际胜出,影像的隐喻和象征意义变得重要和凸显,与80年代之初的形式探索形成接续关系,又与第五代的反思意识和批判精神不谋而合。但其中明显的精英文化意识和现代性思潮,再一次让中国电影偏离了叙事传统。
影戏论和谢晋模式大讨论,现代主义电影思潮盖过经典电影传统,影像再次因现代性之名被强化,影像的象征性符号化运用受到鼓励和推崇,影像的表意探索超越叙事成为时尚。今天再翻阅《黄土地》⑥《黑炮事件》⑦《一个和八个》⑧等影片的创作阐述,可以看到字里行间对主题和意象描述的关注远胜于叙事意义上的时空气氛描述。
新时期电影在造型形式表现性和象征意义上的挖掘,与西方电影现代主义思潮相一致,也与中国文艺传统中“文以载道”“意在笔先”相契合,但缺少影像叙事维度上的深入探索。之后田壮壮在回顾《猎场扎撒》的影像风格时明确表示:“那个时候比较极端,排斥剧作、排斥对白、排斥交代,排斥一切非影像化的东西。从《猎场扎撒》到《盗马贼》,已经到了非常极端的程度。”⑨
四、重回叙事: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电影影像探索的叙事转向
尽管东西方语境中关于叙事的讨论早已有之,但叙事学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在俄国形式主义以及西方结构主义理论的双重影响下才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以1969年法国文艺理论家茨维坦托多罗夫首次提出“叙事学”概念为标志。之后,大量关于叙事作品结构分析的理论著述开始出现。20世纪70年代初期,电影结构主义理论开始由电影符号学转向电影叙事学的研究。80年代中期,叙事学理论开始被逐步介绍到中国,而电影叙事学理论进入中国电影创作视野是在90年代之后了。
笔者查阅1979至1989年十年间包括第四代导演《小花》《芙蓉镇》及第五代导演《黑炮事件》《红高粱》等重要影片的三十余篇电影导演和摄影创作阐述,其中少有对于影像叙事的关注。摄影师的言说和创作阐述中,带有中国传统意味的“意境”一词的使用频度远高于西方电影师经常强调的“气氛”描述。“气氛说”着眼于叙事和写实(时代氛围、地方特色、生活气息、主体处境和情绪状态的描述),“意境论”则着重于意象表现(具象画面的抽象喻意)。意境与气氛的微妙差异,恰恰反映着新时期中国电影影像创作的审美诉求。
拍摄于1987年的《末代皇帝》是对中国电影影像创作影响较大的一部影片,该片摄影师斯托拉罗及其“用光作画”的言说在国内摄影师中颇受追捧,但不同时期中国电影摄影对于《末代皇帝》的关注点有细微差异,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年中国电影对《末代皇帝》的影像研究主要集中于该片色彩光线的象征意义,比如皇帝儿时的红黄色调是对于皇权和帝王生活的表征;皇帝青年时代的绿色和白色调是对于成长和西方文明启蒙的隐喻;而战犯管理所的段落采用的灰冷基调则是对末代皇帝没落和颓态的描摹。90年代后期的著述中开始出现影像叙事层面的分析,刘勇宏《用光参与叙事和表意的电影摄影理念》(2001)分析了该片运用光线和色彩元素对叙事结构的谋篇布局,⑩杜昌博的《聊聊电影〈末代皇帝〉银幕剧作的叙事视点》关注到影像的叙事视点与摄影机视角设定之间的关系,穆德远《故事片电影摄影创作》中则用《末代皇帝》中大量实例进行影像造型辅助叙事的细节分析:英国教师庄士敦要求皇宫内务大臣同意皇帝戴眼镜一段的长镜头,光线辅助刻画了两个相互对峙的人物(庄士敦和内务大臣)的情绪变化,光线变化的节奏与戏剧情节发展的节奏相呼应。摄影师通过独特的光线造型设计,既忠实于真实的空间环境,又发展或是说超脱了现实环境,既叙述了故事情节,又充分发挥了具有个人特色的表现主义风格。
影像,是重要的电影本体元素,也是电影表达的基本语汇。在故事电影中,影像的最基本任务是叙事,包括时空描述、人物及人物关系描述,也包括影像对于情节发展的推动,影像在悬念、暗示等情节和细节上作用的发挥。一直以来,中国电影发展的主导因素在意识形态主导、艺术主导、市场主导之间变化更迭,新时期电影是中国电影的转型期,电影的主导意识从“文革”时期的意识形态主导转向艺术诉求为主要导向因素,重“影”轻“戏”虽然让这一时期电影影像创作获得了良好的发展空间,但也造成电影叙事研究与拓展的弱化,当中国电影市场化到来时,影像的形式诉求被推到极致,缺少叙事支撑的电影形式追求走向了单纯的视觉奇观,这是当下电影影像研究中应予以重视和补偿的。
注释:
① 钟大丰:《论“影戏”》,《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85年第11期。
② 滕文骥:《〈都市里的村庄〉导演阐述》,《电影艺术》,1983年第12期。
③ 王志敏:《现代电影美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6页。
④ 米家庆:《野山拍摄散记》,《西影30年》,第77页。
⑤ 钟大丰:《是否有重谈“影戏”的必要》,《电影艺术》,2008年第3期。
⑥ 张艺谋:《〈黄土地〉摄影阐述》,《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85年第6期。
⑦ 王新生、冯伟:《〈黑炮事件〉摄影阐述》,《当代电影》,1986年第5期。
⑧ 张艺谋、肖锋:《〈一个和八个〉摄影阐述》,《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85年第6期。
⑨ 査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田壮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408页。
⑩ 刘勇宏:《用光参与叙事和表意的电影摄影理念——斯托拉罗的摄影艺术》,《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