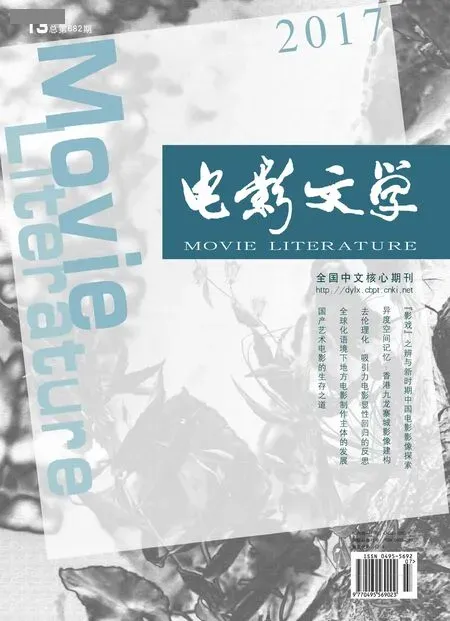《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文化表征研究
李亚玲 曾 超
(1.成都理工大学,四川 成都 610000;2.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广东 深圳 518060)
由于政治原因,20世纪四五十年代台湾当地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集聚地——眷村。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以及眷村房屋的老旧化,眷村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当下许多台湾学者将目光重新放置在逐渐消失且不会重建的眷村文化中。以眷村为题材的影视作品甚多,《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以下简称《牯岭街》)是台湾导演杨德昌所执导的电影作品,长达230多分钟的影像里展现了20世纪60年代生活在台北市眷村的第一、第二代居民的社会风貌和生活状态。眷村里生活的第一代居民思乡情怀浓厚,对无法回归故乡的现状充满了无奈;第二代在眷村成长的青年对自我身份和文化归属产生了严重的困惑。杨德昌作为典型的眷村二代,成长于动荡的台湾社会,历经了白色恐怖时期、少年情杀、青少年帮派文化等事件。青春时期的杨德昌对周遭环境和文化都有着真实且深刻的感受,尔后这些情结都被一一投影在《牯岭街》中。因此,《牯岭街》并不是大众定义上的青春电影或怀旧电影,它直接将青春的不美好甚至颓废的故事赤裸裸地和盘托出,对大众认知的“美好青春”观念进行了颠覆性的解构。究其原因还是来自于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外省人”在自我定位与身份找寻中所产生的一系列困惑,杨德昌在《牯岭街》中进一步挖掘这种迷茫,结合其独特的视听表现手法创作了与时代文化特征高度契合的作品。
一、空间:眷村与社会背景的影像再现
相较其他门类艺术,电影对空间的表达更具优势,导演可以选择自己想要表现的空间环境,通过拍摄角度、色调影调、构图等艺术处理方式对空间再加工。受众看到的是镌刻着导演强烈的主观意识、独特的影像风格和情感倾向所塑造出的电影空间。《牯岭街》中人物设定和故事情节基于20世纪60年代的台北展开,在电影中,最具代表性的空间展现是对眷村的影像重塑。眷村的形成有着特定的历史缘由,1949年,几十万中国大陆官兵和民众在台湾定居。为了安置来台人员及眷属,政府一边兴建集体舍屋,一边续用日治时期留下的集体军队房屋,这些被集中安置的大陆居民在各自集聚地内形成了眷村。
《牯岭街》里对于眷村的空间重塑主要采取了两种方式:其一,对于眷村房屋类型的选择;其二,所采用的艺术手法。笔者曾在台湾眷村文化馆进行实地调研,了解到眷村的建筑风格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日式建筑风格的房屋,这种风格的房屋建于日治时代;另一种是经由大陆来台人员于1949年后所建的房屋。日本殖民台湾时出于长期居住的考虑将房子建得比较牢固,而随国民党撤退至台湾的军人起初来台并没有长期居留的打算,所建设的房子较为简陋。两种不同形式的眷村从建筑外貌上就能清晰分辨,《牯岭街》里所呈现的眷村建筑属日治时期所留下的房屋。方方正正的日式建筑,像镶嵌在画面里的盒子,利用框架式构图,让门、墙、窗形成视觉牢笼,将人们置入其中,观众亦在狭隘拥挤的画面中产生压抑感。这样的构图技巧与生活在眷村的居民备受束缚的情形相得益彰,一来恰切地表现了当时人们处境艰难,二来完成了日式建筑眷村的景象再现。拍摄眷村房屋面貌时,杨德昌多使用固定镜头,用光贴近自然光效。不够敞亮的房间,正如同那个混沌不安的台湾社会,同时亦隐喻出第一代的父辈被房子所“禁锢”在台湾,思乡之情难以排遣,面对现状只能无奈妥协;第二代的孩子们被“困”在了这样的一个空间内,无法完成“我是谁”的身份认同,仅从父母口述的家乡中初次完成“大陆某省人”的身份定位,自身却毫无家乡的亲身体验。
《牯岭街》中纪实的影像风格只是对生活空间的展现,社会空间的表现则依赖于时代背景的架构,故事情节和人物活动亦需要时代背景作为重要铺垫。《牯岭街》的故事发生在1960年,当时随迁的大陆人都知道“反攻大陆”仅剩一个口号,回乡的机会已然无望。出于自我保护的需求,生活在同一眷村的居民会形成相对封闭的局面,在相关文献中也有记载:“眷村内有医院、商店、邮局、学校等,公共设施齐备,所以眷村居民没有大事,一般都不出村子,在眷村形成了他们封闭的生活圈子。”①这些在台湾定居的外省人,与当时的台湾本省人在文化和生活上有较大差异,早期眷村人与台湾当地的本省居民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与台湾当地居民文化的不同导致眷村居民成为台湾当地人眼中的外省人,“外省人”是针对随国民政府来台居住的大陆人士的一种刻意的人群划分。对于早期从大陆来的外省人而言,认清现实并在当时混乱的社会中找到群体力量与话语至关重要。
二、身份:认同困惑与价值观选择
杨德昌用近4个小时的影像铺陈了20世纪60年代的眷村人文和社会风貌,精准地表现了两代人在自我身份认同中的困惑与迷失。“身份认同是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其基本含义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这个词总爱追问:我(现代人)是谁?从何而来?到何处去?”②在《牯岭街》中小四母亲有句台词:“跟日本人打了八年战,如今住日本房子,听日本人的歌。”看似是小四母亲不经意的一句话,恰巧反映了眷村里的第一代并没有忘却当年与日本人的战争,从大陆远离家乡辗转到台湾的共同经历,使他们还满怀强烈的思乡情感。这些人跟随国民政府离开家乡,经历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举家搬迁,又因为两岸的政治原因无法重回故土、与亲人失去联络,心里充满的无奈无处遣怀。他们对台湾居民的认识也是零碎的,也无法真正融入台湾当地人的文化中。这代人肩负着下一代的养育任务,没有亲朋相助,亦无祖辈积蓄,没有政治或军事地位的普通百姓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一如《牯岭街》里小四家的处境。影片中小四的父亲和母亲在一次争吵后,父亲抱紧母亲,说了一句“我只剩下你和几个孩子了”。母亲哭着回应,“以后全靠我们自己了”。生活在眷村的第一代人虽然开始接受无法重返家乡的事实,但还会与同省的老乡说家乡话,还经常聊起在大陆发生的故事,还小心翼翼地保存具有纪念意义的物品,即便是被迫定居在台湾,他们也能清楚地找到自我身份的定位。关于第一代的身份认同非常明显,即中国人,他们可能是四川人、广东人、上海人、南京人等,却不是所谓的“台湾人”。
然而第二代却出现了严重的身份认同困扰。生活在眷村里的第二代从父辈的口中了解自己的家乡,对家乡只有抽象的概念,并无直观经验,他们对于自己是大陆人还是台湾人充满了困惑。《牯岭街》中的小四为典型,一方面,小四的父母常提及在上海的事情,可小四却从没在父辈所提及的上海生活过,很难凭想象在情绪和情感上产生与父辈一代的思乡共鸣;另一方面,在台湾他们是后来的“外省人”,与台湾的“本省人”也无法产生所谓的文化共鸣。相较于第一代而言,第二代在自我身份认同当中遇到的问题更为严重。
三、文化:选择与迷失
《牯岭街》影射出了当时眷村第二代在青春时期文化认同下的困惑与迷失,自身的焦虑和处境的变动都影响着成长在眷村里的第二代。
著名心理学家Tajfel针对社会身份认同提出过重要理论,认为一个人的社会群体成员身份和群体类别是其自我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主张人们努力获得和维持积极的社会认同,从而提升自尊。③之后,Tajfel和他的学生Turner一起发展了社会认同的理论,人们倾向于将自己置于群体当中来构建自己的群体力量以及与其他团体的边界。文化认同是一种有意识的倾向性活动,它出现的前提必须有异文化的冲突。如果人们置身于一个彼此相同的文化中,那么文化认同这种行为也显得意义不大,倘若置于不同文化之间,且文化与文化在相遇时直面碰撞或产生矛盾,文化认同才会成为有实际意义的行为。换言之,文化认同是为了区分本文化与异文化之间的不同而出现的行为,个人作为单一力量的主体寻求团体力量而完成自我强大的过程。国民政府撤台前,台湾社会生态由闽、客、本地居民(平埔族和高山族)三大族群构成。撤台后,几十万从大陆来台的“外省人”势必将与“本省人”展开资源的争夺,由此“外省人”与“本省人”极易形成两个对立面。因此在几十万大陆人撤台较长的时间里,“本省人”对“外省人”都持有倾轧的抵触情绪。文化认同在生活中的表征有:区域相似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情感传达等,认同过程虽然是一种夹带着意识与相似主体间进行的同构联系,但久而久之,文化却会形成一种精神的内涵。不论是出于自身权益的保护,还是出于壮大集体力量的潜在需求,同一眷村内生活的人们会渐而形成一种抱团的行为。
文化的选择与迷失在《牯岭街》中表现为眷村二代价值观念的构造,在眷村生活的居民来自中国大陆的五湖四海,在多元的文化背景中,新成长的一代缺乏正规的社会观念的输入,加之青春期的叛逆情绪,成长期内价值观念的生成没有经过正确的引导。小四所有的价值观都来自于父亲的榜样效应,小四的父亲作为民国时期传统的知识分子,为人处世不够圆滑,甚至有些木讷。小四的父亲有着与当时社会现状格格不入的正义感,在小四受到学校训导处老师不公平的处置时父亲会义正词严地与老师辩驳,并且教导小四为人要正直。一直以来,在小四心中父亲的言行成为他为人处世的度量衡。可是随着在台湾的时间长久起来,父亲的原有性格也被时代磨去棱角。白色戒严时期,父亲因被疑与共产党有政治关系被国民党带走审讯,这次审讯也成为父亲性格变化的转折点。电影无法详细记录父亲在台湾的所有不幸遭遇,但以高中训导处主任为典型的官僚腐败,又遇上白色恐怖时期的警备总部的审讯,杨德昌选择了这些极具隐喻意义的重要事件来积累小四父亲在电影里的戏剧冲突。面对种种不公正的境遇,目睹当时台湾社会的黑暗混杂,小四的父亲已然对台湾当局失去信心。父亲的妥协对于小四也是重大打击,如同人生信仰和价值观念的坍塌。影片最后,小四拿起刀狠狠地捅在了小明身上,嘴里念叨着:“我不能让别人瞧不起你。”小四是无奈的,他自身承受的压力不断累积,作为自己榜样的父亲从刚正不阿到随俗浮沉,最信任的好朋友抢走了自己的“Miss”,喜欢的女生成为别人看不起的下等人。这些事情的叠加足以把小四逼至内心的绝地,他无法说服小明,也不知如何拯救小明,错误的价值观让小四酿成大错,情绪激动地将刀一次次捅在小明身上。杨德昌并没有以猎奇的角度来拍摄“少年情杀”这个故事,而是采用了相对冷静旁观的影像风格创造出《牯岭街》这部作品。在慢节奏的电影中杨德昌给观众留足了思考空间,“文化的选择与迷失”亦完成了本片对社会问题的深层次探讨。
四、结 语
眷村作为台湾特有的一种次文化,在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中,将慢慢地退出历史舞台,政治留下的产物只在特定的时代有其功能和意涵。眷村记录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及眷属在台湾初期的生活痕迹和眷村往后几代的生活轨迹。生活在眷村里的每一代人都有着自己的故事,《牯岭街》无法反映出眷村人文全貌,它像一部“眷村断代史”不急不躁地在近4小时内将1960年台北眷村里社会环境的动荡、不同年龄层人们的困惑以及青少年认同的迷失娓娓道来,深入挖掘了当时社会环境下人们的自我身份及文化认同缺失,解构美好青春,暴露社会问题,完成了严肃社会问题的探索与表达。
注释:
① 张文生:《眷村文化与台湾省籍矛盾》,《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年第9期。
② 陶家俊:《身份认同导论》,《外国文学》,2004年第2期。
③ 张淑华、李海莹、刘芳:《身份认同研究综述》,《心理研究》,2012年第1期。
——以《台北人》与《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