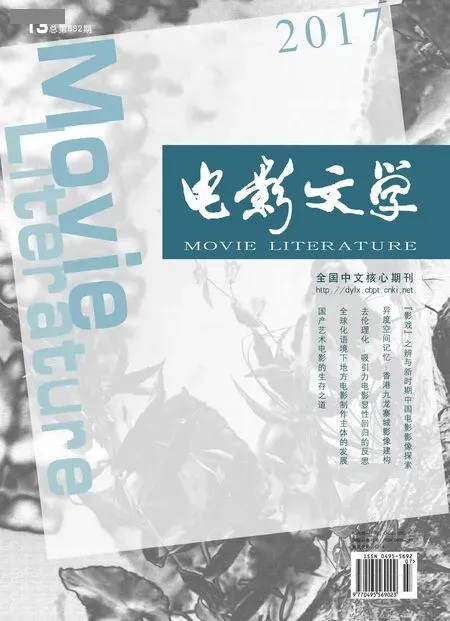《萧红》和《黄金时代》的叙事风格比较
陈寿琴
(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重庆 401520)
中国现代女作家萧红是20世纪30年代“东北作家群”的一员,又得到当时左翼文坛名人鲁迅的提携。她创作的《生死场》《呼兰河传》《马伯乐》等长篇小说均以细腻的描写和哀婉的抒情著称。由霍建起执导的《萧红》和由许鞍华执导的《黄金时代》讲述的都是萧红的坎坷爱情和人生经历。这两部电影都以“传记”的形式在讲述传主(萧红)的人生故事,但是叙事风格差别却很明显:《萧红》较为唯美而富有诗意,《黄金时代》则追求纪录片似的纪实性的真实风格。
一、凄美爱情与多舛人生
两部影片都将爱情和人生经历作为讲述萧红的主要内容,可是侧重点却不同:《萧红》主要演绎的是萧红的凄美爱情故事,而其成长为一个作家的故事被有意无意地淡化了;《黄金时代》讲述的则是与萧红有关的爱情、写作和人生选择,甚至那个乱世。因此,前者的故事比较集中,主题鲜明;后者的故事散淡,主题多维,凸显出人生与时代的繁复交响。
115分钟的影片《萧红》,主要以萧红与未婚夫、萧军、端木蕻良的三段爱情展开。萧红是因为未婚夫解救她于经济困顿之中而感动,进而委身于并非她理想中人的他。后来,萧红被未婚夫抛弃,这使她陷入更为深重的穷困潦倒之中。这段爱情为其爱情故事奠定了凄楚的基调。
萧红与萧军的爱情是浪漫而又痛苦的。“二萧”的爱情始于一见钟情,始于文学才华的相互吸引,有着一种文人式的唯美和浪漫。他们相濡以沫地共患难,一起写作,并出版了合集《跋涉》,过了一段幸福的时光。但萧军在情感上的背叛,使她陷入了情感的危机和痛苦之中难以自拔。萧红深感,每道阳光的后面都有阴影。不过,她没有停止写作,她出版了《生死场》。萧红的内心依然是寂寞的,情无所归依。在经历了浪漫、激情又痛苦的爱情后,萧红选择了爱慕她的端木蕻良,这是她的一种补偿性的选择。换句话说,选择胆小、缺乏担当的端木,是因为她想过正常老百姓的生活。不幸的是,他们热恋没多久就陷入了僵局。端木并没有给予她想要的生活,她又一次经历了痛彻心扉的失望乃至绝望。影片通过爱情经历塑造了一个敢爱敢恨的女人形象,同时也演绎出了一个文艺的、倔强的、寂寞的女作家形象。
与《萧红》侧重爱情故事的演绎不同,《黄金时代》中不同的讲述者讲述的萧红的多舛人生,相互印证,就如一张网疏而不漏地删繁就简:讲述了萧红与陆哲舜、汪恩甲、萧军、端木蕻良等的情爱,讲述了她流浪的人生,讲述了她与鲁迅、许广平的交往,讲述了胡风、丁玲、萧军、聂绀弩、端木蕻良、罗烽、蒋锡金、梅志、白朗等一大批年轻文人在动荡时代的理想与追求,讲述了国土丧失、家国沦陷的流亡与凄惶。
影片以萧红为主轴,展示了一群民国文人的群像图。“传记类影片是要通过记录多样化的人物,引发人们不同的思考。”[1]影片首先引发的是对人生追求的思考:人生的追求虽各有不同,但没有好与坏的差别。首先,“二萧”的感情裂痕与其说是源自人生追求的差异:一个想打游击,保家卫国,一个想要安稳的环境,继续写作;还不如说是爱情观或人生观的不同:萧军的“爱便爱,不爱便丢开”“丢不开就任它丢不开”和萧红的“丢不开”。萧军的粗犷、洒脱不羁与萧红的真挚、执着似乎已经注定了他们的爱情悲剧。其次,丁玲与萧红这两位女作家选择了不同的写作路向:一个顺应了为伟大的战斗书写的社会使命与时代召唤,一个自觉地选择了适合自己的个性化逆向性写作。切入时代的角度不同,也就形成了同时代女作家的不同写作风貌。
《萧红》与《黄金时代》都给予了萧红的爱情浓墨重彩的渲染,而前者侧重于萧红的感伤爱情的叙述,产生了令人悲悯的情怀;后者侧重对萧红多舛人生进行全景式概述,将文与人、人与人、人与时代、个体与社会,甚至将爱与恨、情与理、理想与现实、生与死等多个层次、多个维度的人生之思一应带出,看不出鲜明的主题倾向。
二、自我讲述与他人评述
两部影片都采用了自我讲述和他人评述相结合的方式来演绎萧红的人生故事。不过,《萧红》主要采用的是回忆性自我讲述,因此带有主观性和感受性;《黄金时代》则主要采用了他人讲述与评述的方式,具有客观性和评析性。
《萧红》的主体故事是萧红以回忆性的口吻对她自己的爱情经历进行讲述。影片开始是1941年的香港,萧红卧病在床,骆宾基在照顾她。在他们的闲聊中,她讲述了过去的故事。因为生病,她不可能一次性把所有故事讲完。她将她的爱情故事分成三次讲述,也就是三个爱情故事。她和骆宾基由“逃婚”话题聊起,进行了第一次回忆和讲述:她的未婚夫不计前嫌,扔了差事,专门到北平去找她,还满足她继续求学的愿望,这使感性的她以身相许。在这看似古典浪漫的爱情中,却隐含着萧红的委屈,姓汪的男人不懂她。结局是古典的爱情悲剧,男人对女人的始乱终弃;这使众叛亲离的萧红感到绝望。在骆宾基帮忙抓痒的时候,第二次讲述的是“二萧”的爱情,萧军的出现给她带来了生之希望,带来了梦幻般的爱情。“二萧”在相爱、相携中开始了文学创作的跋涉之路,文学和爱情缠绕着他们。萧军一次又一次的情感背叛,深深地伤害了她。爱情的虚妄使她再次陷入寂寞而痛苦的深渊。这段刻骨铭心、纠结的爱情故事几乎占了影片的二分之一。在接受报社记者采访之后,进行了第三次讲述,讲述的是她和端木蕻良之间的爱情与婚姻,她对端木很是失望。正如她自己说的:“和萧军是一个问题的结束,和端木是另一个问题的开始。”三个片段按照时间先后顺序,组合起来就是萧红一生的爱情经历。
当萧红讲述完自己的爱情故事,影片回到1941年香港陷落,萧红被异叙述者讲述:她的病重和死亡。最后端木和骆宾基埋葬了萧红,两个作家,也是两个男人开始评述萧红。自此,萧红的自我讲述和他人的评述一起构建了女作家萧红的情感世界。不管怎么说,该片对萧红进行了一次诗意化的影像虚构:作为女人的萧红——用全力去爱,却被伤得很重很痛;作为作家的萧红,点明了她的写作源自寂寞和抚慰,她在写作中寻找故乡,追求爱与自由。与此同时,“受众过分关注情节,削弱对人物本身的理解”[1]。
《黄金时代》则主要采用的是他人讲述与评述的方式。影片开始是萧红进行生平的自我概述,接着是萧红的儿时后花园,配以文学作品中的语句独白、“二萧”的对话。之后就是萧红的弟弟张秀珂讲述萧红逃婚、与表哥陆哲舜的私奔及萧红散文《初冬》的内容。舒群、白朗、罗烽讲述萧红与汪恩甲、萧军的际遇及小说《弃儿》的内容。许广平评述萧红的散文集《商市街》,转向“二萧”在商市街的生活片段。萧红自我讲述生活变化的情况,白朗、罗烽讲述“二萧”到上海。聂绀弩讲述鲁迅与“二萧”的交往,《生死场》被鲁迅赏识,许广平和梅志讲述萧红遭遇到的爱情痛苦和精神苦闷,老年萧军讲述自己的不忠。萧红自我讲述其以创作来忘记痛苦的经历和感受。蒋锡金、张梅林讲述到武汉的萧红境况,丁玲讲述她见到的萧红。聂绀弩讲述“二萧”及端木之间的情感纠葛,蒋锡金和白朗先后讲述了萧红在武汉、重庆的经历。周鲸文、骆宾基讲述萧红在香港的生活。隐含叙述者展示了萧红的死亡和让她回到精神上的后花园,引出罗烽、蒋锡金和舒群对《呼兰河传》的评述,从而完成了一个女作家独特价值的完型。
整体来看,《黄金时代》中的他人讲述与评述的分量远远超过了萧红的自我讲述。他人讲述和评述使被讲述者显得客观、真实。于是无数个讲述者眼中的萧红纷纷登场,又纷纷退场,走马灯似的“萧红”或隐或现地如魅影一般飘忽不定。因此,影片意欲还原的被讲述者反而被众多的他人讲述遮蔽了历史的或生活场景的真实,萧红成为语言符号的抽象“所指”。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夹叙夹议中,展开人物真实的经历的叙述,可以说是开辟了新的人物传记制作模式”[2]。
作为传记类型的电影,两部影片用纪录片口述形式“讲述”了萧红的短暂人生。《萧红》主要使用主人公自我讲述的方式,这种带有明显的主观感受性和抒情性的叙述方式,使影片具有一种悠远回荡的感性之美,也给观众一种“仿真”的艺术真实感。而《黄金时代》中的萧红既是叙述者,又是被叙述者,因此作为传主的她“游离于说与被说,看与被看之间”[3]。观众看到了“被说”出的不同的“萧红”:许广平眼中的萧红是痛苦而寂寞的,在处理问题时感情胜过理智;丁玲眼中的萧红是很自然而率真的,少有世故,有些稚嫩和软弱;胡风眼中的萧红是天才作家;鲁迅眼中的萧红爱生病,也是个敢于抗争的文学“战士”等,导演不给出任何主观性的评价,任观众进行判断。
三、忧伤凄婉与客观冷静
两部影片都以回忆性的口吻讲述故事,于是就具有较强的怀旧色彩。相较而言,《萧红》的抒情意味浓烈很多,萧红的爱情故事在凝重而哀伤的凄婉调子中徐徐延展,令观众唏嘘不已。《黄金时代》则大量地使用史料和萧红文章中的内容进行故事的讲述,显出节制的冷静,较难带动观众的情感。
《萧红》中凄婉的抒情格调首先体现在故事结构上,影片一开始就是萧红生着病,悲怆的音乐加以烘托,奠定了忧伤的基调。而萧红的回忆性讲述又首先讲的是祖父的去世,凄冷的冬季里祖父的葬礼,自述者哀痛的情绪感染着观众;影片的结局同样以葬礼,即萧红的寂寞葬礼结束,哀伤久久弥漫。其次是剧情上,萧红自我讲述的三段爱情都是悲情故事,每一段爱情都以她的被伤害和被迫陷入人生困境而结束。在伤痛的爱情经历中,她饱尝人生的被抛弃或背叛所带来的生活苦痛;她两次怀孕、生产,但是都没能真正地做一回母亲。乱世的流离,使她从异乡到异乡,始终漂泊;男人的绝情、不忠、自私使她从一个男人到另一个男人,却始终无法找到爱情的栖息地。再次,在氛围的营造上,病弱的萧红用她舒缓而感伤的语调讲述她自己的爱情故事、人生经历,像是一曲悲伤的挽歌,有着女性的一种自悼意味。而在画面和音乐的搭配上,展示出了萧红对故乡的无限惦念:以骆宾基评述《呼兰河传》的“开阔、浩荡、舒缓、流动着无尽的忧伤”而转入北方山水的冬季景色,画面唯美而伤感。影片快结束时,小时候的萧红看蝴蝶在花丛中蹁跹、背诵诗歌的场景,温馨而富有诗意;接着在悲怆的音乐声中又出现了浩荡的北方那白雪皑皑的原野,一架马拉车在雪地里狂奔,那车上载着苍白的去世的萧红,魂归故里,这个画面达到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哀婉意趣。
获得多个电影奖项的《黄金时代》使用了萧红的自我讲述,有一定的抒情性。该片主要是采用他人讲述的方式——众多讲述者讲述萧红的人生,这些讲述者都是作为被讲述者人生的见证者,所以他们的讲述就显得客观、真实,可是反而弱化了传主的具体可感性;因为是概述,所以故事被削弱,缺乏戏剧性;虽然会让观众觉得没那么“好看”,却呈现出一种客观冷静的叙述特色。不同的讲述者不断地讲述,“讲述”得以强化,讲述对象则被弱化。也可以说,该片的一大特点是“人大于故事”,人的主体性得以强化,人的求解历史真实的意识得以彰显,人的理性精神得以展示,而故事却被消解,凸显的主要是讲述的行为和讲述的人,这确实有一种“探索”的意味。
综上所述,传记电影《萧红》和《黄金时代》都以民国女作家萧红为传主,它们分别倾情演绎和客观讲述了萧红短暂而悲惨的人生。前者用凄美的爱情故事、感受性的自我讲述和哀婉的抒情创造了一个孤寂的萧红,叙事风格极具诗意性;后者用坎坷人生、他人讲述和客观冷静的叙述格调建构了具有“多义性”的萧红,叙事风格具有纪录片似的纪实性。由此可见,传记类电影的叙事风格具有多样性和叙述特点的无限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