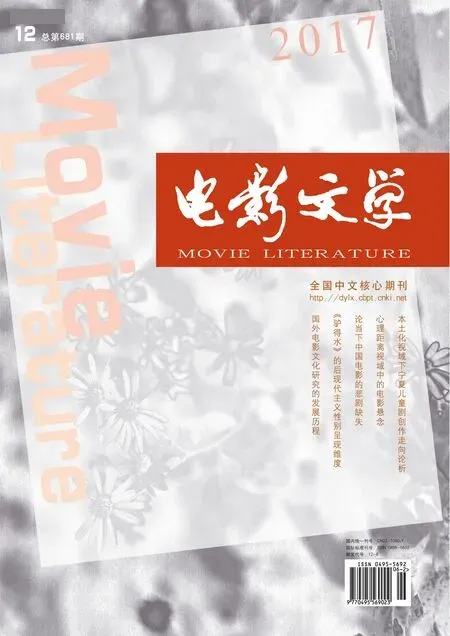《为奴隶的母亲》文学改编的反程式
苏 慧 (聊城大学东昌学院,山东 聊城 252000)
文学经典改编电影是电影业界的常见性现象。一方面,文学提供的脚本能够有效地保证影片拍摄内容结构的合理性,确立电影的风格气质与精神倾向,能够对电影的拍摄成果起到一定的保证作用;另一方面,通过电影的方式重新呈现文学内容也能够有效地促使观众对文学原著产生新的认识和理解。柔石的文学作品改编虽不多,但几乎每一部都是精品,1964年谢铁骊导演的《早春二月》在1983年荣获葡萄牙第12届菲格拉达福兹国际电影节“评委奖”,被国内影评人誉为“十七年”故事片的巅峰;而2003年为纪念柔石诞辰100周年拍摄的《为奴隶的母亲》获得了法国兰斯国际电视节佳音乐奖、星光奖最佳影片奖和“白玉兰”奖最佳电视剧奖,同时《为奴隶的母亲》也是我国唯一获得美国艾美奖的电视影片,影片艺术风格被各国评论家激赏。柔石的作品风格质朴、叙事风格相对写实,然而和当时左联作家的写作风格不同,柔石以家乡小城和自我见闻作为写作素材时,也对素材进行加工,尝试构建叙事矛盾与戏剧性。其影片的创作气质和影片的叙事手法都在文学基础上有较大的突破,因此柔石的作品所改编的电影也可以作为我国文学改编电影的经典对照,尝试探索其中的反传统叙事内涵。本文以《为奴隶的母亲》作为分析样本,探讨柔石的文学作品改编电影的反程式。
一、画面与叙事的互文
《为奴隶的母亲》的影片叙事基调在开场时相当低沉。开场是一段穿插剪辑的蒙太奇,画面里一个女子正在辛苦生产,过程并不顺利,从几段剪辑画面中可以看到,接生婆威胁一旁的孩子:“看什么,你妈生不出来孩子,你就没有妈了。”接生婆用擀面杖碾压女子的肚子助产,女子时不时发出的惨叫、摇曳的烛光和女子脸上的汗珠,这一部分镜头承担了画面的“热”。和这一段“热”相对比的是蒙太奇穿插阿祥在黎明丢孩子的“冷”;画面上一个只能够看见大概身材轮廓的男人提着一只竹篮,走在石板小路上,天色晦暗,黎明前天色将明未明,天空和大海呈现出深蓝色。在两段剪辑中,形成一问一答:阿秀(即小说中的“春宝妈”)从昏死中苏醒,问接生婆:“我的孩子呢?”画面切回阿祥,给他提着的竹篮一个特写;阿秀开始质问:“我的孩子哪里去了?”画面切回阿祥,阿祥站在海边,将竹篮抛进水中;镜头切回阿秀,阿秀悲鸣:“我的孩子!”此段蒙太奇结束。《为奴隶的母亲》的片名出现。在影片开始的两分钟内就已经对影片的内容完成了点题。
在《为奴隶的母亲》中,大部分的背景叙事都是依靠画面完成的。和一部分文学改编电影的叙事策略不同,《为奴隶的母亲》中几乎不涉及旁白和字幕式的人物介绍。叙事是融于画面之中的。画面的明暗和视觉上的冷热兼而形成一种叙事的互文。换言之,在《为奴隶的母亲》这部影片中,影片的叙事价值是构建于画面之上的。在开头一场的阿秀生产结束后,影片依旧保持着相对高速的背景叙事。画面切为明暗两种:阿秀在海边码头逗弄儿子春宝,阳光和煦。这时坐在轿子里的李大太太对阿秀的审视则是一种暗的对照,接生婆沈家婆是此段中唯一有台词的角色,通过沈家婆,李大太太了解到阿秀是一个身体健壮、能够生育的女人。然而这段台词对观众来说是无效的。明暗架构中,已经潜在地暗示了阿秀和李大太太之间的两种隐形的冲突。与此同时,阿祥的境遇同样又和阿秀形成对照,阿祥因为痨病卧床不起,蜷缩在没有点灯的昏暗茅屋内,此时催债人站在门口,镜头作为阿祥的眼睛进行追光,镜头逆光,追债人成为画面中的阴影,而阿祥反而处于明亮位置。此段中阿祥和阿秀虽然同样都处于相对明亮的位置,然而却依旧被暗处的势力所欺侮。通过光影,影片轻松地完成了对角色内涵的建构,这种冷热画面、明暗光线的对比也暗示了角色定位下的基调。
二、女性个体的精神情绪诉说
和一般的文学改编电影不同,《为奴隶的母亲》的文学气质还原相对到位,柔石在该小说中,将女性的价值定位安排得相对复杂,女性因为其故事叙事的功能不同被区分为几个主要类型。然而在电影中,这种标签式的角色特征就被简化了,转而在影片中造就了一个个充满女性气质的角色。这种女性个体的精神情绪诉说,也让《为奴隶的母亲》有别于其他的文学改编电影。阿秀、李大太太、沈家婆三人分别是影片中可以加以提纯的三种典型的女性气质类型,三人之间相互衬托,相互表现,互为表里。
阿秀——“大地之母”的人物化。在影片中,阿秀是不折不扣的主角,她因为身体健康,能够生育被典给李秀才三年,为李家延续香火。阿秀被迫离开原生家庭一节可以看成是其母性的重要体现,她与孩子春宝难舍难分,甚至哀告沈家婆,想要带走春宝。在李秀才家中,阿秀又生下了孩子秋宝,虽然丈夫不同,但阿秀对她的孩子的感情一如既往。换言之,在影片的角色立场中,阿秀是一个完全的母亲,而不是一个完全的女性。她对孩子的关爱既出自于本能,也来自于一种责任。在赛珍珠的《大地》中,曾经塑造了关涉中国女性的“大地之母”形象,她们既不要求身份,也不要求回报,她们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勤劳勇敢,保护家庭、养育子女、生生不息。阿秀在某种意义上,同样属于“地母”的一种,无论是阿秀对于其丈夫阿祥,还是对于其临时丈夫李秀才,她都同样作为情感意义上的母亲而存在。在阿祥告诉阿秀,已经将其典出一节,阿祥的情绪从隐忍到失控,这是一种情绪气质的表达。而阿秀的态度则相对温和,表露出了一种“认命”的态度,她始终都是丰饶和温顺的,这种女性化气质也导致了阿秀命运的悲剧性。在典期过后,她被迫永远离开了秋宝,回到家中,春宝也不怎么记得她了;阿祥和李秀才则对她如弃敝屣——她尝试保护的“孩子们”几乎无一例外地与她成为陌生人。
李大太太——女性气质的丧失者。在电影中描述李大太太的篇幅不多,但几乎每个细节都具有多重意味。其中又以李大太太在17年前夭折的孩子作为李大太太性格塑造中最为重要的伏笔。纵观整部电影,可以看到正是因为李大太太的主持,沈家婆才介绍阿秀作为“典妻”来到李家;在电影的补叙中可以看到,李秀才原本是想取妾的,但是因为李大太太的阻拦,才折中典个妻子回来延续香火,在电影中,孩子几乎成为李大太太的心病;她既羡慕阿秀和秋宝的母子天伦,又担心阿秀会抢走自己家族主母的位置;既嫉妒李秀才对阿秀的关心,又因为其主母的道德垂范,不能明面上反对李秀才种种想要娶阿秀为妾的打算。两种驱动力的撕扯,导致李大太太看起来相当分裂和自私。她既发自真心地喜欢秋宝,却又千方百计地想要赶走秋宝的生母阿秀。影片对李大太太的塑造并不刻板,这一人物在可恨中又杂糅了些许可悲,仅仅因为生育功能的丧失,她就随着礼教成为一具“行尸”。从电影文本上看,她的无法生育在一定程度上也暗示着其女性气质的消逝。
沈家婆——女性外表下的非女性。沈家婆是整部影片中推动剧情的重要角色。在开场时,她为阿秀接生,手段既利索又粗暴,在镜头中,观众只能够看到沈家婆的背影——一个发胖魁梧的老妇。在开场的蒙太奇中,阿秀的惨叫或多或少能够让观众心惊,然而沈家婆却没有,她在尝试用手拖拽婴儿无果后,又用擀面杖推碾阿秀的腹部,希望能够将孩子挤出来;而在阿秀质问“我的孩子哪里去了”的时候,沈家婆则是一个彻底的失语者。在柔石的文本安排中,沈家婆的角色叙事人物并不重,除了作为李大太太和阿祥达成典妻协议的中间人之外,她不承担任何主要叙事。在电影中,她的戏份被有意加重。在劝说阿祥一段,与其说沈家婆像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媒婆,不如说她是一个充满草根智谋的说客:她先是佯装关心阿祥,又以债务吓唬阿祥,最后又动之以情劝诱,最终成功说服阿祥典妻。她和一般的女性角色不同的是,她并没有女性的意识和特质,典妻对沈家婆来说只是一桩普通的生意。观众很难借助影片中沈家婆的形象联想到“母性”“奉献”等意识形象,在叙事功能上,她只是一个推动者,在人物形象建构上,她是一个“非女性”。
三、人的物化与点到即止的抒情
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的现代性表现在其对人的物化上。在电影中,这种物化和价值的交换意义表现得更为明显。在阿祥告诉阿秀被典卖时,阿祥刻意强调了80块大洋。这80块大洋可以帮助家庭渡过这一两年的难关。此时镜头对大洋有一个特写,紧接着,阿秀还想要辩解,阿祥则突然发怒道:“家里这么穷,我们又不肯死,有什么办法?”此时银元被阿祥狠狠丢在桌子上,银元掉落在房屋四处,阿祥又慢慢地将银元一块块捡回来。银元的价值在此时被提升到了与阿祥的尊严以及阿秀的人身自由同等的地位。然而随着阿祥的捡钱,人物的价值又一次固化了。“没有钱,又不肯死”一段,阿祥的叙事语境中,钱被提到的与生存的同等高度。而女性的物化则通过阿秀被典卖而被突出,在李家,几乎人人都知道阿秀被典卖的价格。李秀才曾经想要跟李大太太商量:“我们干脆再出一百个大洋,把她买回来做妾吧?”被大太太拒绝后,李秀才又提议:“那就花三十五十个大洋,再续典她两年三年。”又譬如在影片阿秀怀孕一节,黄妈对阿秀说:“你以前生多少孩子,你都是春宝妈,等你这个孩子生出来了,你就不是春宝妈了。”阿秀反问:“那我是谁啊?”黄妈答:“那个时候,你就是二太太了。”在这种缩略化的“母凭子贵”和典当与被典当的关系中,阿秀作为“物”是没有主宰的权力的。而这种将人物化的对话和角色设置几乎将整部电影的所有角色囊括在内。在阿秀刚到李秀才家时,李秀才曾经对阿秀抱怨大太太“是一直不下蛋的阉鸡”。是否能生育关系到一个人在家中是否有做人的尊严。大太太的地位看似不可动摇,然而在李秀才的眼里,她也就是一个无法生育的“阉鸡”。这种夸张的对比也很容易让观众感受当时时代的世态炎凉。
值得一提的是,在原作小说中,阿祥被设置为一个皮贩,兼做点农活,然而境况却越来越差,债年年积起来。阿祥“烟也吸了,酒也喝了,钱也赌起来了”。阿祥的堕落是有迹可循的,同时与当时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农村经济破产历史有着相互的呼应。然而,这种描述同样也让阿秀的生活变得更加凄惨,小说写道:“……这祥,竟使他变作一个非常凶狠而暴躁的男子,但也就更贫穷下去。……在穷底结果的病以后,全身便变成枯黄色,脸孔黄的和小铜鼓一样。”在影片中,导演给阿祥的性格与境遇做了减法,还能够看到阿祥作为皮贩的影子,但是阿祥是否抽烟、酗酒、烂赌,却没有表现,这种设置也让阿祥和阿秀故事的悲剧色彩淡化,形成了一种虽然悲惨,却还不至于完全失去希望的调子。同样做减法的还有结局处,典当三年结束后,阿秀回家,在家门口看见春宝,春宝已经不认识阿秀了,阿秀呼喊着春宝,春宝躲了起来。整部影片就此戛然而止。这种改编将小说原作中大段的阿秀的心理状态的片段删除,更加直观地表现了作为“典妻”的阿秀的命运,也让影片避免过分流于感情的渲染,在艺术上保持了一定的平衡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