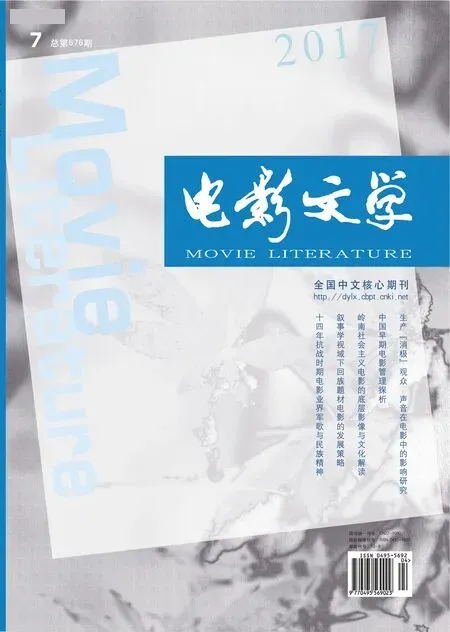主流文化意识下《追风筝的人》的改编
王 凯
(吉林建筑大学,吉林 长春 130000)
小说《追风筝的人》(TheKiteRunner)为作家卡勒德·胡赛尼带来无上荣光,使其成为新世纪以来的文坛黑马,甚至由于这部小说的巨大影响力,胡赛尼在2006年获得联合国人道主义奖。《追风筝的人》是一部思乡情怀极其浓烈的文学作品,胡赛尼将自己儿时的记忆与美国移民经历相融合,描绘了一个让他又爱又恨的阿富汗。2007年,由马克·福斯特执导搬上大银幕的同名改编电影《追风筝的人》远没有小说原著成功,不仅失去了小说原著的韵味,甚至在改编的过程中改变了小说的深层次主题内容。电影《追风筝的人》被注入了美国大国意识,居高临下地讲述了这个残酷动人的故事,美国文化成为最终的救赎,原著的怀乡情结已经被肢解得破碎不堪。
一、小说文本与电影文本的对接
一部小说之所以能够改编为电影,是小说文本的电影画面感决定的,而不仅是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的动人那么简单。小说《追风筝的人》的文本是复杂的,也是纯粹的。作者为我们讲述了一个背叛与救赎、离乡与还乡、温情与残酷并存的故事。主人公阿米尔是一个富家子弟,他的仆人哈桑也是他最好的玩伴。阿米尔生性胆小怕事,对写作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天分,热衷于比赛放风筝。哈桑生性善良、耿直憨厚,尽一切可能满足主人阿米尔的愿望,一切都为了阿米尔着想,甚至在阿米尔放风筝时,甘愿与阿米尔一同追逐被击落的风筝。在一次风筝比赛中,哈桑为了追逐阿米尔击落的第二名的风筝,被仰慕纳粹的阿塞夫等人堵在巷子里强暴了,而阿米尔目睹了这一切,却由于胆怯而逃跑了。阿米尔无法终日面对哈桑的巨大的心理压力和内心谴责,在13岁生日时陷害哈桑偷自己的生日礼物而将其赶出家门。早已洞察一切的哈桑满足了阿米尔的愿望,离开了阿米尔。不久,阿米尔一家为了躲避战争逃亡到美国,从此阿米尔与哈桑真正天各一方。
胡赛尼用文字在小说前半段构建了一个风情独具的阿富汗异域空间,为电影改编提供了丰富的视觉元素,让观众能够了解小说中描绘的真实的阿富汗。小说前半部分淋漓尽致地描述了阿米尔和哈桑主仆二人之间复杂而单纯的情谊,阿富汗的风土人情成为动人的背景画面。胡赛尼用风筝比赛这样具有强烈的隐喻意识又有视觉效果的情节,赋予阿米尔和哈桑的阿富汗生活如梦似幻的乌托邦色彩。哈桑为了阿米尔而遭遇强暴的情节增加了故事的戏剧性,为故事蒙上了一道无法抹去的伤痕。
胡赛尼的小说文本为电影改编提供了一切所需,视觉元素、情感元素、娱乐元素,甚至在叙事结构上都无须重新解构和重构,这样也就在小说文本和电影文本对接的时候,提供了更多的便利和更多的接口。但是,编剧在处理文本对接和改编时,融入了太多美国的大国意识和主流文化,很多在小说中并未出现的细节和情节都让这部电影有了不一样的味道——为观众在潜意识里构建了一个暴乱、荒蛮的伊斯兰世界。这也让文本的对接过程产生了一定的偏差,改变了电影最终的艺术效果。
因而,我们看到影片《追风筝的人》的后半部分,阿米尔跟随父亲辗转流离来到美国,通过多年的打拼终于站稳了脚跟。阿米尔在美国遇到了自己的终身伴侣索拉娅,父亲也随后罹患肺癌去世。影片将阿米尔和父亲逃亡美国看作是新生活的开始,美国成为乌托邦的代名词,给予阿米尔父子希望和美好的未来。在影片强烈的美国主流文化意识的作用下,美国不再是阿米尔追忆故乡阿富汗的成长彼岸,而是幸福生活的安乐窝。片中的美国国家形象潜移默化中发生了转变,阿米尔的美国生活经历也成为推动他赎罪的力量,成为他毅然决然奔赴阿富汗的坚实后盾。
二、主流文化臆想下人物形象的转码
阿米尔是小说《追风筝的人》的主人公。在小说故事中,阿米尔是矛盾的混合体,他虽然家境优越,却十分自卑,自己并不是父亲期待的一个坚强的男人。阿米尔自幼虽然争强好胜,却十分胆小懦弱,反而父亲更偏爱阿米尔的仆人哈桑。哈桑极度忠诚、勇敢、善良,有着原始的人性特征。阿米尔性格敏感,有着鲜明的阶级意识,对于自己和哈桑的主仆关系十分明确,这种主仆关系让他们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既亲近又疏离,这也导致他们永远无法真正成为朋友。
小说中的阿米尔遭受着原罪的侵蚀,这种原罪是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父亲与仆人的妻子通奸生下哈桑,然而同样是贵族父亲的儿子,哈桑却永远无法得到认同,仅仅作为阿米尔的影子,成为阿米尔的“附属品”。在善良、勇敢、坚强的哈桑面前,阿米尔能够随意地发泄自己对于生活的不满和对于父亲的不满,也总能获得哈桑对自己的原谅。更是因为哈桑能够获得父亲的全部认同,而自己只是父亲和好友拉辛汉口中的“身上缺少了某些东西”的孩子。年幼的阿米尔只能依靠自己擅长的放风筝来博得父亲的好感,于是在一次风筝比赛中,阿米尔成功切断了第二名的风筝。哈桑为了将代表着阿米尔成功的蓝风筝拿回来,被曾经找过他们麻烦的阿塞夫一伙人堵在小巷子里强暴了。阿米尔目睹了一切,却为了保护自己胜利的果实——蓝风筝,而选择了沉默,任由这群“暴徒”对哈桑进行侮辱,因此阿米尔深知蓝风筝能够获得父亲给自己的赞赏,潜意识里认为哈桑作为仆人理所应当为了保护自己的蓝风筝而做出牺牲。
因此,哈桑是阿米尔父亲“原罪”和阿米尔人性“恶”的牺牲品,阿米尔在此之后始终无法面对哈桑真诚的眼神和宽恕的内心,最终将哈桑赶出了家门,让自己内心的“恶”战胜了“善”。切断了自己与哈桑的联系之后,阿富汗迎来了战争,阿米尔跟随父亲辗转流离,似乎这段童年恶行可以被时间掩盖。可是,当多年以后,阿米尔在美国成了家,父亲也罹患癌症去世,故乡的忘年之友拉辛汉的一通电话打破了阿米尔的生活,拉辛汉希望阿米尔能够去巴基斯坦的喀布尔拯救哈桑的儿子索拉博,在遭到阿米尔的拒绝后,拉辛汉才告诉他哈桑其实是阿米尔的亲兄弟的事实。因而,阿米尔对索拉博的拯救有了深层次的“原罪”救赎意味,不仅仅是阿米尔对自己当年犯下的罪行做出的补偿。
小说《追风筝的人》中,阿米尔是背负着宗教信仰、思乡情结、赎罪心理的复杂的人物形象。但是,在电影改编的过程中却失去了原有的味道,阿米尔小时候被拉辛汉肯定的文学才华终于在美国大展拳脚,阿米尔和父亲躲过了战争的摧残,踏上了美国的自由土地实现了“美国梦”。影片在展现阿米尔的美国生活时,刻意强调了美国社会的自由气息和人文风光,与阿米尔逃离之前的阿富汗构成鲜明对比,此时的比对和展现,已经在有意无意地“地狱化”“妖魔化”伊斯兰世界,将美国比对为世上最后一片“纯净”“和平”的土地。
电影《追风筝的人》中,阿米尔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代表,正因为身在美国,他的文学之梦才能够实现,束缚在他身上的枷锁才被打开,他的天性才能够被释放,他被注入了美国文化的核心意识。甚至在表现阿米尔来到巴基斯坦的喀布尔拯救哈桑之子,更多地表现出的是阿米尔的拯救者形象,而不是小说原著中描绘的救赎者、赎罪者形象,阿米尔代表的也是美国的大国形象,似乎在片中隐喻美国就是解救世界各国于危难的“拯救者”和“超级英雄”。
三、霸权文化下主体思想的变迁
小说《追风筝的人》深层次表达的是人性向善的回归以及人性的复杂性,整个故事当中蕴含了太多的主题:乡愁、友情、救赎等。尤其在伊斯兰国家的背景下,故事浓厚的异域风情让主题更为质朴、动人。阿米尔的人性救赎是故事的核心,小说作者胡赛尼对阿米尔的人物形象是持有辩证的批判态度的,而不是一味地赞美和推崇,反而对哈桑这一人物形象则是由衷地赞扬。阿米尔代表着接受过教育的新一代阿富汗人,他们接受了外来的新思想,能够读书识字的他们拥有更成熟和复杂的思维方式。尤其是阿米尔在母爱缺失、父爱不专的状态下,他的思想变得更加偏激,他在敬仰的父亲面前无比自卑,总是想要贬低哈桑在父亲心中的形象和地位,将自己优秀的一面凸显出来,展现给父亲。哈桑则是无比纯粹、原始、善良、勇敢的哈扎拉人,他对于阿米尔表现出的绝对忠诚和包容正是人类最原始的美好品格,是一种无法将其融入民族、宗教、社会和世俗规范的纯粹和原始,哈桑从幼年到成人,他所表现出的品格是胡赛尼认为的完美的阿富汗人形象。
阿米尔与哈桑之间的情感是复杂的:一方面,哈桑的绝对忠诚和陪伴为阿米尔带来了生命中大部分的快乐;另一方面,由于哈桑更受到父亲的怜爱,导致阿米尔对哈桑产生嫉恨。阿米尔想方设法地捉弄哈桑泄愤,又总是能够获得哈桑的原谅。但是在哈桑遭遇阿塞夫等人的强暴事件过后,虽然哈桑能够一如往常地对待阿米尔,阿米尔却无法原谅这样卑鄙、懦弱的自己。因而阿米尔对哈桑的背叛,对哈桑的驱逐,对哈桑的忏悔,都是一种现代人的复杂人性对于原始完美人性的对立,阿米尔在故事结尾冒着生命危险完成了个人的灵魂救赎,是他在多年之后做出的反思与人性选择,他最后还是选择了赎罪、人性的善。
改编电影《追风筝的人》从内容细节到人物形象,都体现出美国主流文化的影子,这导致观众无法像看小说一样去看待电影表达的主题内容。对于阿塞夫这样自幼就有着极端反社会倾向的人物,在小说中更倾向于表现他受到的教育和影响,他追求纳粹主义,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认为普什图人高哈扎拉人一等。电影改编将阿塞夫的形象具象化、放大化,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将阿塞夫看作了阿富汗多数人的代表,这从影片中不断出现暴乱的人物可见一斑。并且,影片进一步通过塑造阿塞夫的性虐者、杀人狂形象,来具象化观众好奇的塔利班分子,进一步丑化、妖魔化这群人,这也正是符合当下主流思想的一种创作方式。阿塞夫是十恶不赦的恶徒,从阿米尔和哈桑小时候就欺凌他们,甚至强暴了哈桑。在成人后重遇哈桑和妻子,当街枪杀了他们,并将他们的孩子当作舞童,对哈桑的下一代实施性虐待。阿塞夫是一个绝对的反面人物,在影片中被看作阿米尔和哈桑悲惨人生的痛苦来源,在丰富、具象的影像画面里,阿塞夫的反作用被凸显,反而从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阿米尔人性恶的一面的巨大破坏力,模糊了他的人性黑暗面是导致哈桑悲剧人生的根本原因。
因此,阿米尔从美国回到巴基斯坦拯救哈桑之子索拉博,也就具有代表美国文化的救世主意味,甚至成为英雄人物一般。带着美国文化的光环,阿米尔相信自己能够凭借一己之力去拯救索拉博,当被阿塞夫拳打脚踢满脸是血的时候,反而是索拉博像当年的哈桑一样,举起弹弓射向阿塞夫的眼睛,拯救了阿米尔和自己。影片的主题表述在结尾处呈现一种矛盾的姿态,一方面想要凸显美国主流文化意识,另一方面又要与小说原著相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