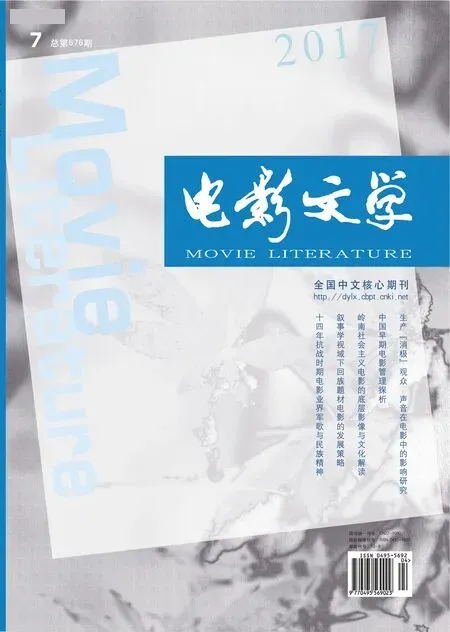《荒野生存》的行为艺术
廖 亮
(河南科技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河南 洛阳 471023)
电影《荒野生存》根据美国畅销纪实小说《阿拉斯加之死》改编。小说作者以美国大学生克里斯多夫·强森·迈坎德勒斯为原型,根据死者亲友的回忆,并在死者最后使用的书籍、照片、日志等遗物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导演西恩·潘被克里斯多夫的故事所感动,在筹备十年后,终于获得克里斯多夫家人的支持,得以拍摄本片。影片在2007年上映后便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人们对主人公克里斯远走荒野的行为褒贬不一,但不可否认的是,克里斯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所展现出的执着勇敢和绝对的行动力是值得赞扬的。这段经历虽因它悲壮的结尾而涂上一抹凝重与疼痛,但这种走进自然、拥抱自然的举动却像生态主义的行为艺术一样表现出一种异样的美。
影片主人公克里斯出身于一个优越富裕的美国家庭,父母婚姻中的龌龊欺骗给他留下深重的阴影,他痛恨社会上一切的虚伪和物质化。在边读书边默默筹备四年后,克里斯以全优的成绩从艾莫里大学毕业,此后他放弃去哈佛法学院深造的机会,捐出存款,销毁证件,不辞而别。他改名为“亚历山大·超级流浪者”,孤身踏上了寻找阿拉斯加的流浪之旅。一路上,克里斯徒步、漂流、偷渡、扒火车、打零工,虽然饱尝艰辛却享受着极简生活的乐趣。
在领略了大自然的瑰美并享受了绝对的自由后,克里斯也亲历了大自然的残酷。然而,当他开始领悟到人生与幸福的真义并找回自我,想要返回尘世时,却发现河流暴涨,来路已断。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克里斯经历了巨大的恐惧和绝望,并最终因中毒和饥饿死去。这个年仅24岁的年轻生命悄然逝去,人们在他留存的相机里找到了他生前的最后一张相片,照片中的年轻人形销骨立,然而脸上却隐约透着恬然镇定,嘴角还保留着一丝笑意。
行为艺术之一——以绝对的勇气和行动力摈弃现代文明
克里斯是一个有着优渥物质条件的青年才俊,然而绝对的物质享受却没有办法弥补他内心的空虚。父母混乱的情感生活以及身边贪慕名利、虚伪狡诈的人们带给他强烈的厌世心理。在内心深处,人类社会的体制和秩序是那样的刻板生硬,人们追逐名利、狡猾势利的言行也早已淡漠了人情温暖,这一切远没有单纯的大自然来得可爱。
旁白中,克里斯的妹妹说过:“他从小就是一个非常聪明,又对自己极为严苛的人。”所以,他对父母之间的虚伪冷漠感到心寒,他自己也曾说过:“我想那么年轻、干净 ,那么寂寞地生活着,直到自己可以毫无防备地突然失踪在马路上的那一天。”这是理想主义者基于残酷现实所萌生出的一种绝对的自由情怀,这种情怀或多或少会出现在每一个人心里,然而绝大部分人过早地,或过于理性地、有技巧地压抑了这种情怀。只有这个过于纯净与理想化的青年真正遵循了内心“野性的呼唤”,为着那个理想中的“绝对自由”而抛弃凡尘俗世与现代文明。
为了给自己一个真正干净的起点,克里斯烧掉现金,弃车徒步,天高水阔地走在路上。他想撇清过去的一切,所以只带着简陋的装备,像原始人一样流浪,他甚至没有给自己定下归期。许多大骂克里斯单纯莽撞的观众嘲笑他在四年的准备期里并没有把工作做足,因为他连野外必备的冲锋衣裤、太阳镜和高帮鞋都没有准备,他甚至要仰仗路人的帮助才能得到一双可以涉水的胶皮靴。只是,不管克里斯是否有意为之,他的确在这种远离尘嚣的自然环境里尝到了人生的快意:在野外生活,没有顾虑和猜忌,没有烦恼,无需交谈。他日出而行,日落而息,风餐露宿,随意行走,累了就搭个便车或随处坐下,闲时躺在菜地里看书或者与苹果对话。他逃离了父母和自己的姓名、逃离了过往,不需要压抑,不需要伪装。他只要活着,去呼吸干净的空气!这是忠于自己内心诉求的一种表达,这也是令人心驰神往的一场流浪!
那么,在整个旅途中,克里斯就未有过迟疑与恐惧吗?为了表达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也为了忠于主人公原型在实际流浪中的真实遭遇,导演安排了一些形形色色的人物来勾起克里斯对尘世的念想。这些人中,有像父母一样关怀他的嬉皮士夫妇,有像兄弟一样教他生存技巧的农场主,有像情人一样迷恋他的乡村女歌手,以及像祖父一样依赖他的老皮革匠……克里斯与这些人相处,从中获取帮助,感受着陌生的亲情、友情、爱情和温情。他与他们激昂地辩驳,捍卫自己的理想。尘俗的情感和众人理智的规劝并没有成功挽留他一直向北的脚步。一路上,他不断从梭罗和托尔斯泰等人的诗集著作中获取精神抚慰和支持,他坚持梦想的心是决绝而坚定的。
为了展现他的坚定,影片中甚至提到了他重归城镇的一幕。流浪一年后,克里斯到了一个陌生城市,在那里,他不期然地又看到了浮华的都市生活以及明净店堂中带着虚伪面孔的红男绿女。他幻想着自己某一天也西装革履却脸戴面具微笑着的可怕模样,这种想象让他恐惧,那一刻,他疯狂地拿起行囊逃走了。
行为艺术之二——以赤诚之心拥抱大自然
在克里斯看来,大自然是一个承载梦想,异于人类社会的美好所在。在导演西恩·潘的镜头里,大自然也的确展示着它广博而深邃的美:白天有明净如洗的蓝天、巍峨连绵的山脉、清冽澄澈的湖水;夜晚有静谧旋转的星空、快乐飞舞的萤火虫、温暖跳跃着的篝火;夏天有草木繁茂和林间的清风,冬天有雪山嶙峋和稀薄的天光;香甜的空气见证着时间的流淌,物换星移,自然在静悄悄地新陈代谢……西恩·潘以绝对的耐心和魄力将这些遥远而可爱的美景交融在天籁般的吟唱和伴奏中,让观影者也忍不住沉迷。除了镜头,西恩·潘还通过克里斯的阅读以及影片旁白来描绘大自然的惑人魅力。影片开头引用了拜伦的诗句:“无径之林,常有情趣;无人之岸,几多惊喜;世外桃源,何处寻觅;倾听涛声,须在海里;爱我爱你,更爱自然。”这也许正是克里斯身处丛林海边时的内心感受吧!
在这一切的感召下,才会出现克里斯攀上废弃巴士欢喜雀跃的一幕。面对白雪皑皑的群山,他张开双臂,狂野豪迈地大喊,“有人吗?——”随后又带点孩子气地轻声作答,“好像没有吧……”凉风掠过他的脸颊和发梢,带起衣衫一角,让人萌生一股随风而去的冲动,就像久旱的旅人猛然品尝了远离尘世喧嚣的甘甜,愿意在这自然又纯粹的美景中沉醉一样。在克里斯的寻梦之旅中,壮丽秀美的自然风光涤荡着他的灵魂,慰藉着他的心灵,在这样的时刻,他才真正感受到自己真实地活着,十几年的淤堵之气瞬间倾泻一空,他开始感受到遵从本心的快乐。这场追逐就像一场救赎,让他在寂静与孤独中思考,在丛林与动物群中感受,那些久久不愿启齿的内心阴霾终于开始驱散,他重新感受到宽容与爱的力量。这一刻,这个艺术探险者真切地拥抱了大自然。
行为艺术之三——在残酷的自然斗争中顽强生活
披星戴月、席地而卧、翻越雪原、仰仗荒野的生活所带来的,当然不仅仅是浪漫轻松的愉悦感受,它还带来了无数的陷阱和无限的杀机:清澈可爱的蓝天或许转瞬便变成无情的风暴,优雅温顺的动物可能带来决绝残酷的杀机,精致美丽的花草可能潜藏剧烈的毒素,叮咚悦耳的清泉可能在不知不觉间汇集成斩断生机的急流。
克里斯在野外体会着这一切。他并不是不知喜乐的苦行僧,相反,他乐观而积极,拥有一个优秀艺术家所具有的全部灵感和热情。他在铁桶的底部戳小孔自制花洒淋浴,透过镜子给自己打气鼓劲,还将大自然里结识的动物当作朋友。他在绿皮车里怪声怪气地分饰司机和乘客自娱自乐,向严肃呆立的猫头鹰挤眉弄眼,甚至热情洋溢地赞美一颗新鲜的红苹果,大方册封了他的属臣——“超级苹果”和“超级巴士”。对大自然带来的挑战,他早已安之若素,他亦奇迹般地独自生活了两年!
当然,荒野中的生活也预示着血腥和暴力。在这里,生存是他最需要认真面对,并拼命争取的东西——与野兽夺食、适应气候变化、辨识花草、攀岩落水,甚至——猎杀动物。当他好不容易因断粮的窘境而举起猎枪瞄准一头驯鹿时,却为了紧随其后蹒跚前行的驯鹿崽而放弃。当他好不容易射杀一头健壮的驯鹿并激动得嗷嗷直叫时,他的第一反应是像每一个喜欢“记录”的现代人一样,赶回“神奇巴士”记下了这一刻,待他返回那头庞大的驯鹿身边时,他先捧着它的心脏虔诚地祭奠,这一切让他错失了风干存储猎物的先机。鹿肉很快便腐烂生蛆,随即被恶狼和苍鹰吞食。他的内心翻涌而复杂,在野兽饱食散去之后,他为驯鹿的遗骸建了一座坟,并在日记中写道:“我感受到了自然的力量,它并不偏向于袒护人类,这个地方野蛮而未开化,那些比我更贴近荒野和动物的人才适合在此生存。”他的心里再一次加深了对大自然虔诚的敬畏之情。
在荒野里,活着,变成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而原来追求的优异学业、良好的人际关系以及恪守的世俗规则都变得可笑起来。在最原生态的自然环境中,克里斯感受到动物和植物最野蛮的力量,他感叹着人类的渺小,并意识到——丢弃以人类为中心的思想、遵循自然生态规律——变得至关重要起来,这是人们在现代工业文明中娇宠自己太久乃至早已遗忘的生态法则。在自然界,生命物种按食物链规律演示着适者生存的那一套法则,大自然并不偏袒人类,人类文明在这个野蛮未开化的世界里显得那样无力,人类的尊严似乎已经丧失。除了遵守自然规律,要想求存,别无他途。
这个理想主义者有着虔诚的哲学信仰,他的家世、成绩,包括他俊美的外表让他在人类社会中光鲜亮丽,然而这个人类文明的杰出继承者却始终没有扛过自然力量的挑战,因为,自然法则与人类法则到底不同。他不能像野兽一样直截了当地上前咬下一块生肉,然后大快朵颐,因为,他是人。人类的肠胃娇嫩得不容轻慢,人类的文明也不能容许它的臣属再做回野蛮动物。所以,这个遗落荒野的人类注定要曝尸荒野,他像一名虔诚的殉道者,在这场生态文明的行为艺术里善始善终了。
结 语
克里斯是一位理想主义的实践者,更是一位从肉体到灵魂都“走在路上”的逐梦者,他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去经历和探索,并带着人们思考:这种为追求野性与自然抛弃一切、不顾生死的行为到底是勇者虔诚与坚定的表现,还是自私荒谬、不可理喻的莽汉的风格?这一点,西恩·潘并不急于表达自己个人的看法,他只是在讲述一个生态主义艺术家最忠于本心的行为表达。在这种认真的表达里,人们在心底也会问自己,生命的价值何在,自然的价值何在,人应该如何与自然共处,应该如何保护生态、尊重自然?
克里斯最终没有走出阿拉斯加,没有回到井然有序的人类社会中,而人类社会又该何去何从,在与自然角逐、斗争的现代社会里,是越走越远,还是停步自省?这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