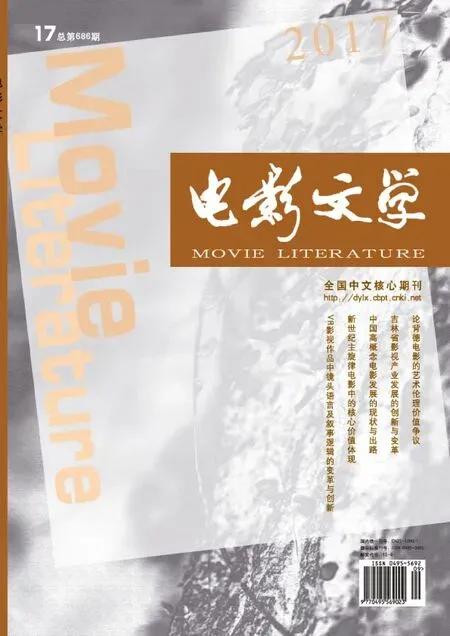试析中国早期动画电影传奇叙事特征
刁 颖(西南大学,重庆 400715;重庆人文科技学院,重庆 401524)
虞吉先生在《中国电影“影像传奇叙事”的原初性建构》一文中说“传奇叙事”有“双重原则”。根据这两大原则来分析《孤儿救祖记》,使之成为中国特有的影像传奇范式文本。动画电影《铁扇公主》在“双重原则”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绘制性特点,形成了动画影像传奇的“三重原则”,使之成为中国动画电影影像传奇的范式文本。从故事的完整性和独立性来说,《铁扇公主》是一部典型的中国影像传奇叙事的作品,推动了之后的《大闹天宫》《哪吒闹海》《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大鱼海棠》等动画大片传奇叙事美学观念的延续与演变。
中国早期动画电影从1922年到1948年的这26年内,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22—1930年技术初创期,代表作品有1926年的《大闹画室》;第二阶段,1931—1936年良性发展期,开始有了完整的故事,并从1935年出现有声动画电影,代表作品有1935年的《骆驼献舞》;第三阶段,1937—1945年战时动画电影时期,代表作品有1937—1939年的《抗战标语》《抗战歌辑》系列、1941年的《铁扇公主》;第四阶段,1946—1949年民国商业动画的衰退期以及新中国动画电影初成期,代表作品有1947年的《皇帝梦》等,其中最著名的《铁扇公主》是民国时期唯一一部长篇动画。
一、从广告到叙事选择
1906年,世界上诞生了第一部公认的动画片《一张滑稽面孔的幽默姿态》。1925年《舒震东华文打字机》的上映(商务印书馆,万氏兄弟),标志着中国动画广告片诞生,也标志着中国第一部动画的出现。1918年,商务印书馆成立活动影戏部。活动影戏部“在风景、时事、教育、新剧、古剧多个题材领域有过系统和大量的拍片实践”[1]。可见商务印书馆不仅是中国电影发展初创期的重要参与者与见证者,也是动画创生的见证者,为日后中国早期动画电影发展提供了技术上的铺垫。这部动画广告片不同于中国最早的电影《定军山》记录京剧片断的叙事方式,而是从商业广告中发端。万籁鸣曾说:“这部简陋可笑的动画广告片却是以后动画片的雏形和先声,为我们提供了制作动画片的原始经验和极为朴素的动画理论根据。”[2]
中国早期的动画电影之所以没有一直延续商业广告的形式走下去,而是走向了电影叙事方式的层面,本文认为有三个重要的原因:第一,动画电影是电影的一个类别,无论是拍摄技术还是播放的媒介方式等都有相同之处。中国电影从1905年的《定军山》到1913年的《难夫难妻》,早已完成了电影叙事的理论建构,因此中国动画电影从1922年的《舒震东华文打字机》到1923年的《大闹天宫》《武松打虎》等,①从商业广告到滑稽动画影片就只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它是在中国电影大环境下转变的,也佐证了动画电影是电影的一种特殊类别,而不是另一种艺术形式。第二,动画有其自身发展属性。动画广告由于绘制的难度在时间上和制作成本上远高于海报广告(月份牌)以及真人影视广告,同时动画广告播放的区域受到院线的局限。在经济收益和传播效果上都存在较大的问题,前景堪忧。商家很快发现同时期的国外动画快速发展,为中国动画电影提供了另一条道路。第三,从历史发展来看。自古“皮影”与戏剧的关系就非常密切,人们通过皮影这种形式来“演绎”故事。可以说皮影在唐朝出现时,中国动画就开始有了雏形,因此动画电影自然也走向了故事叙事的层面。
二、影像传奇叙事选择
《电影艺术词典》上对电影叙事学的解释是:“依据文学叙事学或符号学原理研究影片表述元素和结构的理论。沿袭传统小说叙事学的电影叙事学主要研究故事情节安排、行动动机、人物性格和审美特性,关注电影剧作的技巧层次。”[3]对比中西方在叙事题材上的选择,多选择童话和儿童小说为题材,尤其是美国将动画定位在儿童、低龄上,如《白雪公主》《小鹿斑比》等。而中国清末时期戏剧仍然是老百姓主要的娱乐选择,中国人的叙事传统从唐“传奇”历经宋元“说唱”艺术、南戏、杂剧等到明、清两代的戏曲艺术,这个发展路线是清晰和明确的。因此伴随着小说、戏剧中的传奇叙事方式就被自然地选择于电影叙事之中。传奇要遵循和“承袭唐代文言小说叙事的‘新’‘异’‘超’‘卓’”[4]。而 “新”“异”“超”也属于动画电影自身的特点。在多年的戏剧、小说等的发展中传奇叙事具有“两层指涉”[4]:“其一是‘诗歌音乐形式的原则’,其二是‘关于情节结构的原则’。”[4]由于动画的特殊性应该加上第三个原则“绘制性呈现方式原则”,形成动画电影影像传奇的“三重原则”。
首先,以诗歌音乐形式的原则来看文学作品、音乐、戏剧、诗歌的关系密切。戏剧通过每一段不同的唱腔表现故事情节的或高、或低、或平、或转;诗通过平仄关系讲究“合辙押韵”;文学作品在结构上多讲究“起承转合”。可见在诗歌、戏剧、文学作品等的创作中寻求“韵律”规律的感觉早已属于中国人集体无意识的创作或接受方式,能在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中找到如同中国传统诗歌的韵律规律。如《铁扇公主》中悟空一借扇子的片断:用计逼侍女通报—被铁扇公主用剑砍头—被扇子扇飞—铁扇公主躲回洞中—钻到铁扇公主肚中得假扇;猪八戒二借扇子片断:调戏小妾理亏—不借—偷取晶金兽—骗得真扇—真扇又被骗回。两次借扇共计10个片断,用律诗中的平仄押韵来看,可以说是“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仄”,符合平起仄收的规律。如果以音律关系来看,在中国传统音律中的“宫(Do)→商(Re)→角(Mi)→徵(Sol)→羽(La)”,五个音律同样讲究的是一个韵律。悟空与火焰的对抗以及同牛魔王的打斗中用快节奏的音律(与“羽”相通)来表现激烈的战斗情绪恰到好处,尤其是当牛魔王现出原型追逐孙悟空时,在快节奏的音乐背景下增添了鼓点的敲击(应该是在“羽”中增加了“宫”的音律),使得音乐的层次感丰富。镜头语言上用追逐场景与民众锯树设陷阱的场面平行对切,音乐也在一个节奏中统合两个场景:一个是用鼓点声加牛的吼叫声,另一个是锯树声音加民众喊口号的声音。两个场景的声音相互对切转换,整个片段的音乐层次丰富,在当时的动画电影中这样的配音是“超”“卓”的,也从另一个层面突出了故事叙事的快慢节奏关系,起到快慢、平缓、转折等多元视听效果。
其次,从情节结构原则上看,遵循情节和叙事结构的完整。在1931年的《同胞速醒》、1932年的《精诚团结》等作品中“画面清晰,人物造型生动,为唤起中国人民起来抗日,起到了积极的鼓舞作用”[5]。颜慧在论文中写道:“《抗战歌辑》配合故事片在大后方各地上映时,由于样式新颖独特,很受观众欢迎,起到很好的宣传鼓动作用。”[6]这些作品中的标语和口号对抗战宣传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在故事叙事的整体性和延续性上有一定的消解作用——作品宣传的意识大于故事情节。这些短片无论在叙事结构还是叙事承续方式上都不够完整,因此这些抗战动画短片只是拥有叙事策略、一定情节组织的宣传短片,还不能称其为传奇叙事作品。
《铁扇公主》的剧本以中国长篇神话小说《西游记》为题材。《西游记》从唐代至今历经了不同朝代和不同版本,在说唱、戏曲、评弹等艺术中都有不同的演绎方式。直到今天《西游记》中的“猴戏”依然分为南、北两派。荣格认为:“一个民族的神话是这个民族活的宗教,失掉了神话,无论在哪里,即使在文明社会中,也总是一场道德灾难。”[7]他将神话提到了宗教的高度,并指出它是民族道德的传播媒介。同理,动画《铁扇公主》选择这部神话剧作为蓝本是对它的神奇故事、佛家精神、民族文化等方面的传承,它的神性、佛性、奇异性都符合传奇叙事的特征。它具备传奇叙事中“‘奇’‘异’内容的叙事选择方式,而且与叙事(情节)推进的动力学模式有深入的关联”[4]。“传奇,则以情节丰富、故事跌宕多变为特色;传奇,意味着艺术在对现实的把握中,抛弃普通平凡的生活素材,撷取富于戏剧性的生活内容,又以偶然性的形态显现出来。这些正是中国古典小说、古典戏曲等叙事艺术的一大特点。”[8]在情节结构原则上,“要求情节的整一性,故事必须有头有尾,追求事件的曲折离奇和缝合照应的构思技巧,讲究叙事的规定程序”[9]。《铁扇公主》的故事从西行被火焰山所阻挡;悟空与火的第一次对抗;悟空借扇(被骗两次);悟空与火的第二次对抗;八戒借扇(变化骗取后又被骗走);村民合力与牛魔王的打斗;悟空与火的第三次对抗;继续西行,整个故事情节完整,并有明显的“起”“承”“转”“合”特点。
通常传奇叙事在故事情节中“尽可能把故事的曲折离奇推向极限”[4],影片中通过“三次借扇”“两次骗扇”“两次与火焰正面交锋”一层层将情节推到了极致,当扇子第二次被牛魔王所骗走后,故事进入到高潮,最终在师父的启发下通过正面武力手段取得成功,凸显了影片的主题:“要成功一件事情总是有阻碍的,我们要做这样神圣的事情,就要坚定我们的信念,不能因为有一点困难就中途改变我们的宗旨,我们这次的失败就在于我们既不同心又不合力,假使你们三个人一条心,合起力量一起与牛魔王决斗,事情一定可以成功。”(唐僧的原话)
从传统的传奇叙事特征来看,“中国传统叙事中的人物有充沛的情感,但不必具有独立的意志,情节的动力来自于作者的意愿”[10]。在作品中,有三处大的改变与原著不同,孙悟空与火怪前两次正面交锋;猪八戒取代孙悟空变成牛魔王的模样骗取扇子;唐僧劝众人,大家合力打败牛魔王取代了原著中哪吒三太子捉住牛魔王的片段。这三处大的变动明显符合当时全民抗战的时代背景,“战争期间该片在中国及南太平洋地区的上映也大获成功,因其潜在的‘团结一致反抗侵略’的主题也获得各地观众的共鸣”[11]。除了大的情节上的改动外,还有一些细节上的变化也是主创人员的意志呈现,如铁扇子公主第一次以女将军的形象出现,与当时另一部影片《木兰从军》相互呼应。主创者的主观意识也符合当时社会背景,是这部动画中的亮点之一。影片中对唐僧的人物性格也做出了主观性改变,唐僧不再是软弱的书生形象,而是一位有坚定理想、坚强意志的“新五四青年形象”,具有很强的决策能力、领导能力和号召力。同中国历史上那些“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民族英雄一样,有着家国的信念。《铁扇公主》的主创人员的主观意识是明显的。叙事者为主导,对人物性格的塑造更具有传奇特点,将这部神话剧表现得更具时代性和传奇性。
从绘制性原则上看,动画电影呈现出“非真实”性和“再创造”性,影像与巴赞所说的“真实影像”截然不同,对于动画我们应该“放弃‘光与影’的认知立场,直接关注于‘像’”[12]。动画的绘制性,突出了它在“质“上的不同。“动画所具有的本质属性是‘绘制性’。所谓‘绘制性’,即是说在根本上‘手绘’出来的。”[12]由于“绘”的手法包括了多种形式,使得它具有民族、地区等的差异性和多样性。20世纪40年代,西画(包括油画、水彩、蛋彩等技法)早已进入中国,中国画在原有工笔画、水墨山水画、白描技法等基础上都有参照西方绘画技法的先例,这部影片也不例外,例如《铁扇公主》绘画构图上既有散点透视,在处理人物近大远小的关系上又有平行透视的手法。在建筑的全景图中运用了西画的透视关系,近大远小,三角形构图明显,是一部西方构图与东方传统构图相结合的作品。
人物采用中国画的白描手法加漫画手法,色彩平涂;背景采用国画中的晕染技法,达到前重后轻、前实后虚、层次分明的效果。在人物的造型上,孙悟空的“鼠”脸、玉面狐狸的“贝蒂脸”等都与美国迪士尼动画有着相似性。但西方学者却认为该片的人物造型是典型的中国作品,“角色设计上有种半人半兽的感觉。这种典型的亚洲动画式设计有别于西方动画对动物角色的拟人化、可爱化处理”[11]。在人物脸型的细节上有所借鉴,但总体来说它完全不同于西方的人物造型设计。以牛魔王的形象为例,中国人往往赋予它人的外形、头部稍有牛的特征。在形象上的“奇形”明显与戏剧、民间面具、皮影等有着相通之处。例如,《皮影之旅》一书中的“台湾皮影”图片上展示悟空与牛魔王兽头人身、身穿铠甲、身体直立、手拿兵器,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牛魔王是五指(人手)。[13]而在西方动画如《疯狂动物城》中,警察局牛局长却是三趾(动物性)。以此能看出中西方对于拟人化的人物形象区别,东方更注重动物与人形的结合,是人性层面上的,而西方更注重动物形象被站立后的写实形象,是写实层面上的。影片中的人物形象既有西方动画电影的形象特征,又有着中国传统人物形象特点。它们绘制的形象上表现出的“奇”“异”演变同样遵循了“传奇”性的演变。
三、结 语
早期中国动画电影的发展在中国电影的“大伞”下成长,虽然它只是电影中的一个较小的方面,却也反映了中国电影成长的完整性。它所具有的叙事选择遵循了中国电影影像传奇叙事,映射了中国文人的儒家精神和传统道德精神,同时在动画技术和形式上又有自己的美学特点。它的娱乐性、现实性、虚拟性都是中国早期电影人创作中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统一。借用朱光潜对人间的现实与艺术的美的认识:“人走向艺术,目的就在欣赏,所以特别注意到它的美;人走向现实,目的只在实用,所以没有心思去想它的美。”[14]这些作品作为宝贵的史料成为中国电影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铁扇公主》的绘制性手法在当时无疑是成功的,与真人影像的介质差异就是“奇”。1961年《大闹天宫》中的构图、配色、技法(包括重彩、晕染、勾线方式)图样、音乐等都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提取的。最明显的就是人物形象的设计借鉴了民间的年画、泥塑、雕刻、剪纸、戏剧脸谱等。而今天的数字影像技术包括VR技术、全息影像技术等都在模糊真人影像与动画(虚拟)影像之间的界线和间隔。新的动画影像传奇叙事又将有新的“三重原则”的发展和变化。
[项目]本文系西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民国早期动画电影史述研究”(批准号:SWU1709467)成果。
注释:
① 殷福军先生在《首批中国动画片及作者的考证》一文中写到杨左匋先生从1923年起“拍摄的滑稽画片《大闹天宫》《武松打虎》《暂停》等曾先后放映于卡尔登影戏院和维多利亚大戏院。《过年》这部影片已运往各地放映,并预定在卡尔登戏院放映,这足以说明他们已经制作完成了一些动画片并在放映的过程中产生了商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