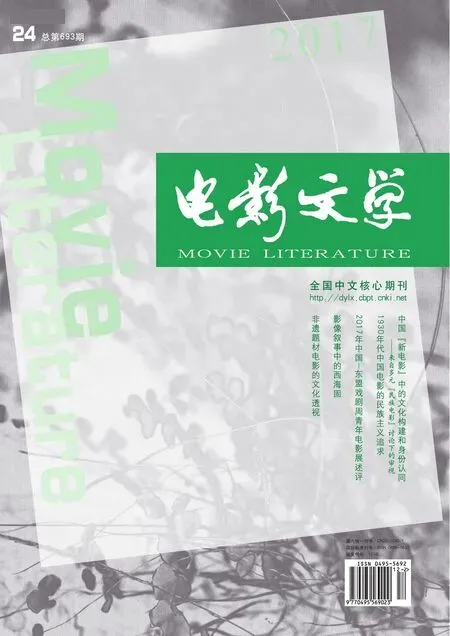电影《塔洛》:身份建构的忧思
樊义红(周口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 周口 466001)
藏族导演万玛才旦的最新影片《塔洛》从诞生到现在一直好评不断,收获了各种荣誉。迄今为止关于这部影片的研究已有一些,本文将从“身份建构”的角度对其做出新的解读,认为该片讲述了一个关于身份建构的“寓言”。
一、多重身份的建构
本片讲述了牧羊人塔洛为了到乡里派出所办理第二代身份证,遭遇理发店的女孩杨措,与后者发生感情瓜葛,并被之欺骗的简单故事。主人公塔洛具有三重身份:第一重是他的自然身份,关乎其身世和职业。他小时候父母双亡,上小学时辍学,靠替村里人放羊为生。他的真名叫塔洛,却几乎被人忘记,大家根据他头上的辫子叫他外号“小辫子”。这一重身份是可怜、卑微和模糊的。第二重是塔洛的政治身份,或者说公民身份。塔洛需要办理身份证,其实就是要获得一种政治身份或公民身份,这是一个成年的中国人必然要获得的一种身份。这重身份其实也具有一种现代的意义——“主人公被重新冠名即是现代社会对他重新实施控制的开始”[1]。第三重是塔洛的道德或精神身份。塔洛虽处于生活底层,却一直有着高尚的道德追求。他能把毛泽东的名篇《为人民服务》倒背如流,希望像张思德一样死后“重于泰山”,而为牧民放羊也被他看作是“为人民服务”的行为。这重身份的建构是影片叙述的一条暗线,也是影片意蕴的重心所在。
人生于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寻求和建构身份的过程。在满足了最基本的物质需要之后,人们就会为身份所焦虑,开始了对自身身份的追求。在现代社会里,由于基本的物质需求一般都可以得到保障,对身份渴求的欲望会变得更加强烈。[2]基于这种认识,塔洛对身份的建构就是一个值得我们重视的问题。应该说,塔洛的前两重身份都带有某种被动性。出身是没法选择的,塔洛悲惨的身世非他所愿。失去了双亲,亲戚也不管他,因为记忆力好,他得以谋得一份放羊的工作来维持生计。甚至办理身份证在塔洛看来也带有某种被迫性。相比而言,第三重身份才是塔洛真正主动的建构。也许在塔洛看来,对道德身份的建构才能超越他卑微的身世和地位,为他赢得活着的尊严和价值。当然,这样的身份其实也更配得上他正在获得的公民身份。
二、身份建构的失败、原因和深层内涵
不幸的是,塔洛对自己身份的建构以全面的失败而告终。他虽然差点就办好了身份证,但因为剪掉了自己标志性的小辫子以致和身份证上的照片不相像了,被派出所要求重新照相办理身份证,从而失去了获得公民身份证的机会。他为了和杨措私奔,私自卖掉了牧民们的羊群以获得巨款,实际上已构成侵吞公共财产罪,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他的想做好人“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也已然破灭。可以想见,塔洛也必将失去原来的放羊人身份,他已经回不到过去了。
塔洛的身份建构之所以失败,从外在的原因看,是因为他受到了理发店女孩杨措的诱惑和欺骗。塔洛误把杨措的诱骗当作爱情,想要携带赃款和杨措远走高飞,殊不知杨措在拿到这笔钱后逃之夭夭。不过,塔洛的失败主要还是归咎于他自身。作为一个孤独的牧羊人,塔洛每天的生活无非是白天的时候牧羊、取水和发呆,晚上的时候喝酒、听收音机和放爆竹吓唬狼。这种单调到极致的生活一方面让他缺少生活经验,因而在面对杨措这种颇有心计的现代女孩时就显得穷于应对。另一方面,这种缺少变化和色彩的生活也吞噬着塔洛的内心,让他产生了一种逃离这片土地的冲动。“塔洛”在藏语里的意思就是“逃离的人”[3],作者对主人公的这一命名颇有意味。终于有天夜里,塔洛因为饮酒过多,导致羊群被狼群咬死数只。闻讯赶来的羊主人狠狠地打了他三个耳光,并告诫他:“记住,你就是个放羊的!”这种对塔洛身份的提醒带有轻视的成分,他把塔洛为这份工作赋予的高尚意味击了个粉碎。而对这份工作的否定其实也是对塔洛道德身份建构的否定。
从故事深层看,塔洛的身份建构其实是藏族传统和现代冲突的一种表现。塔洛无疑体现了藏族传统的一些特征,其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精神趣味等都是如此。而杨措则更多地表现出藏族现代的一些特征。她留着时髦的短发,抽女士香烟,喜欢唱通俗歌曲和听流行歌星的演唱会。她一心向往大都市的生活,想要逃离眼前的环境。和杨措短短几次有限的接触后,塔洛就决意为了想象中的“情人”,和自己过去的生活告别,甚至不惜背离自己的道德追求,走上犯罪的道路。这其实意味着,在现代的魅惑之下,传统轻易就乱了方寸,走向了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表现出不堪一击的虚弱本相。在这个意义上,本片表面上讲述的是塔洛建构身份的故事,实际上讲述的是一个藏族身份建构的故事。当前的藏族社会正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其要走向何方?又该以什么样的民族身份建构未来的自己?通过影片看到,“逃离”成了一种普遍的心理追求,不仅是杨措,甚至连塔洛最终也选择了逃离,尽管其结果并不如意。“逃离”似乎成了藏族社会的一种普遍心态。他们的逃离不是因为生存不下去,而是为了想象中的更加精彩和美好的生活,尽管这种想象中的“很精彩”的“外面的世界”可能会让他们“很无奈”。我们还看到,面对现代的挑战,传统是那么不堪一击,但现代也未必有我们想象中的那般美好。塔洛已在自己的故乡生活了40余年,尽管活得孤寂但也习以为常,以前从未想过离开这里,却在杨措的几番诱惑之下就想要背井离乡。塔洛偷卖牧民们的羊群,实际上也背弃了自己几十年的道德追求,这是他一直以来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对传统的放弃如此不加顾惜,而他所追求的现代生活又如何呢?看看杨措这个女孩的追求就知道了,它们是金钱、物质、感官的享受,情感的淡薄和道德感的丧失。可见,现代未必是好的和先进的,传统也未必是坏的和落后的,简单地用现代否定传统是一种轻率的看法。
三、为了身份建构的艺术形式
结合对“身份建构”主题的表现来看,本片在艺术形式上的一些处理可以说有效地服务了这一艺术目的,同时也增强了本片的审美效果。
首先是对黑白影像的选择。在彩色影像一统天下的现在,该片对黑白影像的选择饶有深意。黑白的世界其实是一个灰色和不明朗的世界,它就像塔洛对自己身份的犹疑不定,也暗指了对塔洛身份选择的一种隐隐的批判。当然,塔洛的身份问题也是藏族身份问题的一种折射。在习惯了彩色影像的观众看来,灰色的世界总让人感到几分压抑和沉重,这正对应了本片对身份问题的严肃思考。其次是对固定机位长镜头的采用。这一方面让影片具有一种“生活流”的风格,带来一种真实的表现效果,引导我们进入一个真实的藏地世界。另一方面,这对于习惯了享受电影“视觉盛宴”的现代观众而言也是一种挑战,它考验着我们的耐心,让我们不得不经常停下目光,把对画面的“凝视”变成一种沉思。身份的问题的确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因为它关乎人们的生存和发展。还有对构图的处理,可以看到,在村里的世界,塔洛基本上居于影像的中心;而在乡镇的世界,塔洛基本上居于影像的边缘。这是对塔洛不同处境和身份的有力暗示,引发着我们对塔洛命运的思考:他是谁?从何处来?要到何处去?哪里才是他理想的所在?或许正如影片结尾处塔洛站在城乡结合部的一条小路上的进退两难所暗示的那样,塔洛和藏族的明天将何去何从也是一个需要反复追问的问题。
——来处已然消失 归途无所觑见
——以万玛才旦的《塔洛》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