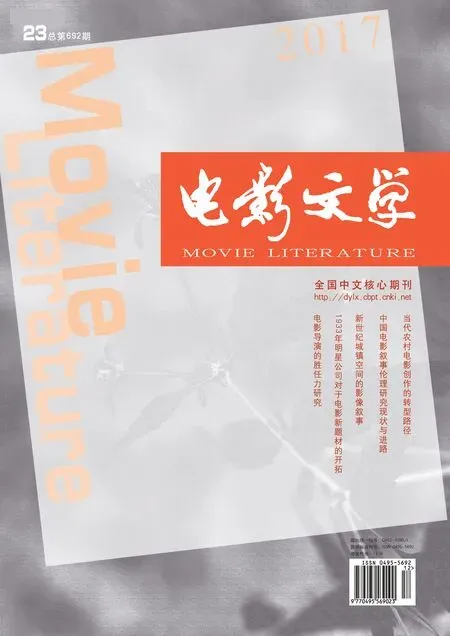1933年明星公司对于电影新题材的开拓
韩 畅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00)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期,而1933年作为其中关键的转折之年,被称为“中国电影年”。彼时,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之下,广大民众开始要求电影反映现实生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多数电影从业人员也自觉地意识到了转变的必然性。终于,1933年的中国电影从“颓废的、色情的、浪漫的,乃至一切反进化的羁绊中挣脱出来”①,之前风靡影坛的武侠神怪题材和各类言情题材都遭到了时代巨轮的无情碾压,关注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新题材开始受到电影界的青睐。明星影片公司作为当时中国电影行业的佼佼者敏锐地把握住了电影界的这一新动向,积极开拓与时代接轨的新题材。1933年,明星影片公司拍摄了多部与现实生活联系紧密的电影,涉及的题材包括破产乡村的天灾人祸、腐化都市的劳资矛盾以及在此基础上所产生的底层劳动者的觉醒与反抗,这些题材都是以往的电影创作中所未曾有过的。
一、破产乡村的天灾人祸
中国文人历来有对于乡村的乌托邦想象,20世纪30年代,随着上海城市化进程的步步深入,都市生活的诸多阴暗面逐渐暴露出来,居于城市的中产阶级对农村地区的社会现实认识有限,再加上中国传统文人一脉相承的对于田园生活的美好想象,他们在电影中往往会将农村描绘成美好的净土,将城市塑造成罪恶的深渊,将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设计为离开城市回归乡村。如1930年上映的电影《故都春梦》,影片中原本安分守己的乡村私塾先生朱家杰在进入城市后开始走向堕落,谋官、纳妾、抛弃妻子、贪污受贿,终至锒铛入狱。出狱后的朱家杰顿悟城市的罪恶,回归乡村,与结发妻子重归于好,于乡村旧居中相携终老。1933年上映的电影《城市之夜》同样是将解决社会矛盾的办法设计成回归乡村。在这些电影中,乡村作为罪恶都市的对立面被塑造成一个可供人们逃避现实矛盾的地方。现实中的乡村真的如此吗?显然不是这样。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农村天灾人祸并行,在水灾、旱灾等自然灾害接连发生的同时,帝国主义国家又将其工业流水线上批量制造出的低成本商品大量倾销于中国市场,中国农村薄弱的自然经济因此而遭受到致命的打击。再加上农村中恶霸劣绅对于农民的欺压剥削以及战争的影响,30年代的中国农村呈现出一派萧条凄惨的景象,处于破产的边缘。此时,明星影片公司关注农村的现实状况,接连推出了多部直击破产乡村天灾人祸现实的电影,如《狂流》《春蚕》《丰年》(又名《黄金谷》)等。
以电影《狂流》为例,影片以1931年武汉大水灾为背景,讲述汉口上游一个名叫傅庄的小村落中发生的抗洪故事,表现了广大农民在小学教员刘铁生的带领下积极抗洪的事迹,同时也批判了乡村中的土豪劣绅欺压农民,侵吞抗洪巨款以中饱私囊的行为。该片被称为“明星划时代的作品”②,其转型意义可见一斑。柯灵认为:“在国产影片当中,能够抓取现实的题材,而以正确的描写和前进的意识来制作的,这还是一个新闻的记录!”③电影《狂流》的上映在当时引起了一阵热议,影片抓取现实题材,将乡村中的天灾人祸真实地呈现在观者面前,所谓“天灾”指的自然是波及傅庄的大水灾,而“人祸”则是使这场灾难不断恶化的主要原因,对此,影片有着明确的展现。
影片中,傅柏仁作为傅庄首富,称霸一方,在连日暴雨,堤坝遇险的情况下傅柏仁搜刮了筑堤捐款却不将其用于修筑堤坝,此举使傅庄的大堤处于极其危险的情形之中。无奈之下,小学教员刘铁生只好带领广大农民赤膊上阵,死守堤坝。当村民们与洪水殊死搏斗的时候,平日里鱼肉乡里的乡绅傅柏仁却带着全家去武汉避灾了。具有经济实力的乡绅在天灾出现的紧急关头非但不承担抗灾责任,还在武汉打出抗灾代表的幌子私吞社会各界的捐款,其种种行为无疑加重了灾难的影响。不仅如此,当武汉洪水泛滥,灾民在洪流中挣扎逃生的时候,傅柏仁一家竟随县长之子李和卿一道雇了小汽轮并躲在汽轮上用望远镜观赏这“难得之景”,土豪劣绅面对天灾不作为、面对灾民无同情心的恶劣行径暴露无遗。试想,如果洪灾初现端倪时乡绅傅柏仁就利用筑堤捐款积极加固堤坝,傅庄还是否会处于险境之中?如果地主、县长等一干有权势者能在洪流中以一己之力救助灾民,在洪灾中丧生的民众是否会减少许多?影片以此告诉观者,这场大水灾起于天灾,发展于人祸,地主豪绅的种种恶行才是灾难泛滥的根本原因。
同样表现水旱等自然灾害对乡村的危害,在另一部以旱灾为背景的电影《人道》中,编剧者却没有加入对于“人祸”的思考。该片将人塑造成灾难的被动承受者,旱灾使主人公家破人亡,人力对此无可奈何。与《人道》不同,电影《狂流》中有明显的表现农民反抗的情节,指出了农民与地主豪绅做斗争的出路。影片中,傅柏仁一家在武汉水势危急的情况下重回傅庄,不久暴雨再度来袭,傅庄堤坝预警。在此等危急的情形之下,傅柏仁还是拒绝拿出他用赈灾捐款购买的木料来加固大堤。忍无可忍的农民终于爆发,他们冲向傅柏仁的后院抢夺木料,傅柏仁指挥工役与农民对抗。但此时堤坝已决口,洪水渐次涌来,工役们面对如此险情纷纷倒戈,加入抗灾阵营,而傅柏仁则被滔滔洪水卷走。影片如此设计情节显然有呼吁广大农民反抗地主豪绅压迫的意味,同时也在启发部分替地主豪绅做鹰犬的人,告诉他们只有和农民大众联起手来推翻地主豪绅的压迫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由此可见,电影《狂流》比《人道》大有进步,它在抓取现实题材表现自然灾害的同时,不忘指出天灾背后的人祸因素,还进一步指出广大民众只有通过反抗欺压他们的地主豪绅才能拯救自身,找到出路。
电影《狂流》为影坛树立了开拓现实主义新题材的良好榜样,影片以武汉洪灾为背景,展现出20世纪30年代破产乡村中的天灾人祸。其实,除却抗洪这条线索,影片中还有一条贯穿始终的爱情线索,展现刘铁生与傅柏仁之女秀娟之间的情感纠葛。对此,当时的多数影评表示了不满,有观众就直言:“编剧者在这《狂流》中硬嵌进这么一个恋爱的故事,实在是太无谓了。”④甚至有影评者认为:“故事的中心偏重在领袖个人的纠葛,而水灾的发展反好像成了旁边的点描,这给主题以相当的打击……”⑤对此,编剧者夏衍虽没有做正面的回应,但在谈及影片结尾为何设置洪水冲走傅柏仁这一情节时,夏衍提到以“女儿背叛父亲,长工推倒东家和保安队背叛指使者来象征绅权之没落”⑥。可见,秀娟与刘铁生恋爱故事的设计并非全然为了活跃气氛,也不仅是以桃色片段吸引观众那么简单。秀娟作为傅柏仁之女,其与以刘铁生为代表的农民大众分属于不同的阶级阵营,她离弃豪绅父亲和县长之子投向刘铁生的行为很有寓意,编剧者以此暗示观众地主豪绅终将没落,加入农民大众的队伍才是正确的人生选择。所以,这条爱情线索的添加并非无谓的赘笔。
二、腐化都市的劳资矛盾
以往都市题材的电影往往表现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反映市民阶层在大都市上海的生存状态,关注其情感问题、职业问题等。如明星影片公司1926年出品的表现小市民在爱情与利益面前艰难抉择的电影《爱情与黄金》以及1927年出品的表现青年剧作家浪漫爱情幻想的电影《湖边春梦》等。同样以都市空间为表现对象,1933年的明星影片公司关注到了腐化都市中的劳资矛盾这一新题材。在农村破产的背景下,无数农民怀着对都市的美好幻想涌向上海,“‘到都市去’,这是无数农民所喊的口号”⑦,那么现实中的都市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呢?《女性的呐喊》《上海二十四小时》等电影给予了观众最真实的回答。
以电影《上海二十四小时》为例,影片讲述了一个童工受伤,无钱医治,最终伤重身亡的故事。影片中,老陈一家从破产的乡村来到大都市上海谋生,老陈的妻子在周买办的公馆里帮佣,老陈的弟弟妹妹经妻子介绍来到周买办任职的工厂里做工。灾难在猝不及防间突然降临,老陈的弟弟在一次拾纱中被飞速运转的机器轧伤且伤势严重,贫困的老陈一家想为弟弟治病却无钱去请医生。按说老陈的弟弟在做工时受伤,其所在的工厂理应担负相关的医疗费用,但当工头将小陈受伤的消息报告给周买办时,周买办的回答竟是:“自己不小心,有什么好说的。”⑧资产阶级的麻木冷漠由此可见一斑。得不到工厂补偿的老陈一家只好另想办法,老陈去周公馆向自己帮佣的妻子要到了3块2毛钱,他便用这点可怜的钱去为弟弟请了医生。老陈的邻居老赵因可怜小陈伤重无医,铤而走险去周公馆行窃,想要将窃得之物换了钱为小陈请医生。但不曾想,周公馆发现失窃后报了案,前一天曾到过周公馆找自己妻子的老陈被当作窃贼投入了监狱,老陈的妻子也因此遭到了买办太太的解雇。这个贫困的家庭屡遭变故,雪上加霜,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此时,周买办夫妻却在摩登的大都市中竭尽所能地寻欢作乐,钱在他们手中如流水一般被花出去。老赵不忍看朋友代自己受过,他主动承认了自己的盗窃行为,老陈因此得到释放。但当老陈赶回家时,小陈已经伤重身亡。
电影《上海二十四小时》运用对比的手法将腐化都市里的劳资矛盾展现得淋漓尽致。老陈来到周公馆找妻子要钱,妻子搜集所有也不过凑出了3块2毛钱,而此时,一位兽医来找买办太太收取其宠物狗的医药费,买办太太竟然拿出了30块钱支付给兽医。老陈夫妻见此情景呆若木鸡。如若买办太太还有一丝良知,拿出几十块钱来给老陈夫妻,小陈也许就不会死去。或者买办太太允许老陈的妻子提前预支几个月的工钱给弟弟看病,之后再让她通过做工补回来,小陈也还有一线生机。然而她并没有这样做,可见,在以买办太太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眼中,贫苦工人的命还不如自己豢养的一只宠物。如此人不如狗的黑暗都市怎能不让人痛恨!
原本在1933年底便摄制完成的电影《上海二十四小时》因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阻挠而迟迟不得与观众见面,直到1934年12月这部电影才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期待已久的观众如潮水般涌入电影院。其实,电影《上海二十四小时》在上映之前就已经遭到了国民党电影检查机关多达十余次的审查和删改,其情节的连贯性也因此而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但其表现的思想内容还是获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有观众曾这样评价道:“画面已经失去了它的连贯性,处处地方都显出了生硬和不自然。当然,我们应该原谅导演是为了环境的关系……他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他完全是真实的抒写。”可见,电影《上海二十四小时》所选题材紧贴现实,暴露了腐化都市的罪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观众愿意为此而包容它的不完整。
三、底层劳动者的觉醒与反抗
1933年,明星影片公司的电影创作在新题材的开拓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描绘乡村天灾人祸和都市劳资矛盾的同时,明星影片公司还关注到了压迫之下的反抗。农村中辛勤劳作却衣食无着的底层农民、城市中出卖血汗却难以生存的底层工人在环境的压迫下不得不走上反抗的道路,《女性的呐喊》《铁板红泪录》《香草美人》等电影都或多或少地表现了这些底层劳动者的觉醒与反抗。
以电影《铁板红泪录》为例,影片不仅描写了农村中恶霸与农民之间的矛盾,还清晰地表现了底层农民的觉醒与反抗。影片塑造了三类农民形象,分别是以小珠父亲刘正兴为代表的隐忍顺从的老一代农民,以周老七为代表的具有反抗精神的青年农民和以二蛮子为代表的企图通过依附恶霸来欺压他人的不觉悟的农民。其中,周老七的形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是农村中具有自发反抗精神的“可造之才”,被迫逃离家乡的遭际为他提供了接触新思想的可能性,在党的影响下,他成长为一个具有正确革命认识和清晰革命目标的人。这样的人就像一粒火种,当他再度回到农村就会带领其他村民点燃斗争的熊熊烈火。刘正兴、二蛮子虽没有周老七的觉悟和际遇,但也在遭遇了切身的不幸之后觉醒并最终走上了反抗的道路。
影片中,农民刘正兴有个名叫小珠的女儿,同村的两个青年农民周老七与二蛮子都喜欢小珠,而小珠却只对周老七有感情。在小珠等人生活的村庄中有一个名叫孙团总的恶霸,他以买枪防匪为借口强迫农民们上交“枪捐”,此人欺压乡民,横征暴敛。二蛮子因得不到小珠的爱而心生怨恨,投靠了恶霸孙团总,而周老七则因反抗孙团总的“枪捐”而受到迫害远走他乡。此二人代表了“压迫生活下的两种农民:一种是依附的,一种是反抗的……依附的农民想借军阀的势力来压迫他同类的农民”⑨,而反抗的农民恰恰相反,他们的“首导行为启迪了集团的行动”⑩。至于刘正兴,作为老一代农民的代表,面对恶霸的横征暴敛,他隐忍顺从,只求安然度日。但令他想不到的是,周老七走后,二蛮子依仗着孙团总作威作福,二人合谋抢走了小珠,还打伤了自己。影片以此暗示观众,对恶霸存有幻想,不敢与其做斗争的人终会被自己的懦弱所害。
终于,孙团总强行收租的恶劣行径引起了全村人的不满,长期以来如刘正兴般隐忍不发的广大农民终于忍无可忍,村庄中爆发了“抗租抗欠”的农民斗争。而从外地归来的周老七更是接受了党的影响,变成了一个眼界更加开阔、思路更加清晰的斗争领导者,带领村民们展开了有组织、有计划的斗争。多行不义的恶霸孙团总此时已经成为众矢之的。投靠孙团总的二蛮子也在小珠被孙团总害死后彻底醒悟,认识到孙团总是站在农民对立面上的恶霸,投靠恶霸是没有出路的并最终开枪打死了孙团总。
电影《铁板红泪录》描写四川农村中底层劳动者的觉醒与反抗,情节曲折,感染力强,其对于新题材的尝试受到了当时影评者的肯定,石凌鹤在对该片的评价中这样说道:“(影片)将现实的题材加以明确说明,使观众体验中国农村的真实,这无疑是中国电影值得夸耀的地方。”
与乡村中的广大农民同为底层劳动者的还有城市中的工人群体,《女性的呐喊》《香草美人》等电影就表现了城市工人的觉醒与反抗。以电影《香草美人》为例,面对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王老二主张罢工抗议,害怕失业的王阿大委曲求全,拒绝参与王老二的反抗行动。但最终一系列打击使得王阿大失去了生活的全部希望,兄弟二人狱中相见时,王阿大已经觉醒并有了反抗的决心,他主动向王老二问询办法,王老二告诉他穷苦人们只有团结起来反抗资本家的压迫才能争取到美好的生活。无论是王老二的自发罢工,还是王阿大历经打击后的艰难觉醒,二人最终都走上了相同的反抗之路。他们的选择是符合时代要求的选择,多数观众在观看电影时,都会由对他们悲惨遭遇的同情发展到对他们所选择的反抗道路的支持,此类电影在传达左翼斗争精神的同时也在客观上给明星影片公司带来了不菲的票房收入。
综上所述,明星影片公司1933年对于电影新题材的开拓,不仅使其收获了优秀的票房成绩,还帮助其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肯定,在无形之中为自己树立起了关注社会现实、承担社会责任的良好企业形象。
注释:
① 洪深:《1933年的中国电影》,《文学杂志》,1934年第1期。
② 蒋青:《介绍〈狂流〉》,《申报》(电影专刊),1933年2月23日。
③ 芜邨:《关于〈狂流〉》,《晨报》(每日电影),1933年2月25日、27日。
④ 红:《我对于〈狂流〉》的批评》,《申报》(电影专刊),1933年3月7日。
⑤ 席耐芳:《〈狂流〉的评价》,广电部电影局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中国左翼电影运动》,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年版,第415页。
⑥ 丁谦平:《〈狂流〉的编剧者的话:读了诸家的批评以后》,《晨报》(每日电影),1933年3月8日。
⑦ 火:《〈上海二十四小时〉将公映》,《申报》(电影专刊),1934年12月12日。
⑧ 《上海二十四小时》,广电部电影局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中国左翼电影运动》,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年版,第246页。
⑨⑩ 舒湮、克尼、黑星、唐纳、常人、江天:《〈铁板红泪录〉六人合评》, 《晨报》(每日电影),1933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