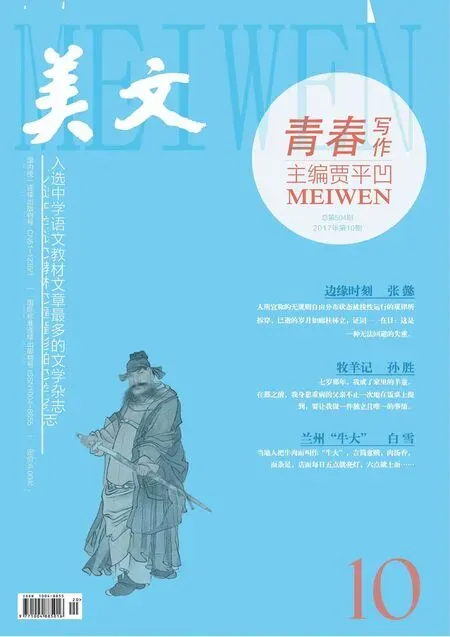没有标题的爱
没有标题的爱
之一
秋天来的时候,我的锋利也跟着钝化下来。
总是有这样的时期,对于黑暗的嗜血症状减轻,整个人松散下来,像一把未拉满的弹弓,或是未经挤压的弹簧。我像一把匕首,因为找不到自己的寒光而恐惧。
我原本是清晰地了解起点,也了解终点,甚至熟悉抵达的路径的,我知道这一切都很安全,包括在哪个拐角应当摄取什么,一切似乎都可以在掌控之中。必经的痛苦,反抗的方式,放弃的模式,经由多次重复而变得可亲可近,像一只宠物刺猬,每一次扎出伤口都令我更加爱惜它,又回避它,如同小心翼翼地回避自我。自我是丑陋的海上毒沫,身为精神的鱼每吸食一点,就会麻痹窒息一回。然而这依然安全:你掌握痛感的来源,并精心梳理其纤维,并试图将其伪装成美。驾驭这种勾当,你轻车熟路。
但或许是因为南方,也或许是因为秋风,我却轻而易举地踏上了陌生的分径。我谨慎而缓慢,怀抱着在下一刻钟成为一滩碎瓷的风险预估,走着。秋天的密林,光线时亮时暗,有人从时间里,切下铜钱大的白烛光,为我沿路安放。我依然看不见昼的轮廓,凭着人造光一一指认林中隧道的曲折。我有时会害怕地哭起来,希望握住一只不存在的手,兔子也好,狐狸也好,那急匆匆过去的土拔鼠也好,握住那种灵动跳脱,不要走得像一个踯躅的象形汉字,尤其是在秋天。
我怕自己会被再次吹灭,我更怕失去进入丛林深处的勇气。我害怕失去自己的锐度,又渴望进入一片明亮的旷野,夕阳照着,我如谷垛般柔和,色泽细腻,蓬松而微温。我隶属于我的犹豫,我是它的陀螺,在十月的寂静里,被我的矛盾反复抽打。
然而最终我还是背叛了自己,在陀螺减速的间隙,突然向宇宙叫出了一声:等等我。
之二
我们不要去雪山了吧,像我这样,烟雾一样的东西,会和我的文字,我的说话,还有我的小心思一起,全部变成整齐的冰块的。给人拿去砌成房屋,砌成桥梁,会有咕噜咕噜的呓语,在星星蓝得像海水的夜晚,泡在空气里,扰人清梦的。
那样可太糟了。
还是去赤道搭建凉棚吧,把耳朵深深埋进沙里,变成热风吹过时的小小丘陵。四肢绵软,满储宝藏;头发里全是绿洲,骆驼从额头东边升起西边落下,像金色的雪。让一切为之旋转一分钟,再轻轻落回原地。忘了悲伤,忘了担忧,忘了夜晚要终结于白天,忘了人生的难。让生活干燥疏松,不含水分,所有的盐都用以酿造水晶,在腹地的幽冥里。
眼泪呀,眼泪是最珍贵的雨,是倒流的森林,谁也不要舍得让对方落下。
之三
我的眼睛天生带着雾气,无论看什么,都隔着清晨的一片大雾。我清晰辨出过的只有死神的手,冰冷而充满怜悯。我常在人的丛林与平原里感觉恐惧、慌张、不知所措。我始终无法处理好与生存的关系,汗从脚底爬上来,像挣不脱的蛇。
然后你来了。像冬日缓缓洒在结满白霜的屋宇、枯枝、草地的阳光。
我很久没有这样安静地观察过自己的疆域与地貌了,我凝视着你,看你的光芒将霜气化而为露,万物被折射于一片晶莹当中。你轻轻拨开我眼里的雾气,我害怕得想逃避,脚步却没有挪开。我看见我所有的屋檐都潮湿,所有的枝叶都颤栗,所有的草尖都青碧,我在你手心快乐地发抖,心中知道,这一刻在爱情的时间线上,将几乎等同于悲伤。
我这样畏惧着爱,又心甘情愿被它的灼热收买。我靠近你,像一只初生的麋鹿靠近树林,在你面前暴露我的脆弱与欣喜,仿佛不知爱是最久远的孤独。
不应当无所防御,然而,那个吹走雾气的人啊,他看起来像积满厚厚落叶的林中空地一样安全,他有金色的温暖胸膛。他是我的平均率。
之四
血在世界的某个角落纷飞,颅骨上盛开大朵无辜的玫瑰。怀抱用来温暖深爱的人冷却的躯体,吻献给已经停止的哭泣。愤怒与绝望是两匹野马,将瑟瑟发抖的心分尸。黑夜像一个漏雨的避难所,流弹从屋顶漏了下来,落在手无寸铁的恐惧之上。
而在另一处,人类为人类划上界限与等级,人类为人类制造恐惧,区分敌我,人类的心拥有着最险恶的气候,并以自相残杀为乐。
但我们相爱。不免带着罪意与歉疚,为这人世间所有我们无法拯救的不幸。像在战斗间歇的壕沟上,无视着牺牲者的鲜血而忘情拥吻,想要以此确认一息尚存。哪怕假如下一刻死去,射穿你的子弹也会射穿我;而作为幸存者,我们将一起对着烟花颤栗,像嗅到美与危险的豹子,在对同伴痛苦的回忆里,紧紧衔住对方的脖颈。我们会是再次日出之时,废墟上升腾起的最后的尘气:一缕湿润的炊烟,一块文明的尾骨,一个攥紧历史的拳头,一对爱情的遗孤。
让我们重新教雨走路,教它以温柔的脚趾,安抚遍布大地与时间的伤痛。
之五
我走向你的时候像是一只孟加拉虎,赤着脚,湿淋淋的。你打开你的丛林,如同打开岩石层的合页。
我曾是羁留其中的化石吗?亿万年过去,灵魂留下物化的痕迹。在你尚未出现时,就守着星球变迁的秘密。
你望着我,像月亮低垂在水面上。我的忧郁是湖水,很快吞没了你的投影。黑暗是一串铰链,牵制我的时候也浸蚀你。
但我们相拥着,就像从陨石坑向地球回望,只见大陆低悬,山峦耸立,万家灯火汇聚,你我的影子像两块洲际拼图,被洋流移挪。
我大声叫喊,想听到山谷目击者般的回音,却只听见地球那庞然无声的寂静。无人作证,爱情像一段对神的告解。
你在真空里抱紧我。而我怀抱着来自一个年轻身体的欲望,不知如何是好。
之六
所有的故事都始于夏季。夏天真好啊,我在夏天是最快乐的,体态轻盈,四肢舒展,没有扰人的疼痛。
我依然觉得你像初夏,温和而晴朗,乐天的像一架手风琴。我咚咚走过,随手拉响你的音阶,你就让旋律跟在我身后,轻快地跑动起来,像一匹紫色的马。当我懊恼你为何这样欢快时,你就变成一只蓝色的小鼓,咚咚地,用你海水一样的眼睛看着我,用你的海浪包围我。
我愿意你的眼睛没有风雪,如果一定要有的话,还是让我来做你眼底那淡淡的阴影。
不需要取悦全世界了,取悦你,或者我,就好。恋爱的人都是自大的自私鬼,这是仅仅属于他们的权利。而我把这份权利交给了你。
你丢失清晨的时候,我也丢失了傍晚。梦的舟楫交互滑过,我听到你的灵魂在睡梦中低吟的声音,像封禁的热带雨林,丛林茂密植物蔓生,充满多汁而饱满的香气。我看见你的心长出屋宇,金属的飞鸟在其间轻轻碰撞,成为白昼的容器,夜来时便盛满飞旋的流光;而你的眼睛,是地心引力,是星系,是时间,我可以旅行很久。
之七
恋人一经拥吻就化为酒,将彼此啜饮。酒是星河,淌过你肋间的铁轨,也淌过我腹部的稻田。我岩浆般的支流零散而细小,带着所有的火光和炽热流向你,而你是幽深的河床,以金色而空旷的回声为我导航。
你这光的孩子,陨石一般,在我的宇宙撞开一个裂口,教自己充盈其中。我看见你,在漂浮着微小记忆的尘埃里,透明而耀眼。爱几乎是痛苦的,你的话语像春天的手指,在我的地表覆上薄薄的青苔,又以抚触,要求我沉睡的种子一一醒来。吻是一种小型的炸裂,像铃声突然在风里抖落,我的灵魂也为之一震。
我抵挡不了你。
我要如何抵挡你呢?你让我觉得自己是广漠的草原,狂沙、灌木、跑马、平静时波浪起伏般的舒滑。你让我觉得自己是落日低垂的山峰,雪是我的脉搏而你是我身上的针叶林。你何曾赋予什么,你不过是要我自己显现。那无限的可能性令我迷恋。
你就像是一个无法诉之于人的愿望,我独自抱着不怀希冀的构想,在渺茫的海里飘荡。你看见了我,你伸出地平线召唤我,并以我无法预知的方式,解开了自己。
我竟满足得害怕起来:为什么,又一次交出了深深依恋?
之八
牛羊从不在我的山坡上跑,牧童也从未吹响竹笛,乡野是一种想象,仅存在于他人的语言地质层里,那是别人的矿藏。我只拥有一个古老、衰败的小城,和它那被灾难埋葬的往昔,那缭绕其上的伤感,那潜流于平静生活下的痛楚。无需掘地三尺。
我是没有心理上的故乡的,我的乡愁在诗经,“我徂东山,滔滔不归”,在汉乐府,“回车驾言迈”,在唐诗,“花重锦官城”,在宋词,“买花载酒长安市,又怎似家山见桃李”,在你,你是我一个人的诗,从前往后,再不会有人这样将你写起——我不许。你就是我的“采采卷耳,不盈顷筐”,你就是我的“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是我的“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也是我的“待得归鞍到时,只怕春深”。我不费丝毫力气就可以将你想念。
念你,念你的岬角、港湾,念你的半岛与瀉湖。你远的像在另一个宇宙,存活于另一套生态系统,有自己的地貌和物候。我触不到你,我只能眯着眼辨认,可你就像一张旧时的黑白照片,底色模糊了,容颜也迅速褪去,视觉被置于一片灰蒙之中,那笼盖万物的灰色带着起伏的颗粒,在指尖形成一种令人心碎的触感。此时我听见自行车散漫而急促地摇着铃,犬吠着,越剧从旧收音机里吱吱嘎嘎传来,你从童年汗水涔涔跑来,经过我,又跑向了你的现在。我们像两列火车,在某趟旅行的中途并行停下。你的车窗映着我的桌椅,你的乘客对视着我的旅者,彼此大胆凝望,然后,微微别过脸。时间为此走了弧线。它为我拉开一张弓,而你是我弓上迟迟不肯发出的箭。
念不到你,只能将你的故乡怀想。我真羡慕你,你的乡愁多么具体,不像我,只能寄之于人。我曾经一次又一次想起那些白鹭、稻田与河流,你上学必经的工厂和山坡,在心里拿了手指细细描摹,直到成为最为稔熟的版图。我连自己的故乡,都没有过这等熟悉。那景象一半来自于你偶尔的简短提起,一半来自于我的想象。抛却虚构成分以后,我发现我是不了解你的故乡,也不太了解你的。然而我依旧对那块土地怀着一份难以言喻的柔情,就像我对于你,满怀着的无非是一团混沌的温柔。你在我身上唤起的,是一种无端的惆怅,影子一般跟着,我却舍不得剪。
那种惆怅大概叫童年。又大概,是一种我所不能真正明白的乡愁。
之九
每天,你在你身体里活上二十四小时,并在我的文字里活上一分钟。你的时间如鱼群,而我是你温柔的掠夺者,觅食的鱼鹰。
吾爱,我想以月光的方式抵达你。无论时间如何套叠、弯转,我都能准确无误地找到你,潜入你,像一行诗与另一行切合,像一个音节嵌入另一个。月光是我的百合花束,将在你的唇上缓缓舒展。
春天尚未到来,我就开始破译你的韵脚。一切青葱的事物都像你,你就是生机勃勃的代名词。风吹过,你就会满山坡长毛茸茸的小草,那是你苏醒时的下巴。而我将随意地走着,散漫得毫不经心,直到伏身听见你的心脏在十亿颗种子里跳动的声音,才惊觉你就是春天黄昏的鸽哨:
一吹,东风就满了。我的心像一叶绿舟,在你的声音里,渐渐浮了起来。
之十
为了抵抗时间的万有引力,我们在深夜醒来,在夜的浓荫之下,爱像地衣一般生长。我在暗处,在地界,把等待充作刺刀,斩开不断朝我涌来的荆棘。而你在光的彼岸,在神启的东方,你像一卷饱蘸雨水的蓝色预言,宛然伸展,道路漫长;你要走遍人间,才能抵达我,每天每天。
你的身体像一丛密实的纸莎草,我要以手指采集你,以双臂环抱你,再将你浸在我尼罗河的水里,用吻不断敲打,才能萃取你薄如纸的精华。然后裁你为舟,为马,为灰雁,教你在飞山渡水时,更为轻盈迅捷,教你在秦桑燕草间行走时,记得我视线的温度,你于是要在每一步里背负我的思念。
我想成为你的刺青,因我是骄蛮的自私的。我还要在你身上织锦。你看不见我的绣线,我耐心地在你的生命里回溯,把你所分赠予我的往事,清洁、浸泡、炼而为丝为线,再一针一针,绣成我的图案。我不必将你修葺一新,我只要一丛杂草,几片瓦砖,一两件你所废弃的家具就够了。我要做你的金缮匠人,在你所空缺的地方,统统补上我。
我知道我是太蛮横了,然而我也不为之道歉。我知道这一切,我都不能。我只能等雨燕自你的屋檐向下垂直飞行时,奉上一个潦草的信号,要你踩着夜的脊骨,到我的疆域来。我陌生的异界。
如果你不来,我就以自己为火种,烧去地界的植被,炼掉寓居于我的鬼魅,再无可烧了,便冷却、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