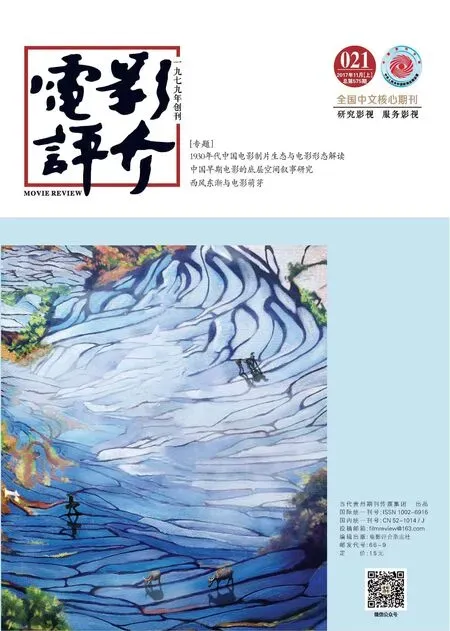诗意影像:对经典纪录片情感表达的再讨论
李共伟
诗意影像:对经典纪录片情感表达的再讨论
李共伟
纪录片影像的力量来源于哪里呢?有人说是“真实”。由生活的经验来看,真实并不一定就是打动人的唯一条件。比如在生活中每天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真实的事件,但很多时候都被人们所忽视。可是,当这些事件被纪录片的导演拍摄下来,并呈现在屏幕上的时候,反而更能引起人们的关注,这又如何解释呢?这是因为纪录片是创作者对现实生活进行选择的结果。纪录片可以像其他艺术一样来表现人的思想和情感,影片所拍摄的现实生活正是这种思想和情感的一种反映,因此,纪录片之所以能够打动人,是因为它浸润了创作者的情感。
作为艺术的纪录片,所蕴含的情感包含哪些内容呢?我们这里提到的情感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影片中人物本身的情感,一是创作者蕴含在影片中的情感。在影片中,前者作为一种真实存在,就是说,人物的情感是现实生活中的客观存在,创作者必须尽力保证这一真实。而后者代表了创作者对于现实生活的看法、立场和倾向性,一般来说,这一情感是通过现实生活反映出来,因此,创作者的情感和表达这一情感的方式是非常主观的。可以说,纪录片于真实之外又必有情感。
一、情感在创作中的作用
(一)纪录片是情感的显现
情感之于纪录片创作是一种动力因素,缺少了这一因素,纪录片创作是无法完成的。从创作的过程来看,导演内心对外部世界的刺激、信息、符号和材料的积累,本质上是一种情感的积累,是导演内心情感对现实世界中的形象进行加工处理的过程,经过情感的浸润之后,导演心中的形象不是现实世界的再现,而是一种不完全复现,这种复现是导演所体验到的他与原事物之间所存在的一种情感,而这种情感对于创作是必不可少的。
从这一点上来说,纪录片的创作与文学创作非常相似。在艺术创作中,情感可以导致深层意蕴的发现。艺术之所以需要情感,在于通过情感能发现并赋予客观事物以意蕴。缺少了情感,艺术创作就不可能完成。由此可以看到情感对于艺术的重要性。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作为艺术的纪录片。
(二)情感是无限的
在纪录片的创作中,想象和联想只能解释导演有可能选择这一景物,但却无法解释他为什么在许多景物中单单选择这一景物。只有从情感出发,才能准确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
因为情感是生生不息的,纪录片也是生生不息的。一种情感产生一种影像,一种影像造就一种境界。景可以生情,情也可以生景,所以纪录片是拍不尽的。
二、情感表达容易出现的问题
(一)情感的主观与客观
作为导演,不可能成为影片中的任何一个人物,那他为什么能够感受到他们的情感呢?与其他艺术家一样,纪录片导演必须具有一种“入乎其内”和“出乎其外”的本领。他们在拍摄一个人时,就要钻进那个人的心里去,成为那个人,体验他的生命,感受他的情感。所以我们观看这些影片时,觉得它与情理深度契合。通过这种心灵的联通,可以体会到生命之间的联贯。
《三里冢·第二防线的人们》实际上是导演小川绅介对三里冢农民抗争日本政府修建成田机场的过程的认识。但是小川绅介在拍摄时不能陷入自己的情感中。他必须暂时跳出自己所处的情境,看看它像什么样子,才能找到如何表达三里冢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对抗。这就是说,他在拍摄时须退到客观的位置,把自己对这一事件的印象和认识当作一幅画来看。在这一时刻,他就已经由拍摄三里冢人民抗争政府修建机场这一事件的导演“化身”为普通的观赏者了,就已经在实际的生活人生与艺术之间拉开了一种距离。
小川绅介以一位来自三里冢之外的人来拍摄三里冢的人和事,他的影片可以说是客观的视角。但是他在拍摄这部影片时,一定要设身处地地感受三里冢人民抗争的情况如何。同时,他必须像一个外来人一样,拿他们的遭遇当作一幅画来欣赏。在想象到聚精会神时,他达到前面所说的“物我同一”的境界,霎时之间,他的心境就变成他们的心境了,他已经由客观的观赏者变而为主观的享受者了。
总之,主观的纪录片导演在创作时也要能“超以象外”,客观的纪录片导演在创作时也要能“得其环中”。
(二)创作中情感的虚与实
作为艺术的纪录片的乐趣在于玩味,就是通过人物的行为体味人物的内心情感,而不是让他们像交代问题一样直白地说出来,从另一方面来看,情感如此复杂也无法完全靠语言说明白。
艺术对情感的处理最忌讳的就是过于直白。一般来说,在纪录片中,导演并不将直接描写人物的情感,而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和动作,来暗示出人物情感的变化和复杂。通过展示日常生活的种种细节,让观众体味到人物内心的复杂情感,这是一种虚写,这种将情感隐藏在人物日常生活的行动当中的情感处理方式,就是一种情感的虚写,所以比较值得玩味,观众可以通过不断揣摩玩味达到一种独特的审美乐趣。
纪录片的创作者要表现人物的复杂情感时是离不开日常生活的。众所周知,纪录片直接将日常生活作为拍摄对象,在表达人物的情感时,理所当然的离不开日常生活。但值得纪录片导演思考的仍然是如何虚写人物的情感。比如,张以庆拍摄的纪录片《英与白》中,导演表现熊猫饲养员白与熊猫英之间的情感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没有直接表现二者之间那种相互无法离开的情感,而是将这种情感通过几个生活细节来表现,英发情时,白喷了香水,然后走到笼前拥抱安抚英。在给英喂竹子时,白会细心地剪下最嫩的枝叶。通过这样的生活细和动作细节的积累,展现了英与白之间的复杂情感。
杰出的艺术作品首先必须通过复杂的情感打动观众,才能够向观众传递一种价值。这种打动观众的情感,并不是通过直白的诉说完成的,而是通过一种艺术独有的虚写情感的方式创造出一种审美感受来完成的。除了《英与白》,瑞芬斯塔尔拍摄的《意志的胜利》、伊文思拍摄的《雨》等影片对情感的处理方式都值得纪录片创作者学习。把隐含的情感都用直白的方式来表现,就容易把复杂的感情变得廉价,这种处理方式就使得艺术作品中的情感廉价而浅白,也就失去了艺术的意味了。
三、创作中情感的表达方式
(一)蕴含在整体之中的情感
纪录片的情感表达必须从整体来看。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纪录片是一种旧经验的新综合。在没有综合之前,导演内心的影像是散乱的。综合之后,影像成为一个谐和的整体。这种综合的原动力是导演的情感。一部纪录片不能拆开来看,说这个镜头好,那个镜头不好,因为完整的全体中各部分都是相互融合的。不能脱离纪录片的整体单说这个镜头拍得好,那个镜头拍得不好。欣赏或创造一部纪录片,都必须先注意到总体,不能离开总印象而单论细论枝节。
创作一部纪录片也要从总体上来把握,而不能纠结于某一句对白或某一个镜头。在伊文思拍摄的纪录片《雨》中,透过阿姆斯特丹的城市景象,创造了一种印象派风景画的意象。阳光中的屋舍、河上和街道的行人,一阵轻风之后,落在运河上雨点,在水面上激起了水花,随着雨越下越大,镜头反复展示乌云、湿漉漉的马路上的反光以及斗篷、雨伞下的行人和被雨淋湿的行人,当最后几滴雨点落下之后,城市又恢复了日常生活,单看这些事物,并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将它们组合在一起,整个影片就制造了一种诗意,这座城市多美啊。
情感是综合的要素,许多本来不相关的景物如果在情感上能协调,便可形成完整的有机体。《雨》拍摄的画面大多都是物景,我们仔细玩味这部影片时,并不觉得景物的反复出现令人感到重复和厌烦,反而觉得它们天生就是一个有机整体,互相烘托,互相融合,这是因为它们在情感上是和谐的。
因为有情感的综合,原来看似散漫的景物可以变成不散漫,原来似重复的景物也可以变成不重复。伊文思拍摄的《雨》中,鸟儿是一个反复出现的形象:雨前在阳光中飞翔的鸟;雨刚刚下起来的时候,在灰色天空中飞翔的一群鸟儿;暴风雨来临之后,几只惊慌失措,到处乱飞的鸟儿;雨停了之后,几只安闲停留在一座桥的栏杆上的鸟儿,这些形象反复出现在影片中,那么,导演何必把它拍了一遍又一遍呢?因为人的情感是往复徘徊、绵延不尽的。纪录片中反复出现的某个形象在意义上看似有些重复,但在情感表现上却是合理的。
(二)物像并置对情感的表达
通过物像的并置,省略不必要的过程描述,可以将陈述句子变成情感语句。唐代许多诗人在创作诗歌时,常常采用这样的情感处理的方式。比如,杜甫在处理情感时,像一部影片的导演一样,常常通过对人、事、景“画像”的方式传达出来,这与情感的虚写方式有些相似。
作为纪录片的导演,可以从中国唐诗、宋词里借鉴一些这样的情感处理方式。比如,杜甫在《秋兴八首》中采用了颠倒语序的方式表达情感:“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正常的语序应该是,鹦鹉啄余香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通过语序的变换将动作转换为对事物的画像,杜甫将一个叙述语句转变为情感的表达,这对于纪录片导演来说,是一个非常值得借鉴的表现人物复杂情感的方式。
那么,在纪录片创作中,如何通过景物并置来实现对情感的表达呢?在纪录片创作中,可以通过省略的方式减弱叙事功能,从而将叙述语句转换为情感语句。因此,纪录片导演在表达情感时,就不能单纯叙述事件,讲述发生了什么和事件的发生过程,而是必须将叙事镜头转换为景物并列来表达情感,通过转换,把观众推到一个浸润式的意象之中,观众看到不再是事件过程的描述,而是直接感受情感本身,成为一个情感体验者,而不是一个被动的信息接受者。
纪录片《最后的山神》中,导演孙曾田采用了同样的省略方式,减弱了镜头的叙事功能实现了对情感的表达。比如,在拍摄鄂伦春族老猎人孟金福打猎时,导演并没有将他如何与一头野猪搏斗作为拍摄重点,只拍摄了孟金福从家里出发和打到猎物后两个段落,省略了打猎的过程,导演打猎前和打猎后的并列,降低了镜头的叙事功能,将事件的因果逻辑转化为通过情感将事件连缀在一起,表达情感成为镜头的主要任务,这也是影片中诗意的来源。
(三)空间对情感的表达
在纪录片中,空间完成了从物理空间向精神空间的转化。纪录片的导演都会对画面中的事物“进行安排”——我们把这样的安排称为构图——使得人们能像阅读文字一样来认识电影空间,观众通过拍摄主体以及他所处的空间能够了解到情节的发展和人物的情感变化。因此,影像中的空间就更加个人化,环境成为导演对人物情感进行表达的一部分,完成了从承载人物活动的物理空间向精神空间的转化。
在阿伦·雷乃拍摄的纪录片《夜与雾》中,空间成为导演表达情感的重要载体。影片包括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法国人和盟军解放集中营时拍摄的黑白影像来表现残酷的过去,一部分是雷乃用彩色胶片拍摄的破败的集中营建筑。将黑白与彩色画面中的空间对比,你会发现虽然集中营的物理空间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观看两者的感受却完全不同。在黑白影像中,集中营的空间更多是作为事实的一部分出现,在这里,纳粹杀害了上百万犹太人和其他民族的普通人。在彩色的画面中,这里只是一个破败的空间。当摄影机缓慢地划过颓败的建筑、冷却的焚尸炉、关押犹太人的牢房等等事物时,给观众带来的感受却发生了巨大变化,这里的一草一木所构成的空间都浸润在导演的情感之中,用这样的影像空间,导演表达了他的人道主义情感和立场,也表达了他对人类如何对待这一残酷记忆表示了担忧。通过这个空间,观众能够感受到创作者内心那种难以诉说的情感,空间也完成了从物理空间向精神空间的转化,因此获得了生命,有了情调、声音、呼吸和温度。
结语
综上,作为艺术的纪录片首先是通过情感打动观众,进而影响观众的思想。纪录片中出现的事物,以及创作者在其中表达的思想必定是受情感饱和的。情感或出于己,或出于人,导演对于出于己者必须跳出来观察,对于出于人者必须钻到他的心里进去体验,发现最易打动人的情感,影片中所蕴含的思想和情感才能为人们所理解。因此,纪录片更应该是一种诗歌,而不是一种报道。
李共伟,男,山东烟台人,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