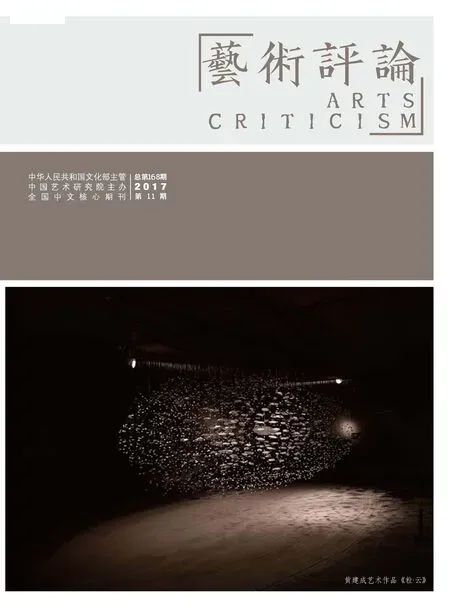数字媒体影像时代的未来书写
——中美科幻电影的赛博空间与赛博格身体的文化想象
陈亦水
21世纪之后,随着电影特效技术的日新月异与智能时代的到来,赛博空间(cyber space,亦称“网络空间”)和赛博格(cyborg,亦称“人机一体化”)被重新赋予了新的意义,这些1960—80年代的旧词汇,大量活跃于当代主流科幻电影的创作之中。
冷战时期,好莱坞科幻电影迎来了第二个黄金时期,一系列以太空旅行为题材的科幻电影作品成为经典之作。相比之下,21世纪主流科幻电影则以赛博空间和赛博格身体为主要表现对象,更具有未来面相,而这些充满后人类主义色彩的科幻元素,不仅与西方科技文明的发展保持同步,还是历史上殖民时期的帝国主义和冷战时期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当代延续。
而反观近年来中国科幻电影的未来书写方式,很大程度上都是在西方的文化逻辑与价值系统中进行创作的。在此意义上,厘清赛博空间、赛博格在西方流行文化语境下的演变过程,有助于反观中国科幻电影创作的文化逻辑,进而为中国科幻电影创作寻找突破西方为中心话语体系的可能性。
一、美国意识形态的赛博格银幕化身
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观察,当代科幻电影对于赛博格身体的塑造,不无明显地呈现出一种对于性别、种族、民族、宗教、阶级等等意识形态身份的重塑状态。这一重塑状态直接将现实的文化身份问题,引向了一种后人类主义式的、关于未来的文化身份想象。
作为一个技术术语,“赛博格”指涉的是一种“自我调节的人机系统”(selfregulating human-machinesystem),亦即人机合成体。最早提出“赛博格”假设的是美国数学家、控制论之父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他在1948年出版的《控制论》(Cybernetics)一书中,通过逻辑严谨的数学推演方式设计出自动机器人的控制系统,维纳的机器人是建立在“信息(information)—反馈(feedback)”的控制系统之上,而“研究反馈的任务需要建立在工程学设计和生物学研究的共同合作基础之上。信息、检测和传输信息技术的研发,则需要工程师、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所有学科研究人员共同努力”。维纳认为,人、动物、机器没有本质区别,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科幻电影的创作。不过,在大众文化领域里,1930年代的早期科幻片尚未从B级片定位和恐怖片类型中独立出来,正如《科学怪人》里的弗兰肯斯坦仍以中世纪的怪物为主要原型,西方科幻文学作者与电影人,尚未认识到弗兰肯斯坦这个科技与野兽杂糅体身上所具有的强大的未来魅力。
但在政治领域中,美国政府努力地将弗兰肯斯坦强大的未来魅力付诸实践。1960年代,美苏大国太空争霸赛期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试图在军方支持下,试图通过机械、药物等技术手段对人体进行拓展,以增强宇航员身体性能,使其变成一个“自我调节的人机系统”,以适应在太空环境下无负担地生存、作业,同时对苏联方面展开军事行动。
美国好莱坞的科幻电影的第二个黄金期,恰恰诞生于美苏太空争霸赛如火如荼的70年代。美国导演乔治·卢卡斯,充分认识到弗兰肯斯坦这一未来属性,于是他将这头中世纪怪兽从30年代的恐怖片类型中“解放”出来。1977年,卢卡斯制作了影片《星球大战》,故事里可以在外太空行走、具有超强战斗力的帝国冲锋队暴风兵,就是美国军方研制的赛博格身体的银幕化身,极具浓厚的冷战意识形态色彩。
美国后现代女权主义人类学者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在理论上将赛博格身体的后人类主义讨论,引向了一条推翻美国政治意识形态的反叛道路,旨在强调“女权主义—社会主义”身份政治的建构问题。她在《赛博格宣言》里宣布,一个赛博格统治的后人类时代业已到来。所谓赛博格身体,是一种“控制论有机体”(cybernetic organism),一个“生物体与机器的混合杂交物,是一种社会现实,也是一种虚构的创造物。”哈拉维认为,赛博格身体是一种充满不确定性的身体,而女性身份恰恰是在于父权制度下被压迫的一种性别认同,她由此推论,赛博格时代将带来一种新型的权力统治与反抗压迫的关系,这需要全球妇女实践的参与。时至今日,“赛博格电影永恒的主题,是关于控制的科学事业”,人机杂交体承担的是一种反乌托邦修辞,抒发的是“与器官移植、输血和外科移植手术失败的类似焦虑”,表达的是“基于现代医学科学的紧张,更直指生化科技或许是无法超越身份/认同的后人类”。尽管在西方电影中,赛博格主题的确以西方科技的(反)乌托邦面目出现,某种程度上治愈着西方人对医学生物科技的恐惧,例如“蜘蛛侠”系列电影中发生变异的蜘蛛侠、“复仇者联盟”系列电影中的具有特异功能的变异人等等,但经过一套完整的“超级英雄拯救地球”的好莱坞文化逻辑的编码,“现代医学科学的紧张”与“外科手术失败的类似焦虑”,巧妙地转化成为某种“充满费勒斯中心主义幻想的福特主义模式”,无不彰显了美国资本与军事力量。
不难看出,赛博格理论在理论层面上具有反主流文化的激进特征,但现实中的美国科幻电影对于赛博格身份的塑造方式,则体现着美国主流文化价值观念。2001年,“9·11”事件发生之后,银幕上的这些赛博格身体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表现为“脆弱的、后现代模式的,因为它们遭受着不断的爆炸”。这是当代美国反恐意识形态在大众文化领域的显影,直接投射出美军与伊斯兰世界军事对抗的挫败和焦虑。例如,美国漫威电影工作室第一部独立投资、制作完成的大电影《钢铁侠》(2008)里,主人公托尼·史塔克第一次试验钢铁侠战服成功之后,便穿上它瞬间降落到中东地区的伊拉克、干掉了几名恐怖分子,作为赛博格的银幕化身、美国最受欢迎的超级英雄之一,钢铁侠第一次亮相就旗帜鲜明地宣布了他的身份立场:全球范围内打击中东恐怖分子,捍卫美国与全人类的世界和平。
此外,还有影片《源代码》(2011)中在伊拉克反恐作战中脑死亡的、肉身不完整的海军陆战队员,依靠电脑联线人体的交感神经系统,一次次地“回到”开往芝加哥的列车爆炸之前的时刻,其灵魂进入车上一名陌生乘客的肉身,继续开始他“生前”在现实维度的反恐任务;《阿凡达》的主人公,也是一位人类身体有缺陷的残障人,同样也是依靠电子交感技术重组,在充满“交感幻觉”的虚拟现实潘多拉星球中成为一名能跑会飞的阿凡达战士;还有《极乐空间》(2013),将未来设定为一个地球内外两极贫富空间,穷人在地球上开矿、生产,为生活在太空的空间站里的富人提供补给,地球上的男孩成为一名依靠生化控制系统操作的超强机甲人,他依靠后脑勺嵌入的机械交感系统而控制全身的金属骨骼,使之能够以一敌百……无论是开往芝加哥列车上的平民乘客,还是异星上的阿凡达,或是贫穷的“地球人”机甲人,都是各种形式上的赛博格人类身体,而这些在人类肉身基础上的赛博格身体的重组,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人类肉身自身缺陷不足,进而完成了对当代美国文化身份的重组,以及对主流价值观的修复和再次肯定。
二、赛博空间影像的反乌托邦思潮之退场
世界电影特效技术的日新月异与科幻电影创作的发展,几乎是同步进行的。首先,电影史论界将1976年《星球大战》的制作年称为“特技效果的新生”(电影正式公映于1977年);其次,1999年沃卓斯基兄弟(姐妹)导演的《黑客帝国》,以360°摆放照相机的方式拍摄的“子弹时间”(bullet time)这一摄影技术的成功运用,标志着科幻电影上升至一个新的历史台阶;最后,2007年,詹姆斯·卡梅隆执导的电影《阿凡达》,全面提升了动作捕捉和虚拟摄影的特效技术的水准,其诞生年份被誉为“3D电影元年”,引发了全球观影风潮,使之成为一部青史留名的佳作。
科幻电影技术对于虚拟现实空间影像的表现力的不断进步,都旨在诠释“科技如何改变人类生活”,千禧年之后的世界科幻电影创作,在银幕内外高调宣布着一个指向未来人类现实生活的赛博空间时代的到来;赛博空间从此成为科幻电影中主要展现电影特技的奇观场域。
在赛博空间正式登场之前,从空间塑造上来看,美国科幻电影空间的文化表达主要以大航海时代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当代后殖民理论的学者们认为,《星球大战》开启的70年代好莱坞科幻电影黄金期中,类似于“星际迷航”“星球大战”“异形”等系列电影的空间想象方式,表露出美国人对于“第三世界”领土及其种族与文化,实际存在着某种“矛盾的帝国主义”(ambivalent imperialism)情结,故事中的星际联盟、星际舰队、生化军队等人类为主体的社群,对于外星人通常采取带有种族灭绝性质的入侵行为,以防止异类的自然进化。这些未来书写方式,某种程度上隐含着对于“异形”(alien)身份的想象方式,直接来源于美国本土社会对于黑人等有色人种的外来移民的恐惧和排斥心理。以星际开拓为主题的美国好莱坞科幻片中,对于地外太空的空间想象和宇宙英雄身份的认同方式,有着历史上的殖民时期的帝国主义传统和现实中的种族主义文化逻辑在其中。
直到1980年代,随着个人计算机在西方社会的普及、互联网技术的发明与电脑游戏玩家文化的流行,赛博格人机混合技术的概念,催生了“赛博空间”(cyber space)的诞生,为科幻文学写作与电影创作带来了一个关于未来空间的全新想象。其中,赛博空间中的赛博格身体,成为这一时期赛博朋克流行文化的主题,其身份政治之复杂性,理论上为科幻文学和电影创作打开了更广阔的文化空间。
1984年,美国作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出版了反乌托邦科幻小说《神经浪游者》(Neuromancer),他定义赛博空间是一种依靠计算机模拟出来的“交感幻觉”(consensual hallucination),推动了文学和艺术界的“赛博朋克”(cyberpunk)运动。所谓赛博朋克文化,指的是“一群生活在反乌托邦未来的高智商罪犯,生活并困在一个由技术所统治的人口过剩与都市退化的世界。这个世界由计算机无限的力量所控制,同时,广阔的计算机互联网络也为高智商罪犯们提供了新的空间。通过计算机进行时空旅行是罪犯们的家常便饭,他们在这个电脑化的未来里依靠窃取和买卖信息和虚拟货币为生”。这种具有反乌托邦色彩的未来书写,正是20世纪80年代科幻文学的主题。
那么,如何分辨赛博格与人类身份呢?当维纳的赛博格设想把人类、动物、机器三位一体地视为一个有机运行系统时,就已经将人类身份推向了被质疑的位置。几乎与维纳创造“控制论”的同时,服务于英国军事情报系统的计算机之父与密码学家阿兰·图灵(Alan Turing),开始研究人工智能机器与人类身份的区别;1950年,他设计出来家喻户晓的“图灵测试”(The Turing test)。美国后人类文学评论家凯瑟琳·海尔斯(Katherine Hayles)在《我们如何成为后人类》一书中提出,图灵测试是一种存在悖论的分辨人机身份的方案,因为它所证明的是“扮演和再现身体的叠加,再也不是一种自然的必然性,而是一种因情况而定的生产,这是一种由技术决定的关于身份的生产,并且不能从人类主体中分离开来”,无法脱离于人类主体的分辨方式,却反身证明了电脑或者人工智能的无法分辨性,更重要的是它与人类难以区分,正如难以从根本上划分异性恋与同性恋的性别身份一样。海尔斯进一步指出,在知识爆炸的时代里(20世纪的最后十年),相反,人类的肉身只是后人类身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信息和人性一样,拥有“具身化”(embodiment)的特征,例如它依附于物态的实体,可以被毁灭却不能被复制,一个后人类和人工智能一样,在接收了外界信息之后,可以在自身内部形成了一个“信息反馈回路”(informational feedback loop),这样一来,所谓自我就成了一个具有流动性的、多种形态的实体。海尔斯用了这样一个比喻后人类身份的特征:“当你凝视着电脑荧屏上向下滚动的闪烁的光标时,无论你具体属于哪种实体的身份认同,你便已经成为了一个后人类了。”
在西方科技史上,图灵测试的出现,被人们追加为后人类时代的到来,这也是《银翼杀手》(1982)、《人工智能》(2001)、《机械姬》(2015)等科幻电影中反复出现的赛博格身份认同主题,然而这些影片中的关于赛博格身体的文化政治表述则大相径庭。
美国导演雷德利·斯科特拍摄的赛博朋克色彩浓厚的影片《银翼杀手》,根据反乌托邦科幻小说巨著《仿生人梦见电子羊了吗?》改编,讲述一名生活在核爆之后的都市警察抓捕仿生人的过程中,却发现自己可能是一名仿生人的故事。创作者将人类与仿生人身份的讨论,上升至美国文化主体中的自我与他者身份异质性杂糅的反思维度。故事里,人类警察主人公作为国家机器的一员,表现为一个充满现代科技文明与美国主流文化意识形态创伤的身体;影片里的仿生人(即赛博格)也没有简单地被视为外来移民与少数族裔的化身“外星人/异形”(alien),而是旨在反思自我与他者之间不可分割的文化杂糅特性。
在今天的主流科幻电影创作中,赛博空间的表现力极大地推动了科幻电影创作在影像与叙事上的双重革新。《阿凡达》中蓝色的奇异潘多拉星球、人类与克隆纳威人之间依靠电子交感传输系统进行沟通的大胆想象,如今已成为展示视觉影像奇观的想象力的基本来源。人们对于想象力的影像实践方式,必然离不开数字虚拟技术的电影手段,然而更重要的是,从地域空间的塑造与文化身份的建构来看,赛博空间与身体的想象与创造,在世界电影工业生产中已成为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逻辑的定势思维,延续着“赛博格”词汇诞生之初的冷战意识形态,成为这个电影“赛博格帝国”内在的文化主导策略。
随着冷战的结束,曾经在《神经浪游者》《银翼杀手》等反乌托邦科幻小说中不断出现的赛博格身份认同困境,在近几年的科幻电影中被表现为一种积极、向上、肯定美国社会主流文化价值观的面相。这是千禧年之际的《黑客帝国》和2007年的《阿凡达》对于赛博空间的主要表达主题。赛博空间看似为科幻电影创作打开了一个更广泛的空间,但是正如美国科幻电影研究者凯文·罗宾斯(Kevin Robins)清醒的批判,在大众文化生产中,赛博空间所带来的乌托邦视觉建构方式带有强大的欺骗性,一个基于现实的仿真世界诞生了,新技术看似可以为人类创造一个新的乌托邦世界的可能、让人类以为赛博空间创造出来的仿真世界意味着对现实世界的某种解决方案,但现实却恰恰相反:视觉文化让人类变得更加厌倦旧事物和陈腐之物。在此意义上,《黑客帝国》系列电影并非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反乌托邦科幻作品,而是一种以反乌托邦的科幻叙事手法,对主流文化及其统治结构进行认同。除了第一部《黑客帝国》(1999)具有人类身份觉醒、底层反抗独裁统治的激进意味之外,在《黑客帝国2:重装上阵》(2003)和《黑客帝国3:矩阵革命》(2003)里,人类生活的现实锡安与“母体/矩阵”(Matrix)统治的反乌托邦现实和乌托邦赛博空间,其实都是母体/矩阵所设计出来的程序。换言之,在“黑客帝国”系列电影中,革命被想象为统治阶层的一部分,是修复和改良统治阶层的内在设定。北京大学电影文化研究学者戴锦华教授近年来十分关注科幻电影,在针对《黑客帝国》的解读中,她强调:“虽然现在在数码特效上相当用力,但在故事的选择、结构的编织上都有点弱,包括故事深度、角色深度,乃至科学幻想的深度,则进行了玄学化的处理”,三部曲系列进而从一个赛博朋克文化的反乌托邦科幻传统的反思,最后逐渐沦落为“反叛的领袖与统治的集权者其实是朋友,压迫与反抗是结构好的游戏”的模式,人类反抗者最终选择与计算机握手言和、拥抱科技文明。从沃卓斯基兄弟(姐妹)对于赛博格身体的塑造方式来看,人们想象革命的方式与反乌托邦叙事,本质上是反—反乌托邦式的、反—反主流文化激进革命的。所以,人类与母体/矩阵最后达成了协定,也就消解了赛博朋克反乌托邦科幻写作传统内在的反主流文化的激进力量,最终达成了对主流社会及其统治机制的认同。
《黑客帝国》系列对于赛博朋克文化的改编方式与赛博空间的未来书写策略,在21世纪之后的科幻电影中不仅继承了下来,还在“后9·11”时代语境下,转变为一种反恐演习的虚拟训练场,在包括《源代码》在内的影片里成为宣扬美国国家意识形态的主阵地,1980年代的反乌托邦科幻文化创作传统就此退场。
三、中国科幻空间与未来身份定位
从当前为数不多的中国科幻电影创作中可以发现,中国科幻电影创作中的赛博格虚拟现实空间的想象与文化参照,始终以西方科幻电影为准绳。
在科幻电影的塑造方面,中国人对于地球的关注度在某种程度上要大于美国科幻电影。相应地,中国科幻电影对地表之外、架空现实的赛博空间的表述力,则相对羸弱很多。更重要的是,赛博空间的想象能力指向的是一条通往未来人类生存空间的想象之路,中国电影则整体呈现出创造力方面的匮乏,取而代之的只是一味地追求科幻空间的视觉奇观效果,反而使得地外空间、赛博空间的文化坐标暧昧不明,这些架空现实的虚拟空间所定位的文化身份位置,也因此语焉不详。
例如,影片《长江七号》里唯一呈现宇宙空间的方式,是小狄躲在黑暗的衣柜里,依靠不明的外星生物所散发出来的全息影像才看到了地外星系的整体面貌,这既可以看作是一种赛博格虚拟现实空间,也可以读解为是小狄与长江七号进行心灵感应之后看到的视觉幻象;《卧龙岗》里的外星人珠子返回星球的空间展示方式,是一个经过了纯色处理的黄色的异度空间,同样,它既可以视为赛博空间,也可以看作是人类与玛雅人相告别的精神空间;还有影片《拯救爱情》里洞穴般的蓝色T星球,以及《词与物》中封闭的“异托邦”空间等,中国电影人对于赛博空间的想象,总呈现出一种被动、封闭或者暧昧不明的状态。
自晚清以来,西方科技、工业与文明对中国人而言意味着一种可以带中国脱离当时民族国家耻辱的先进文化事项,中国启蒙知识分子对其寄托了摆脱民族危亡与屈辱境地的希望。西方先进的科学理念与文化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重塑中国民族性格与国家身份的可能。在中国科幻电影创作中,我国电影人对于西方科技文明,延续了晚清以来的极大的快乐憧憬;对于赛博格身体人机合成状态的身份混杂的处理方式,也充满了乐观、肯定的自我认同,而这种身份混杂的自我认同状态,内在地包含了对西方科技文明的他者认同。
中国科幻电影中的赛博格身体,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人类/中国身体与机器/西方科技文明的合成体。最终,该合成体的后人类特征的中国文化身份表述方式为缺乏反思力的,对赛博空间、虚拟现实以及地表之外的空间的无限向往。
例如,香港科幻电影《女机械人》(1991)、《超级学校霸王》(1993)等塑造的赛博格身体,所谓人机合成体表现为一种由身份错乱而引发的搞笑噱头,既传递出“九七”回归之前“香港文化焦虑与身份想象的紧张”,更体现出香港在当前地缘政治格局中文化身份的无根性。在同时期大陆拍摄的科幻电影,如《凶宅美人头》(1989)、《合成人》(1988)以及《毒吻》(1992)等,尽管体现出对于西方科技文明与生化技术的恐慌心理、具有一定的反乌托邦色彩,但从创作者对于赛博格身体的塑造方式及其身份想象来看,这些影片无意探讨未来科技文明时代的中国身份定位,赛博格人类仅作为一种身体奇观而展示,旨在刻意营造某种恐怖气氛,以最大程度挖掘娱乐价值。随着中国人快乐地拥抱西方科技、成为其忠实信徒之后,中国科幻电影很快陷入了对影像的奇观化呈现之中,文化身份的位置也因此难以定位。
千禧年之后的合拍片时代里,无论是《公元2000》(2000)里的人工智能,还是模仿美国科幻电影《人工智能》(2001)里的机器人造型的《机器侠》(2009),或者是《未来警察》(2010)与《全城戒备》(2010)中人机混合体的超能警察形象,以及《长江七号》(2008)中的外来科技宠物狗塑造,同样无意于在赛博格身体上寄托某种关于未来身份的想象与文化定位,而是不断地将赛博格诠释为西方科技文明的符号,描绘的是一副拥抱高科技文明的快乐乌托邦情景。
关于赛博空间与赛博格身体的后人类影像塑造,是一种在西方科技文明观念体系之下,建构未来西方文化主体性及其身份定位的方式。但在中国电影人的创作之中,一方面是一味地追求效法好莱坞人机合成体的视觉奇观,而落入了西方文化主体性身份的他者认同之中;另一方面,后人类主义的影像实践也被想象成一种解构主体性的策略,用以定位“第三世界”地区边缘化的身份位置。例如,台湾学者甚至提出了“赛博格—台湾”的说法,认为“台湾本身并无固定、完整内容,而是不断生成、具有复杂即身性的流动过程。如果有所谓的台湾主体,它也是一种缺乏本质与内容的赛博格主体”。的确,诸如为数不多的台湾科幻电影《骚人》(2012)中的“网络建国”设想与世界青年集聚在山谷中迎接世界末日的狂欢景象,还有根据法国作家马歇尔·埃梅的短篇科幻小说《穿墙人》(2007)改编的同名科幻片里困在虚拟现实情境中的主人公们等等,都通过赛博空间的影像表达,塑造了一个充满流动性的“赛博格—台湾”身份,潜在地表征了某种“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式的台湾未来身份危机。
然而,和其它具有解构性质的后现代理论一样,例如后殖民、酷儿理论等等,后人类视域下的赛博格身份讨论有着自我边缘化、逃避现实身份困境的特征,作为一种策略,非西方的、“第三世界”国家与地区的赛博格身体的形象塑造方式,本质上缺乏一种具有建构意义的、直面现实和想象未来的动力。
四、关于中美科幻空间与身份的文化差异
纵观中美科幻电影对于赛博空间与赛博格身体的表现方式可以看出,美国科幻电影自有一条清晰的“科学—政治—军事—流行文化”领域互融共进的发展脉络,然而中国科幻电影,则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因想象力匮乏而文化身份暧昧不明的状况。但是,如果撇开中国科幻思维的西方文化影响,可以发现中国的科学观、科幻观与西方的科技文明导向有着本质区别。
首先,根据中国地缘文化认同的本土思维模式,中国人自古以来以“华夷之辨”为地缘文化认同之基础,进而对“四海之外”的空间展开想象的。
前现代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天—地—人”合而一体的宇宙观,在中国电影创作中有着深刻的影响。例如,在取材于“鬼吹灯”系列小说的影片《九层妖塔》(2015)里,创作者对外星人身处的空间与身份形象,进行了中国式本土化的创作:外星人所寄居的超越地表的空间,不仅不像好莱坞科幻片那样处于地表之外,反而在地球内部的洞穴之中;妖塔的奇幻空间塑造方式,也取材于前现代中国原始民俗文化的审美特征。这和同时期美国好莱坞科幻片对于“外星人来自外太空”的想象方式,在空间的想象层面上有着根本区别。影片里,中国创作者将外星人与中国少数民族身份进行了联结,并且根据现实中的少数民族差异性文化,创造了一个名为“鬼族”的外星人族群,它既是外星人,又是中国这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少数民族分支。
同样,在影片《美人鱼》(2016)里,超越地表的空间,也是高度内在于地球之中的。无论是影片中的日本研发出来的杀海豚的生化科技,还是西方学者追踪史前神秘海洋生物过程中使用的高科技手段,都在影片里被塑造成一种负面的、具有讽刺意味的科学主义价值观念。这些刻画超越地表空间的、对未知生命体进行想象描绘的影片,同时也溢出了科幻类型片的范畴,为中国电影之于未知空间的想象开辟了一条亟待拓展的创作小径。
其次,中国“天—地—人”的宇宙观,表现出来中国人看待人类与地外空间关系的另类视角,理论上在中国科幻空间的塑造方面大有作为。
对于西方人来说,土地即是地球,正如好莱坞科幻电影《星际穿越》(2014)所呈现出来的西方科技文明的空间观念那样,看护土地、守候地球的取向在影片中被视为保守、落后的农民身份(即墨菲的哥哥),而大胆地朝向太空冒进、在其它星系中开拓殖民地空间的行为,则塑造成激进、富有冒险精神和承担人类物种使命的宇航员身份(如库伯和女儿墨菲),影片无不以“好莱坞式的发展主义、以科学来拯救科学灾难的逻辑而胜出”。对于中国人而言,这一空间的想象逻辑则恰恰相反,中国人某种程度上更倾向于人类家园的守望者,而非朝向地球位置空间以及地表之外开荒破土的殖民者,而这正是好莱坞科幻电影中所有意和无意忽略的空间观念。
再次例举《美人鱼》中的人类与海洋空间关系的呈现方式,其中半人半鱼的身体既已包含了身份杂糅的特质,一方面,时空不明的地域空间与历史年代“弥散着一种历史观念和精神特质,将怀旧的两难和宿命的疑惑集于一身”,标着了香港电影人关于故乡与他乡的“后九七”时代里的文化困境;另一方面,美人鱼作为人类的他者,与依靠未来科技文明而拼凑的赛博格后人类人机合成体不同的是,这种非人类的他者身份的塑造方式,主要是通过清理历史上人类与海洋生物的共存关系而指向的是一个关于环保主题的未来人类文明想象,具有对人类世代生存的土地/地球与超越地表的地域空间进行重新描绘的可能性。
最后,关于赛博空间与赛博格身体的未来书写,中国科幻电影创作目前在这一方面本质上仍处于空白状态。无论是对于计算机文化的反思力、赛博空间的建构力还是赛博格银幕化身的身份政治的想象力,中国电影人都急需摆脱晚清以来对于西方科技文明的盲目崇拜思维,进而立足本土文化科学观念进行科幻电影创作,在21世纪人工智能时代里发出不同于美国好莱坞的中国自己的声音。
结语
从目前关于未来赛博空间的影像塑造方式与文化身份表达来看,占主导地位的仍是美国好莱坞电影中表露出的当代反恐意识形态与美国精神的文化逻辑。一方面,美国科幻电影有着基础牢固的反乌托邦科幻文学写作传统;另一方面,随着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对流行文化话语权主导能力的增强,当代美国科幻电影几乎改写了1980年代赛博朋克文化的反乌托邦政治立场,转而宣扬当代美国反恐意识形态。
反映中国科幻电影无论是外太空及的宇宙探索,还是关于虚拟现实空间的塑造方式,都在一定程度上处于缺席状态,只是一味地效法好莱坞科幻电影的创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本土空间与文化身份的表述能力。但是,中国科幻电影对于超越地表的空间塑造方式,仍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中国式的科幻思维模式的特点,这潜在地包含了一种非西方式的描绘未来图景的影像与叙事可能性。这急需当代中国电影人,对于当前西方科技文明的发展格局,以及整个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化进程,在技术现状、政治视野和文化立场方面进行深度分析和全面判断,才能在21世纪之初的后人类思潮复兴之际,准确定位中国本土空间与主体性文化身份位置,进而提供一个关于整个人类未来空间与政治身份的新的未来想象。
注释:
[1]Mike Featherstone, Roger Burrows.“Cultures of Technological Embodiment”.Mike Featherstone, Roger Burrows Ed.Cyberspace/Cyberbodies/Cyberpunk: Cultures of Technological Embodiment.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Press, 1996:2
[2]Norbert Wiener. Cybernetics: or the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65:vii.
[3]事实上,《星球大战》的片名就取材于当时美国军方公布的《战略防御倡议》,这是一个针对苏联可能对美国发动大规模洲际导弹攻击的战略防御系统,最终目的是为了抵挡苏联的核弹,俗称“星球大战”计划。
[4]Donna J. Haraway. Cyborg Manifesto: 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alist-Feminism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Milan: Feltrinelli Press, 1995:3
[5]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哈拉维的理论创建对未来人类身份想象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但显而易见的是,她对于赛博格身体的思考脉络及其后人类时代的断言,尚未考虑到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远未完成,有些不发达地区甚至尚未开始;再加上经济全球化趋势,一方面使得世界各地的金融货币、商品贸易、信息传播的流通速度加快乃至同步,另一方面,也加剧了世界地缘格局内部的贫富分化与性别、种族、宗教、阶级等方方面面的不平等。这都使得哈拉维所构想的后人类时代里的新型压迫与反抗关系的革命前景,显得略微简单与乐观。
[6]Fran Pheasant-Kelly, “Cinematic Cyborgs,Abject Bodies: post-human hybridity in T2 and Robocop”, Film International, Vol. 9, No. 5 Nov 2001:62.
[7]Anne Allison, “Cyborg Violence: Bursting Borders and Bodies with Queer Machines”,Cultural Anthropology, Vol. 16, No. 2. May, 2001:244-249.
[8]陈亦水. 尾巴的耻辱:中国电影科幻空间的科玄思维模式与身份困境[J].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2015(6):114.[9]游飞、蔡卫. 电影新技术与后电影时代[J]. 当代电影.2000(4):66.
[10]马良. “冻结时间”特技摄影的历史发展和演变[J].影视制作. 2010(7):34-37.
[11]Ericka Hoagland and Reema Sarwal.“Introduction: Imperialism, the Third World,and Postcolonial Science Fiction”. Ericka Hoagland and Reema Sarwal ed. Science Fiction,Imperialism and the Third World. Jefferson:McFarland & Company Press. 2010:7.
[12]在现实中,所谓“异形”(alien)恰恰是辨认“非美国人”的官方词汇,美国移民局用来标识那些所有居住在美国国土内、非美国公民的外来人身份的词汇,包括外国留学生、访问学者或者教授,以及拥有永久居住权的绿卡持有者等。
[13]William Gibson. Neuromancer. New York: Ace Books Press. 1984:51.
[14]赛博朋克是80年代之后的反主流文化科幻写作主题,内容往往围绕网络、电脑、黑客等等,以展现一个反乌托邦的黑暗未来。
[15]Katie Hafner and John Markoff: Cyberpunk:outlaws and hackers on the computer frontier.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Press, 1991:9.
[16]图灵测试内容为一系列简单的问答对话,测试者需要根据被测试者的回答情况,判断后者的人类或电脑身份;问答对话结束后,当超过30%的电脑回答让被测试者相信是人类时,则电脑通过图灵测试。2014年,俄罗斯科学家研发的尤金·古斯特曼(Eugene Goostman)聊天程序成功通过了图灵测试。
[17][18][19]N. Katherine Hayles. How We Became Posthuman: 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Literature, and Informa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xiii, 49, xiv.
[20]Kevin Robins. “Cyberspace and the World We Live In”. Mike Featherstone, Roger Burrows Ed. Cyberspace/Cyberbodies/Cyberpunk:Cultures of Technological Embodiment. London:Sage Publications Ltd. Press, 1996: 135-154.
[21]戴锦华:《雪国列车》中的阶级愤怒与反抗[OL],2014-07-14,1905电影网。
[22]戴锦华. 科幻电影研究专题[OL]. 北京大学系列讲座,2015年9月—12月。
[23]戴锦华. 未来的维度[OL]. 2016-11,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的演讲,腾讯文化。
[24]Sophia Siddique Harvey, “Mapping cyborg bodies, shifting identities, and national anxieties in Cyber Wars”, Chinese Cinemas, Vol. 3, No. 1,2009: 53.
[25]林建光. 导论一[A]. 林建光、李育霖主编. 赛伯格与后人类主义[C]. 台中:台湾中兴大学出版社,2013. 8.
[26]在英文中,土地与地球的表达通常是一个单词“earth”。
[27]许荻晔. 戴锦华:现在年产几百部电影,有价值的还不及年产100部时[OL]. 澎湃新闻网. 2015-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