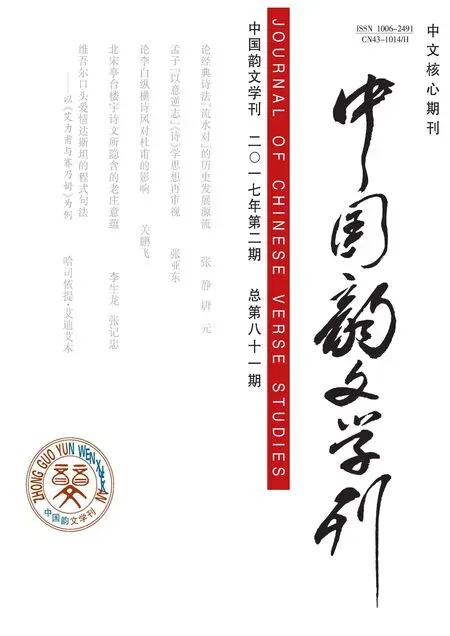“地下”唱酬
——“文革”时期的梦碧词社
杨传庆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地下”唱酬——“文革”时期的梦碧词社
杨传庆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文革”期间,以寇梦碧、陈宗枢、张牧石三人为核心的梦碧词社“地下”唱酬,以诗词慰藉苦难,抒写了动乱时代知识分子的迷茫与苦闷,展现了特定时期文人的心灵世界。在词学旨趣上,他们以梦窗、碧山为宗,推崇清季词学巨匠朱祖谋与郑文焯,创作上主张情真、意新、辞美、律严,体现了传统词学在当代的新进展。
“文革”;梦碧词社;寇梦碧;梦窗
“文革”浩劫期间,在极为恶劣的环境下,以寇梦碧(字泰逢)、陈宗枢(字机峰)、张牧石(字介庵)三人为核心的梦碧词社,“地下”唱酬,用诗词记录了时代心声,保存了历史真实,展现了特定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梦碧词社具有明确的理论诉求,以梦窗、碧山为模范,推崇清季词学巨匠朱祖谋与郑文焯,其词学宗尚延续了晚清词学之传统。词社创作上主张情真、意新、辞美、律严,这体现了传统词学在当代的新进展,也丰富了我们对当代文学批评的认识。
一
梦碧词社曾是活跃于一九四○年代的一个著名词社,关于其活动时间,寇梦碧《霜叶飞》(题斜街唤梦图)一词小序云:“天津梦碧词社尝集于癸未、戊子之间。”可知梦碧词社倡立于癸未年(一九四三),民国时期的活动结束于戊子年(一九四八)。据杨轶伦《梦碧沿革小记》一文记载,梦碧词社在四十年代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初立于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即以本年纪年命名,称癸未文社,活动分为诗词、诗钟、谜语诸种,而以词为主。翌年因进入甲申年,易名甲申文社,社务经向迪琮、姚灵犀、周维华等倡导,迅速发展,此时社长为姚灵犀。至是年秋,姚再次将社团更名为吟秋社。抗战胜利后,社团因成员离津而去,一度中断。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夏,寇梦碧重新邀集旧日社友,并于报纸征求新友,以“梦碧”之名成立社团,正式执掌社务。社址位于天津东门外南斜街天津市电业公会院内。沽上原如城南、冷枫、玉澜等社成员也先后加入梦碧词社,社事极一时之盛。
一九四八年后,梦碧词社社集式微,谢草(寇梦碧笔名)曾记云:“庚寅春,吟侣星散,侘傺无聊,时至黄家花园小坐。不期而至者有李石孙、刘云若、姚君素、张轮远、徐振五、杨轶伦诸君子。时名诗词家周学渊息庵客居津门,亦不时会晤。”可见至庚寅(一九五○)年春,词社吟侣星散。尽管此时词社名义虽不存在,但实际上居津社友仍不时会晤小集,“每集或连句,或折枝,或为商灯之戏,不过三五人而已”。小集地点有冯孝绰小不食凫斋、姜毅然十二石山堂、杨轶伦自怡悦斋、陈芳洲槐阴小筑、王伯龙摩诃室、王禹人恬静斋等。进入五十年代后,由于寇梦碧的努力,词社并未消亡,特别是张牧石、陈宗枢参与唱酬后,“二三素心人,荒江野老屋,风雅正脉,薪尽火传”,在艰难年代里延续着传统词学,培育着诗词种子,尽管影响不大,但“对于百年词史乃至千年词史之功勋劳绩可谓甚巨。”
张牧石五十年代与寇梦碧结识,具体时间未详。陈宗枢与寇相识于一九六○年秋,寇梦碧云:“忆癸未间,予倡为梦碧词社,姚衮雪先生尝荐君入社,后因故未果。庚子秋,得牧石介,一见如素识。”癸未年(一九四三)梦碧词社初立之时,姚灵犀曾推荐陈宗枢入社,但因彼时陈耽于昆曲,故未果。一九五七年,陈宗枢因演戏与张牧石相识,其时张牧石正从寇梦碧学词。后经张介绍,遂与寇相识,一见如故,引为同道。之后,寇、陈、张三人关系密切,成为“文革”动乱期间最为亲密的词友。陈宗枢回忆这段岁月记云:“时为一九六○年秋,正值米珠薪桂的艰难岁月。从此经常在晚饭后随牧石去梦碧家谈词,有时一谈便到深夜,乐而忘倦。他对词的选调、谋篇、炼字、用典、上下搭配等方面选用实例,辨析毫茫,多有前人未发的精辟议论。”“以酬唱、联句、诗钟、酒令为常课,三五日必一聚。”因政治气候恶劣,此时寇梦碧虽未张词社之名,但由于他的努力,梦碧词社实际在三人手中延续。
“文革”爆发后,文网严密,文字狱大兴。诗词创作的权利被剥夺,写作诗词可能会随时招来灾难,就如姚雪垠《咏怀杂诗》(八首)所言:“片言可能招横祸,告密风行举国喑”(其三),“牢狱牛棚随地设,是非颠倒易寻根”(其七)。在“文革”劫难之中,梦碧社员多遭戕害。如陈宗枢感慨社友姜毅然命运时云:“苍黄须臾变,怎禁得牛棚一住。”注云:“姜老自刻十二石山堂主人印,山字作△形,被诬为国民党特务,盖国民党旗恰有十二个△也。”寇梦碧也成为“专政”的对象,冯晓光在寇氏去世后所撰回忆文章中记云:
有一次谈到“文化大革命”,他感慨颇深,他说:“那真是提心吊胆呀,早上出去上班,不知晚上能否平安回家。晚上要参加‘学习’,也不知会出什么事,还能否再回家与家人见面,亲朋同事之间都不敢说心里话,怕被罗织罪名。多少次我在晚上到海河边走来走去,真想栽下去了此一生,只是想到有家庭的牵累,有妻子儿女,没有我他们怎么办……他激动地抓住我的手,眼里噙着泪水,声音颤抖地跟我说:‘晓光,真是心有余悸呀!’”
尽管面临着生命危险,寇梦碧对诗词仍是一腔衷爱,“雁口鹑网之间”,“虽担惊遭谤”,亦不改此志。他仍然在恶劣环境之下,坚持诗词创作与教学。陈宗枢记云:“有一次梦碧告诉我说,为了避免被人察觉的危险,他把若干首近作七绝诗抄录成册,每首前注上元明两朝间二三流诗人的名字,当作选录的古人诗。”曹长河在回忆文章中记拜师时寇梦碧之语云:“我至今还在学校挨整,最主要的罪名就是教年轻人学诗词,宣扬封建腐朽文化,与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所以你绝对不可对人提及咱们的师生关系,甚至不可让人知道你在学诗词。”“我今天冒着前程甚至生命的风险教你,不只是为你为我,还为了不使诗词成为绝学。”在动乱的岁月中,寇梦碧招入了曹长河、王蛰堪、王焕墉等几名弟子,教这些年轻人学习诗词写作,为梦碧词社的延续留下了种子。
寇梦碧在《琴雪斋韵语序》中说陈宗枢浩劫期间“所遇最酷”,并云:“当日怪云压地,惊泪浮天,予与君暨牧石时复觅句河干。篝灯窗隙,斯时觉人人皆可为仇为敌,只有同道相濡相呴,则槐根藕孔之间,不啻兰亭觞咏矣。”可知,灾难之下,寇、陈、张三人相濡相呴,借觞咏慰藉恐惧与无聊。陈宗枢云:“十年浩劫间,因余罹厄,不晤年余,及高潮过后,同属逍遥派,相聚乃益勤。”(《琴雪斋韵语跋》)在此期间,每逢立春、除夕、元宵、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寇、陈、张三人必相聚唱和。而日常之时,三人每周至少亦聚会四五次,“夏天几乎每晚都在海河岸边相会,春秋冬季则分别在三人家中碰头。”每年海河岸边逭暑唱酬是词社最为重要的活动,寇、陈、张外,张伯驹也偶尔参与。郁青霞(寇梦碧笔名)《诗钟》一文云:“十年浩劫,鬼蜮横行,词友罹难者甚多,艺苑荒芜,诗词更无人敢作。当时寇梦碧、陈机峰、张牧石相约每年夏晚于海河岸边小集纳凉,时作诗钟之戏,写出劫罅遣日,相濡相呴的友情。十年以来所得约千余条,曾汇为一编,名《七二钟声》。”陈宗枢后来说:“海河岸边避暑是我平生最快意最难忘的事。梦碧、牧石和我晚饭后在岸头树下席地而坐。谈词,作诗钟。远处传来的战车声,口号声喧阒不休,而我们充耳不闻。相濡相呴且觅今宵欢畅,休问明日祸福。”海河逭暑唱酬以作诗钟为主,联句诗词次之。一九八二年,寇、陈、张将“文革”时期所作诗钟选录数百首,附张伯驹和作若干首,编为一集,名为《七二钟声》。寇梦碧又拟编唱和诗词为《大河集》,惜未果。
“十年”动乱期间,寇、陈、张三人正值人生盛年,创作精力旺盛。在风雨如磐的岁月里,他们只能潜入“地下”,偷偷地创作诗词,来抛掷苦闷与压抑。诗词也成为他们遭受厄运时的精神支柱,让他们在艰难逆境中踽踽前行。
二
新中国建国后,历经沦陷与内战烽火的梦碧词侣走进了安定蓬勃的新生活,此时他们抑制不住内心的强烈激情,讴歌新政权,歌颂新成就,表达了知识分子对建设新天地的诚挚之情。如寇梦碧《东风齐着力》(毅老绘绣球花膺出国画展之选,为赋两首)(一九六二年)云:“拨雾见青旻。东风拂,百花容态全新。探芳越秀,山色借丰神。更喜蓬瀛飞盖,鲸波换、麝霭氤氲。恍金镜、五云捧出,天地同春。”陈宗枢《东风第一枝》(庆祝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发射成功)云:“看此日昂首神州,东亚巨人飞步”,“南针在手,有何畏风狂怒涛,听沸歌共唱康哉,绚日万旗红舞”。词人感受着天地同春、百业竞进的喜悦,奔放豪迈的词情溢于言表。
然而随着“文革”的爆发,梦碧词人的创作发生了巨大变化,喜悦豪迈变成了灾难之下的惊愕与迷茫。寇梦碧《八声甘州》(饯梦边词人)云:“正排空风雨怒于潮,金声裂危弦。历虫沙千劫,魂飞血舞,惊泪浮天。多少覆巢燕侣,零梦了西园。等是无家别,休唱阳关。 ”此词为张牧石饯行而作,“魂飞”“惊泪”二句写动乱之下面临摧残时的恐惧,血泪涟涟,魂飞魄散。“覆巢”以下写被批斗抄家,无家可归之苦。其《百字令》(题机峰夜坐读书图)云:“回念内库烧残,天街踏遍,金粉都尘土。边腹纵教留一笥,能贮燔灰几许。”词中用韦庄《秦妇吟》“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之语,写动乱之中对文化遗产的疯狂毁坏。“文革”期间,众多知识分子惨遭劫难,身陷囹圄。陈宗枢《木兰花慢》(辛亥重九前一日赠梦碧)词有“怪天胡此醉,任磨蝎,厄清才。叹抵死沉吟,不辞搔尽,鬓缕霜埃”,“牢落九秋肺腑,为谁青眼重开”,“新哀汩狂待理,误身边魑魅几惊猜”等句,写出了知识分子遭遇厄运,无路可走的悲郁,“魑魅惊猜”之语,也可见词人对身遭构陷的愤怒。残酷的迫害与打击让人心中惊悸,时有忧生之嗟,张牧石《鹧鸪天》(题秋风闻雁图)词上片云:“雁路冥冥响弋风,劫云一霎幻千重。惊天血影埋心碧,欺梦窗痕压眼红。”词中以雁自喻,“冥冥”写前路昏昧,难以预料;“弋风”写心中忧虑时时会受到打杀;“劫云”写世道纷乱难辨;“血影”句写眼中所见令人惊惧之惨象。寇梦碧激赏此词,以为勾画出浩劫之惨影,堪称“词史”。
政治气候翻云覆雨,面对如此劫难,词人们陷入了迷茫。寇梦碧《莺啼序》(用觉翁韵)词云:“怪湖山、装梦瞒忧,问天何意。”词人问:为何会有这样的动乱?在《金缕曲》(题斋毁石存图)词中他再次发问:“是何因、禺强一怒,猛翻鳌极。大块訇豗鸣土鼓,闪烁妖光红碧。”“禺强”为统治北海之神,“鳌极”为女娲断鳌足所立的四极天柱,为何海神发怒,翻折撑天之柱,致使人间不再安宁?张牧石《蝶恋花》(人日立春用稼轩元日立春韵)一词也反映了浩劫中的迷茫苦闷,词云:
春字纵堪簪巧胜。几见春风,肯上迎春鬓?别梦莺花休再省,疏香那抵盈盈恨。 更苦人间无处问。浅黛深螺,若个能相近?辗转芳心初计定,临汝偏又难裁准。
是词以立春簪胜之女子自喻,抒写心中的愁闷。浩劫中有众多“革命”组织,杂乱无序,各言其好。到底谁好?可以去问谁?谁来回答?可以和谁相近?由“无处问”“难裁准”之语可知词人在乱世之下无所适从的苦衷以及心底深处的迷茫。既然无法甄别,干脆逃身世外,所以张牧石在《立春前二日微雪梦碧课题拗体七律》中云:“黈纩无妨暂充耳,任他羯鼓更四挝”,成为“逍遥派”,转入“地下”,以诗词托寄心灵成为梦碧词社在动乱中慰藉自我的法宝。
“文革”期间,梦碧词社时有分题唱酬,如寇梦碧《祝英台近》(庚申除夕立春和梦窗韵),陈宗枢《祝英台近》(庚申除夜立春,和梦窗韵,梦碧兄嘱作),张牧石《桂枝香》(分拟乐府补题得赋蟹)等等。另外社集还有联句作词,联句时,由寇梦碧选词牌,定韵脚,联句之后,也由寇修改润色。这一时期参加词社联句主要是寇、陈、张三人,张伯驹、孙正刚亦偶尔为之。由于寇、陈、张三人功力相近,思路、灵感共通,所以此时联句自然顺畅。三人联句词不下数十首,可惜原稿多散佚,仅存数首,如陈宗枢词集中存留的《一丛花》(辛亥中秋,梦碧、牧石集寒斋赏月,时牧石拟迁家郊区)(一九七一年)、《雪梅香》(壬子除夕大雪,梦碧、牧石在寒斋守岁联句)(一九七二年)、《凄凉犯》(癸丑上元夜与梦碧联句和白石)(一九七三年)、《沁园春》(癸丑重阳前三日东梦碧)(一九七三年)、《破阵子》(乙卯中秋与梦碧、牧石小集赏月)(一九七五年)等。通过这些联句词,我们可以清晰看到这个“地下”词社的创作情形。如一九七二年除夕雪夜,寇梦碧、张牧石深夜至陈宗枢舍守岁,联成《雪梅香》一首:
饯残腊,凭将雪意画春踪。(机)认题香前地,依稀往梦犹同。(牧)衰鬓愁添絮花白,小楼闲话烛花红。(梦)漫料理、岁晚心期,分付琼钟。(机) 匆匆十年事,过眼沧尘,节物都空。(牧)旧颦新笑,醉来只任朦胧。(梦)幽抱犹堪托溅素,峭寒差是隔帘栊。(机)今宵尽,漏转晴云,还待东风。(梦)
“衰鬓”句感慨愁苦之中老之将至,“匆匆”句写十载岁月蹉跎,结句“漏转晴云,还待东风”则表达了未来的期盼,渴望严冬早去,春日来临。一九七三年上元夜寇梦碧至陈宗枢舍,二人联句作《凄凉犯》(和白石韵)词,下片有“应驰金吾禁,宝马蕃街,纵情游乐。那知此夕,暗灯坊万花齐荡”之语,对动乱造成的百业荒废,民生萧条充满悲慨。一九七三年秋暮,寇梦碧与陈宗枢又在陈舍联句作《凄凉犯》,词云:
怪禽格磔霜天冷,残魂画出昏月。夜风渐峭,髡枝曳影,淡燐明灭。幽宫路茀,更衰草、烟迷乱碣。锁千年、鱼膏焰弱,恨碧自沉血。 休问生前事,照乘明珠,列门金戟。石麟夜语,似依稀、戍笳呜咽。坤轴惊翻,等犹是、沧桑一瞥。下幽都、恐被卷入土伯舌。
全词充满鬼气,正如陈宗枢所言“有意说怪话”“颇有长吉诗的味道”。词的上片写霜天昏月,怪禽鸣叫,髡枝摇曳,淡绿色鬼火明灭于乱石荒草之间,词人营造了一个阴森可怖的词境,这自然是现实环境在心灵的投射。“坤轴”句写惊恐于乾坤失序,“幽都”句则想象身陷阴曹鬼帝之口。这首联句词的风格恰如寇梦碧所称可当“荒艳幽怪”(《六合小溷杂诗序》)者。而这种幽怪风格,则是对浩劫之中人妖颠倒,皂白不辨的折射,词人愤世嫉俗,故借“鬼”托情。寇梦碧、张牧石均有题《鬼趣图》诗,寇诗云:“荒荒三界人神鬼,鬼下宁知有聻存。我已沉沦鸭鸣国,羡君高卧冷枫根。”《太平广记》有云,鬼死为肃,居鸭鸣国。俗传鬼居十八层地狱,则鸭鸣国更在十八层地狱之下。诗人称“沉沦鸭鸣国”,则其遭遇之惨有甚于鬼,故而对《鬼趣图》中之鬼也心生艳羡,其语后悲愤之心可以想见。张牧石《鬼趣》二章云:“大块幽幽夜色低,青磷一点走荒畦。漫嗟胔骼多狼藉,自有头颅到处携。”“惊秋恶籁起蒿阴,夜壑敢为秋外吟。偶共老狐闲赌句,不知斜汉已横参。”其写鬼域之趣反衬的恰是人间恐怖之酷烈。
海河唱酬是梦碧词社“文革”时期的重要活动,每到夏日,寇、陈、张都到海河岸边逭暑唱酬,以诗词消磨苦难。寇梦碧《海河逭暑》其二云:“七不堪中何处去,逋逃薮在大河滨。谁知月黑灯昏夜,老树狰狞来攫人。”身为“牛鬼蛇神”,潜至大河之滨,希望缓解紧张压抑的情绪,然而月黑灯昏之际,依然惊悸不定,感到老树面目狰狞,竟然伸手攫人,可见其时惊骇之状。只有在诗词世界里,词侣们才能获得了恐怖时世之下的一丝快乐,其三云:“河干三子自成世,今夕江山属我曹。”他与陈宗枢、张牧石三人在海河边诗词消遣,虽处困厄,仍有诗兴,诗歌的力量让他们化郁愤为欢悦,故而吟出“云为车驾风为马,十万红珠照我归”之句,在这月黑灯昏之夜,十万萤火照亮归途,尽管微弱,在这片刻赶走了黑暗。
海河唱酬以诗钟为主,这是词社寄托情志的又一重要方式。郁青霞云:“十年动乱中,我与张伯驹、陈机峰、张牧石避暑河干,篝灯窗隙,时作诗钟以遣无聊之思。所作不下千余条,名《七二钟声》,其中不乏佳作。例如陈机峰‘平默’二唱云:‘飇平始觉千林瘦,蛩默还留四壁秋。’写出大乱暂时平定以后的寂寞心情。”此时所作诗钟分咏格最为出色,就内容来看分为托志与讽谕两类。托志类如:远山、鸡:“纵使烟云迷秀色,不因风雨废长鸣”;李贺、扇:“算来投溷原知己,悟到捐秋是放闲”,又“人间早已捐秋箧,天上犹能识鬼才”;樱桃、地狱:“未见摘珠来海上,偏教变相到人间”;好、薄:“唯唯诺诺堪行世,战战兢兢似履冰”。讽谕类如屈原、蝇:“怀瑜握瑾怜情质,引类呼朋乱色声”;《山海经》、猿:“读之漫道能终古,冠也依然不似人”。不难看出,这些诗钟寄托了动乱之中词人们的废弃之苦、生存之优以及对小人当道的痛愤。
梦碧词社“文革”浩劫之时的唱酬联句及诗钟之作,非为风雅,非为游戏,也不仅仅是一般的应酬唱和。陈宗枢提及遭难之后,彷徨失路,心情凄黯时寇梦碧赠《虞美人》两首,“托比兴以传深情,读之倍感亲切”。浩劫之中诸人心意相通,真情相慰,互相关怀,以诗词温暖人心。陈宗枢《祝英台近》(庚申除夜立春,和梦窗韵,梦碧兄嘱作)词中说:“脱刀俎。谁与相呴相濡。相怜共心素。哀乐纵横,氤氲大河路。任他漫衍鱼龙,烟云变幻,总难忘鸡鸣风雨。”正是这种相濡相呴的支持,词苑才不致一片荒芜,才留下了“文革”劫难之“词史”。正如刘梦芙《五四以来词坛点将录》论及陈宗枢时所云:“十年浩劫中,老辈多辍笔弗为,先生与寇翁酬唱,创作颇丰,伤时忧国,郁极悲深,胆识可称卓绝。”“北国风骚,绵延未坠,二公砥柱中流,词史宜大书一笔。”
三
谢草在《四十年代的天津梦碧词社》一文中说:
“梦碧”之命名有二:一以南宋词人吴文英梦窗,王沂孙碧山为宗。……远宗清常州词派周济标举宋四家:周邦彦、辛稼轩、吴文英、王沂孙。近承晚清四家:王鹏运、郑文焯、况夔笙、朱孝臧。门径虽仄,对五代、北宋诸家皆宗尚之。惟屏退浮滑叫嚣之作,乃有意转移词风耳。
可知,寇梦碧一九四六年重建梦碧词社时,鲜明地标举以梦窗、碧山为宗,并且学习晚清四大家的创作。寇梦碧推举吴文英,延续了周济、郑文焯、朱祖谋等人的词学思想,是针对胡适、胡云翼词论影响词坛所致粗鄙叫嚣之弊而发。至建国后,他对梦窗的尊尚并未改变,他说:
刘大杰《中国文学史》:“吴文英的咏物词,大半都是词谜。”也就是说,大半都是文字游戏。未免贬斥过甚。只因梦窗词沉晦费解,就遭此厚诬,实在有欠公允。细读一下,梦窗咏物泰半和他的身世,情遇有关。虽是托物言志的传统写法,但又有所突破。至于其情之浓挚,其志之高远,则绝去咏物之畦町。
刘大杰是与胡云翼同时,被认为词学研究“现代派”的代表人物,其《中国文学史》论及宋词亦延续胡适之论。寇泰逢驳斥刘大杰之论,为梦窗词所遭“厚诬”鸣不平。梦窗词托物言志,与其身世情遇相关,绝非文字游戏。一九六○年代,胡云翼编《宋词选》风行,褒扬苏、辛之“豪放词”,而贬低周邦彦、姜夔、吴梦窗、王沂孙等人之词。由于时势之因,处于“地下”的寇梦碧之论自然无法和胡云翼所倡相抗衡,在彼时可谓声音微弱,而自今观之,却也可见其理性一面。
寇梦碧对梦窗的推崇深刻影响了加入词社的张牧石、陈宗枢等人。张牧石曾云:“忆四十年前,余负笈京都,从先师寿石公习篆刻倚声诸艺,于四明四稿,虽经涉猎,然终未窥门径。返津后得识梦碧先生于珠光阁,始幸获闻梦窗词之奥秘,三十年交往受益尤深。”(《夕秀词跋》)张牧石少读南唐后主词,后来负笈北京,由寿鉨处涉猎梦窗(《张牧石诗词集自序》)。寿鉨词“刻意生涩,自谓近四明”(《论近代词绝句》),“火传梦窗,力求僻涩”(《读词枝语》)。而从张氏“未窥门径”之语可知其并未由寿氏得梦窗神髓,其真正得入梦窗之室乃是受寇梦碧影响。寇梦碧《琴雪斋韵语序》云:“机峰倚声,初学苏、辛,自入梦碧词社后,改宗梦窗、碧山。丽而有则,艳而有骨。”陈宗枢“于诗词一道本无师承,少时读《唐诗三百首》、胡适《词选》、《静安词》等书。似懂非懂,率尔操觚,不娴韵律。”加入梦碧词社后,受到寇梦碧影响,改学梦窗、碧山,他说:“梦碧喜评泊古今人词兼及词法,所谈多具卓识,余之为词实受其熏陶而有所进益,不啻益友而兼良师。”
远宗梦窗之外,梦碧词侣在近代词坛找到的词学导师则为郑文焯(大鹤)与朱祖谋(彊村)。陈宗枢云寇梦碧“于当代词人中崇尚彊村、大鹤,所作为邃密婉约一路。”对于大鹤之追念,寇梦碧作有《长亭怨慢》(题大鹤山人遗札)、《踏莎行》(题戴亮吉丈鹤馆得书图),张牧石作有《玲珑四犯》(得亮吉翁书告大鹤山人昔客沽上,寓紫竹林,因访遗址,感成此阕,依白石调)、《石湖仙》(亮吉翁属题鹤馆得书图)等,二人对大鹤生平及词情极为熟稔,且将自我的失意与大鹤所遭乱离绾合。一九六五年,张牧石得朱祖谋为凭吊珍妃而作《声声慢》落叶词手稿,之后广征题咏,张氏作《玉漏迟》(得彊村侍郎手书落叶词初稿,慨然赋此,并寄榆生丈沪渎),他两次题咏手稿,对彊村及其词极为尊崇,体现了在心理上对彊村词之皈依,正所谓“衍彊村、大鹤之余绪”(寇梦碧评张牧石语)。于彊村词手稿,陈宗枢曾详析云:
定稿“寒信急”,原稿作“谁与料”。按“寒信急”言秋气逼人,暗指八国联军进逼北京的急报传入内庭。比“谁与料”三字多一层意思。且在上片叙事中避去待感情的字眼。这句一改,相应地把“有神宫凄奏”的“有”字改为“又”字。又为避免重字,把首句的“寒墄”改为“颓墄”。改得确实好。又在定稿下片中“才知思怨无端”,“才知”原稿作“沉沉”。下片抒情,所以用感情字眼,“才知”比“沉沉”更能传出蛾眉婉转就死前的怨恨之情。再次,定稿中“怕夜深,流恨湘弦”,这一句当也是避免重字而改的。
陈氏将彊村手稿与晚年定稿比勘,体会到彊村词雕琢字词并非仅仅追求形式上的完美,更在于完美地传达出内心情感。彊村作词谨严不苟、细致入微的作风,无疑会对梦碧社侣的创作产生影响。
梦碧词侣崇尚梦窗,追随彊村、大鹤,尽管人少声微,但亦深得词学同道褒美。施蛰存先生《挽寇梦碧》云:“梦窗新句丽,遗箧碧山研。”黄畬称“梦碧翁一代词宗”,其《鹧鸪天》云:“金碧檀栾语最工,楼台七宝爱玲珑。”张伯驹赞美张牧石云:“学梦窗而又能自树,岂徒嗜饾饤者可同日语耶?”龙榆生称其词“婉曲厚丽,四明法乳”,并云“读《梦边词》可知七宝楼台不容碎拆也”。刘梦芙更推崇其为“二十世纪词坛梦窗词派之殿军”。诸人之论不乏溢美,但确也道出了梦碧词侣的词学趣尚。如张牧石《莺啼序》(香山登高,和梦窗丰乐楼韵):
湉湉绀波漾晚,浸明霞倒倚。豁愁眼、旷宇高寒,数峰青蹙眉际。蓦惊觉、阴晴片霎,颓云织黑笼新霁。殢秋吟枫老,江桥败叶红坠。 佳节登临,念往自苦,甚孤筇倦倚。恁禁得、百感苍凉,湿烟依约凝翠。尽霑衣、霜花遽泣,滴鲛泪、都成铅水。暗低徊,萧倅年年,暮蝉身世。 银华洗魄,玉醁湔肠,通道醉乡美。嗟病里、呜局松馆,莳艳梅圃,暂理闲娱,亦嫌多事。香羞独,骄矜群莠,沧浪清浊从休问,怅何楼、占尽人间地。风骚堕劫,千丝网结长生,映天怯看星纬。 茝芸苔焰直。苜蓿盘空,况夜阑漏迟。待盼到忧怀消歇,险梦苏醒,帝遣乘轩,碧城十二仙居,惯望尘缘轻误,幽霾如幂。霄路隔,谩欷歔,偷掩哀时袂。堪他溆雾林霏,作足凄迷,断魂万里。
此词作于“文革”之初,数易其稿,可称最能代表张氏词风者。词人香山登高,眼中毫无秋色之美,所见黑云败叶令人顿生荒寒衰飒之感。词人将知识分子面临浩劫的压抑悲郁,以及身陷幽霾,毫无未来可期的苦闷心态,写得生动入微。在声律上,张氏细入毫茫,严守梦窗字声;字句上精于锻炼,密丽新涩;景物摹写逼真梦窗,词境扑朔奇幻,可谓已入梦窗之室。
在词坛早已打破清季以来的梦窗崇拜局面下,梦碧词社仍然鲜明地推崇梦窗、碧山,表明传统词学具有顽强生命力,这当然也是特定环境下抒发情感的需要。寇梦碧云:“予生丁桑海之会,既非古人所历之境,自非古人所为之词,或病其沉晦,则亦不复计焉。”(《夕秀词自序》)其词“沉晦”之风与时代形势密切关联。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政治气候严酷,文人噤若寒蝉,表情达意必求曲晦,故而古典诗词为文人所青睐。正如“反右”时被流放,“文革”时又身陷牢狱的聂绀驽所言:“旧诗适合于表达某种情感,二十余年来,我恰有此种情感,故发而为诗。”(《散宜生诗自序》)古典诗词适合表达在高压的政治环境下郁积于心中的忧愁、苦闷、不满。所以,在随时可能因言得祸的高压时代,为了逃避文字狱,将诗词写得隐晦成为必然。这也是梦碧词社宗尚梦窗、碧山的重要现实因素。
尽管寇梦碧等以梦窗为宗,但并不画地为牢,寇氏教学“从无门户之见”。王蛰堪云:“我在未识先师之前,喜稼轩豪放风格,遣词造语,力求摹拟。今既然从先生学,误以为必须改学梦窗、碧山为正途。先生说:‘词固有婉约、豪放之分,就如同绘画中工笔与写意,书法中真楷与狂草,只有风格的不同,无优劣上下之分。无论哪种风格,不从基础入手,皆难能臻临妙境。真正善写草书者,无一不从真书入手的。而真书写不好,便欲写草书,故弄狂怪,终是自欺欺人,毫无益处。学词亦然,稼轩才气大,加之其所处时代背景,故而感慨亦深,是稼轩之为稼轩也。今人读书少,题目小,而刻意为稼轩之豪,则难免有叫嚣之嫌。我意先从真书入手,待功夫深到,再学草书、篆、隶为宜,君识得否?’”又记寇语云:“稼轩是大家风度,非读书多、感慨深,不易学到。其‘绿树听鹈鴃’‘楚天千里清秋’‘更能消几番风雨’‘千古江山’诸阕,千古绝唱,后之作者,能有几人?若其‘杯汝来前’则万万不可学,要知大家未必首首好,即如梦窗等人的一些无谓之作,亦不可学。学习前人,宜取其佳处,弃其糟粕,是为善学。”在寇氏看来,梦窗、稼轩并无优劣之分,只有风格之别,并且二人亦均有“无谓”之作,此“无谓”之作断不可学,应取其精华来学,而能当得上精华的首先就是那些感慨深沉的作品。不论何种风格,情感真挚是第一位的,所以梦碧词侣提出了情真、意新、辞美、律严的衡词主张。
张牧石《夕秀词跋》云:“先生衡词以情真、意新、辞美、律严为准则”。张氏自己论词也主张内容新、形式新、格律严。陈宗枢《北双调新水令·祝天津诗词社成立》(胡十八)也说:“任你学李杜,效苏黄,翻别谱新腔。第一是情真韵雅耐参详。说甚北胜南强,分甚宗派门墙。可怜无补费周章。”诸人都将情感内容作为词作优劣的第一要素,然后再强调文辞之美与声律至严。寇梦碧对“真”尤为注重,其《六合小溷杂诗序》云:
《六合小溷杂诗》一卷,泰半为八年沦陷、十年动乱时所作。夫灵均哀郢之赋,少陵北征之篇,不遘乱离,讵有斯作。……予避兵藕孔,匿梦槐根,间或稍志所感,得截句若干首。其中梦心篇、鬼趣图、海河逭暑诸作,荒艳幽怪,固有违诗教。然既非古人所历之境,自非古人所为之诗,此差堪自许者。
寇氏深知自己在“文革”中的诗词荒怪沉晦,有违“诗教”,但仍将其看成值得“自许”者,分外珍视,其原因就在于这些诗词立足于真实生活,是乱劫之中的心灵体验的生动记录。
不过,光有真情实感也不行,还需要用最佳的形式呈现,所以梦碧词侣又强调意新、辞美、律严。寇梦碧“反对合乎格律而无真情实感,也反对有真情实感的叫嚣”,他在教学时非常强调对词的修改。他对王蛰堪说作词要“反复推敲,认真修改”,“宁可十天作一首好的,不可一天作十首糟的。”其弟子王焕墉曾于《渊鉴类函》得一蛙部典故:龙王令斩水部中有尾者,故鼍惧诛而哭,蛤蟆无尾亦苦,鼍问其故,蛤蟆言曰:“吾今幸无尾,但恐更理会科斗时事也”。王焕墉欲用此典写“四人帮”批算旧账,颇为切意,并以之征求寇梦碧的意见。寇云:“典故虽切,‘无尾堪忧’的份量不足,将‘忧’易为‘惊’。”后王焕墉写成七绝《听蛙》:“向人犹作不平鸣,鼓吹徒劳到六更。倘或龙君追宿欠,须知无尾亦堪惊。”修改之作意新、语新,深得寇梦碧赞赏。
梦碧词社远绍梦窗、碧山,近承彊村、大鹤,因此他们对声律之谨严亦格外看重,将其作为独立的论词标准。梦碧词社在创作上恪守声律,可当施议对先生所言二十世纪词坛尊体派中之“极右派”。寇梦碧不主张盲目打破戈载《词林正韵》的分部方法,认为要有审慎的态度。张牧石则更显“顽固”,其云:
当今某些创新派的词章家们,高倡要打破旧格律缚束,要用合辙即可的新诗韵词韵,要写得人人皆懂。他们说这种创新是为了弘扬祖国传统文艺,为了普及诗词,为了使诗词长久传流下去,总之一句话,他们认为搞诗词是要“为人”。这种宏伟壮举对我这专门“为己”的顽固派来说,却永远视为畏途而不敢问津的。
(《张牧石诗词集自序》)
张牧石反对在诗词格律上的“创新”,抵制使用新诗韵词韵,坚持传统诗词在字声、韵律上的要求。
“文革”时期,词业凋零。梦碧词侣于夹缝中“地下”唱酬,以诗词为血泪之呻,展现了浩劫之下知识分子的真实心态,其创作不乏文学价值、历史价值。诚若李遇春所言:“在那个政治风暴频仍,尤其是到了‘十年浩劫’的灾难岁月里,我们的旧体诗词却迸发出了让同时代的新诗汗颜的诗歌力量。……无不在艰难时世中发出了不平之鸣,其人其诗都将在当代诗史上不可磨灭。”梦碧词社又是当代词坛典型的“尊体派”,它与清季以来的词学传统密切相连。他们的词作及词学追求体现了传统词学思想的延续与发展,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有机组成。
[1]寇梦碧.夕秀词[M].合肥:黄山书社,2009.
[2]魏新河.词林趣话[M].合肥:黄山书社,2009.
[3]寇梦碧.枫根吟语[J].学诗词.(3).
[4]谢草.四十年代的天津梦碧词社[J].天津文史丛刊,1987(7).
[5]马大勇.二十世纪诗词史论[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4.
[6]陈宗枢.琴雪斋韵语[M].自印本.
[7]陈机峰.忆梦碧[J].天津文史丛刊,1990(12).
[8]姚雪垠.无止境斋诗抄[M].姚雪垠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9]冯晓光.回忆寇梦碧先生[J].天津文史丛刊,1990(12).
[10]曹长河.春蚕到死丝方尽[J].天津文史丛刊,1990(12).
[11]郁青霞.诗钟[J].学诗词,(2).
[12]郁青霞.诗钟[J].学诗词,(创刊号).
[13]刘梦芙.二十世纪名家词述评[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6.
[14]寇梦碧.《宴清都·连理海棠》释句[J].学诗词,(3).
[15]张牧石.张牧石诗词集[M].天津大港光明印刷厂印刷.1997.
[16]陈声聪.填词要略及词评四篇[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
[17]施议对编纂.当代词综[G].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
[18]陈宗枢.彊村落叶词手稿[J].学诗词,(创刊号).
[19]聂绀驽.聂绀弩全集[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4.
[20]王蛰堪.传灯琐记[J].天津文史丛刊,1990(12).
[21]知月.著名词人金石家张牧石[J].学诗词,(3).
[22]王焕墉.回忆先师寇梦碧先生[J].天津文史丛刊,1990(12).
[23]李遇春.如何看待当代旧体诗词创作[N].文艺报.2012-1-20(2).
责任编辑 徐 炼
2016-06-27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天津市社科规划项目(编号:TJZW12-005)
杨传庆(1981— ),男,安徽六安人,文学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词学。
I206.7
A
1006-2491(2017)02-009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