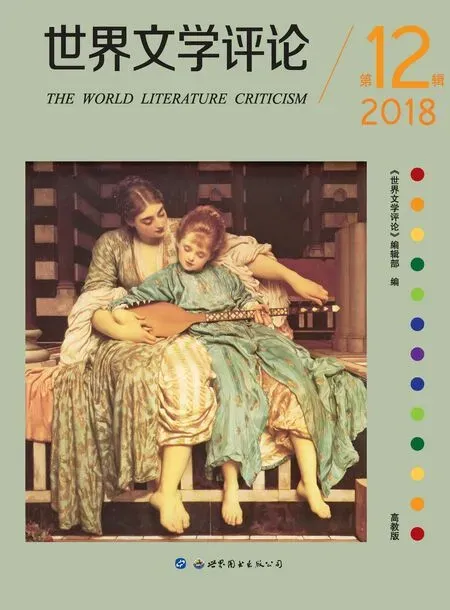细评弗罗斯特The Cocoon一诗的汉译
蒋坚霞
罗伯特·弗罗斯特(以下简称为“弗罗斯特”,1874—1963),是20世纪美国最受欢迎的诗人,曾先后4次获得普利策奖和其他各种大奖。早年曾长期居住和工作在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乡间农场,他常常以乡村自然景物和风俗人情入诗,融入个人情感和观点,最后进入哲理的境界。“他的生活环境使他的诗富有生活气息,‘像斧头和锄头那样质朴和率直’,被称为‘农民诗人’和‘桂冠诗人’”。他的诗歌形式与传统相近似,但不追求外在的美。他用日常口语作诗,描写细腻、耐人寻味。The Cocoon
是弗罗斯特的一首名诗,创作于1928年,被编入诗集《小溪西流》(West-Running Brook
)中,请看英文原诗与拙译:The Cocoon
by Robert Frost 蚕茧 蒋坚霞译1 As far as I can see this autumn haze 放眼望去这秋日的雾霭 (10)a
2 That spreading in the evening air both ways, 在傍晚以两种方式散开, (10)a
3 Makes the new moon look anything but new, 使新月看上去不是很新, (10)b
4 And pours the elm-tree meadow full of blue, 让榆树草场流泻出靛青, (10)b
5 Is all the smoke from one poor house alone… 全是破屋里冒出的炊烟…… (10)c
6 With but one chimney it can call its own; 它也只能有个烟囱冒烟; (10)c
7 So close it will not light an early light, 很隐秘它不会早早点灯, (10)d
8 Keeping its life so close and out of sight 保持着其生活隐秘无痕 (10)d
9 No one for hours set a foot outdoors 几个小时没人外出一步 (10)e
10 So much as to take care of evening chores. 去处理傍晚的农家杂务。 (10)e
11 The inmates may be lonely women-folk, 屋里也许是些孤单女人, (10)f
12 I want to tell them that with all this smoke 我想要告诉她们说她们 (10)f
13 They prudently are spinning their cocoon 在谨慎地用这炊烟作茧 (10)g
14 And anchoring it to an earth and moon 牢系在地球和月亮之间 (10)g
15 From which no winter gale can hope to blow it,— 那里朔风别指望把它吹动—— (10)h
16 Spinning their own cocoon did they but know it. 这作茧之事她们原本就懂。 (10)h
全诗意象淡雅优美、文义简洁畅达、音调柔婉动听。诗人在一个秋高气爽的傍晚,站在开阔的农场草地上,但见孤零零一间农家小屋的烟囱里冒出浅白色的炊烟,与空中的薄雾融合弥散升腾,像蚕吐丝结茧一样,此时天色尚明,呈半透明状,天空新月朦胧初现,静谧安详,地上榆树和草地泛着淡蓝色光彩,影影绰绰,小屋里尚未点灯,所有景物被一层薄纱般浅白色的清朗雾霭笼罩,犹如一幅巨大的印象派优美画作定格在天地之间,令人沉醉。诗人觉得这一人间大美的创造者正是屋里烧火做饭的女人们,她们用炊烟做成一个硕大无朋的蚕茧,与天地牢固相连,即使冬天里凛冽的狂风也休想把它吹动。诗人本想将此事告诉屋里的女人们,但转而又想,这作茧造美之事原本就是她们的自觉行为,自己何必自作聪明、多此一举呢?
现在简要地从三个方面来欣赏这首诗的结构美。其一,从外形音韵看,全诗共16行,前14行每行各为10音节,双行叠韵,是典型的十四行诗形式,最后两行各为11音节,同样叠韵,整齐有致,音调柔美;其二,从词语句式看,使用日常简单的口语和句式,明白晓畅,亲切感人;其三,从意蕴内涵看,前10行是对空旷疏朗淡雅的场景的客观描述,第11行至第14行是触景生情所产生的神奇浪漫的联想,可以说,把秋日傍晚的景物与辽阔天地比喻成一个巨大的蚕茧,也许是世界诗歌史上的第一回,最后2行进入哲理的境界:点出小屋里女人们作茧造美是有意识的自觉行为,更令人回味无穷。读着弗罗斯特原诗是一件多么赏心悦目的精神享受啊!
再来看弗罗斯特此诗的曹明伦先生的汉译:
茧 曹明伦译
1 就我所见,这秋日傍晚的阴霾,
2 这正在以两种方式蔓延的阴霾,
3 这使新月显得不像新月的迷雾,
4 这使榆树变成蓝草颜色的迷雾,
5 全都是那座破房子冒出的浓烟……
6 仿佛只有烟囱是那房子的体现;
7 它那么隐蔽所以不会早早点灯,
8 它让屋里的生计完全避开世人
9 甚至一连数小时也没有人出屋
10 来料理一下傍晚时的农家杂务。
11 屋里也许只有喜欢孤独的女人。
12 她们在用浓烟,我想告诉她们
13 小心谨慎地作着她们自己的茧,
14 并把茧往另一地球或月球上搬,
15 那儿不会有冬日里的风凄雨苦——
16 但她们该知道这是在作茧自缚。
读罢曹译,可以看出译者的翻译存在诸多问题:由于用一连串的“阴霾”“迷雾”和“浓烟”等词语,从一开始就把原诗生动形象的比喻和优美淡雅的意境搅扰得面目全非。事实上,曹译的严重错误和缺失在很多方面是相互交叉的。本文力求避免以主观浮泛印象进行评论,而是采用20世纪美国“新批评派(New Criticism )”主将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1906-1994)的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亦即“死抠原文”方式,从原诗本体入手,严谨、准确、精细而客观地分析指出曹译种种谬误之所在。
一、原诗优美意象被歪曲被破坏
原诗前5行中的this autumn haze,in the evening,the new moon,the elm-tree meadow,the smoke,one poor house等词语,均是诗歌意象的组合元素,而meadow是此诗的中心词或“诗眼”,是诗人有感而发的场景依托,同时也是诗人着力表达和渲染的主要对象,在名词词组the elm-tree meadow中,elm-tree(“榆树”)是修饰meadow(“草地”)的定语,意思是“长着榆树的草地”。在欣赏和翻译诗歌时,必须对中心词予以相当的注意。然而曹译中压根儿见不到meadow(“草地”)的踪影,其忠实性大打折扣。这种“遇到自己读不懂的就‘跳’过去,遇到不好译的就做‘减码处理’”的“权宜性叛逆”,自然不可能“做到余光中先生所说的对source language之体贴入微和对target language 之运用自如”,所以“倒不如不译!”在翻译前5行时,曹先生采用定语从句的译法将一个haze译为使读者眼花缭乱、连续两个“阴霾”和两个“迷雾”,再加上第5行最后一个“浓烟”,曹译的场景被阴霾笼罩、被浓烟充斥,而“新月”呀,“榆树”呀,“蓝草”呀,“破房子”呀,等等,总共6个“的的不休”定语句式,尽管“的”字6次重复叠加,却说不清这些具体的景物到底在什么地方:是在海边呢,还是在山里?抑或是在湖区?读者不禁要问:诗人的表述会是这么啰嗦而不明朗吗?知名度如此之高的美国大诗人为什么要把“阴霾”“迷雾”“浓烟”这些颜色深浓的词语用于色白或半透明的“蚕茧”所存在的环境中呢?这样的诗会是优美的好诗吗?已故著名诗人艾青说:“诗比其他文学式样更需要明朗性、简洁性、形象性。”以此判断,曹译因漏译原诗明确交代的表示场景和地点的重要词语meadow而变得晦涩不明,原诗的优美意象在曹译中因缺少场景依托变得阴霾浓烟漫天飞舞,而使原诗面目全非、诗意全无!
原诗第一行最末haze一词,是诗人营造的一种朦胧而美妙的意境,更是诗人将这一意境想象成The Cocoon(“蚕茧”)的主要依据。诗人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观望草地上的农家小屋,小屋升腾的袅袅炊烟令诗人看到了屋内的生机。因此,作为全诗的第一个意象,如何准确理解与翻译haze一词对于全诗的意境会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haze意为a small amount of mist,smoke,etc.in the air; a sort of light mist or smoke in the air,强调“量少(a small amount)”和“稀薄(light)”,指的就是“薄雾”和“轻烟”。因此haze在原诗中的使用精到准确,真实而客观地反映了晴朗秋日黄昏时分乡间农场空旷草地的上空轻薄雾霭疏朗漂浮的天气状况,因而下文中的the new moon(“新月”)虽被haze(“雾霭”)遮蔽,但因其密度不大,还能隐约可见,只不过“不是很新”而已,就像一条蚕刚作了一个薄薄的蚕茧,在半透明的状态下,人们还看得见蚕的头部和身子在里面摆动吐丝,影影绰绰。可见诗人对天象的观察多么细致入微;对景物细节的捕捉多么准确无误!而译者曹先生因缺乏在这一自然美景中的亲身经历而对眼前景物毫无感知,读不懂原诗也就是必然的了。
曹先生曾发表专文指出:在译此诗前5行时,用的是定语从句的翻译方法,“在实践中将定语从句的翻译方法坚持用于诗歌翻译可以取得理想的效果”,既能“完全保留原诗的形式”,又能做到“原文中的定语从句在原文中依然是定语,而且译文文从字顺,主次分明,语气贯通,其语义和风格亦不悖原文”。但笔者认为,曹先生不懂英语和汉语一个明显的差别,那就是英语重“形合(hypotaxis)”,汉语重“意合(parataxis)”,若在完全读不懂原诗的情况下,采用定语从句的译法来翻译英诗,要想译出“其语义和风格不悖原文”的上乘之作,无异于痴人说梦。
二、急功近利的胡译乱译
曹先生在没有下功夫精读原诗文本和正确理解原诗意蕴的情况下,对其译诗自我感觉良好,并且首先批评有些人“对汉语尚不能运用自如”,他本人只知道“用定语从句的翻译方法翻译诗歌会取得理想效果”,而他头脑中又毫无英语重“形合(hypo-taxis)”汉语重“意合(parataxis)的差别概念,自我感觉良好地把原诗中一个定语从句变成了4个汉语定语结构,而且还动用了8个汉字(即两个“阴霾”与两个“迷雾”)去译一个单音节的haze,但是这种臃肿呆板颇生歧义的译诗,与简洁易明亲切感人充满诗歌情调的原诗,无论在形式风格上还是在意蕴情味上,两者实在相去甚远!haze被拆译成“阴霾”和“迷雾”是翻译的硬伤,原诗意象被损伤得惨不忍睹。“阴霾”与“迷雾”都具有量大浓密之意,与haze的“量少”和“疏朗”有很大差别;而汉语中,“阴霾”与“迷雾”的语意并不等同,“阴霾”意谓天阴沉而有雾气,是一个用以描绘阴雨天气的词语,明显具有贬义,而且中国人见到这个词会产生“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的联想。另外,常识告诉我们,出现阴霾天气是看不见月亮的。而“迷雾”乃“浓雾”“大雾”之意,“迷雾”过后通常是晴天,“迷雾”出现时眼前景物都难以看见,天上的月亮就更看不见了。原诗明明说的是看得见月亮(只是“不很新”),而曹译提供的天气条件却偏偏是看不见月亮,既然天上“阴霾”遮蔽,欲雨不雨,不见新月,地上“迷雾”笼罩,“浓烟”弥漫,看不见“农舍”“榆树”和“草地”,那么这首诗还有什么美可言?又怎么能与诗题“茧”扯得上边?曹译显然与原诗标题The Cocoon
(“茧”)所表述的意境风马牛不相及!这些枝蔓横生乱成一团的文字组合能说是“语义不悖原文”的忠实而理想的译文吗?这是由于译者不了解英汉两种语言文字有着“形合”与“意合”特征差异而又执意用汉语定语结构翻译英语定语从句惹出的祸。原诗第2行首词That与其前后词语构成是英语典型重“形合”的例子,下面举出一个汉语重“意合”的例子:“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李清照:《夏日绝句》)”,第3句和对4句可改为“至今思恋不肯过江东的项羽”,但改了后的句子不是汉语固有重“意合”的说法,当然更不是简洁优美的诗歌语言了。原诗第5行the smoke from one poor house 被译为“那座破房子冒出的浓烟”,而第12行中的with all this smoke被译为“她们在用浓烟”,原诗场景的浓度和暗度被一再加深,这只能说明曹先生对英文原诗优美画面缺乏敏感的心灵和鉴赏的能力。原诗描述的真实场景是,在薄雾朦胧的月色之中,“榆树草场泛着浅蓝色光彩”,“小屋里冒出袅袅炊烟”,而傍晚时分农家女烧火做饭时屋里冒出的炊烟,英美人说smoke,曹先生说成“浓烟”,给译文读者留下“浓烟滚滚火光冲天”的极不美好的印象,加上前面又有“阴霾”和“迷雾”的反复出现,于是原诗清丽优雅的诗歌意象和给予原诗读者赏心愉悦的盎然情趣在曹译中消失殆尽。
原诗第6行With but one chimney it can call its own被曹先生译为“仿佛只有烟囱是那房子的体现”也成问题,原句说得确切肯定而不含糊,译句增添原句没有的as if而译为“仿佛”,很不忠实,此其一;其二,With but one chimney it can call its own的真实意思是“那房子只有一个烟囱”,动词短语call one's own是口语中的一种习惯用法,是possess或have之意,就这么简单!如:He is so poor that he doesn't a good suit of clothes to call his own是“他穷得连一套(称得上是自己的)像样的衣服也没有”。如果英语学得不扎实,只看大意就胡乱猜想,那么又怎么能够把诗译好呢?
曹先生引用翻译家傅雷的话告诫青年译者:“要以艺术修养为根本,无敏感之心灵,无热烈之同情,无适当之鉴赏能力,无相当之社会经验,无充分之常识(即所谓杂学),势难彻底理解原作,即或理解,亦未必能深切领悟”;同时他也反复强调,翻译中凡遇不知其所以然的问题,一定要查阅书本,探赜索隐,切不可望文生义,率尔操觚。”上述引文其实恰好是针对着曹先生本人说的。再看一例:曹译曲解原诗第14行And anchoring it to an earth and moon的意思,译为“并把茧往另一地球或月球上搬”,谬误实在太多太严重。anchor是一个比较常用的词,作名词是“(船)锚”,作动词是“抛锚(使船停稳)”,此处是“固定(不动)”“系牢”,即fix firmly。曹先生草率理解为截然相反的move,即“搬”或“搬动”,而“搬”的对象往往是重物,需要费大力才可将之移位,可是“茧”是由重量可以忽略不计的细丝构成,把一个很轻的“茧”挪到另一位置,中国人绝不说“搬”!原诗所说的Cocoon,由炊烟和雾霭形成,悬挂于地球和月球之间,虽硕大无朋,却是轻盈之物,即使想要挪动其位置,也不能用一个“搬”字!还有an和another,两者意思迥异,为何an earth成了“另一地球”?这“另一地球”又是什么地球?它与我们所在的地球有何不同?又,and分明是并列连词,为何要把它理解为选择连词or而译为“或”?再追问一下:这“另一地球”与“月球”又是什么关系?
原诗第15行From which no winter gale can hope to blow it是英语否定转移结构,其真实语义是(the)winter gale can not hope to blow it,也就是说“有风”,只不过“风不能指望把它吹动”;而曹译是“不会有(冬日里的)风”,是“没风”,毫无疑问,曹译是误译。否定的转移是英语中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如:He didn't run fast enough to catch the bus(他昨晚跑得不够快,没赶上那辆巴士),意思是:不是说他没跑,而是说他昨晚跑还是跑了,只是跑得不够快,没赶上那辆巴士。“风凄雨苦”是生造成语,是想跟“作茧自缚”押韵生造而成,无论如何,这一与恶劣天气产生联想的怪异说法,还给人以境况悲惨凄凉、阴森森、惨兮兮的感觉,与原诗给予读者的审美愉悦截然相反;gale只是“风”而不含“雨(rain)”,曹译擅自引入“雨”的具象,很不明智,试想:倘若“茧”被雨淋透了,变得湿淋淋软溻溻的,那么还有什么美感可言?原诗中由“茧”所唤起的优美意象还能够存在吗?
原诗第16行Spinning their own cocoon did they but know it,被望文生义地译为“但她们该知道这是在作茧自缚”,既然是“作茧自缚”了,就是已经受困被茧包住了,那么曹译第14行“女人们”是如何能够从“茧”中出来,再去“搬”“自己的茧”的呢?而且还偏要“往另一地球或月球上搬”呢?四字成语“作茧自缚”是“看见别人遭受灾祸反而高兴”,可是原诗中那里存有这样的阴暗心理呢?这里还碰到了一个跨文化交际中十分可笑的问题:怎么能够一见到英语单词cocoon就跟汉语成语“作茧自缚”扯到了一起呢?就算是在一首汉语诗歌中看见有一个“茧”字,也不能轻率地作这样的联想。总之,译者不了解原诗语言所蕴含的文化特色,不熟悉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乡间的地理生态环境与气候变化状况,如果只凭主观想象,天马行空,粗制滥造,再加上“语文造诣甚浅,表达能力不足”,那么翻译时不错误百出才怪!曹译“但她们该知道这是在作茧自缚”,更糟糕的是给人以责备、嘲弄和有幸灾乐祸的感觉,因为还有四字成语“作茧自缚”是“别人遭到灾祸时,自己心里高兴”,而“该”是“应该”“活该”,所以整句曹译带有责备、嘲弄、教训和幸灾乐祸的口吻,心理恶念极其阴暗!读了这样的拙劣的译诗,译文读者真的会感到疑惑:诗人的格调怎么如此不高?这真是天大的冤枉。因为原句给予原文读者的感受是充满了赞叹和欣赏,还含有自愧不如之意!
三、译诗有悖于原诗的语言风格
原诗是不折不扣的诗歌艺术精品,意象清晰明朗,语言寻常如话,原诗中即使有极个别相同词语,也是或者因为语言习惯使然(如As far as中的两个as),或者是写作时的恰当表达(如the new moon…new中的两个new),但都是地道而漂亮的英语,毫无矫揉造作之感;曹译却不然,曹译语言呆板繁赘,原诗语言风格在曹译中完全走样。原诗巧于变化的前5行,在曹译中变成了由5个“的”字构成的雷同定语结构;除“的的不休”和“这这不断”外,曹译中类似的雷同词语同样十分惊人,如前述一个haze被译为两个“阴霾”, 两个“迷雾”,还有两个“使”字,在区区短小的5行曹译中,雷同词语竟然达到15个(次)之多,既重复啰嗦,又单调乏味,特别是4个“这”字和6个“的”字,齐刷刷竖行直着排印下来,非常刺耳扎眼,严重地破坏了原诗简洁凝练巧于变化的语言风格,同时也极大地违背了中国文人惜墨如金用字尽量避免重复的写作传统。
原诗第4行And pours the elm-tree meadow full of blue,曹译为“这使榆树变成蓝草颜色的迷雾”,意思怪谲,令人费解。前已指出,汉语“迷雾”就是“浓(厚的)雾”,迷雾弥漫的阴霾天气,能见度很差,十步开外的景物都难以看见,更别说看得见“榆树”颜色的变化了!就算看得见“榆树” 颜色的变化,在同样背景条件下,能够改变“榆树”颜色的“迷雾”,怎么改变不了“蓝草颜色”呢?“蓝草颜色”是什么颜色呢?“榆树”原本又是什么颜色呢?为什么“榆树” 变成“蓝草颜色”,而“蓝草颜色”不变成“榆树”颜色呢?必须指出,“蓝草” 纯属生造,何为“蓝草”?有谁知晓?自然界就压根儿不存在这种植物,人们只说“青草”“绿草”,当然“兰草”是有的,但“蓝”与“兰”音同义不同,写法也不一样。“兰草”的一种草本植物,叶子披针形,边缘有锯齿,可入中药;“兰草”也指“兰花”,丛生草本植物,叶子细长,花味清香,供观赏,也称“兰花草”,如著名歌唱家郁钧剑唱过根据胡适早年白话诗《希望》谱曲的“我从山中来,带来兰花草”。由于自然界中根本没有“蓝草”,所以《现代汉语词典》不予收录。而所谓“蓝草颜色”的说法也怪异别扭,因为“蓝草”本身就够怪的了。人们只说“红花”“绿草”“蓝天”“白云”什么的,哪里听过什么“红花颜色”“绿叶颜色”“蓝天颜色”“白云颜色”这些古里怪气、添油加醋的说法呢?诗歌是语言的艺术,更加讲究修辞,讲究语言凝练简洁、文辞顺畅、意思明朗。诗歌的永恒的美,绝不是靠堆砌华而不实的辞藻,玩弄似通非通的文字伎俩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译诗和原诗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与对照。
四、译诗对原诗形式的模拟并不理想
原诗形式颇为讲究,总共16行,前14行是十四行诗(sonnet)形式,每行10音节;最后的第15、16 行两行各为11音节,全诗总计162音节。曹译对原诗的模拟虽比较接近,但并不理想,曹译除第1行为12音节外,其余15行每行均为13音节,也算整齐,但曹译总计197个汉字,比原诗和拙译多35个音节/汉字,大大超过一首七言律诗的用字容量,而这多出的字数表现为大量的相同字词的重复,如:10个“的”,5个“这”,3个“是”,3个“在”,3个“一”,2个“使”,2个“阴霾”,2个“迷雾”,2个“浓烟”,2个“新月”,等等。众所周知,诗歌语言贵在精辟。巴尔扎克说过:“艺术就是用尽可能少的事物来表现尽可能多的思想”;简练的言语风格,也是我国历代文论家极力推崇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仪对》中指出:“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可见,古今中外都认同一个真理:简洁明朗是好的诗文不可缺少的美,名家高手在写作时无不惜墨如金。译诗要想接近于原诗,忠实、准确、精练地使用词语相当重要。
曹译语言曲解原意,闹出了世界上不存在的怪诞的玩意儿:“蓝草颜色(第4行)”,“另一地球”(第14行);使用了粗俗平庸、佶屈聱牙、词不达意的说法:“这正在(第2行)”,“作着她们自己的茧(第13行)”,“冬日里的风凄雨苦(第15行)”。在韵脚方面,原诗双行叠韵,韵脚巧于变化,如原诗前4行按照a/ a/ b/ b押韵,即第2行的ways与第1行的haze 押韵,第4行的blue与第3行的new押韵,都是用不同的词押韵;而曹译押韵重复而呆板:第2行的“阴霾”与第1行的“阴霾”押韵,第4行 的“迷雾”与第3行的“迷雾”押韵。所有这些都表明:曹译语言既缺乏斟酌推敲,又没有精心打磨,根本无法与原诗语言的形式与意蕴媲美,原诗充满诗意的本质性的东西在曹译中损伤殆尽。
结 语
诗歌翻译质量没有最高,只有更高。评判译诗的质量要客观,不能只凭主观浮泛印象或慑于译者威名妄下结论,而是必须紧扣原文,提供大量可靠事实阐明理由,同时评判的标准恶尺度要一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只有通过比较才能鉴别译诗质量的优劣。时代在前进,人们的洞察力和识别力在迅速提高,更多没有知名度却有真才实学的人的言论和观点会在自由民主的学术氛围中得以发表,所有名家都必须以新的知识修改旧的成见,永远被时代考验,永远接受新的甄别和新的评价。
在结束本文的时候,笔者不由得记起了著名诗人兼翻译家余光中先生的经验之谈:“读译诗……通常的经验是一肚子闷气,可叹又一篇佳作甚至杰作,平白给人糟蹋掉了。”著名诗人北岛在批评诗歌翻译家李笠时说:“我为诗歌翻译界感到担忧。与戴望舒、冯至和陈敬容这样的老前辈相比,目前的翻译水平是否非但没有进步,反而大大落后了?……而如今,眼见着一本本错误百出、佶屈聱牙的译诗集立于书架上,就无人为此汗颜吗?”上述言论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