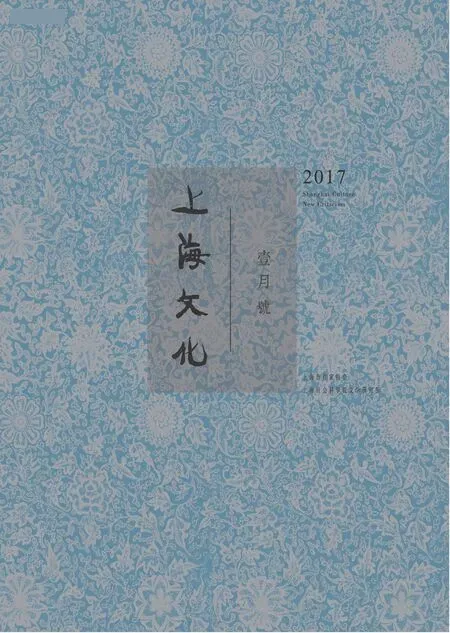流血与流放:奥德修斯的最后之旅
纪 盛
流血与流放:奥德修斯的最后之旅
纪 盛
一
《奥德赛》讲述奥德修斯历经磨难成功归乡的故事,整个过程起于诸神的议允,终于众神的调停。史诗在神与人的和解中落下帷幕,又两次以预言的形式交代主人公奥德修斯的结局。此预言共十七行,字里行间耐人寻味,诸多细节值得探讨。本文将从这段诗文出发,尝试解释奥德修斯的“最后之旅”。
史诗提及,重获王权的奥德修斯没有就此回归平静的生活,他还要去往远方,履行并实现盲先知忒瑞西阿斯在冥府中对他所做的预言(《奥》 11.121-137);奥德修斯归乡与妻子佩涅洛佩团圆后,又一字不差地复述了这一预言(《奥》 23.268-284)。这段诗文在诗中重复出现两次,足见其重要性。且以总二十四卷的史诗结构来看,其布局并非随意为之,首次出现在上半部的倒数第二卷(卷11),再次则在下半部的倒数第二卷(卷23)出现。
预言诗文如下:
……
你要出游离家,背一把造型美观的船桨,(11.121)
直到抵达一个地方,那里的人们
不知道大海,吃用的食物里不搁咸盐,
也从未见过涂抹了枣红色的船只和
造型美观的船桨,那是海船飞行的翅膀。(11.125)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明显的标志,你不会错过。
当有一位路人与你相遇于道途,
称你健壮的肩头扛着一把扬谷的簸铲,
那时你要将造型美观的船桨插入地里,
给王者波塞冬准备美好的祭品, (11.130)
一头公羊、一头公牛、和一头(暴躁的)公猪,
然后动身回家,举办丰盛的百牲大祭,
给执掌广阔天空的全体永生的神明,
一个个按照次序,不能落下。你的死亡将会从海上降临(你的死亡将远离海洋),
平静地,让你在安宁之中(11.135)
享受高龄,了却残年。你的人民
将会昌盛。……
这段诗文耐人寻味的疑问颇多。比如,预言中提到奥德修斯的死亡方式(《奥》11.134;23.281),έξàλòς究竟是“死亡将远离大海”,还是“死亡将从海上降临”,历来存在理解的分歧。如拉蒂莫尔(Richmond Lattimore)的译文倾向于前者:“死亡将从海上降临”(death will come to you from the sea),菲格尔斯(Robert Fagles)的译文取后者:“死亡将远离大海”(your own death will…far from the sea…),而曼德尔鲍姆 (Allen Mandelbaum)则译作:“将不会死于海上” (you will not die at sea)。国内两个流行的中译本也存不同译法,王焕生先生译作“死亡将从海上降临”,陈中梅先生的译本则是“死亡将远离海洋”。学者们多主张“从海上降临”一说,认为这样“合乎逻辑”。我认为,从某种程度而言,这一模棱两可的说辞恰恰符合预言少讲逻辑的特点,不仅凸显了预言的神秘感,也呼应了读者在阅读奥德修斯的最后旅程时常常感到的困惑。奥德修斯为什么要再次远行(流亡)?为什么要携带船桨(簸铲)并向神明献上不寻常的祭品(牛、羊、猪)?史诗11和23卷重复出现此预言又有何用意?
二
希腊人在讲述英雄故事时似乎总离不开流亡的母题。要理解奥德修斯的这次离家,我们可以先来看两个相类似的英雄故事。在忒拜王族的悲剧故事里,俄狄浦斯因为犯下“罪业”(弑父娶母)给忒拜城邦带来了灾难,身为国王的他为解决城邦的疫情(nosos)便流放了自己。同样的情节发生在阿伽门农家族的故事中,其子奥瑞斯忒斯为父报仇,杀死了母亲克吕泰莫涅斯特拉,因而受到了神的折磨(欧里庇得斯, 《奥瑞斯忒斯》 582),变得既“疯” (埃斯库罗斯, 《奠酒人》 1056)又“罪”,于是逃离家乡,到处流亡。俄狄浦斯和奥瑞斯忒斯为何要这么做?俄狄浦斯的叔父克瑞昂有过明确的解释:“流放或流血”,乃是“净罪”的方式(索福克勒斯, 《俄狄浦斯王》 100)。
因杀人而流亡的主题在《伊利亚特》中多有提及,这里仅举五例。特勒波勒摩斯打死了自己的舅爷,亡命罗德斯岛(《伊》 2.661-667);墨冬杀死了继母的兄弟,远离故乡(《伊》 13.694-697);吕克弗戎原居伯罗奔尼撒以南的库塞拉岛,因欠下人命投奔萨拉米斯的埃阿斯(《伊》 15.430-433);厄培勾斯因杀了一位亲兄弟,逃至佩琉斯的领地(《伊》 16.570-574);帕特洛克罗斯的亡魂也回忆了他与阿喀琉斯的相遇,因他误杀安菲达玛斯之子而逃离原乡(《伊》 23.85-89)。《奥德赛》中也有三处流亡故事,分别出现在奥德修斯对幻化成牧羊童的雅典娜所编的故事(《奥》 13.256-275)、牧猪奴对乔装的奥德修斯诉说的埃托利亚“骗子”的来历(《奥》 14.379-381)、先知后裔特奥克吕墨诺斯对外出寻父的特勒马科斯介绍自己的身世(《奥》 15.271-275)。所有这些流亡事件的相同之处,都是当事人杀人犯罪之后背井离乡。
此外还有一个不易察觉的共同点,《伊利亚特》中的这几位流亡英雄统统战死沙场,暴毙而亡,无一幸免。特勒波勒摩斯被宙斯之子萨尔佩冬的长枪刺穿颈部而亡(《伊》 5.628-669);墨冬被阿芙洛蒂忒之子埃涅阿斯所杀(《伊》 15.332);吕克弗戎、厄培勾斯和帕特洛克罗斯三人均不敌特洛伊王子赫克托尔(《伊》 15.430-435;16.571-580;16.786)。《奥德赛》中的三个“流亡”故事稍有不同,此三处都是诗中人物的说辞,奥德修斯编故事欺骗女神,牧猪奴转述“骗子”的自述,先知后裔(注意其特殊的身份)不愿透露真相所做的自我介绍,故此三处均非真实发生的流亡事件。换言之,两部荷马诗中,除奥德修斯以外的流亡英雄避罪保身的行为最终均以失败告终。
奥瑞斯忒斯弑母后逃离故土,后经阿波罗以血为其净罪,才得以返回家园恢复正常的生活。美狄亚为助伊阿宋盗取金羊毛,杀死年幼的弟弟,逃往异乡,其姑母基尔克(即《奥德赛》中指引奥德修斯去到冥府的魔女)以同样的方式(以血洗血)为伊阿宋和美狄亚两人净罪(阿波罗尼俄斯, 《阿尔戈英雄纪》 4.699-709)。由此可见,以血净罪十分困难,这一方式只由极少数的特殊群体所掌握。
《伊利亚特》中还有一段题外话,同样隐藏着一个流亡英雄故事,值得注意。这段故事的主角是伯勒洛丰(《伊》 6.119-236)。特洛伊方的盟友格劳科斯,祖辈原居柯林斯,与阿尔戈斯关系甚密,后来流亡至小亚的吕西亚。格劳科斯与迈锡尼联军中的阿尔戈斯将领狄奥墨德斯在战场上“拉家常”,因祖辈曾经交好,遂按照习俗互赠礼物,结果格劳科斯的价值百头牛的金甲对换了狄奥墨德斯的价值九头牛的铜衣。格劳科斯在这时提到祖父伯勒洛丰从希腊转辗去到吕西亚的往事,原来“他遭到众神的憎恨,独自流落于阿雷俄斯平原”(《伊》6.201)。荷马诗中并未说明伯勒洛丰为何“遭到众神憎恨”。依据阿波罗多洛斯后来的记载(《书库》 1.9.3,2.3.2),伯勒洛丰杀死了自己的兄弟,从柯林斯流亡至阿尔戈斯,当时的阿尔戈斯王无法为伯勒洛丰净罪——就连他自家的女儿们犯了渎神之罪,也得经由外乡先知才能治愈。于是,阿尔戈斯王将伯勒洛丰送往吕西亚,吕西亚王又将伯勒洛丰安置在荷马诗中提到的“阿雷俄斯平原”。这里说的阿雷俄斯平原地处克珊托斯河(《伊》 6.172)的入海口。该河位于吕西亚境内,向南流入地中海。
流亡英雄伯勒洛丰被安置在阿雷俄斯平原,这个细节值得关注,因为,还有另一则流亡故事也把流亡的终点定在河流的冲积平原。这是阿尔戈斯英雄阿尔科迈昂的故事(阿波罗多洛斯, 《书库》 3.7.5)。阿尔科迈昂乃是在《七将攻忒拜》中出过场的安菲阿勒俄斯之子,传说父亲赴死前曾嘱咐阿尔科迈昂为自己复仇,杀死不忠的妻子。阿尔科迈昂成年后弑母复仇,并因此而流亡至阿卡迪亚地区。但他的“病”始终没有好转,于是前往德尔斐求神谕。女祭司指点他,要避开复仇女神的追捕,必须去到某个“新生的地方”(the newest land,保萨尼阿斯, 《希腊道里志》 8.24.8),那里尚未被他母亲的鲜血玷污。于是他去到希腊境内的阿刻罗斯河边,在河中新隆起的一处小滩上定居下来。在这个神话故事里,阿刻罗斯河中新隆起的滩涂,与克珊托斯河的阿雷俄斯平原一样,都是“新生的”土地。
希腊神话中的流亡故事可以理解为某种净罪仪式,主要表现为从城邦内部驱逐某个罪人,旨在恢复洁净,稳定共同体秩序
从德尔斐女祭司的话中不难看出,英雄的流亡行为无不是要避开复仇女神厄里尼俄斯。在古希腊早期思想中,厄里尼俄斯属于某种有翼的“灵”(库瑞斯),库瑞斯即是疾病精灵的总称。厄里尼俄斯与血的关系尤为紧密,这是因为她们诞生于天神之血(赫西俄德, 《神谱》 185),因而称得上“嗜血如命”。不义受害者的血会玷污大地,比如奥瑞斯忒斯所杀的母亲的血让大地变得潮湿(埃斯库罗斯, 《复仇神》 261-263),并呼唤着复仇(埃斯库罗斯, 《奠酒人》 400-404)。同样,该隐杀死其兄弟后,神说道:“你兄弟的血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你必从这地受诅咒”(《创》 4.10-11)。在希腊古人的思想里,不义受死者的鲜血所流淌的地方必有复仇女神厄里倪俄斯的身影出现。这也是为什么阿尔科迈昂一开始的流亡没有使“病”好转。从某种程度而言,流亡不是别的,就是摆脱厄里倪俄斯猎犬般的追袭(埃斯库罗斯, 《奠酒人》 1054)。
同样,奥德修斯返回伊塔卡皇宫后的血腥杀戮污染了大地。如果说觊觎王位的求婚人被杀是罪有因得的话,那么,无辜者的死就是奥德修斯的罪,比如预言者勒奥德斯,他对求婚人的种种恶行感到不满(《奥》 21.310-329),却同样惨遭斩首(《奥》22.310-329)。若不是儿子的劝阻救下歌人菲尼奥斯(《奥》 22.356),奥德修斯或将杀死更多的无辜者。因此,为了躲避厄里倪俄斯的追捕,奥德修斯不得不再次离开家乡,走上流亡之路。在诸多古代文明中,杀人者必遭被害人的血亲复仇,罗马法律明文写着“杀人者,死” (《十二铜表法》八表二十四项),犹太人律法则更明确,“报血仇者必亲自杀死凶手” (《民数记》 35:19)。无时无刻不在思考人神关系的希腊古人更是将这个问题纳入神圣的维度,犯罪者必触怒神明,罪人流亡,在神话叙事里被说成是为了摆脱复仇女神的追捕,以便从病态中恢复。流亡行为还涉及城邦与个人的两种思考角度。从城邦角度看,谋杀和血亲复仇必将扰乱城邦共同体的秩序,罪人流亡有助于保持相对的安定。作为流亡者的罪人则有不同的命运归宿:多数流亡者暴毙而亡,比如《伊利亚特》中的英雄们;少数成功摆脱神的追捕,在“新生地”安居下来;还有极少数安然返回家园,比如奥瑞斯特斯。那么,奥德修斯的流亡又面临何种命运呢?
三
希腊神话中的流亡故事可以理解为某种净罪仪式,主要表现为从城邦内部驱逐某个罪人,旨在恢复洁净,稳定共同体秩序。在古希腊语中,此类仪式也称为Pharmakos,既指“解药”,也指“毒药”。有时,解药与毒药不仅仅是剂量上的区别。从某种程度来讲,净罪仪式对城邦社会来说是“解药”,对被驱除者来说就是“毒药”。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苏格拉底作为替罪的牺牲(Pharmakos)服毒(Pharmakon)而死。类似的同词异义还有不少,比如ara既是“祈祷”,又是“诅咒”。《伊利亚特》开篇,老祭司(arēter)克律塞斯向鼠神阿波罗(Apollo Sminthos) “祈祷” (ara),对希腊联军下“诅咒”(ara) (《伊》 1.35-42)。同样,摩押王巴勒命先知巴兰去诅咒以色列人(《民》 22:5-6),先知反而祝福了以色列人(《民》 22:41-24:10)。既然Pharmakos对流亡者来说是“毒药”,那么,奥德修斯这次流亡如何才能摆脱“毒药”的诅咒呢?先知特瑞西阿斯的预言中其实已经提到化解毒药的方法。
当奥德修斯抵达“不知大海且不食咸盐”的民族所居住的地方时,这位远离家乡的英雄已经完成了他作为罪人的流亡。此地风俗未必是诗人的想象,古代先民很可能经历过不食盐的漫长历史时期。汉语典籍中即有记载。司马迁曾提及某种古礼:“大飨之礼,尚玄酒而俎腥鱼,大羹不和,有遗味者矣。” (《史记·乐书》)忒瑞西阿斯的预言提到,会有一名异乡人将奥德修斯携带的船桨当成扬谷的簸铲。伯纳德特指出,“船桨”与“翅膀”具有比拟意味,指称某种尚是“未知”的东西,与奥德修斯在独眼巨人面前自称为“无人” (outis)遥相呼应。此外,如果参考杜梅齐尔在研究北欧萨迦的资料中所发现的有关船桨与簸铲的类似混淆,那么,此处的船桨似乎还有特殊的宗教仪式意味。换言之,先知在预言中预设下某种特定的时机:在外乡人误认的那一刻,奥德修斯的船桨在异邦国度也就实在地变成了簸铲。关于簸铲的用途,我们知道它不仅可以用来去除谷壳,还是重要的古代宗教器具。伯克特提出,古代有两种用于洁净仪式的器具不太容易为今人所理解,一个是洋葱,另一个就是簸铲。关于簸铲与净化相关的记载同样屡见于希伯来旧约圣经:犹太人专门用簸铲清理祭坛上的灰(《出》 27:1-3;38:1-3;《民》 4:14);腓尼基工匠希兰为所罗门圣殿铸造的铜铲用于清理祭坛(《王上》 7:13,14,40,45);巴比伦人后来入侵以色列从圣殿中夺走铲子(《王下》 25:8,14;《耶》 52:17-18)。旧约用语多次使用扬谷的簸铲与净化之间的譬喻关系,比如神许诺会差遣“扬谷之人”居鲁士大帝(《赛》45:1)攻打巴比伦,“扬净”其中的居民(《耶》51:1-2);神也借巴比伦人之手“扬净”犹太人,击打和驱散他们(《耶》 15:7);神又通过先知以赛亚应允以色列人终将把敌人压成碎糠,“扬到风中”(《赛》 41:14-16)。新约中的施洗约翰也预言,弥赛亚仿佛手拿“扬谷大铲”,要把“小麦”和“糠”分开(《太》 3:12)。这样看来,奥德修斯手中的“船桨”,其实可以理解为某种最后的净化仪式所必须的器具。
我们可以大致判断扬谷的簸铲具有宗教的净化意义,然而使用的方式我们却无从得知,也未见有相关描述或史料记载。这里不妨大胆假设,方法就是把簸铲 (船桨)插入大地,因为先知让奥德修斯这么做了。这似乎和坟墓无关。坟,高地;墓,丘也。史诗并未提及筑土为丘。这似乎也非传教。中世纪荷马注家尤斯塔斯修斯认为,奥德修斯肩扛船桨四处游历,是为了向内陆民族传播波塞冬的崇拜,显然这样的解释受到了基督宗教影响。事实上,不立神像,简单地支起木桩祭神,这在古代欧亚大陆是普遍现象。此外,插入大地的“大铲”可能象征土地上的界碑,因此,将簸铲(船桨)插入大地,可能寓意着界定和区分。
奥德修斯随后在此地举行一次奇特的献祭仪式。史诗提及,奥德修斯在归家途中冒犯了波塞冬,刺瞎了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诓骗了礼仪之邦菲埃克斯人,他们均系波塞冬的后裔。他必须向波塞冬献祭“一头公牛、一头公羊、和一头公猪”。这一牺牲的组合十分奇特。在古代希腊社会,公猪不见于祭祀神明。荷马史诗中另有一处提到与公猪相关的仪式:阿伽门农与阿喀琉斯谢罪言和时,向宙斯祈祷并宰杀了一头公猪,随即扔进大海(《伊》 19.266-268),并未焚烧献祭。此处绝无仅有的牛、羊、猪三牲组合,显然不是普通的献祭仪式,并且很容易让人想到汉语典籍中被称为太牢的祭礼。“牢”原是关牲畜的栏圈,故祭祀时并用牛、羊、豕三牲叫做“大牢”或“太牢”,“太牢”专用于隆重的祭祀,一般只有天子才能用太牢:“天子社稷皆大牢,诸侯社稷皆少牢” (《礼记·王制》)。太牢若非天子之礼数,也是上宾的待遇:“饩之以其礼,上宾大牢,积惟刍禾,介皆有饩” (《仪礼·聘礼》)。无论如何,先知指点奥德修斯这一奇特的献祭仪式,好让奥德修斯化解流亡之“毒”(Pharmakon)。奥德修斯的最后之旅不像《伊利亚特》的流亡英雄们那样是有去无回的赴死之路。同样,他没有像阿尔科迈昂和伯勒洛丰那样定居在“新生之地”,也没有像奥瑞斯忒斯和伊阿宋那样经历“血的净洗”,而是采用忒瑞西阿斯传授的方法:将大铲(船桨)插入大地,并献祭太牢(牛羊猪)。奥德修斯成功了。因为,预言在最后提到,他将安全地回到家乡,诸神将再次接受他的献祭,历经磨难的英雄将如愿以偿安享晚年。
四
英雄流亡是古希腊史诗和悲剧中常见母题。英雄往往为应对一个危机而引发新的危机,以致不得不经历苦难去流亡。奥德修斯的流亡便是如此。古希腊人十分看重神和人的关系,关注如何维持有死的人与不朽的神之间的有序平衡。由于某种人为过失,导致社会群体陷入动荡不安的状态,希腊古人认为这是神人之间的秩序的某种失衡。流亡便是解决这一失序状态的净罪仪式,其中不仅体现出宗教含意,也有其政治意义。这一思想影响在古希腊世界根深蒂固,不但奥德修斯等神话英雄出离流亡,历史中也多有真实发生的事例。比如雅典立法者梭伦。他曾离开雅典外出游历,后来也安全返回了故乡。“流亡”的起因据说是城邦秩序出现了危机——疾病(nosos) (狄奥根尼, 《名哲言行录》 1.50-52)。梭伦去到的第一个地方位于尼罗河三角洲:“尼罗河洪流入海之地,靠卡诺坡斯不远” (普鲁塔克, 《比较列传》 “梭伦传” 25),此地亦是一处“新生的”地方。传说中充满智慧的梭伦想必是遵照了古老的宗教习俗。
奥德修斯的最后旅程及其相关预言呼应了《奥德赛》的开篇:奥德修斯放弃留在卡吕普索神女身边,放弃神女允诺给他的永生,而选择归乡,选择终老一死(《奥》1.59)。从整部史诗的结构和预言出现的位置来看,奥德修斯首次提及这段预言是在费埃克斯人的岛上,他伪装入城,以竞技征服费埃克斯人,凭借言谈赢得女王阿瑞塔的支持。当他说完这段预言时,女王最后一次发言,承诺给予他荣光和财富。随后奥德修斯回忆了冥府中与诸英雄鬼魂的交谈,最终获得国王的帮助开始归乡的最后征程。同样,奥德修斯再次提及这段预言是在伊塔卡岛上,他伪装回宫,以武力肃清求婚人,以言辞赢回王后佩涅洛佩的信任。当他向王后诉说还将离家的预言时,他的妻子在史诗中说了最后一句话,安慰他这是神明的安排,他有望结束苦难并将安享晚年。随后是冥府中诸鬼魂间的交谈,最后奥德修斯得到了父亲(前国王)的帮助,不难想象,此后发生的当为预言中的奥德修斯的最后旅程。我们看到,这两部分叙事存在明显的平行对应关系,围绕两次出现的预言叙事,恰好构成两个典型的环形结构(以上仅列出几项):
D1到达费埃克斯
d1到达伊塔卡
C1竞技
c1杀戮
B1阿瑞塔的支持
b1佩涅洛佩的信任
A 预言
a 预言
B2女王阿瑞塔的发言
b2妻子佩涅洛佩的安慰
C2英雄们的鬼魂
c2求婚人的鬼魂
D2 离开费埃克斯返回伊塔卡
d2离开伊塔卡,流亡并复归
《奥德赛》以预言的形式交代了但求终老一死的凡人奥德修斯的归宿。有关奥德修斯历经磨难只求一死,柏拉图有过精妙的说法。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说奥德修斯的灵魂“因为前一生中的种种苦难而停止了对名誉的热爱,转而寻求一种普通平民的生活”(620c-d)。与同为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们选择各种动物(如埃阿斯变成了狮子,阿伽门侬则是雄鹰)的生活不同,奥德修斯选择的是一种成熟审慎、智慧通达、安分守己之人所应有的生活方式。在柏拉图对话中,奥德修斯的转变发生在奥德修斯死后的冥府之中。然而,从某种程度而言, 《奥德赛》里已然涵盖了奥德修斯的这一根本转变,从“伊利亚特”式的奥德修斯到“奥德赛”式的奥德修斯的根本转变。诗人在史诗开篇即借宙斯之口说到,凡人遭受灾祸是因丧失理智,僭越命运的限定(《奥》 1.33-34)。“奥德赛”正是英雄奥德修斯的一次重新与神“立约”的自我认知之旅。
❶ 译文主要参考王焕生先生的版本,略有改动。
❷ 黄瑞成:《盲目的洞见——忒瑞西阿斯先知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 62页。
❸ (英)赫丽生:《希腊宗教研究导论》,谢世坚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年, 192-217页。
❹ (美)伯纳德特, 《弓弦与竖琴》,程志敏译,华夏出版社, 2003年,117页。
❺ (法)迪梅齐尔:《从神话到小说:哈丁古斯的萨迦》,施康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29页。
❻ Burkert,Greek Relig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p76.
❼ 参见:《弓弦与竖琴》,117页及相关注释;以及《盲目的洞见》, 61页。
编辑/张定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