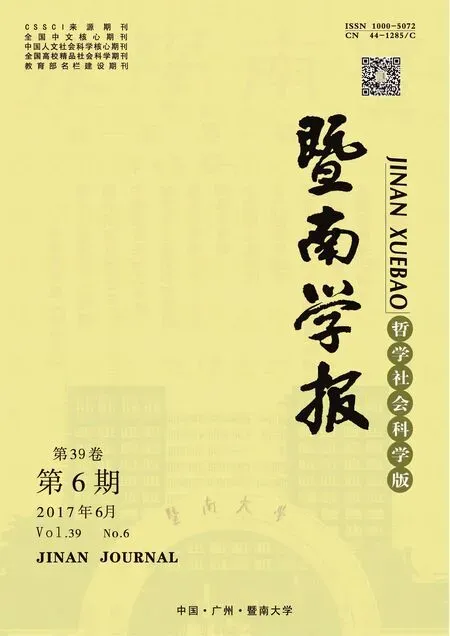梁启超关于颜李学研究的路径及其逻辑演进过程
胡顺强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2)
梁启超关于颜李学研究的路径及其逻辑演进过程
胡顺强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2)
作为民国颜李学研究之开拓者,梁启超在“中国文艺复兴”的内在诉求和“理学反动”的解释框架之下,对颜李学的理解经历了从“新旧过渡”与“兼反汉宋”到“清学支流”与“实用主义代表”的演进过程。尤其是1923年后,他更追逐时趋,引入杜威实用主义学说,一方面把颜李二人再塑成反理学的思想家,并将其二人置于清代反理学谱系中的开端,从而奠定了他们于清代思想史中革命派的角色和地位;另一方面梁以西释中,彰显出颜李学教育思想的现代价值,将该领域研究引入新天地。梁氏之研究虽存在诸多偏颇之处,但在当时民国学界产生了不小的示范意义。
颜李学; 梁启超; 理学; 实用主义
作为清季民国的著名学者,梁启超于清代学术史领域造诣颇深。在其清学史阐释系统里,推动学术思想发展的动力是“反动”,其津筏乃“复古”,“解放”则为最终目的。换言之,“反动”、“复古”与“解放”,构成了梁氏解释清学史的三个关键要素。梁氏清学史作品大多在其浓厚的“学术经世”关怀之下,被打上了具有典范意义的“理学反动说”烙印。其颜李学研究自不会例外。
一、关注颜李学之缘由
梁启超之所以关注颜李学,大致出于如下三个原因。
第一,颜李学作为清代学术史中极具特色且颇为重要之一支,其地位不容忽视,故自然纳入梁氏清学史研究的视野当中。作为清初学术界一个流派,颜李学派虽既未像程朱理学般备受清廷重视,跻身官方之学,也未能如汉学那样蔚为大国,成为一时主流,但它仍以其宏阔的学术气魄和鲜明的学术特色独树一帜。因此研究清学史,颜李学是题中应有之义。在《近世之学术》一文中,在梁氏所推崇的明末清初十六位学术大师中,颜元赫然在列。后来梁还自称:“吾于清初大师,最尊顾黄王颜,皆明学反动所产也”。
第二,梁氏关注颜李学,亦与杜威实用主义的影响密切相关。1919年4月30日,杜威抵达上海,从而开始了在华巡回讲学的历程。其所主张的实用主义学说也被中国知识界各派人物普遍接受,风行一时。梁启超也积极投身于这场热潮当中。作为对杜威实用主义学说的回应,梁启超于1923年相继撰写了《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和《实践实用主义:颜习斋、李恕谷》两篇应时之作。梁氏亦并不讳言实用主义对他的启发与刺激:“自杜威到中国讲演后,唯用主义或实验主义在我们教育界成为一种时髦学说,不能不说是很好的现象,但我们国里头三百年前有位颜习斋先生和他的门生李恕谷先生曾创一个学派——我们通称为‘颜李学派’者,和杜威们所提倡的有许多相同之点,而且有些地方像是比杜威们更加彻底。所以我想把这派学说从新介绍一番。”可见梁氏认识到杜威实用主义与颜李学说有某些相似之处,这便激发了他研究颜李学之兴趣。
第三,“戴东原生日二百年纪念会”成为梁启超精研颜李学之契机。戴震学研究无疑是梁启超晚年清学史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梁氏关注戴震学的触发点正是发起筹办“戴东原生日二百年纪念会”(癸亥十二月二十四日,公历1924年1月19日)。为了更好地宣传与纪念这位“科学界的先驱者”和“哲学界的革命建设家”,梁氏作出表率,拟撰文五篇,“一是东原先生传,二是东原著述考,三是东原哲学,四是东原治学方法,五是颜习斋与戴东原”。后因时间短促,梁未能按计划写就,仅成《戴东原先生传》一篇。恰在撰文期间,为了觅求有关戴震哲学思想渊源的线索,梁启超仔细研读颜李学派的不少论著,从而“深信东原的思想,有一部分是受颜李学派影响而成”。并在赶写纪念戴震相关文章的同时,他还特意抽空写就长达两万余字的《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一文。要之,“戴东原生日二百年纪念会”不仅是梁氏深入研究戴震学的开端,正因为戴震学与颜李学之间的学术渊源,也成为其精研颜李学之契机。
二、“新旧过渡”与“兼反汉宋”
以1923年底倡议发起“戴东原生日二百年纪念会”为标志,恰可将梁启超的颜李学研究界分为两期,第一期为发起纪念会之前,此期的相关著作为《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和《清代学术概论》。
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梁氏并未把颜李学派单独拿出论列,而是将颜元同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刘继庄并称为“新旧学派之过渡者”。就五人所共有的学术特色,梁氏总结为四点:“以坚忍刻苦为教旨相同也”,“以经世致用为学统相同也”,“以尚武任侠为精神相同也”,“以科学实验为凭借相同也”。至于颜元独有的学术特征,梁氏也有所涉及。第一,他认为“习斋专标忍嗜欲苦筋力之旨,为学道不二法门。近世余杭章氏以比诸罗马之斯多噶派,谅矣”。将颜李学比作古罗马时代的斯多噶派,恰反映出梁氏认为中国也有文艺复兴时代的内在诉求。在其看来,颜元控制欲望、重行轻知,与古罗马时代的斯多噶派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正是清代乃“古学复兴时代”之极佳例证。第二,梁启超又根据“理学反动”的观点指出颜元“事事而躬之,物物而肄之,以求其是,实宋明学之一大反动力,而亦清学最初一转捩也。雍乾以后,学者莫或称习斋,然顾颇用习斋之术,但其术同,而所用之目的地不同,以实事求是一语,而仅用之于习斋所谓其距万里之书,习斋其恫矣。乃者余杭章氏极推习斋,以为荀卿以后一人,其言或太过,然要之为一代大儒必矣”。梁氏之所以套用该解释模式,其用意在于以颜元为例,说明清代学术思想的历程恰是以复古为解放的形式一步步演进的,颜元“并宋明而悉弃矣”,乃其中之一环。
时隔十六年,梁启超于1920年所撰《清代学术概论》中,基本保留了之前对颜李学的主要看法,并进而展开论析。对于颜元的学术特色,梁氏仍认为“其学有类罗马之‘斯多噶派’,其对于旧思想之解放,最为彻底”。其最核心的主张可概括为“劳作神圣”。“质而言之,为做事故求学问,做事即是学问,舍做事外别无学问,此元之根本主义也”。在梁看来,也正是过分执着于清教徒式的苦行实践,“在此现实界而惟恃极单纯极严冷的道德义务观念,教人牺牲一切享乐,本不能成为天下之达道”。致使其学绝非常人所能践履,故成为阻碍其学说传播的一大弊端,该学派也因之中绝。
由颜李学派与斯多噶派的类似到指出颜李学派的衰落与苦行密切关联,说明梁的颜李学研究较之清末确有所深入。不过,这里尚需辨析的是,梁启超实则并未真正了解斯多噶派的学说内涵。因为斯多噶派最重要的哲学理念是理性与情欲的二元对立。此派学者认为人类本身即具有理性,然而同时又存在非理性的情感及欲望与之对抗。在普遍的情况下,人的理性常不能控制其非理性的成分。故而以理性控制情欲,便成为他们的贤人理想。宋明理学家所倡导的“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反颇与斯多噶派相似。故梁氏认为颜李学派与斯多噶派主张类似的说法便显得非常牵强。
出于同样理念,梁氏仍于“理学反动”的解释框架下考察颜李诸人的主张。梁氏断定颜元“则明目张胆以排程朱陆王,而亦菲薄传注考证之学,故所谓‘宋学’、‘汉学’者,两皆吐弃,在诸儒中尤为挺拔,而其学卒不显于清世”。颜元之所以既不认宋学为学,亦不认汉学为学,其原因在于“学问绝不能向书本上或讲堂上求之,惟当于社会日常行事中求之”。梁启超这样看待颜李学与汉宋学之间的关系,一方面的确凸显了三者之间的学术差异,不过如此绝对化的结论在另一方面也忽视了三者之间的学术关联。其实颜李学并非无所依傍,凭空而生,它的产生与明末清初的学术氛围密不可分,其间既有对其他学术流派的吸收与承继,亦有反思与超越。如颜元就认同并借鉴了宋学家陆世仪的主敬思想,李塨更是充分吸取清初经学家的学术成果,运用考据方法著书立说,为颜李学寻求学理支撑。故对汉宋两派,颜李诸人更多的是批判,而非“吐弃”,梁之论断不免有失偏颇。
除却以上对以往主张的延续,梁启超于《清代学术概论》中亦对颜李学提出新的见解,他认为颜李所倡导的实学,与刚引入国内的杜威实用主义思潮有所近似,按梁之原话:“以实学代虚学,以动学代静学,以活学代死学,与最近教育新思潮最相合,但其所谓实所谓动所谓活者,究竟能免于虚静与死否耶?此则时代为之,未可以今日社会情状绳古人矣。”所谓“新思潮”,即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思潮。只是梁氏对该思潮了解尚浅,故未详加论述,不过这毕竟为他1923年之后的颜李学研究埋下伏笔。
三、“清学支流”与“实用主义代表”
承上所言,梁启超颜李学研究由第一期折入第二期的契机为“戴东原生日二百年纪念会”。至于具体肇因,则应从梁氏1923年11月于汤山养病谈起。笔者于国家图书馆查阅史料时,发现北海古籍馆藏有一部梁启超手批本的清同治十年(1871)南山冶城山馆版的《颜氏学记》。在该书封面,署有梁氏题款:“癸亥十月养病汤山精读一过 启超记”。癸亥年即1923年,由于梁氏采用阴历纪年,故“十月”应是当年公历11月左右。至于其养病经过,梁氏在当年十一月十六日写给女儿梁思顺的信中也有所交代:“我半个月前痔疮复发,初时不以为意,耽搁了好几日,后来渐觉得有点痛楚,才叫王姑娘入京服侍,又被你弟弟们逼着我去汤山住了几天,现在差不多好清楚了。”由此可以推断,1923年11月初,梁启超因病在汤山小住几日。也正是于此短暂的养病期间,梁氏通过精读戴望的《颜氏学记》,对颜李学的认识有了较大改变。
现藏国家图书馆的这本梁氏手批本《颜氏学记》,内有梁启超批语一千余字。通观梁氏批语,梁氏研读《颜氏学记》所获新见大致有三。一是断定戴震学与颜李学颇有渊源。当读到“乾隆中戴吉士震作《孟子绪言》,始本先生此说言性而畅发其旨”一句时,梁氏不禁写道“东原之学本习斋,渊源甚分明”。同时梁认为不仅戴氏之学源自颜李,姚际恒似亦受该学派影响,于是又在该页空白处随手记下一句:“《文献征存录》云:‘徽州姚际恒作《庸言录》,谓周程张朱皆禅,其说本颜元。’立方之得阅习斋学。”在《学记》另外章节中,亦能看到梁氏有关戴震学与颜李学之间渊源的批语。如在卷二开篇,梁氏读到颜元《驳气质性恶》及《明明德》中批判理学二重化的人性论和气质之性为恶的观点,认为“后此戴东原之说颇似之”。再如对于卷九的程廷祚的《论语说》,梁氏读后亦断定“东原说所本”。二是关注颜元的教育思想。之前已提到杜威实用主义学说的引入使得梁启超颇受启发。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教育家之一,杜威的教育理论备受当时中国学人推崇,教育界形成一股“杜威热”。梁启超也难免不受该热潮影响。这种看法在其批语里有所体现。在《学记》卷二,颜元认为改善“引蔽习染”对气质之性影响的方法即在于“习”,其具体途径在于“熟阅《孟子》而尽其意,细观赤子而得其情,则孔、孟之性旨明,而心性非精,气质非粗;不惟气质非吾性之累害,而且舍气质无以存养心性,则吾所谓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艺之学是也。是明明德之学也,即谓为变化气质之功,亦无不可”。梁启超遂下断语认为“习斋是教育万能论者”。同时,他指出颜元这种重视习行的教育方式也存在弊端,即“习诚善矣,而以古礼为之具,所以等于虚习。习斋之教不能大昌在此”。三是开始认识到颜元、李塨师徒二人在治学上的相异之处。在之前的研究中,梁启超对李塨的评论较少,表现出明显的“重颜轻李”倾向。这实与他对李塨学术作品涉猎较少有关。通过阅读《颜氏学记》,梁氏不仅翻阅了颜元的主要论著,同时也接触到李塨的不少作品,这使其得以更深入地了解其学术思想。通过研读,梁氏感到虽然李塨在治学大旨上与其师并无二致,但在具体主张和方法上仍有不少差别。如就颜李二人在知行观上的分歧,梁认为“知在行先一语与习斋似有异同。习斋释格物致知(其意)说非亲下手一番不能知。意谓必行乃知也。恕谷知在行先之说离,分析较密,毋乃又为支离之学所藉口手”。这可谓是梁氏只眼独具之处。梁氏还就颜李二人的治学特点简作比较,指出:
恕谷之学:(一)理习较习斋□□; (二)事功阅历较深; (三)闻见精博。
可知他对颜李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的理解更趋深入。
通过对《颜氏学记》的一番研读,加之纪念戴震诞辰二百周年活动的触发,梁启超对颜李学的关注程度较之以往大为增强,其研究也自然转入第二期。此期他完成了两篇专论《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和《实践实用主义:颜习斋、李恕谷》。
综观如上作品,梁氏依然将颜李学派视为明末清初“反理学运动”的重要力量,“有清一代学术,初期为程朱陆王之争,次期为汉宋之争,末期为新旧之争,其间有人焉举朱陆汉宋诸派所凭借者一切摧陷廓清之,对于二千年来思想界,为极猛烈极诚挚的大革命运动,其所树的旗号曰‘复古’,而其精神纯为‘现代的’,其人为谁?曰颜习斋及其门人李恕谷”。并且梁氏还指出颜李学派属于清学的支流,其特色乃“排斥理论提倡实践”,“这个支流,屡起屡伏,始终未能很占势力”。不过,由于对颜李著作阅读量的增加和引入实用主义这个新式理论阐释工具,梁启超于第二期的颜李学研究呈现较大的转变,主要概括为如下三点。
第一,颜李学派的知识论是“唯习主义”知识论。在梁氏看来,颜李学派的核心思想,就在于“习”,“一个‘习’字,便是他的学术全部精神所在”。具体来说,颜李的这个“习”字有两种含义和修行方法:
其一,他不认为先天禀赋能支配人,以为一个人性格之好坏,都是由受生以后种种习惯所构成,所以专提倡《论语》里“习相远”、《尚书》里“习与性成”这两句话,令人知道习之可怕;其二,他不认为实习之外能有别的方法得着学问,所以专提倡《论语》里“学而时习之”一句话,令人知道习之可贵。……有两种“习”法:一为修养品格起见唯一的工夫是改良习惯;二为增益才智起见唯一的工夫是练习实务。
同时,在梁氏看来,颜李并非极端的“读书无用论”者,他们“反对读书,并非反对学问,因为他认定读书与学问截然两事,而且认为读书妨害学问,所以反对。”他们“反对读书,纯为积极的,而非消极的,他只是叫人把读书的岁月精神腾出来去做学问”。其次,“见理于事”亦是其“唯习主义”的重要主张。一般而言,宋明儒家说理及明理的方法有二:一是天理,即天道,或指一个仿佛空明的虚体,其明理之法在于“随处体认天理”;一是指物理,其明理之法为“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从而达到“一旦豁然贯通,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境界。其实,“两事只是一事,因为他们最高目的,是要从心中得着一种虚名灵觉境界,便是学问上抓住大本大原,其余都是枝叶”,颜李学派对于这种主张极力反对,因而提出“见理于事”的概念。他们主张士人们“礼、乐、兵、农更精其一”,“水、火、农、教各司其一”,学问必定会日益精进,也可避免宋明儒生泛滥无归、终身无得的弊病。总之,“颜李对于知识问题,认为应该以有限的自甘,而且以有限的为贵,但是想确实得到这点有限的知识,除了实习外更无别法,这是他们知识论的概要”。
此外,对于颜李学派“唯习主义”知识论的不足,梁氏也有言及。他指出其知识论“和近世经验学派本同一出发点,本来与科学精神极相接近,可惜他被‘古圣成法’四个字缚住了。一定要习唐虞三代时的实务,未免陷于时代错误。……他这个学派不能盛行,未始不由于此,倘能把这种实习工夫,移用于科学,岂非大善?”
行文至此,笔者尚需略作延伸。无须讳言,梁启超对颜李学派“唯习主义”知识论的解释,是以杜威的实用主义学说为参照系的。然而梁氏实对杜威的知识论之主旨了解未深。虽然颜李和杜威在知识论方面皆注重因行以求知,因行而得知,持知行合一的观点,但二者在具体主张上存在的差别亦非常明显。首先,颜李仅注重实行的知识,亦即哲学之知;杜威除却注重实行的知识外,并注重感觉的知识及推理的知识,也就是科学之知。其次,颜元反对读书和著书,也就是不主张士人专门从事于知识的探究;反观杜威,他认为根据社会分工合作的原则,有一部分人去专门从事知识的探究工作,是无可厚非的,故这是二者在知识论上又一不同之处。要之,梁启超对于颜李学派与杜威学说之间相似性的比较,存在牵强不实的失误,这同其对杜威学说知之不深密切相关。
第二,颜李学派是一种功利主义学派。在梁启超看来,颜元也是一位功利主义者,证据就在于其对传统儒家重义轻利、义利对立观念的反对与纠正。传统儒家在义利观上,大都喜谈仁义而不讲求逐利,最具代表性的说法便是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长此以往,便形成了中国哲学史中的义利之辨,其实质即理论形态上的道义论同功利论的二元对立。在梁氏眼中,传统义利观虽“是学者最高的品格,但是把效率的观念完全打破,是否可能。况且凡学问总是要应用到社会的,学问本身可以不计效率,应用时候是否应不计效率,这问题越发复杂了。我国学界,自宋儒高谈性命鄙弃事功,他们是否有得于‘为而不有’的真精神,且不敢说,动辄唱高调把实际上应用学问抹杀,其实讨厌”。颜李学派对这种现象极为不满,因为若不重视对利益的追求,只会使社会停滞、百姓贫困,于是公开提倡功利,认为应“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他们还以天下为己任,主张学问皆归于致用,专提《尚书》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为标帜。是故“颜李也可以说是功利主义者”。
当然,仔细研读梁氏有关论证颜李乃功利主义者的文字,则会发现他对于“功利主义”这个概念的认识并不透彻。颜李学的功利论,有着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的性质。这是以利人、利天下为善恶价值标准的社会功利主义。这一以利他为特征的功利主义,不否定正当的个人利益,但与近代西方的以是否满足个人幸福为善恶标准的功利主义有明显区别。西方功利论认为达到“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是个人活动的唯一目的,即把个人看作是社会利益的基础,社会利益只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所以人类行为的唯一目的是求得幸福,促成幸福是判断人的一切行为的标准。只有在行为结果具有意义时,才应当区别道德上的善与恶。这种以个人为社会基础的功利主义,到了20世纪之后才由梁启超、陈独秀等人介绍到中国。梁氏在此处所谈的“功利主义”,更多是受杜威影响的西方功利主义思想。与颜李学相比,“杜威所追求的人生价值虽未否认道义,但不容置疑的是颇倾向于功效利益的,这终究不如习斋兼顾义利的立场来得妥当无弊”。可见梁启超在对中西功利主义学说的理解上尚未达到这一层面,故他对颜李学功利主义属性的总结便显得十分模糊。
第三,指出戴震学与颜李学之间的渊源关系。如上文所述,在汤山养病期间,梁氏已从《颜氏学记》中得出戴震学源出于颜李学的论断。之后,梁氏结合研治所得,提出了更为系统的证据,大体说来,有三条线索:
其一,方望溪的儿子方用安为李恕谷门生,望溪和恕谷论学不合,用安常私自左袒恕谷,是桐城方家有能传颜李学的人。东原和方家人素有往来,方希原即其一,(集中有《与方希原书》),所以他可以从方家子弟中间接听见颜李的绪论。其二,恕谷很出力地在江南宣传他的学派,当时赞成和反对两派人当然都不少,即如是仲明这个人。据《恕谷年谱》知道,恕谷曾和他往复论学,据《东原集》又知道他曾和东原往复论学,《仲明年谱》中也有批评颜李学的话,或者东原从他或他的门下可以有所闻。其三,程绵庄是当时江南颜李学派的大师,绵庄死的时候,东原已三十岁了,他们两位曾否见面,虽无可考,但程绵庄和程鱼门是挚友,鱼门、东原交情也不浅,东原最少可以从二程的关系上得闻颜李学说乃至得见颜李的书。
就如上三条而言,皆属推测,明显不能将两学派存在渊源关系一事坐实。毕竟梁氏此文出手仓促,许多细节考虑欠周。不过,梁氏这一论断却激发了民国另外一位学人胡适的兴趣,促使他于日后在该领域耕耘颇勤。“醉翁之意不在酒”,梁氏积极寻求戴震学与颜李学之间的学脉关联,其意图乃通过沟通二者来为其毕生追求的所谓“中国文艺复兴时代”提供更充分的理由。
四、结 语
综上所述,在“中国文艺复兴”的内在诉求和“理学反动”的解释框架之下,梁氏对颜李学的探讨总免不了借镜西方的历史背景与理论工具。1923年之后,他更追逐时趋,引入杜威实用主义学说,使得烙在颜李学之上的西学底色愈加浓重。故梁氏之研究有着明显的诉求与意图,并非从纯历史或学术的角度去审视颜李学。这种做法虽存在不少偏颇之处,却在当时民国学界产生了不小的示范意义。具体而言,首先梁将颜李二人再塑成反理学的思想家。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是一个层层建构与不断积淀的过程。回顾晚清颜李学研究历程,近代颜元、李塨二人学术形象的塑造其实有一个逐步延展的内在逻辑。颜李学复兴之初,戴望已把二人称为经世学者,并有意将戴震学的渊源导引至颜李学名下,实已隐含颜李学与宋明理学对立的意味。随着晚清学人对颜李学传播和阐释的日趋广泛,其对颜李形象的改塑也因之展开。宋恕、章太炎、刘师培诸君,一面将颜李誉为反清复明的民族主义者,一面又赋予其沟通中西的称号,于是颜李二人距离西方近代科学精神似被人为地拉近了不少。故到20世纪20年代初,颜元、李塨二人批判理学、融合中西的形象已渐成共识,梁启超积薪而上,再进一步,将二人塑造成反理学的思想家,并将其二人置于清代反理学谱系的开端,从而奠定了他们于清代思想史中革命派的角色和地位。其次梁将颜李学的教育思想研究引入新天地。早于梁氏,已有如刘师培、邓实等人开始探讨颜李的教育思想,不过这些讨论既不系统,也较乏新意,加之当时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学科尚未建立,故此时的研究尚处于萌芽阶段。1924年初,梁启超所撰《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一文于《东方杂志》发表,虽然此文乃应景之作,但其写作初衷之一即为“盼望这派的教育理论和方法能够因我这篇格外普及而且多数人努力实行,便是我无上的荣幸”。故该文之于颜李教育思想研究领域的开拓意义不容忽视。在是文中,梁氏结合当时的现代教育思潮,即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说,同颜李二人的主张作对比研究,以西释中,从而彰显出颜李学教育思想的现代价值。通篇涉及颜李教育思想的多个方面,如教育目标、培养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学校建设、重视体育和性教育及强调师道尊严等,可谓国内第一篇全面阐述颜李教育思想的学术文章。其后,许多学者便沿着梁氏所开启的研究思路对颜李教育思想进行深入探索。故由此可知,之后胡适等人的颜李学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便是沿着梁启超的阐释思路展开的。
[责任编辑 王 桃 责任校对 李晶晶]
2017-02-22
胡顺强(1978—),男,山东临沂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党史以及中国近代史等方面的研究。
K252
A
1000-5072(2017)06-007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