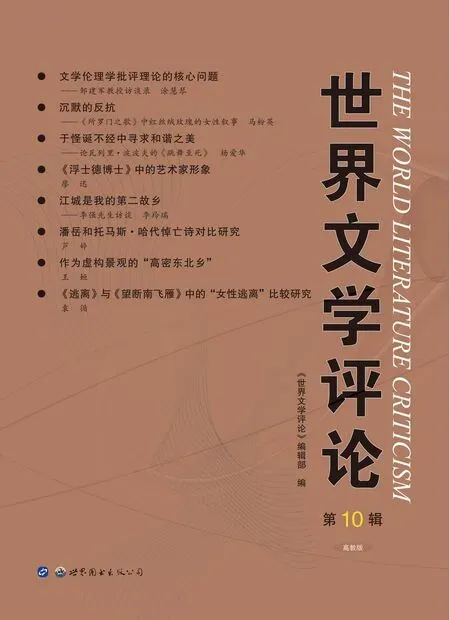江城是我的第二故乡
——李强先生访谈录
李羚瑞
江城是我的第二故乡——李强先生访谈录
李羚瑞
李强,男,汉族,河南上蔡人,当代著名诗人。曾任湖北省委办公厅经济处副处长,武汉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武汉市江汉区委副书记、区长,武汉市江汉区委书记。2015年7月,任江汉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
李羚瑞(以下简称“瑞”)
:一个人的写作总是有他的背景,有他的历史,有他的原因。您是在什么背景下开始写诗的?李强(以下简称“李”):
孩子没娘,说来话长。因为历史的原因,上大学前根本就没有认真地学习,包括学语文。1979年考上华中工学院机械工程二系锻压专业,也与诗歌风马牛不相及。接触新诗,纯属偶然事件,就是一不小心在华工邮局买到了1979年10月的《诗刊》,这一期是朦胧诗专号,上面有当时崭露头角以后引领风骚的北岛、舒婷、顾城等诗人的作品,我一看就喜欢上了,完全可以说一见钟情。大学四年,主修主业之余,也偶尔“学而时习之”,人生历程从此与读诗写诗相伴随。前一阵子见到《诗刊》副主编李少君,还谈起此事。我至今还珍藏这期《诗刊》,至今还能背诵其中的一些诗句,如湖南诗人徐晓鹤的《珠江》:“你的歌声是珍珠般晶莹的闪亮,你的欢笑价值整个春天的芬芳。我知道你流过一片富饶的土地,那里是红豆和甘蔗生长的地方。”关于诗歌创作的状态,说起来惭愧,断断续续,若有若无。自我解嘲曰:“职业属主序列,创作属个体户。”1983年大学毕业后,先后进工厂、读硕、读博、从事社会科学研究、调县、区、市、省四级党政机关,知天命之年后就任大学校长,职业生涯不停变动,诗歌创作一直如新手上路,摇摇摆摆。主要原因不能归咎于忙,而是主观上从没有把写诗看得太重,完全没有成名成家的冲动;客观上既没有拜师学艺,也没有抱团取暖,在提高与发表上均处于不利地位。到目前为止一共写了五百首左右,搜搜箱底,也到不了六百首,多数在媒体公开发表,包括《人民文学》、《诗刊》、《星星》、《中国诗歌》、《长江文艺》、《芳草》、《汉诗》、《楚天都市报》等。发表最多的媒体当属《长江日报》江花版,发表分量较重的当属《中国诗歌》2015年4月份的《头条诗人》。
关于诗歌创作的风格,内容上追求现实主义,形式上追求浪漫主义。说俗点,只有感而发,不无病呻吟,不语怪力乱神,不在修辞学上下苦工夫。清新,优雅,朗朗上口,特别适合朗诵。并且,我能够背诵自己大多数的作品。
到江汉大学工作一年多了,毫无任何征兆,诗歌写作居然渐入佳境。2015年10月底启用了《湖畔聆诗》微信公众号,每周一期,从第9期开始,几乎全部是新鲜出炉的作品,现在已经是第40期了,阅读量稳定在300位以上,并且尚无江郎才尽之感。当然,诗的质量如何,读了自见分晓。
瑞:
每一位诗人都会有自己的故乡,然而对于某些诗人而言,也许不止一个故乡。您的诗歌写作有没有自己的故乡?您的诗作与江城之间的关系?李:
我17岁到武汉读书,21岁大学毕业,尔后两年在咸宁工作,接着两年在哈尔滨读研究生,1987年至今,一直生活在武汉。算起来,整整33年了,自己的梦想、奋斗、记忆与情感,无一不打上武汉的烙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0年我经过公开招考,调任武汉市委政研室副主任,三年后就任武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六年后就任江汉区区长、区委书记,兼任过区人大主任、武汉中央商务区管委会主任,武汉中央商务区投资控股集团公司董事长,一晃又是七年,是作为参与者而不仅仅是见证者,经历了这座城市“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蝶变过程,这其中的辛酸与喜悦,不足与外人道也!2004年我写过一首诗《一点点爱上这座城市》,用来回答这个问题再恰当不过了:
我在少年时走进这座城市
我在远游后回到这座城市
我把父母亲安葬在这座城市
我把青春期安葬在这座城市
这么多年 我彷徨、苦闷、梦想、耕耘
一天天老去
在这悠久、大气、地灵人杰
略显粗糙的滨江之城
我曾在雨天伫立喻家山顶
冥想往事、未来以及爱情
我曾在傍晚散步东湖岸边
带着一天天茁壮的儿子
一天天淡漠的雄心 以后
从一个院子到一个院子
从江南到江北
有一种感悟无法诉说
有一种开始不容稍停
一点点爱上这座城市
当纸鸢高高飘在越来越蓝的天上
当风车稳稳转在越来越高的楼前
当上下二桥极目江天的辽阔
当走遍三镇聆听百姓的欢欣
当一种沉甸甸的责任
教我懂得并珍惜
坚定、执着、可贵的默默无闻
关于这座城市我知道多少
为了这座城市我做了多少
爱她的人
穷其一生
也没有止境
瑞:
一位成熟的诗人,总是有自己的代表作,并且不只一首。请问您的代表作有哪些?是如何产生的?李:
2013年1月,长江日报《爱上层楼》读书会邀请我分享读书心得,会上回答了书友们的提问,并在见报时附上了两首代表作,一是《萤火虫》,一是《微笑》。诗作好比自己的孩子,是否聪明可爱,自己说了不算,广大读者说了才算。诗圣杜甫曰:“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晒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是金子还是沙子,要经过长时间的检验才行呀!好诗是如何产生的?不清楚。首先要有灵感,而灵感是风吹来的种子。蒲公英的种子随风飘呀飘,落到诗人的心田上,于是就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了,就是这么回事。
回到现实中来,从自己诗作“矮子中间挑长子”的话,有点特色的诗歌有四大类:一是武汉系列,二是家乡系列,三是旅途系列,四是花朵系列。一定要挑出一首代表作来,难,当局者迷。近期关于家乡系列的写得多些,可能是年龄作祟吧!附上一首新作《小苏》,算是今年的代表作:
小苏从小就灵醒
长得就端正醒目
说话、做事总比别的孩子机灵
街上人都知道小苏
有一回
小苏低头过马路
与一台江西来的解放牌碰个正着
好个小苏
一骨碌钻到车身下面
拍拍灰就去上学了
街上人都知道小苏
街上人都会说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小苏就是活生生例子
街上人都说错了
三年后小苏随老苏搬离了龙港
又过了三年
小苏在一口小水塘淹死了
瑞:
中国古代诗歌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我们从小就会阅读唐诗宋词,并且数量较大。您是如何评价中国古典诗词的?您最敬重的中国古代诗人是哪一位?李:
中国古典诗词太伟大了!这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瑰宝,是龙的传人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读中小学时适逢文革,没怎么读书,完全不知道什么唐诗宋词。在华工学习时,当时学校开了中国古典文学的讲座,我是热心听众,可以说场场不落,启蒙就此开始。班上有位湖南同学易生跃,文学功底不错,拉我竞赛背《唐诗三百首》,比了四年,我会背300首时,他能背500首,我输了。大学入学20年聚会时,我问易生跃,我还能背300首,我们比一下?结果他认输了。最敬重的古代大诗人是谁?确实没想过。一定要说,就说李白吧,没准我还是他的后代。
瑞:
作为一个当代中国诗人,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西方诗歌不可能没有阅读。请问对您影响最大的外国作家是哪几位?为什么?李:
前面说过了,作为诗歌个体户,一直处于无师无友、无门无派的状态,接触、学习国内外的诗歌名家名作太少,惭愧!知道并喜欢的外国作家屈指可数,如庞德、艾略特、惠特曼、里尔克、泰戈尔、普希金、华兹华斯。到大学工作,可支配时间多了,要制定一个阅读计划,好好补上这一课。
瑞:
童年与少年时代的生活,往往成为一位诗人一生中斩不断的创作之源。您认为一位诗人与出生地方之间的联系是什么?您在诗中是如何表现自己的故乡的?李:
生活是五谷杂粮,诗歌是琼浆玉液,创作就是发酵过程。诗人与故乡的关系,宛如胎儿与母体,密不可分。我生长在鄂赣交界的一个山区小镇上,幕阜山群峰耸立,朝阳河玉带绵延,青石铺就的街道光滑可鉴,原木搭成的门窗吱呀有声,偏僻贫瘠不掩古朴宁静之美。三月油菜花开,满畈金黄。四月杜鹃花开,漫山红遍。五月兰花的芬芳沁人肺腑又若有若无,藏身于杂树乱草丛里而难觅踪影。一条砂石路连接武汉南昌,路的两旁是整齐高大的白杨树,树叶泛黄的时候,新学年就开始了;落叶纷飞的时候,春节就要到了,就会有更多的烟雾和香气弥漫开来,经久不散。朝阳河从我家附近流过,一座石桥横跨在20米宽的河上,一座石井雕龙刻凤,和台阶上青葱茂盛的苔藓一同见证着年代的悠久。一年又一年,我在河里淘米洗菜,捉鱼摸虾,浸泡在缓缓东去的河水里仰望蓝天白云发呆。“坐井观天的日子,云彩变幻如梦。吸一口远方来的风,就深信最终会飞起来。”多少年后,我以一首《与往事干杯》记录了青少年时代的梦想。
海德格尔说过:“诗人的天职就是还乡”。如何还乡?一看情怀,二看风格。我以为,未必乡村总是黑色记忆,未必生命总是苦难旅程。我笔下记忆中的小镇龙港,是质朴、温暖、亲切的,而不是阴森森的、惨兮兮的。太平盛世,好的诗歌应给人慰藉,而不是给人绝望。
瑞:
您如何认识诗的美学本质和道德教诲之间的关系?您在创作中是如何做到以诗艺为先的?李:
太专业了,实话实说没怎么想过。杜甫诗云:“好雨知时节, 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诗歌的第一要务是发现美、呈现美,其中可以暗含道德教诲,也可以与道德教诲无关。时至今日,板着脸孔、强行说教那一套,已经完全失去市场了。瑞:
每一位诗人都会有自己的诗歌观念,即对于诗歌的本质、起源、形式、技巧及传播会有自己的认识。请问您在诗歌创作上有什么主张?李:
三年前,有幸与一批卓有成就的大诗人相聚一堂,曾向他们讨教过三个幼稚或者说是愚蠢的问题:诗歌只能咏叹小我而非大我吗?晦涩而非直白才是表达的最终捷径吗?诗与歌可以合二为一吗?场面混乱,答案不一。按文责自负的游戏规则,我的选择或者说是偏好不妨公布如下:其一,好的诗歌既能见小我,也能见大我。我们不能对这个大时代视而不见!其二,好的诗歌应面向大众,兼顾小众,能直白地说就不要晦涩地说,可以让人脑筋急转弯,最好不要让人猜谜语。其三,在《诗经》时代,诗与歌是一体的,如今分道扬镳、渐行渐远,这并不正常。应当互相尊重,融合成长。诗变成歌才能生出翅膀,飞越万水千山,飞进千家万户。我作过此类尝试,如《感动江汉》、《长江英雄》、《梦想之城》被作曲家谱曲后,在一定范围内受到欢迎和好评。瑞:
您对当代中国诗歌创作有什么样的评价?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您对当代诗人有什么样的期许?李:
“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作为诗歌创作个体户,坐井观天,对整个诗歌创作的整体情况知之甚少。近年来与主流诗歌刊物编辑们接触多了,相对有所了解。不过,恭敬不如从命。关于对当代中国诗歌创作有什么样的评价,套用一句耳熟能详的话:“成绩是主要的”。当代中国诗歌总体状况确实令人乐观,可以说供需两旺。老诗人屡有佳作,新人类后来居上,80后、90后、00后中新人辈出,好些作品令人眼睛一亮,经久不忘。网络的普及,微信公众号的出现,为诗歌的创作、发表与互动,开辟了崭新的天地。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个人可支配时间越来越多,对包括诗歌在内的精神文化需求自然也日见增长。从某种意义上讲,“重回盛唐”是可以期待的。说到底,诗歌“重回盛唐”是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
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不太清楚,一种感觉是“井水不犯河水”,圈子里的诗歌与社会上的诗歌缺乏交流,学院派诗歌与草根性诗歌缺乏交流,一个圈子里的诗歌与另一个圈子里的诗歌缺乏交流,国内外的诗歌交流也只是浅层次的、随机性的。第二种感觉就是各种评奖多了,但权威性、公正性受到质疑。有没有“少数人评奖或在少数人中评奖”的问题呢?也许有,至少有不少人怀疑。第三种感觉前面也说到了,写诗的不写歌词,写歌词的不写诗,你玩你的,我玩我的,习以为常,其实并不正常。
对当代诗人有什么样的期许?从大到小排序,写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诗歌,写出有益于世道人心的诗歌,写出让人心动、心悦的诗歌。
瑞:
您在江汉区工作了这么多年,对楚文化传统有什么样的认识?对您的诗歌创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李:
武汉人俗称的“老汉口”,主要指的是江汉区老京汉铁路线以南的部分,即满春、民族、民权、花楼、水塔、前进、民意这七个街道办事处范围,面积只有2.54平方千米。从历史上看,汉口人称武昌、汉阳是乡下,江汉人称江岸、桥口是乡下,江汉人又分道南、道北,似乎道南才是地道的“老汉口”。当然,现在武汉三镇均衡发展,这些说法也渐渐消失了。楚文化是个大概念,汉口文化或者武汉文化是个小概念。楚文化是源,汉口文化或者武汉文化是流,这是毫无疑问的。另一方面,我理解的楚文化与农耕与战争息息相关,如“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而汉口文化、武汉文化更多基于商业、贸易活动,有学者称武汉文化实质上是码头文化,是有一定道理的。
汉口五百年,货到汉口活。基于武汉通江达海,九省通衢的地缘优势,码头是武汉成长的活力之源,码头工人是武汉兴旺的关键因素,码头文化是武汉精神的天然色彩。码头文化有什么特质呢?诚信、机智、抱团、舍得,敢为人先,事到临头豁得出去。负面评价则是马虎、无计划、得过且过,骨子里不怎么追求卓越。作为一个在武汉生活了33年的新武汉人,这些负面的东西已经有所显现了。惭愧!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诗歌创作也不例外。说具体点,我的诗歌确实保持了不断探索、创新的特点,无论是写什么还是怎么写,无论是结构、节奏还是起承转合,都不保守,而在不断尝试之中。当然,基本的特点还是有的,就是干净、流畅、优雅。在追求卓越上严重不足,没有“语不惊人誓不休”的雄心壮志,写出来的诗基本上不改,同一主题的诗基本上不重写。
瑞:
艺术是诗人的护身符,一个不讲究艺术与形式的诗人,往往不可能成为一流的诗人。您在诗歌的艺术与形式上有什么的追求?李:
你说得对!诗如其人。或者说,诗是诗人的第二张面孔。还是回到上面我谈到的“写什么和怎么写”的话题上来。写什么?我手写我心,写让自己心动的内容,写生活中的真、善、美,写惊鸿一瞥后难以释怀的人与事,“不语怪力乱神”。怎么写?向中华传统文化学习,向李白、杜甫、白居易学习,向北岛、舒婷、顾城学习,向外国诗人、网络诗人、身边诗人学习,也向码头文化学习。“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比如说码头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汉口竹枝词”就很有意思:“六月天气热,扇子借不得。虽然是朋友,你热我也热”,有意思吧。“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学习是一辈子的事,但学习、借鉴不能丢掉了自己的本色,否则就成了大杂烩。我希望在不断学习、借鉴、探索、实践的过程中,保持自己干净、流畅、优雅的诗歌特色。
李羚瑞,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比较文学与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