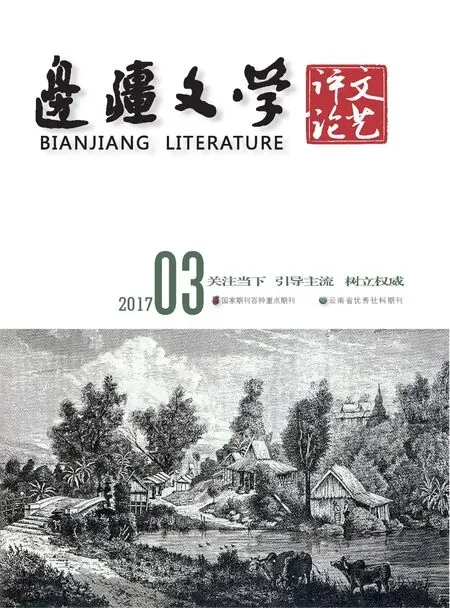浅析傅泽刚小说的审美特质
阿 传
浅析傅泽刚小说的审美特质
阿 传
傅泽刚曾是云南“红高原诗派”领军人物,但在沉寂多年后,却在2007年以小说复出。先后在《钟山》《十月》《中国作家》《人民文学》《小说月报》《山花》《边疆文学》等国内重要期刊发表了一系列颇具分量的中篇。尤其新近推出的《东方血线》(长篇小说),引发不小的关注。应该说,傅泽刚此次的复出,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了的,从其一系列的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些关键词:生态、环保、忧思以及诗意。下面,我就其近些年来发表的一些小说,简要谈谈作家在作品中存在的一些审美特质。
一、诗意的表述和忧思的人文主义关怀
在云南作家群中,有相当部分作家,都存在着这样一个“惯性”:即早年的出道,几乎都是以一种诗人的身份去叩开文学殿堂的大门的。比方前几年曾以《好大一对羊》荣膺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的夏天敏,以前曾长居昆明、现在《人民文学》从事着诗歌职业编辑与鉴赏的朱零,无一不是这样。个人觉得,诗歌和小说,存在着某种因果的联系——年轻时经验尚浅,文化积淀不够,这时的写作,通常表现为荷尔蒙挥舞下的一定才情的写作。这时,或许不能手捧诗人的桂冠去叩开诗歌的大门——但这过程似也很重要,至少在语言锤炼和意境搭建等方面,会为今后的创作奠定一定的基础。应该说,傅泽刚就属这一类。也许正是基于早年诗歌创作的习惯,傅泽刚的小说,语言总自觉或不自觉地为我们营造一种斑斓的意境,唤起读者对自然和田园生活的反思和迷恋。如《天堂鸟》一文中,在“我”和妻子办理离婚手续后,“我”对家便发出了一段几近“哲学式”的告白:“……家在何方,家在每个人的情感深处。那是一幅暖色调的黄昏景象,几只鹤鸟站立湖岸,芦苇丛中隐约可见一座残垣石屋,整个画面辉映在温暖的夕阳晚照中……”再有,也同样是《天堂鸟》,作家则是这样诗意的描述作品中那个“落雁山”的,“……落雁山锁在云雾之中,上了落雁山就到云雾之上了,所有的城市和凡俗的日子都沉入了下界,云海之上的落雁山是最接近太阳的地方,深沉而明亮,黑颈鹤就选了这块梵天净土靠水而居,当我们进入月亮湖区的时候,很难置信自己还在凡界……”这样的文字,灵动、清泠,流露出一种温暖、祥和的诗的气息,直抵闹市那些荒凉与芜杂的内心。
但此番傅泽刚的“重出江湖”,绝不仅是想通过小说这一媒介来实现自己关于诗学方面的理解,他应带有更大的“野心”和“抱负”。长篇《东方血线》,便是一例。批评家吴义勤在评价傅泽刚小说时说,“在自然大美中救治自我……并希望借此重新获得心灵的宁静与升华……”的确,无论是前面列举过的《天堂鸟》一文,还是《黑雪》,都流露出作家的一种忧思的人文主义关怀,流露出作家对云南本土的焦灼和迷恋。随着现代文明的飞速发展,人们一面不断向自然显示着自我的强大;一面又不断为自我设置着囹圄和创伤。在《黑雪》这个中篇中,颇具音乐天赋的小姑娘“乡雪”,因为长期生活在被污染被破坏的“乌岭煤区”,以致自己患上无法治愈的“肺肿病”。在作家笔下,“乡雪”无疑是作家苦心孤诣的一个“美和善良”的典型,可就这么一个“美和善良”的典型,就这么早早的夭折在我们日趋严峻的生存大背景下。读到这里,我们禁不住要扪心自问:假以时日,我们那“诗意的栖居地”到底还在哪?因而,就这一点来说,傅泽刚这篇小说的结尾,也可以说是一种几近寓言式的结尾,“……我说,别哭,我马上赶到。我刚调过车头,眼前突然一闪,一个响雷在我头顶炸开。”鲁迅先生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一个响雷”,与其说是“我”(云老师)不愿接受“乡雪”死亡时的心理错觉,还不如说是作家傅泽刚对“乌岭人”肆意索取和过度采伐的一记当头棒喝。
二、注重“生态环保”和地域化的“向内转”写作
谢有顺先生曾说,“这是一个向内转的时代。”那么,什么是“向内转”呢?照我的比较肤浅的理解——注重自我和人物内心发掘的写作,即为“向内转”写作。2007年自文坛“复出”以后,傅泽刚就相继在全国大型文艺月刊发表一系列以“生态环保”为主题的中篇小说。应该说,“生态环保”,是个比较热也比较大的主题,最易写也最不容易写好,稍不留意,就会陷入“概念化、教条化”的主题先行中去。面对这一“瓶颈式”制约,傅泽刚显然有着自己独到的“套路”和“理解”。云南是个“植物王国”和“有色金属王国”,这就为傅泽刚小说提供了一个阔大的生存背景。他的小说,要么通过主人公曲折离奇的运命关系,展现现代人与现代人彼此存在的一种隐秘和暧昧关系,如《天堂鸟》中画家的知青经历,画家与灵子以及梅三人之间扑朔迷离的关系;要么通过都市人对自然的忧思与敬畏,表现他们以期达到心灵净化和精神放养等复杂心理,如《一棵树或另一棵树》中的画家、《天堂读书声》的天琴老师、《风生水起》中的禾子、《天堂鸟》中的知青画家等,无不昭示着作家朝“向内”这一向度的努力和发展。
关注现实,关注脚下的土地和生存状态,这是文学赋予每个写作者义不容辞的使命。傅泽刚小说,在“众神”林立的当下,主题上可谓另辟蹊径,风格上可谓独树一帜。因为生于斯长于斯,故在“向内转”写作到“向外转”宣传这一“地域化”过程中,诗人出身的傅泽刚总不忘在构筑云南文化和生态地标时,打造云南秘境和人文疆域,同时,让生态意识和云南民族文化从细节与情感层面,进入文本。比如《黑雪》,“翻过一个山梁,我惊奇地发现,原本茂密的山林,渐渐变成矮小的灌木丛,最后连灌木丛也从原野上消失,本该红色的土地,已经变成了灰色,甚至黑色,我极想弄清其中缘由,所以决定前往乌岭……”这些文字,可说是带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浓厚的云南风情的。所幸的是,作家并没单纯停留在“生态恶化”的文字表面,而是借助迂回曲折的情节故事,巧妙地把“生态恶化”的事实潜藏于小说自身的内核中,并试图给读者造成一种强大的视觉冲击力和内心战栗感;同样,在《谁是小偷》一文中,作家则将小说发生的背景,直接放到了自己谙熟的昆明,“……窗外倒是通透极了,树动影摇,风在自由地飞翔,一路的抒情和浪漫,黄昏的光照中,路两旁的绿化带和花卉,及花花哨哨的广告门面,在急速的车窗外,幻化成流动的晚霞,待到霓虹灯眼睛一眨,昆明就相当妩媚和暧昧了……”难怪作家陈建功一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提到昭通作家群,我就想到了诗人傅泽刚,还想到了昭通籍国学大师姜亮夫及前辈作家艾芜……我是从读傅泽刚的诗认识云南昭通的……”因此,就这一层面来说,称傅泽刚是云南“向外”宣传的一张“名片”,我觉得也不为过。
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实验性”写作
傅泽刚是诗人出身,所以他的小说,一旦触及情景的描绘和意境的塑造,便会下意识的给读者呈现一种诗的意境和壮美。他小说的环境,重线条,重色彩,有鲜明的视觉美感和视觉冲击力。读罢之余,就会不自觉的陶醉在所设置的语言“陷阱”中。小说,说到底也依然是语言和情节的艺术。傅泽刚显然深谙这其中之理。傅泽刚小说的语言,因为总爱表现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的才情和禀赋,所以就连文本自身也总爱充斥着一种瑰丽的想象和强烈的个人抒情愿望。如“……我的窗户依然,所以我的西式油画框依然,不依然的是那幅以树为主景的画面荡然无存,就像一段往事被强行删改,取而代之的是那面水泥墙,墙面单调乏味,就像一块粗布糙料,或者一块灰白色膏药,贴到我视觉上,让我如同盲人。太阳躲到楼后面,窗外由此变得阴森,并且灰暗。”再如,“……疤子举起酒壶,对着夜空喝了一口,妈的,爽。有酒,这个夜晚就是快乐的。酒一下肚血气就上来了,他拿出一把匕首,习惯性地在空中比划了几下,刀锋把月光戳得千疮百孔,寒光飞溅,谁见了都会不寒而栗,都会想到血液、伤口和疼痛这些字眼……”
当然,作为一种激情的艺术,“浪漫主义”在小说的演绎和搭建等方面,难免会出现与这种“激情表达”相悖离的时候。比方小说讲究的是冷静和迂回,诗歌讲究的则是抒情与狂欢。所以通常情况下,高明的小说家一般都不会在自己的小说中去直抒胸臆或宣泄自己个人“观点”,有时即便为了一定价值取向,“观点”也会显得相对“模糊”和“隐秘”。傅泽刚小说,里面哪怕有时是关于“生态”的现实性描绘,作家也“固执的”表现作为一个诗人的浪漫和喜好,比如《水逝》一文中,在穿插“根爷”当年引“沙河”进“沟村”时,傅泽刚就曾作了这样的描述,“……一声怒吼之后,人们看到根山村长满脸是血,一脸的愤怒和绝望,身子一扭,又倒在河水中,那一刻,沙河四周的天地,在他倾斜的目光中,也颠倒过来,愤怒、绝望,甚至哀求,也跟着倒下了……”难怪评论家胡平在谈到此类现象时会说,“……傅泽刚过于诗意了些,我认为他还需要继续追索,使诗与小说达到完全的融合……”因而,就“实验性写作”这一课题来说,我觉得傅泽刚小说,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注释】
[1] 吴义勤《生态忧思与人文情怀——读傅泽刚小说集〈一棵树或另一棵树〉》
[2] 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全集.坟》)
[3] 谢有顺《小说课堂之九.内在的人》
[4] 艾自由《云贵高原璀璨的文学星空——解读昭通作家群与昭通文学现象》,(原载《中国文学》2011年第7期)
[5] 胡平《诗与小说的融合——读傅泽刚小说集〈一棵树或另一棵树〉》
(作者单位:昭通镇雄县堰塘中学)
责任编辑:杨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