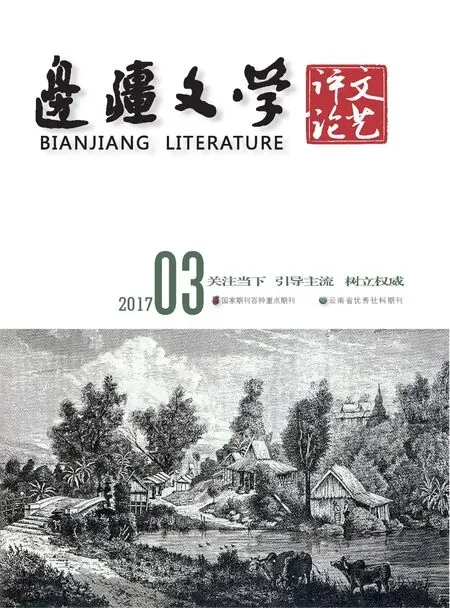《野草》的超越虚无之路
任瑞卿
《野草》的超越虚无之路
任瑞卿
虚无主义是我们定义世界和理解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在这种方式中,生命是一个表象。在鲁迅的哲学中,虚无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而代表了其所有哲学的《野草》正体现了鲁迅虚无的本质。“反击/超越”的生存虚无,成就了鲁迅的哲学思想,也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化中最富有创造性的哲学。本文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围绕《野草》文本从体认与超越两个方面分析鲁迅的超越虚无之路。
一、苦难/黑暗/虚无
《野草》向来被人们认为是鲁迅最为晦涩的作品,毫不夸张地说,《野草》也许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最为幽深诡丽的文集。鲁迅曾经表示他的哲学都包括在他的《野草》里。说鲁迅的哲学,并不是说鲁迅是作为专业哲学家的存在——自觉提出一套有逻辑体系的思想结构出来。之所以说鲁迅的哲学是因为他意识到了生命的某一种境遇,意识到证明中的某一个问题。虚无是一个价值论的问题,是生命中没有意义价值的生存状态的称谓。而所谓虚无体认则是对于这一没有意义价值的生命状态的自觉意识,与之相伴,才会有“反抗/超越”生存虚无的生命创造的出场。同时,意味着自我生命觉醒意识与创造意识的虚无体认,往往是对某种既有的现成意义价值信条的无情揭露和积极否定。在鲁迅早期的创作《呐喊》《彷徨》中,他对于自己意识到的虚无问题迂回、缠绕,吞吞吐吐、欲言又止,一直止于隐喻暗示,而不得以正面集中的言说。正如那个著名的“铁屋子理论:”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吗?
在《野草》中,鲁迅开始了对自我生命虚无的正面冲击。《野草》未发表之前,鲁迅从未在作品中直接宣示:“我不如彷徨于无地”、“唯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可以说《呐喊》《彷徨》中的多数作品,一方面固执地承载着鲁迅在长期“沉默”中所持有的虚无感和绝望感;另一方面又同时展示着鲁迅开始对峙自我生命的虚无,试图反击自我生命虚无的精神律动。而到了《野草》时期,鲁迅已经走到了正面反击,超越自我生命虚无反抗的重大时刻。经由对虚无的正面体认与集中冲击,鲁迅最终再度“出世”,他超越自我生命虚无,创造自我生命意义,反抗“苦难/黑暗/虚无”人世界。《野草》中的哲学是富于它自身的内在性隐秘性的,《野草》不断或暗示或直白呈现着创作主体鲁迅所意欲透视、对峙或反抗超越的对象。在《野草》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充盈着人间苦难与生命虚无的世界。但是“野草世界”的核心主题是虚无,是对于生存虚无的透视与对峙,尤其是“自我”对于虚无的反抗与超越。
二、言说与体认
“虚无”这个词最早来自于拉丁语,意为“什么都没有”。我们在《野草》的许多篇目中发现大量关于虚无的言说,如在《影的告别》《求乞者》《复仇》《希望》等一系列连续的篇目中,鲁迅反复使用到“黑暗”、“虚空”、“虚无”、“无聊”、“绝望”、“虚妄”等字眼,从这些词语的频繁使用上可以看出,再明显不过地向我们表露了他直指虚无而言说的自觉意识。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然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
朋友,我不想跟随你了,我不愿住。
我不愿意!
呜呼呜呼,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
……
我能献你甚么呢?无已,则仍是黑暗和虚空而已。但是,我愿意只是黑暗,或者会消失于你的白天;我愿意只是虚空,决不占你的心地。
我愿意这样,朋友——
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
这是鲁迅《野草》中最早正面言说虚无的文本,这里蕴含着一种积极主动生命求索的意志。“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我”宁可独自面对虚无,也决不向自身不愿意停留的地带妥协,这是对环境秩序中的既定价值体系,价值信条的否定。不认可他人所谓的天堂,黄金世界,更遑论地狱了。正因为你们那里有我所“不乐意的”,“我”便决意不去。在这里,我们便可看出鲁迅正面质疑和否定现有环境秩序的积极意志。
紧随其后的是《复仇》和《复仇》(其二),这两篇同时作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复仇》和《复仇》(其二)虽然不是直白的虚无言说,却可以看作是虚无的生动形象的画面转述。《复仇》是先于小说《示众》更为凝练的散文诗文体,同样展示了虚无中的众生本相,弥漫着生命存在的虚无。在文本中有着近乎直白的表现:“他们俩将要拥抱,将要杀戮”,“路人们从四面奔来,密密层层地,如槐蚕爬上墙壁,如蚂蚁要扛鲞头”,“衣服都漂亮,手倒空着”、“在广漠的旷之上,裸着全身,捏着利刃……他们俩这样地至于永久,圆活的身体,已将干枯,然而毫不见有拥抱或杀戮之意”,“路人们于是乎无聊;觉得有无聊钻进他们的毛孔,觉得有无聊从他们自己的心中由毛孔钻出,爬满旷野又钻进别人的毛孔中……甚而至于居然觉得干枯到失了生趣”。在这里,路人完全以他人的生死,爱恨情仇,相爱相杀,将任何可以看的东西都作为他们混沌无聊的人生短暂的食料,他们的生命完全是空洞的无聊的,毫无存在的意义。鲁迅在《〈野草〉英文一本序》中谈及《复仇》时提到:“因为憎恶社会上旁观者之多,作《复仇》第一篇。”由此我们似乎可以看出鲁迅对周围的“看客”,这堆无聊的“路人”深恶痛绝,“他们俩”也正是以这么样静默的站立“也不拥抱,也不杀戮”的方式去回馈挤着看热闹的“路人们”,去报复他们。不过至此,如果你将旷野中的“他们俩”与“路人们”看作是一种对峙关系的存在的话,那只能说明你并没有从本质上看清“他们俩”与“路人们”真正的生命存在的方式。虽然“路人们”的确无聊,但毕竟“他们俩”既不相爱也不相杀,从始至终毫无动作,只是那么样“捏着利刃,干枯地立着;以死人似的眼光,鉴赏着路人们的干枯”。在虚无的路人的围观中,“他们俩”也一样处在生命的虚无当中——即便“他们俩”意在报复路人,但终究也逃不脱虚无的状态,本质上依旧与混沌的“路人”同处于虚无的本质中。在与虚无的围观者本质上区别开来的是《复仇》(其二),耶稣作为《野草》中超越虚无的第一个生命创造者出现了。如果说在《复仇》中只是体现出干枯无聊,碌碌无为的消极生命状态,那么《复仇》(其二)看上去则“积极有为”。从开头我们便可直观地感受到他们这群人的热闹忙碌,兵丁们给他穿上紫袍,拿苇子打他,吐他,屈膝跪地朝拜他。做完戏又把他衣服给脱了,给他喝没药调和的酒。但实质上他们确是在血腥暴虐的言行中上演了生命的虚无。他们凌辱、钉杀了那个最爱他们的人,那个最希望他们能生活幸福,彼此相爱的人。人性本恶,耶稣来到人间本是为了拯救这些有着戴罪之身的人类,他用自己的身体代替全人类的罪,可未曾想却遭到人类的围堵和杀害。表面看来人类钉杀耶稣无关自己,实际上他们钉杀的正是他们自身,他们已经把他的生命和他们自己的生命都毁灭了——“钉杀‘人之子’的人们的身上,比钉杀了‘神之子’的尤其血污,血腥。”
而耶稣并不仅仅是在暴虐,自私,恶毒的人性之恶中简单地死去,并且是在人心的死寂、混沌中,在生命的昏昧无知中,在一个生命虚无的人间被人们充满成功喜悦地给“钉杀”了。对此,鲁迅也有着鲜明的提示。“兵丁们给他穿上紫袍,戴上荆冠,庆贺他;又拿了一根苇子打他的头,吐他,屈膝拜他;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紫袍,仍穿他自己的衣服”,“路人都辱骂他,祭司长和文士也戏弄他”,就连“和他同钉的两个强盗也讥诮他”。“十字架竖起来了;他悬在虚空中”“遍地都黑暗了”。于是耶稣在“虚空”中,在“遍地”的“黑暗”中走向了死亡。这里的“虚空”指的是空洞混沌的生命,“遍地”的“黑暗”是指生命之光的寂灭。但我们在《复仇》(其二)中分明可以看到耶稣是作为“大爱”之人而存在的,正是基于这一点,耶稣成为了其生命意义的创造者。无论蒙昧的人类如何对待他,他总是“悲悯他们的前途”,“仇恨他们的现在”,不论怎样,这都是对人类的至爱。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仍然希望人类能够醒悟意识到并更正自己的行为。因此,《复仇》(其二)不仅表现出混沌蒙昧下人们虚无的生存状态,而且也体现出创造的价值,闪耀着生命的光辉。
三、反击与超越
其实在《复仇》和《复仇》(其二)中,鲁迅其实已经表现出与整个虚无世界的对峙态度——而不仅仅停留在对虚无意义的体认上。在《复仇》中,“他们俩”以“不作为”的姿态——不拥抱也不杀戮去迎击奔驰而来的路人们。但这种“不作为”是以自身的虚无为前提的,以此去报复那群无聊同样处于虚无状态的“看客们”。在《复仇》(其二)中,耶稣作为“神之子”的存在,他开始拒绝喝下那用药调和的酒,他要看清楚这群人类是如何对付自己的,他要借痛“玩味”,他要清楚地记忆那钉尖穿透身体,他要清醒地感受这彻骨的痛楚,绝不会借“没药”忘却了虚无的人群和混沌的世界。
到了《希望》中,真可算得上是鲁迅正面迎接虚无,并以战士的姿态面对他,开始公然挑战它的一个小高峰了。这是对没有爱憎、哀乐、颜色与声音的平安的不满,如此静穆的平安在某种程度上依旧是一种虚无的状态。但“我”作为一名战士,如何能忍耐这生命之光的寂灭?“我”的心分外地寂寞,“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我只得由我来肉搏这空虚的暗夜了,纵使寻不到身外的青春,也总得来一掷我心中的迟暮。但暗夜又在那里呢?……青年们很平安,而我的面前又竟至于并且没有真的暗夜”“绝望之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向我们传达着一种思想:人们常常不自觉的处在虚无中。“暗夜又在那里呢?”“青年们很平安,而我的面前又竟至于没有真正的暗夜”,却不说青年人面对眼前的虚无毫无察觉,就连我自己身在其中,也常常并不觉处在虚无。这种处在虚无而不自知的状态在鲁迅的《复仇》中也可以看出。在《雪》中写到江南青春般的雪野以及孩子们手塑的罗汉,将暖国的雪与朔国的雪做一对比,不似暖国的雪,“朔国的雪花在纷飞之后,却永远如粉,如沙,他们决不粘连,……在晴天之下,……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雪》 与开篇的《秋夜》写法十分接近,都是借以描写周边的自然景物隐喻所要表达的深层意蕴。而《风筝》则写了“我”阻止正十几岁的小兄弟放风筝以致将他正在糊着的风筝骨折断,多年以后我谈起儿时旧事想要请求兄弟的原谅,得一句“我可是毫不怪你呵”以求心安,可小兄弟竟像听别人的故事似的,早已忘记。由此道出了“我”对于20年前的一幕精神虐杀的不安,以及在自省与悔悟中的我,面对当年的被伤害者小兄弟早已完全忘却我所谓精神虐杀时的悲哀。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一个明明自己身受伤痛却全然忘记的生命个体与《复仇》中忽视他人生命混沌的虚无生命距离又有多远呢?如果一个连自己受过的苦难与伤痛都无法铭记的人,那么他也不会有长期坚守生命的勇气与意志。
在《希望》之后的《雪》《风筝》等篇的短暂过渡之后,就进入了鲁迅真正对抗虚无的阶段了。其中《过客》体现出作者那种对自我生命意义价值创造的追索。《过客》中的“我”没有名字,只知道一路向前走,不愿意回到从其来的那里去,就这么一直往前走却不知哪里是终点,何处是尽头。“我”要“走完”那坟地,“我”想知道走完这坟地之后的情形。在海德格尔的哲学中,我们知道“坟地/肉体死亡/精神虚无”间的内在联系,那么“过客”事实上就是想要走过坟地,穿越“肉体死亡/精神虚无”,期待虚无之后的世界。但是走过精神虚无之后的世界到底是怎样的?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过客”不愿回到“那里”——没有一处没有名目,没有一处没有地主,没有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有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有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我”只得走了。至于《过客》中呼唤“我”的声音是什么?笔者认为应该是跨越时空的呼唤,呼唤着人们穿越死亡与虚无,创造出活着的意义。“过客”不停地往前走,前面是还没有抵达的坟地,而那声音正是虚无世界之后的新世界的旋律,但要追寻这旋律绝非易事,你首先需要抵达坟地,失去肉体,在虚无中披荆斩棘方能抵达虚无之后的新境界,但这新境界又以何种面貌示人,是更好还是更糟的世界,没人知道。所以当“过客”问及老翁是否听到过这样的声音,老翁的回答是:“他似乎曾经也叫过我”,“他也就是叫过几声,我不理他,他也就不叫了”。可见一个人要想达到虚无的彼岸,不仅要有穿越障碍的勇气,还要满怀希望与憧憬,对终点有着不悔的信心。前面是什么地方?在小女孩看来,“那里有许多许多野百合,野蔷薇”而老翁说那里有坟地,只有“过客”不这么看,前面既有可能是鲜花盛开的地方,也有可能是坟地,但无论如何“我”都会走下去。“我”所期待和希冀的是坟地后面的世界,而穿越了坟地的新世界正是一个穿越了“死亡/虚无”的生命世界,是一个经历了彻底的否定与虚无之后,再度闪耀生命之光的全新境界,为生命价值的创造凸显出真正的路径。
(作者系云南民族大学2015级现当代文学研究生)
责任编辑:杨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