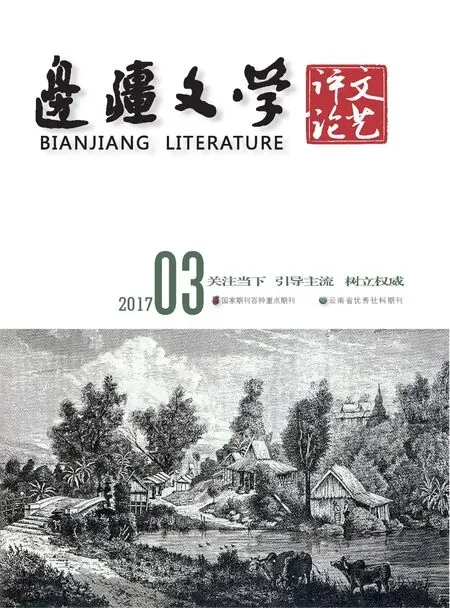纳张元散文中的赤子情怀与民族隐痛
农为平
纳张元散文中的赤子情怀与民族隐痛
农为平
诗人荷尔德林在《故乡》一诗中曾说:“我是大地的儿子,我拥有爱,同时我也拥有痛苦。”作为一名倾心自然山水、热爱故土的诗人,荷尔德林的爱是朝向自然、故乡、神祇的,同时又忧虑于人类本性的迷失、精神家园的失落,这样,爱与痛苦,很自然地构成了荷尔德林诗作的核心情感意蕴。在云南乡土作家中,纳张元常自称是大山的儿子,在他的散文中,类似爱与痛苦这样一对既矛盾又谐和的情感诉求同样充溢其间,只不过在具体内涵上有所偏移:一方面抒发对故土的深情眷恋,一方面也直面它的贫瘠、落后,表现出深沉的忧思与一定的批判精神,这种内在精神取向使得他的散文具有丰富内涵而极具情感张力。
一
作为一名从偏远大山深处走出来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纳张元对自己的故乡、民族始终怀有特殊的感情,这从他的文学创作中即可窥见一斑。不论是小说、诗歌还是散文,总有山风乡情扑面而来,地域倾向极为鲜明,故乡彝山的人、事、风物一直是其中的核心、重点,是源泉也是旨归所在,影响并决定了作品的主要情感走向,这使得他的创作裹染上了浓郁的边地氛围和民族气息。
一般来说,乡土作家们常常会有意无意地在创作中构建一个专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乡土世界,借以表达情愫,抒写心志,譬如鲁迅的未庄、废名的黄梅小镇、沈从文的湘西、福克纳的约克镇、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马孔多、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商州大地……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具有作家鲜明个性的地域书写,已在无形中成为一种作者自我的符号和标记,也常被作为衡量乡土文学成功与否的标准之一。纳张元的散文给人留下的一个鲜明印象即是其中鲜明而张扬的地域色彩,“彝山”、“大山”、“千里彝山”是频频出现在他笔端的地域词汇,也是散文中的主要书写、观照对象。对于作者而言,“彝山”是场域,是家乡,更是情感寄托之所在;而对读者来说,“彝山”是一个带有异质色彩的阅读、体验、审美对象,充满新奇和神秘,让人情不自禁地意欲探究其里,而在阅读之后,脑海里已不知不觉存留下一个古老而顽强、荒凉而坚韧的彝山形象。从这一点说,纳张元通过文字成功地构建了一个极富鲜明地域特性的“彝山”乡土世界。
山,作为一种自然界的客观存在,给人的印象多是巍峨雄伟之类的视觉感官感受,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凸显的是泰山的雄奇高峻,苏东坡感喟“不识庐山真面目”,慨叹的是庐山的丰富多姿,他们的文字,在历史上深深镌刻下了这些大山的卓越风姿。纳张元笔下的彝山虽不能与泰山、庐山这样的名山相比肩,然而自有其个性特色。“千里彝山,枯瘦如柴”(《山寨岁月》),“整座彝山瘦骨嶙峋”(《彝山速写》),“似卧牛、如睡狮、像走蛇,一座座奇形怪状的大山挤在一起,构成了连绵起伏,蜿蜒曲折的千里彝山”(《秋天的困惑》)……作者善用极简洁的文字描摹彝山,“枯瘦”、“嶙峋”、“挤”、“连绵起伏”、“蜿蜒曲折”等词汇,栩栩如生、生动传神地勾勒出彝山的形貌来,读之使人如临其境,如睹其容。很显然,彝山既非高林大木密布的崔巍高山,也非草木郁盛的灵秀山峦,它陡峭、险峻、荒凉、寂寥,重重叠叠,绵延不绝,既不同于陶渊明笔下“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纵横,鸡犬相闻”的理想家园,也迥异于莺飞草长、芳草萋萋的江南沃野,它粗粝狂放、原始古朴,充满不羁野性。天空里盘旋的是苍鹰矫健的身影,树林草丛是各种蛇类的乐园,庄稼在贫瘠的土地上顽强地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人类显得渺小无力,大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主宰者。正如作者的感慨:“生在山中,从小与大山结缘,抬头低头,睁眼闭眼,都是山。近处是山,远处是山,直到看不见的地方还是连绵不绝拥挤不堪的群山。山与山之间是令人头晕目眩的深谷,谷两边的人可相互问话,有时甚至能看清对方叼在嘴上烟斗的模样,却走得腿肚子转筋也到不了对方所在处。”(《城市牧歌》)“那山陡得连猴子过山都要淌眼泪,岩羊下山也要滚皮坡,一条山草绳一样细细的小路,弯弯曲曲地挂在壁陡的山腰上,行人像壁虎一样贴着悬崖小心翼翼地移动,稍不留心脚下轻轻一滑,人就像鸟一样在峡谷中飞起来,一直飞下万丈深渊。”(《父亲的三双鞋》)
严苛的生存环境,注定了彝家人生活的艰辛,命运的多舛,“先民们祖祖辈辈就在这丛山峻岭中讨生活,世代相传,生生不息”(《城市牧歌》),“火塘像一个魔鬼的怪圈拴住了一代又一代想向山外挣扎的人,苦难的先人用追赶麂子的速度跋涉了一生,累得脚杆露筋,最终还是在那个冒着浓烟的百年火塘边打转,悠长的岁月像一个魔力无穷的魔术师把无数血气方刚的彝家汉子揉搓成皱巴巴的干瘪老头”(《永远的红房子》),大山困住了一代代彝族人的脚步,遮蔽了人们对生活的美好希冀和幻想,但是也赋予了彝山人如山一般朴实爽直的性格和坚毅顽强的生活品格,他们把根深深扎入大山,在贫瘠的土地上辛勤劳作,耕耘着微薄的希望,“千里彝山每一片壁陡贫瘠的山地,都布满了牯牛们世代耕耘的足迹,彝山的高坡深谷至今仍回荡着牯牛们急促的喘息声和彝家汉子悠长的吆牛声”(《彝山速写》)。作者的父亲就是一个能干且倔强的典型彝山汉子,“他年轻时,走路飞沙走石,没人敢走在他前面。他曾凭着三尺多长的一截酸楂树棒棒,与一头大公熊搏斗,从太阳偏西一直厮打到天黑,双方都精疲力竭,谁也胜不了谁”,(《父亲》)生产队时代,他用两条大牯牛犁田,犁一条,休息一条,这条不行了,再把另一条换上来,牛休息,他不休息,最多灌几口黄酒解乏,最终活活累死了一条大黑牯。而村里那些须发俱白的老汉们聚在火塘边回忆早年赶马帮的经历时,却是像小孩子一样容易流泪,他们都说,年轻时太要强,把眼泪都往肚子里咽,现在需要补偿一下。面对民生艰辛,杜甫常怀“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之感,在纳张元的文字里,可以感受得到他对生活在彝山的父老乡亲的眷挂、敬重,同时也很自然地流露出对他们所遭受的苦难生活的同情与悲叹。
二
纳张元散文的主要描写对象是千里彝山,但又并非单向度地进行观照,在他的书写体系中,可以明显感受得到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话语方式,或者说他常常通过一种对比的形式来呈现乡土生活,即城市与乡村的对比——尽管这种对比往往是无意识的。毕竟,作者已经是与自己的祖辈父辈有所区别的新一代大山人,重叠的大山已经阻挡不了这一辈人对热闹繁华的山外世界的向往,正如作者所说那样:“到了我们这一代,突然打破了先人们几千年来的生存法则——不再寻找森林,不再向往高山峡谷,而拼命辨认那些蚂蚁脚杆模样的汉字,以期挤进充满现代文明的城市,与城里人站在同一地平线上仰望高空,傻看日月星辰。”(《城市情怀》)第三代诗人韩东曾在其有名的诗作《山民》中表达了不满于现状,急欲超越父辈、追求改变的热望,这首诗歌可说正是纳张元这一代人的真实写照。时代的变迁,外界新气息的诱惑,已使得他们不再甘于重复父辈的老路,不再屈服于命运,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挣脱了“像魔鬼怪圈”的火塘,冲出大山的重围,走进都市,过上了另一种新的生活。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城乡在不断碰撞中交融的结果。然而对于裹卷进另一种形态的人们——尤其是像纳张元这样第一批真正走出彝山的人来说,注定会遭遇来自生活和精神上双重的不适应。城市与乡村两种文明形态的差异与对立,必然会投射进他们的目光与思想之中去,并由此形成矛盾、困惑,甚至是对异质文化的反感与排斥。这种症候,在很多乡土作家的创作中都有所反映,最为典型的就是沈从文。在他的作品中,湘西小说与都市小说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话语体系,作者的爱憎界限分明,鲜明地表现出他试图用淳朴本真的传统文化对抗现代文明异化的文学审美理想追求。由于时代语境的差异,纳张元所面对的社会自与沈从文的时代有着诸多差别,但城市与乡村两种文明形态之间的对立依然存在,两种差异甚多的生活形态必然会在当代乡土作家的文字里发生碰撞,促使他们思索并反思。这种内在的驱动很自然地形成了纳张元散文创作中的两种导向:一是对乡土生活的深情回顾,一是对都市生活的冷峻批判。
俗话说,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对于外界来说,彝山也许只是一个地域符号,是荒凉贫瘠之所在,而对于作者而言,彝山是生养自己的故土,是沉甸甸的情感堆积。那里有情深义重的亲人,有忆不尽的悠悠往事,因而对家乡人、事的描写自然成为纳张元散文中的一个重要维度。他写父亲、母亲、爷爷、儿时玩伴、父老乡亲,他写故乡沉默的大山、沧桑的古树、翱翔的苍鹰,回忆童年趣事、放牧经历、求学历程,也写彝家独特的打歌、对歌等民俗文化,字里行间充溢着真挚的情感和深深的眷恋之情。而另一方面,作者毕竟是已经走出大山融入现代都市生活的知识分子,都市生活不可避免地成为他观照的另一个对象,但是可以明显感受得到,作者在这方面的着力甚轻,叙写的痕迹较浅,更缺少深入细致的描写。在更多情况下,他仅仅是把都市作为乡村的一个对立面而呈现,写到的也多是对都市文明中一些阴暗面的批评。作者直接表达他对于现代化对人类生存、生活方式所造成的摧残和异化的反感,对都市人孤独灵魂的深刻审视,感叹“有些人在住进越来越高的高楼的同时,人格也越来越变得猥琐卑微,他们一方面粉脸笑迎四方客,另一方面却津津乐道于厚脸皮黑心肝的官场斗术的研究。人格分离已经成为一种像感冒一样普通的传染病。”并坦言,在经历了真正的都市生活之后,“我才惊讶地发现:城市不是我的家。我的民族造就了我一副土头土脑的农民模样,我固执的农民脾气与这个城市格格不入。”(《城市情怀》)这确乎近似于沈从文反复强调自我的“乡下人”身份。二者之间虽有主客观上的差异,但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他们都视乡村为淳朴自然之所在,反感于吞噬人性本真的都市的奢华与矫饰。这种不无偏激的对抗本身蕴含着作家对淳朴宁静的田园生活的向往,对真实自然的美好人性的呼唤。正如沈从文宣称要建造人性的希腊小庙一般,纳张元也直言自己的文学追求:“我不止一次体味到,物质享受与精神追求是游离的,命运常常把人置身于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让人在夹缝中生存。一方面,对于现代文明的诱惑,我们无法拒绝,另一方面,我们的灵魂常常无法适应喧嚣嘈杂的生存环境,而游离背叛肉体,四处漂泊,去寻找宁静祥和的精神家园。但真正的精神家园是子虚乌有的,每次寻找,都只是一种简单的回归,于是,地老天荒古朴苍凉的千里彝山常常成为我反复吟唱的精神乐途,大山和子民是我赖以生存的唯一精神寄托。”(《城市情怀》)可见,作者在文字里对故土一遍遍的书写,已不仅仅是纯粹的回忆、怀念、留恋,而且还潜藏着更为深层的精神还乡、灵魂寄托的旨归。
可以进一步指出的是,这种思想倾向并非现代产物,而是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老子反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醉心于小国寡民理想社会的营造;屈原不满时政混乱,在汨罗江畔孤独苦吟;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退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王维退出尔虞我诈的官场,在辋川念佛吟诗作画……总体而言,这种追求难免有与时代相违的消极保守层面,但其中所传递的避恶向善的共性追求,依然具有可取的积极意义。尼采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说:“我爱那些大轻蔑者。因为他们是大崇拜者,射向彼岸的渴望之箭。”
三
在城市——乡村两种文明形态对立的格局中,纳张元虽然明显地偏向乡土社会,但他也并非如沈从文那般为反对人性异化而刻意为乡村唱赞歌,他的情感表达显然要复杂得多。一方面,他肯定乡土生活的古朴自然,人性的率真朴实,无违于天道人情,而另一方面,他也不可避免地用深受现代文明熏染的眼光来烛照自己无比熟悉的乡村世界,从而发现了其中所潜藏的种种落后弊端——这是由于历史、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所造成的。所以在下笔书写时,他必然面临着微妙的情感分裂:浓浓的乡情与清醒的批判意识。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像鲁迅那样成为乡土社会彻底的批判者,还是如沈从文那般站在都市的对立面全力维护乡土社会?纳张元并未极端地进行判断选择,而是采取顺其自然的方式,任由情感的波涛自由地流淌,因而在他的散文中,时而是深情的回顾,时而又悲怨叹息甚至不时闪现批判的犀利锋芒。这样的处理方式难免会给人造成一种情感态度前后不一、行文不够严谨的印象,但并无损于作品的品格,因为从中可以感受得到作者内在情感的纠缠、复杂与矛盾,情感表达更显真实细腻,使文字更具张力。
作者满怀思乡之情,同时也痛心于家乡的荒凉凋敝,“那些苍凉悠长的岁月,像一把朽钝汗腻的篦子,在蜿蜒如大蛇的千里彝山上反复梳刮,整座彝山瘦骨嶙峋,树木稀疏如百岁老人的牙齿,连跳蚤都为无处栖身而发愁,以致神经衰弱。那些关于打虎猎熊的壮举,早已成为老辈人向晚辈夸耀自己的童话,笨重的火枪高挂在黝黑的墙壁上早已积满尘灰,祖先们和野兽赛跑的脚步声早已是空谷足音。”(《彝山速写》)尽管父老乡亲辛勤劳作,日子却是逼仄艰辛,“我老家的山民们几乎都不穿鞋,一方面是大家都很穷,穿不起鞋。但主要原因还是山高路险,有鞋也穿不成”(《父亲的三双鞋》)。当然,作者也不避讳家乡的落后与人们精神的困顿:小镇破旧肮脏,人们随地大小便,成群的苍蝇蚊子嗡嗡乱飞,嘴尖毛长穷凶极恶的癞皮狗在小镇上四处乱窜,不顺心时会莫名其妙地咬人,让人心惊肉跳。生存环境的恶劣与生活的贫困,早已使人们驯服且麻木,作者返乡时,“寨子里的人们一个个老青猴似的蹲在路边的石坎上,傻乎乎地仰着没有表情的脸,睁着迷惘的眼睛,痴痴地看着我。古寨人不会看人,这我是知道的,但他们毫不含蓄的目光仍然让我陌生和不适应。他们急促的喘息声好像是夏日里疲倦的耕牛,咽口水的喉结响动声如同吃过巴豆后的腹泻。有一个婆娘说了一句很下流的话,逗得大家一齐笑起来,笑声像在大铁锅里洗碗。”(《远去的故乡》)山里的日子贫乏枯燥,酒成了极佳的精神麻痹剂。男人们把山里的粮食、水果背到山镇上卖了之后,钻进路边的小食馆喝得酩酊大醉,有的倒在路边人事不省,舔食他们呕吐物的狗也醉倒了。在一篇名为《走出寓言》小说中,纳张元用写实的手法进一步状写古寨的日常生活情形:人们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男女在房前屋后随意方便时若无其事地打招呼,女人们忙着生火做饭,一个个眼屎巴秋衣冠不整的汉子则坐在寨子边的石头上哈欠连天地烤太阳,捉虱子。从这样一幅图景里,读者不难读出其中所包蕴的信息:落后、麻木、困顿。作者这种直面现实、自揭短处的做法,并非为满足读者猎奇的心理,而是隐含着深沉的民族隐痛,也寄予着作者启蒙的热切希望。鲁迅先生曾毫不留情、鞭辟入里地直陈国民劣根性,对愚昧的民众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所谓爱愈深则恨愈切,在他犀利的文字下涌动着大爱的潜流。显然,纳张元继承了这样的批判启蒙传统,他对本民族沉疴的不留情揭露,“主要源于纳张元强烈的民族身份意识及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他看到了民族传统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为民族的未来深深忧虑。”
在直陈民族落后面的同时,纳张元也意识到一些属于大山、属于民族的美好东西正在慢慢地消失,令人惆怅心痛却又无可奈何。在民族的古老传说和古歌中,彝族的先民曾在密林中打虎猎熊,与野兽赛跑,是何等神勇。而如今,彝山已是瘦骨嶙峋,树木稀疏如百岁老人的牙齿,打猎的弓箭高挂在墙壁上,早已落满灰尘;彝山的汉子们也渐失血性,很多人懒惰,酗酒,无所事事。彝山古老的打歌,是彝家人的集体狂欢,也是青年男女交际的重要方式,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借打歌传情达意,寻觅意中人,但作者不无遗憾的发现,近年来彝山的小伙子姑娘们都纷纷进城打工,春节回家每个人都捏着一个稀奇古怪的手机。他们通过打电话、发短信来谈情说爱,吵架骂人,不再借助打歌场来交际,他们到打歌场纯粹只是为了凑热闹。除了生活方式、民俗文化在变异,彝家人世代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也不断遭到破坏。广袤的彝山曾是鸟兽的家园,百鸟大战的故事至今依然在山民们口中津津有味地流传,翱翔长空的雄鹰是彝山最生动的点缀,它们孤独而高傲。在《远去的鹰影》一文中,作者的父亲曾捕捉了一只鹰,但它不吃不喝,每天用阴鸷的目光冷冷地看着人,最后绝食而死。父亲把鹰皮挂在菜地里吓唬鸟雀,却遭来鹰群对家禽的轮番攻击,最终作者的爷爷把鹰皮送到山顶的一棵大树上,鹰群才停止攻击。由此可想而知,那时彝山的自然界是充满勃勃生机的。可是,随着刀耕火种的砍伐声,森林成片倒下,老虎、熊等动物渐渐在彝山消失了踪迹,天空中也失去了鹰雄健的身影。“自从天空中没有了鹰,风调雨顺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不是久旱不雨,就是恶风暴雨。天空无鹰,不仅是鹰的不幸,也是人类的不幸”,“那些鹰击长空的美好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留给我们的是疏离远影,唯余慨叹。在没有鹰的日子里,寂寥的天空格外苍白浅薄。”(《远去的鹰影》)作者慨叹的不仅仅是鹰的消逝,更是对生态环境恶化的深切忧虑。自从人类社会迈进工业化时代以来,对大自然的破坏日益加剧,人类的生存环境危机四伏。在偏远的千里彝山,现代化仅仅显示了模糊的身影,但由于生产生活方式的落后,依然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面对家园的变迁,作者一方面感到惆怅、痛心,“我本能地感觉到,离我远去的并非仅仅是童年时代的生活,我分明感觉到整个故乡都已经离我越来越远”(《远去的故乡》),另一方面仍在充满希望地呼唤:“那些曾经在千里彝山上空缓缓盘旋的高傲身影,你们现在在哪里?”(《远去的鹰影》)
海德格尔曾说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其实,岂止是诗人,对于每一个优秀作家来说,在倾注了情感的文字背后莫不饱含着或隐或显的还乡企愿。纳张元散文最朴实也是最动人之处,就在于作者虽然游走于都市与乡村之间,却始终不忘初心、本心,执着地在文字里搭建还乡之路,一路追寻精神家园,努力去亲近最真实的人性本源。
【注释】
[1] 尼采,《查斯图斯特拉如是说》,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第85页。
[2] 陈思和等,《漫谈大山里的文学——纳张元作品研讨纪实》,《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03期。
[3] 彝族一种踏歌起舞的民间广场集体舞蹈,是彝家人喜庆的集体狂欢。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杨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