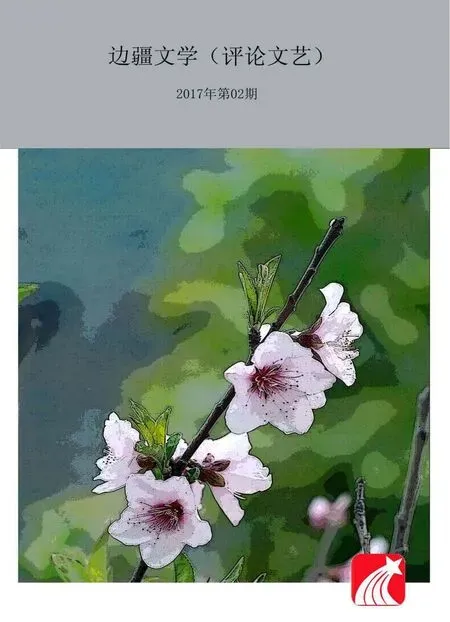千灯有影,众陂成平
——读谢轶群文化批评论集《千灯有影》
李文炳
新锐批评
千灯有影,众陂成平——读谢轶群文化批评论集《千灯有影》
李文炳
·主持人语·
本期“新锐批评”发三篇书评,三位作者都是有心的读书人。云南的年轻评论家谢轶群新近出版了文化批评论集《千灯有影》,很快引起了不凡的反响,并进入“云南好书”评选。李文炳做了深入的解读,可以说切实地抓住了这本书以及谢轶群的批评特征。熟悉谢轶群的读者读这篇文章常会有会心一笑之乐,不熟悉谢轶群的读者读罢此文再去读《千灯有影》,会对谢轶群有更丰富的认识。因为谢轶群的那桀骜不驯,激扬文字的神态已经跃然纸上。徐霞也对谢轶群这本新著情有独钟,这篇评论更偏重于对作品的解读,兼及作者,更多地体现出图书编辑的特色。我们往往对文艺作品给予关注,对评论家及其论著则少有关注,其实,这是很不应该的,对年轻的评论家应该给予更多的及时的评析,由此推动云南文艺评论的健康发展。《飘动的云》是张永刚新出的诗集,刘建国给予了及时的评论。张永刚在繁杂的行政事务和教学之余还始终不忘诗心,尤其难得。刘建国对这本诗集的解读有他的独特之处。(宋家宏)
房屋在地上建成一个事实之后,众人参观,一看大多明白。就算傻子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评点:这里偏了,那边矮了——说实话,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对艺术家与批评家关系的理解,一度仅仅停留在这样的层次。
不因举烛,便自高明,囿于萤火虫般的识见而自以为是,本身即是痴暗。
是的,在原创性严重不足的当下,真在建房的只是极少数,如果让众多的评点者来架房构屋,他们确实可能连鸡窝都搭不起一个。相比于文艺作品的生动饱满,大量评论文章我弃之不读,原因也多半在此。
但如今,经验和观念都要改写了:真正的批评家与真正的艺术家一样难得。
批评家谢轶群先生新出版的文化批评论集《千灯有影》,可能将彻底更新普通人对批评家的一般见识,并且现身说法、开幽揭隐——
中国的当代批评该何去何从?好的批评家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情怀、特殊禀赋和专业门槛?
在批评界的荒芜长夜,《千灯有影》有如高擎的文化心灯,投下长长的沉思侧影,集中喷发的智慧焰火,不仅足以豁人耳目,亦可启发人们深思批评家的真正价值。摧邪显正、破暗烛明,细细品读集中文字,颇有沉着痛快之感。
素养:说出有道理的“成见”
谢轶群许多文章的立论之勇,仿佛是专为“犯众怒”而来。
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旧体诗词和传统国学“复兴”潮流中,他偏偏站出来,给那些立于潮头大声鼓与呼的发热头脑猛泼冷水,认为旧体诗词已丧失复兴的可能性,而今日之所谓“国学热”更俗不可耐、疑点重重。
他对“知青”一代高唱“青春无悔”的论调冷嘲热讽甚至嗤之以鼻;而当一些批评家提出苛责知青叙事的“美化”观点时,他又不以为然,理由是批评家这种道德式批判简化了事情本身,过于低估了梁晓声们的反思能力,并且有意无意地虚化了时代背景、掩盖了事件背后更为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原因。
他力倡“专业作家”体制应予保留,又忧叹影视“颂皇热”是民族凶兆。
他揭示出风行校园的“穿越”作品不是对现实的超越,而是对现实的逃避,不是新一代人理想的曙光,而是理想委顿、价值错乱的令人心忧的阴影。相反的情况是,著名学者张鸣先生发出言论,批评 “载不动许多爱”的80后、90后大学生因“溺爱” “滥爱”而惯出许多 “毛病”,担忧大学生会因此而“废掉”,谢轶群不惜为这代人“犯上”抗辩,认为张先生脱离时代,以陈旧的成年标准来硬套当下,并且存在一种急需打破的“80年代大学生神话”的幻觉,这种幻觉麻醉使张先生固化了某种居高临下的陈旧意识。就此谢轶群反问道:既然那代人如此优秀,为什么他们主导的这个社会还有严重的“毛病”、尤其还贪腐盛行呢?他认为,那代人虽没有享受到“溺爱” “滥爱”,但少年时遭遇尽谎言宣教、狂暴诱导和欲望压抑的不良环境,成长过程中心灵吸收了大量毒素无法自净,到其成为社会主导群体,就会带来这样的恶果……
因为“制片人跪求影院经理多排片”的“悲壮”宣传,担心“势利市场埋没优秀艺术”,许多观众进了影院,致敬“曲高和寡”的吴天明导演及其《百鸟朝凤》。谢轶群立即尖锐发声——导演没有新的表现手法、与众不同的视角和思想,导致此片实质上是严重落伍于时代之作,是还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水平的“一曲陈年哀歌”。与之相比,即便是很容易概念化、空洞化的主旋律电影,如《阿佤山》等,一旦创作者有自己的精神高度,有建立在情感体验基础上的艺术表现,影片照样可以“意深虑周”,成为杰作佳构。
谢轶群抛出的一个又一个论点,不依傍他人,不盲从潮流,不察看权威的脸色和作品本身已有的声势,独立而醒目,深刻而犀利,无疑带有“成见”的个人观念和视角。火候不到,很容易流入常见的惯于宣泄情绪的“愤青”队伍,执着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路,陷入无条件地反对一切的思维泥淖中不能自拔;或者会染上一些人最爱犯的毛病,沦落到这样的田地:以怀疑主义为核心,无立场、无原则,仅仅追求片面深刻的快感,精神上只是一片彻底的虚无。
谢轶群四面出击、极少苟同大众的状态,太容易让人误解了;何况有时他竟狂放到要公然与千年经典唱反调的地步!
可以举个例子,看他是如何对古老腔调进行批判和现代性阐释的。
曹丕在《典论》中批评“文人相轻”为不良现象,后世几无质疑者。谢轶群反弹琵琶,认为不可一概而论:文学是浸透了个人生命体验汁液的极其个体化、个性化活动,对于成熟作家而言,这种心态剔除其妄自尊大的一面之后,恰恰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它最容易刺激作家,激发并保证作家进入到创造过程中的活跃、自信状态……
很明显,如果不识创作的真正甘苦,没有实际生活的深刻体验,没有灵心慧眼的超越观照,是很难在这种千年定论上轻置一辞的。
他的这些话,乍听起来十分刺耳,是最易犯“众怒”的“成见”,没有多少人会立即心悦诚服。只有按捺住情绪、平心读过去的人,才会发现他的“成见”并非一味的偏激之语,矫枉过正之后,往往较多公允持平。谢轶群的剖析游刃有余,一种清晰理性的性格,在强大的逻辑感和严密的论证中渐渐浮显。先前你自己先入为主的某些印象式判断,相形之下反而露了怯:它们最经不起细细推敲,有着“自动化”的特点和轻薄浅俗的底色。
这一种阅读的体验和发现,不禁让人联想起金岳霖对哲学的解释——哲学就是说出有道理的成见。
《千灯有影》里,批评家谢轶群表达的也是一种“有道理的成见”。
批评家当然应该具备哲学的知识和思维的基本素养。至少也应表现出高人一等的类似哲学的体验和思考的穿透力。现代西方许多文论家本身就是哲学家,最显著的如本雅明对波特莱尔“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的理论界定,文本分析中“机械复制时代”与“光晕灵韵”的概念并举,同时就是新的哲学洞见的表达。
可以说,谢轶群的《千灯有影》,已经隐隐指出当代批评的一种新方向、隐喻出一种新精神。批评家就应该表达自己一个又一个的“成见”。
所谓“成见”, 对谢轶群而言,就是独特的个人视角,见性见情的观点表达,鲜明痛快、针针见血的卓识灼见——这一切自然有别于四平八稳、言之无物无味的“正确的废话”,而这样的评论如今正充斥报章!
更为关键的是,这些“成见”要避免成为意气之争、偏颇之见,就得讲道理;要说得“有道理”,特殊的专业素养必不可少。谢轶群拥有当下中国人最为稀缺的常识心态,洋溢着健康的理性精神,再辅以清晰的逻辑说服力,让我确实体会到了真正批评家的那种特殊禀赋、专业训练和素养的较高的门槛。
态度:没有路的地方姑且走走
谢轶群是专业的文学批评家,而《千灯有影》的文章论述已大大越出了文学范围。他的关注面极为广阔,各种文化热点、媒体事件无不纳入其反思范围。即便谈论文学,也是在宏大的社会思想背景下、开阔的文化视域中,一步步论述和展开。
在专业分工日益严格的当下,单看目录,内容涉猎过广,很有理由怀疑他的论述会因之肤浅、泛化。况且,这不大符合当今高校学者的学术旨趣和常规追求——花精力经营评论,怎比得过埋首高头讲章?最识时务的选择和追求应该是构建庞大的学术体系,开宗立派,摇旗呐喊,在学术江湖中啸聚为王以后,才能夺取相应的话语权,获得人人羡慕的学术资本和个人利益。
“大道甚夷,而民好径”,谢轶群似乎对自己的生存形态不太上心。他有专业,却不做流行的“砖家”;他重视学术,更热心思想;他更愿意孤往前行,固执地发出与当今世道不甚和谐的批评声音。
他笔下的内容是驳杂的。高校题材小说,官场题材畅销书,春晚,影剧,文化史,编辑制度,流行歌曲,网络话语,社会思潮……月到花前弄影,风来水面生纹,大小精粗,人间万象,都不避尊卑高低地来聚笔端。
谢轶群的思维有时是险峭的跳跃。他可以从苏轼《定风波》中的旷达引到鲁迅笔下的阿Q精神,再经鲁迅联系到韩寒,几番对比腾挪,得出使人心跳的结论,譬如这一段——
去掉鲁迅的深邃,加上一份俏皮与流气,这就是韩寒。韩寒不是山寨版的鲁迅,鲁迅不是中年版的韩寒,他们不过是同一座阴暗庙宇中的灵童转世轮回。生于1982年的韩寒与鲁迅年纪差了一个世纪只减一岁,禀赋造就他,经历造就他,技术时代造就他,关键还是这片土地、这个国度、这个民族造就他。关键之处,与鲁迅完全重合,一个世纪的光阴似乎没有流淌。
这样的思维,让我想起刘小枫那本以深奥晦涩著称的《拯救与逍遥》,把屈原、鲁迅、贾宝玉放在一起,颠来倒去且述且论,天马行空得同样让人瞠目结舌。这一点,谢轶群和他有得一拼;不过,说到文章,谢轶群晓畅流利,深谙其道,说到要害处,突然引而不发,常以“你懂的”方式,让读者一瞬间如蒙光照。
谢轶群的表述也常常不符合学术范式,上引文段居然冠以这样一个“洋泾浜”式的“奇葩”题目:“韩寒何时会out?”
其余如《文化的花落与燕归》《写在页边总是疑》《无法遮蔽的少年心灵光影》《这一炉温暖的余烬》等等充满文学意味的标题,都于理性研究的通行话语有隔。
处于还要争生存的中年环境里,这样的写作方式,在私人的利益算计上相当不精明,已经显出有些不食人间烟火、只听从内心的迂阔和任性;而细读其文,读者又常常折服于其才华、灵气与见识。作为论文写作课教师,谢轶群精熟于现代学术规范和论文格式,结果却不愿在这种文章体式内得心应手、四平八稳地“做项目”,而宁愿走上旷野的险道迷途。
谢轶群思考问题时大胆奔放,可以看出他从不在思维上设禁区。
思维无禁区,可惜世界有条律,常常一不小心,他的行文就触到某些禁忌的临界点。对此,他有时是率性地揭示:“《建国大业》没有要探索什么,而是要调和什么;片子的背后,不是充满个性的艺术家,而是一群一手拿文件一手拿剧本的文宣干部。”
有时不能畅所欲言,比如对《废都》的真正意义,只能隐晦地“欲说还休”。
这固然符合写作的“冰山原则”,只是压抑的体验和曲折的心路历程,表现为文字,就充满某种张力的婉曲和压迫的致密,比如他评影片《一九四二》——“相类似的历史苦难,尤其是发生时间比1942年河南大旱离我们更近的重大饥荒及其思考,自然浮现在有心观众的脑海中。”
又如《韩寒何时会out?》的结尾:“中国依然,则韩寒及变种的韩寒热度依然;对滞水能起波澜悲观,则对韩寒不out乐观。”
谢轶群的写作是发散、辐射型的。呼应时代,与时代个案的紧密互动,使他着力点繁多,击打面过大。但是,透过他对纷繁事件的点评剖判,可以隐约看出其一以贯之的态度:对文明、理性、民主、自由等现代世界共同价值的深情呼唤,对专制、愚昧、奴性、僵化、保守等各种负面价值的强烈批判和民族劣根的坚决摒弃。他常常超越左、右意识形态,悠游于更高远文化时空的自由心志,宗教感般对某些“永恒主义”价值和情怀进行坚守与凝望……
谢轶群以《千灯有影》作为书名,隐隐透出几分天机:灯影相合之处的对景——视域融合之场域——亦非可以固执持之的实相,可能只是一场虚幻、一种主观之假。然而摒弃具体特殊,一般无从显现;离此灯影虚幻,真理从何而观?
借假成真,登岸舍筏,孔圣的“知其不可而为之”,鲁迅先生在大幻灭之后的昂然奋迅,是一种消极里的积极,绝望处的希望,无执中的固守,看破后的豁达。
行文看似畅快淋漓、又在字里行间常有大孤独大悲抑的谢轶群,是否也如他的前辈鲁迅一般,心怀启蒙之志,以火热情怀处冰冷之世,经历了本可不写又不甘不写、姑且写写又往真里写的矛盾彷徨之后,终于出就有为?
只能说,此道不孤;在没有路的地方,姑且走走。
我相信,谢轶群的胆识和觉悟,都是基于这样的态度而来,以就千灯而成影的本质洞察,行一往无前之决心,热情拥抱当下,即此用,离此用。
这是谢轶群的精神,也是当代批评该有的精神,他给批评家们树立了一个榜样,即必须找到个体独立的言说立场和超然态度,那就是——
在没有路的地方,姑且走走吧。
进境:让事物表述它自身
个人的禀赋以及身处的特殊时代,使谢轶群的文化批评有些复杂难解。
坚守的立场、趋于稳定的世界观及已经成熟了的一整套价值坐标,使他如海自深,不择细流,需要不断参与到大众关注的大小热点事情中去争是辩非、论黑说白,藉每一个可能的机会去渗透理性文明、播洒启蒙之光。有时不惜金刚怒目,便给人一副得理不饶、咄咄逼人的好辩者形象。笔锋所及,触处是凌厉险峻之风。
此刻一个不小心,人们就会忽略谢轶群温暖宽和的一面。
评述“春晚”, 他对流淌在记忆中的各种影像生动描摹、细细回味,“矛盾的盛宴与扭曲的欢颜”的冷峻结论,依然斩不断不舍与依恋的情感丝缕。
回顾黄金时代的台湾流行歌曲,他对邓丽君、姜育恒、张雨生等歌手风格的美学定位,对罗大佑、李宗盛、陈玉贞等作者歌词内涵的体贴剖析,无不充满着温暖的“同情之理解”。
在艺术和思想上对吴天明导演表示失望,并不否定吴天明执善固执的情怀;对汪国真诗歌的整体水平评价甚低,也如实赞扬了个别清新之作,论定这一诗歌现象背后相对应的社会文化心理之期待,肯定汪国真浇筑世道人心堤坝、熏陶理想主义情怀的正向价值,且对汪国真生活中的善良人品、回应批评时宽仁温厚的君子之风表示尊崇。
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欣赏品味和情趣偏向,也有绕不开的人情圈子,批评家并不是生活在真空里。谢轶群对自己的情感偏好不遮掩,不故意将自己修整成一副绝对客观的模样,他的身上难得地保留着批评家独立清醒的批判意识,和只为良知、公义负责的道德自觉。即使是碍于人情的文字,也有自己的择取标准和言说角度,从这一个到这一类,特别善于借题发挥批评的真意。他的评论常穿透人情,而无阿世之态——这是一种不为势利所屈、亦难被情感收买的真正批评家的风神。
谢轶群文化批评的选择和取舍标准,来自于事物本身的曲折程度。更确切地说,他的任务是为那些被扭曲、被遮蔽、被误解的事物和情状仗义执言,通过自己思想向特定方向和角度的集中发力,矫正偏向、纠正错误、厘清混乱……
所有的批评阐释终究脱不了是一场钟上的雪,阐释的目的是努力使自身成为多余。这是海德格尔阐释荷尔德林的诗时做过的著名比喻,如果把批评工作也作这样的理解,甚至认为可以不经过个体的艰苦劳作和自觉奋斗,事物本身就会自然主义地如实呈现,批评家的工作也可依此自行消失,我想谢轶群决不会同意。因为,从《千灯有影》里的一些文章来看,他的批评已经是另一种形态的思想原创,本身就具备独立存在的资格,如《苏轼〈定风波〉中的旷达与阿Q精神》《韩寒何时会out?》这类来自天才直觉的体悟深刻的文字。
另外,没有他的批评,很难想象事物会如实呈现。就如很难想象我们会从少年的接受美学角度,发现本为政治宣教而入选课本的《驿路梨花》在许多人的少年记忆中常开不败的深层原因,竟是文本存在着的 “乡野传奇”“物质饥饿”等多重“召唤结构”!也很难会对“被编辑改动过的出版物文字——无论改好改坏——对作家作品来说都是不能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评论家其实都是文学出版物评论家”这类闪光的见识,于阅读的当下猛然有省。
但是,谢轶群目前做得还不够充分而又为我辈所惦记、所寄望于他的地方,正是批评家最终的努力,确实需要在恰当的时候,抛弃我执及成见,主动退居幕后,让事物在人们眼前自行涌现,让事物如其所是地呈现它自身,进而能够以其本身的逻辑,自动开口说话——让它自己表述自己。
不能说谢轶群没有这样的意识。
谢轶群谈及中国古代文论语意模糊、交流困难、深度有限、理论“干货”贫乏等毛病,乍看起来是个反传统论者;可是在与西方文论对比,剖析了在现代学术范式影响下文学研究的经验教训后,他却得出非常公允的结论:“真正考虑文学特殊性的学科标准确立,中国古代文论也许会释放出它的光彩。”而经过否定之否定,古代文论的原则“竟始终是正确、先进的”。
曾为“朦胧诗”正名的批评名家孙绍振不满小说《白鹿原》“蹩脚”的语言,嫌其“笨重”“啰嗦”“拖沓”,并列出大段文字试图删减。谢轶群感慨“识途老马这回怎也闻岔了气息”,与孙先生略作辩驳,孙先生自身的审美缺陷即暴露无遗。可以说,因为谢轶群的完胜,终于避免了陈忠实《白鹿原》繁丰雄浑的艺术特色语言在理论权威的错误裁定下蒙冤。
书中在批评境界上最具突破性的文字,当数《李广田的乐观与郭沫若的“佯媚”》这一篇。
谢轶群如现象学主张那样,把一切理论和先行立场以括弧悬搁起来,穿梭游刃于各种道德观点的比较辨别中,以事实说话,随物赋形、水到渠成地得出可能连他自己也未免大吃一惊的结论来。
最精彩的部分是对郭沫若的“佯媚”的解读。通过郭沫若记不起自己对领袖诗词的牵强解读,并以正常的艺术直觉自己反对自己写下的注解,大胆推想:郭沫若在“文革”中令后人瞠目的文字,很可能是一种有意为之的“佯媚”,是以“自虐”的方式立一标本,传之后世,为荒诞年代传神写照……
从谢轶群本人的个性来说,他不见得会喜欢自己的结论——他不可能在情感上接受那些文字,也没有为郭氏说好话、做翻案文章的义务,何况还会遭人误解,有居心不纯、刻意开脱之重大嫌疑。有道德洁癖的批评家可能会因此给他扣上个屎盆子。但是,谢轶群就冒着这样的道德风险,不设立场,如理表述,如实表述,让事物自己来说话。
做过律师的美国总统林肯,曾经不管国人如何痛骂,挺身而出,坚决为死刑犯辩护,他对不理解的人们申说道:“我之所以要为这些狗杂种辩护,就是为了从一开始就要防止专制的产生!”
制度的专制始于思想的专制。在民族、民粹主义很有市场,道德批判泛化,常识匮乏,非理性思潮涌动的当下,谢轶群的批评精神,具有别样的意义。他的意见可能不大中听,他的态度立场也许存在偏颇,而为着一开始就防止思想专制的产生,同样也应捍卫他的表达权利。越是不同众人的言论,越是值得人们去倾听、去尊重和深思。批评家貌似偏激之姿,正是为矫求公正之实,正是——
千灯有影,众陂成平。
我以为,这就是《千灯有影》一书核心价值的所在。这里是谢轶群心萦梦绕、精血灌注之后九曲回肠的一路情感风光,也是他反复思考辨诘、不断实践突破、一步步螺旋上升的思想进境。
(作者单位:昆明市新迎中学)
责任编辑:杨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