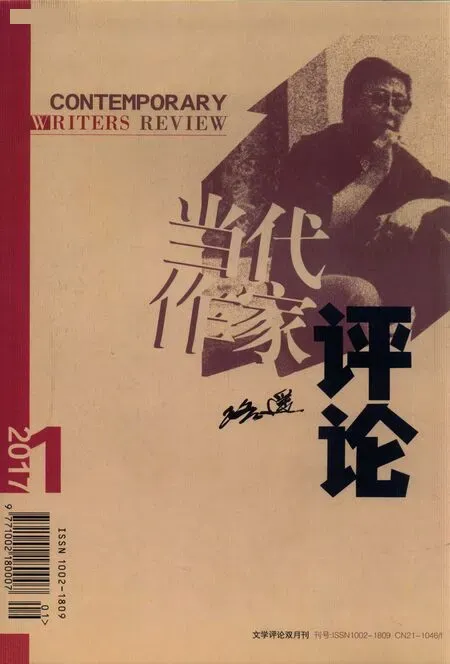传奇、虚无与历史意识
——有关《独药师》的几个面向
赵 坤

——有关《独药师》的几个面向
赵 坤
也许从《楔子》中抖散掉的“一百多年前的尘埃”开始,就注定了这将是一个“流逝与追忆”的故事。被尘封在图书馆里的古旧档案,平面的残纸断页,在小说的文本形式里变得立体,索引出百余年前的革命故事,更勾连出始自秦皇的东方长生秘术。这样的故事,一定不会因为《楔子》和附录的齐全,就被那些布满历史缝隙的材料定义为揭秘历史真相的文本。它有更广阔的、关于当代的历史真实,在书写传奇、虚无与历史中,有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对已经消失了的仁善观的恢复,以及绝望的年代里对希望的重建。
一、传奇,或“类神话”叙事
在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视野里,《独药师》近于传奇,也类似神话。它有传奇小说的“记述奇人奇事”,也有神话小说的“初民自造众说,以解释天地万物、变异不常”。从古代小说的源流看,传奇或神话,在内容和主题上实无太大的差别,如果说是上古神话和先秦寓言孕育了志人志怪小说,那么“传奇者流,盖源于志怪”也就在系谱上连通了传奇与神话。但具体到叙事的边界,美学属性上相交叉的两者还是存在细微的不同。传奇以现实中生长的人事为基础,多有英雄、爱情和冒险故事;神话则更多的取材于天地自然,草木禽人万物都是可描述的对象,整体上追求玄幻超验的审美体验。以这样的角度来看,《独药师》中的革命加恋爱的历险故事,是当代的传奇叙事,而书中大量的长生、修持与仙化故事,则可算作神话的范畴。
只是,《独药师》中的“神话”叙事无论从描述对象、篇幅比例、玄幻程度还是主题结构的设置,都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神话。它不似《帝王世纪》对华胥之洲的诞生及人类来源的细节想象,或《山海经》明确地“记海内外山川神祗异物及祭祀所宜”,也不像《聊斋志异》制造了一个不同于人间的鬼狐花妖的新世界,《独药师》更像是接近于神话的“类神话”。尽管从半岛的仙源说起,也由“长生”贯穿全篇,但修持仙化的故事始终是镶嵌在人世之间。书中可追溯的最早的神话始自秦皇,是有据可考的历史,“几千年前西去咸阳献宝的方士并非精华人物,这当中最深奥的人士都留在了半岛,秘笈得以保存。季府中存下的大量樟匣中的就有这一部分。”将神话传说的起源置于可证历史之中,相比上古神话的去时间化,时空的距离缩略了故事的悠远绵长,虽然加深了传说的可靠性,却也削弱了作为神话本身的光彩。此外,小说《独药师》虽然对养生秘术与羽化成仙多有描述,但大多点到即止,并不直接地参与作品的叙事或表意的功能。比如,对于小说中最为神秘的、支撑季府成为半岛世家的“独药”,作者常常顾左右而言他,只强调该药丸药效神奇,配方绝密,甚至历代炼丹过程的严苛,众人梦寐以求的程度等等,对该药的诞生过程却始终粗略带过,所以我们认为,以“类神话”进行文体上的表述,或许比神话更准确。
因为即使是镶嵌在人间,即使是玄幻程度描述得有限,那些带着东方神秘主义的、超出我们审美经验之外的故事,比如曾祖父宴请海上仙、诸神醉酒升天,邱琪芝的淫邪秘术,或日常修炼中的“目色”“遥思”,及气水运行等等,也已然通向了一个我们从未曾涉猎的、新的想象世界。
相比之下,作为“当代传奇”的《独药师》,则有着较为完整的传奇式结构,一个革命加恋爱的冒险故事。以真实革命者为原型的季府养子徐竟,是席卷了半岛、江北甚至整个中国的革命活动中的重要领导者。他每一次秘密的归来或远走,都是上个世纪初中国革命可追寻的轨迹,他偶然流露的思想和革命诉求也可视为中国早期革命的行动主张。由他一点点透露出的关于革命的有限信息,最终以管窥的形式描述出整个起势、酝酿、暴动、流血、失败,再起势的完整过程。直至将季府也卷入时代的涡心,成为“革命的银庄”,甚至季昨非这样一个并不理解革命、从长生的角度质疑暴力革命道德性的人,也被革命的浪潮裹挟。同时,革命叙事还推动了季昨非的爱情,在屡次追求陶文贝未果的情况下,是对革命人士的营救事件再次联络了两人,并最终促成二人的好事,完成了一系列的冒险故事,并将恋爱嵌入革命的叙事里。此外,小说大量的奇人奇事也是构成传奇文体的要素,比如革命要人的隐秘身份,激烈的刺杀行动,暗藏玄机的小白花胡同,以及陶文贝的身世之谜等等。
在当代文学的视野里,传奇与“类神话”文体的复活,是小说《独药师》的特殊贡献。它意味着被新文学斩断的中国古代传统小说文体形式在当代写作中的重建。尤其是“类神话”叙事。如果说五四之后,传奇还可以在通俗小说或革命文学中偶然觅得踪迹,神话叙事却几乎在启蒙话语的覆盖下完全消失了。虽然也有借势西方的宗教传说,或科幻故事等文学类型,但其西式的、宗教的、甚至以科学理性主义为基础的写作,根本无法置换成蕴藏中国古老幽思、意绪、天地想象和人事归途的“玄幻”故事。那些“浓缩、凝聚,形成艺术上可见的东西”(巴赫金语),提供了超越世俗生活和理性逻辑的景观,是只有中国人的语境里才能水落石出的原始想象,也是只有中国人的经验才能理解的千古玄思,和万古况渺。
二、“生活世界”的危机与虚无主义者的诞生
作为季府第六代继承人,新一代的“独药师”季昨非似乎已经很难复现祖辈们的修持神话。那些流传了半个世纪的仙化传说,盛行于半岛和整个江北地区的神秘丹药,以及百年季府的养生秘笈,在季府新主人、19岁少年季昨非这一代,渐渐露出不可遏止的倾颓之势。尽管自少年时代起,季昨非就在对先祖的瞻仰与怀念中立志,要绵延家族的荣耀,以传家秘仪实现“阻止生命的终结”的“人类历史上至大的事业”,却不得不在每况愈下的力不从心中承认一个事实,那些始自秦皇的经史典籍,流传千年的历史经验,根本应付不了人类自身的精神孱弱、分崩离析的转型期社会,和半岛盛极转衰的历史命运等现世的问题。
对季昨非来说,先辈祖训和父亲遗言里的“养生”,是季府乃至半岛地区长久以来回应世事万变的“不变”。“我们遇上了数一数二的乱世,人在这时候最值得做的其实只有一件事:养生”。生逢乱世,更需养生,季家的祖训显然是在无数次的生存危机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以一种认识论上的理性主义,追求老庄式“内心的虚静”,在超验的形气修持里,唤起旷古的玄思,以“道之无名,所假而行”(《庄子·则阳》)的“无名之名,不在之在”,应对世事莫测的变幻。
然而认识论上的极端理性主义,却很容易折损于行走在人间的实践。原本应该追求“无己”的季家人,却是连根本的“克己”都无法守持。进入半岛传说的两位季家先祖,从海蚀崖上纵身一跃羽化登仙的真相,竟然是为了女人跳崖身亡;而季昨非的父亲季践,也因为与世事纠缠过度才早夭。如果说从“无己”到“克己”,是承认欲望的“无”和“有”,那么,历代独药师所信奉的超然于物,遁形于世的“内心的虚静”,落实到实践上,更像是一种被理性主义抽空了意义与价值的“虚无主义”,因为动摇了“生活世界”的意义,而阻碍了人物的自我认同。
小说中的主人公季昨非,正是这样一个从始至终都无法完成自我认同的虚无主义者。在尼采的一般虚无主义观里,“那种历史过程,在其中,占统治地位的‘超感性领域’失效了,变得空无所有,以至于存在者本身丧失了价值和意义。”如果说这里的超感性领域来源于柏拉图对现实世界和超感性的理念世界的划分,那么对季昨非来说,他的“理念世界”无疑是流淌在家族集体无意识中的关于“长生”的种种假设。从19岁到26岁,“长生”的修持带给他的只有不断地陷入欲望的深渊,在数次沉沦中几近濒死,直到蚀筋抽骨耗尽精血,也没有从此中得出丝毫的意义或价值。他甚至没有因此获得任何自救的能力,无论是小白花胡同、朱兰的深闺还是陶文贝的阁楼,季昨非结束一段关系的方式永远是陷入一段新的关系,在自以为是的修持中,永远等不到来自理念世界的半点提示,“我可能永远都搞不明白:这是命中必有的一个关卡,还是无比老辣奸诈的江湖术士设下的圈套?”
被抽掉价值和意义的存在天然地缺乏主体的自觉性,在季昨非身上,有宿命的悲剧,也有自身精神的孱弱。作为半岛最显赫的季府主人,拥有巨大的物质财富和众人梦寐以求的长生秘术,生活在食物链顶端的季昨非似乎生来就被命运锁定了,被赋予荣耀,也被授以家族使命。务虚的宿命让他脱离真实存在,更在“生活世界”里丧失了主体性。在胡塞尔对“生活世界”的阐释里,“现存生活世界的存在意义是主体的构造,是经验的,前科学的生活的成果。世界的意义和世界存有的认定是在这种生活中自我形成的。因此,世界的存有(客观主义对此不加提问,把它视为不言自喻的)并不是自在的第一性的东西,因而不应该只问什么东西客观地属于这种存有意义。实际上,自在的第一性的东西是主体性,是它在起初素朴地预先给定世界的存有,然后把它理性化,这也就是说,把它客观化。”可见,“生活世界”并不是简单的日常生活的经验,而是超验的主体性的产物。被理性主义抽空意义的虚无观,正是因为动摇了“生活世界”的基础,主体性的建构就变成了一件颇为困难的事。比如小说中的季昨非,一方面他自少年时代起就不断提醒自己(不断提醒也意味着他并没有完成认同)是半岛上第六代独药师,肩负着家族和人类的使命;另一方面,却永远在现实的存在里被欲望所挟持,无力自拔。因此,他既自负于家族的独药秘方,却又禁不住对方鹤发童颜的诱惑,向亦敌亦师的邱琪芝学习方术。刻苦钻研修持方法,却从不思考清修的意义,以精细膳食滋养脏腑,却又几度陷于欲望,任由情欲和粗粝的饮食销蚀身体。他甚至无法自主地结束任何一段不伦的关系,所谓斩断欲望的闭关自囚,也在尚未出关时就陷入新一轮的欲望深渊。如果说承认杀了清廷的特派专员是他唯一一次行为上的自觉,那也是虚弱灵魂里的自毁冲动,或一时的心血来潮,而不是对某种意义或价值的允诺。
因此,当兄长徐竟以“革命为最大的养生”与其辩驳时,他“回答不上来”,觉得“一言难尽……说不好”;当心仪的女子陶文贝问及他的信仰时,他觉得“惭愧”,认为“自己好像没有什么信仰”,只能“嗫嚅”地、“小心谨慎地”求证:“关于独药师的坚毅和事业,算不算一种信仰呢?”说到底,季昨非并没有完成任何形式上的自我认同。对此,附录里的《管家手记》最能说明问题,季府的少主人季昨非,与其说是他保护了季府,不如说是季府一直在庇佑他。
三、历史意识的思辨及其他
无论养生还是革命,《独药师》中描写的主体群象,都处于社会顶层。或者说,无论是旧时代的逻辑,还是新时代的话语,《独药师》关注的,始终是直接参与社会变革的群体。半岛巨富“独药师”季昨非,革命党的直接领导者徐竟,首创新学的王保鹤,隶属美国南方教会的麒麟医院,以及革命党要人、清廷太子少保、海防营总兵等等。按照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观,张炜的历史书写是传统历史的写法,而藏于其中的,是作者极具思辨性的历史意识。一方面,“长生”的态度是追求与天地自然“齐物”,那么以个体的生命长度丈量历史,也就是以无限的自然生命丈量有限的社会历史,是生命本体论的历史意识。而另一方面,改变社会属性的革命运动,以少数人的牺牲换天下的大同,是作者对社会本体论的历史观。这两相思考,具体到小说中,是季昨非以个体生命的立场质疑暴力革命的非道德性,与徐竟“革命目的论”的道德性之间的论争:
“既然要死那么多人,而且提前知道,那为什么还要光复?这值得吗……要不是因为你,是不会死那么多人的!”
“你可以这样想。这是必要付出的代价,我们不能做个胆小鬼。”
“我想问,你们这些策划者、首领们,有几个死在这次行动中?”
“暂时还没有。”
“也就是说,那一千多个年轻人里没有一个策划者,他们都不是胆小鬼,也不能做胆小鬼,而首领们却安全多了,你们……”
“老弟,你想说我们这些策划者指挥者是胆小鬼。不过我要告诉你,你错了。”
如果说这场讨论是生命本体论的小胜,面对民族内部的厮斗和杀伐,作者肯定了生命本体论的历史态度。作为一线伏笔,小说结尾处徐竟的被捕行刑,作者又将革命的正义性放到最大,“最令我震惊的是兄长,他居然放弃了我送去的药,直赴刑场,面对满河滩的人大声宣讲革命,直到喊哑了嗓子……这让我想起了耶稣受难日。”徐竟的历史责任感,在神学的意义上唤起了作者关于“启蒙”与“力抗时俗”的精英意识,是偏于社会本体论的历史认识。也就是说,在《独药师》的历史思辨里,生命本体论的“长生”已经淹没在更广大民众的福祉之中,可民族内部战争语境中析出的社会本体论又显出了吊诡的一面。也许这就是作者张玮历史意识的生成机密,在二元的思辨中先否定二元。
类似的思辨方式还发生在新旧社会的转型期,关于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旧世界与新时代等等。例如与新学创办人王保鹤的讨论,“我想知道新学与教会学校的分野何在?二者是否殊途同归?王保鹤说究其实质还是不同的,那所学校完全是洋化教育,而我们的新学只是吸纳当今世界新知,仍以国学为本。‘这其中尚有体和用之别。’”对中西医的讨论就更有趣了,麒麟医院治好了季府药局主人的牙疼,季府药局治好了麒麟医院院长的眩晕,从前剑拔弩张的中西医关系,在彼此的互助合作中岁月静好了。虽然作者似乎并不喜欢二元对立的思路,但他又常常将自己置于二元结构之中,以否定的形式不断生成主体的认识论。最能表明作者立场的也许就是和麒麟医院的女医生陶文贝的关系。在教会医院出生、受洋化教育长大的陶文贝是典型的西方文明的符号,与季昨非的结合也象征了中西方文明的交汇。颇为有趣的是,在季昨非的苦苦追求下,他与陶文贝的结合冲动是在一场“再晚就来不及了”的社会变革前完成的,如果说这具有某种暗示性,指向的就是作者对上世纪初的西方文明的态度了。
当然,拥抱西方文明并不意味着放弃传统精神。在批判理性主义和多元化的视野中,依然遭遇了现代性的心理危机,外部世界迅速变化导致时空感错乱,内部的“长生”信仰又急速衰落,在“死去元知万事空”的大虚无中丧失了自我意识的季昨非,还是依靠内在的修持重新唤起了对未来的追求。尽管我们并不知道最终是对革命还是对爱人的追求重建了他走下楼的勇气,因为燕京这个地方既是爱人所在之地,又是政治漩涡的中心。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哪一种,这“追求”都关联着对现世、对至爱、对理想和一切美好的能指链。显然,惯于思辨的作者并不在意再一次在二元的结构中敞开选择,走下楼去的季昨非,似乎有无数的可能性。
〔本文系山东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项目编号:J16YC10)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王 宁)
赵坤,博士,青岛科技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