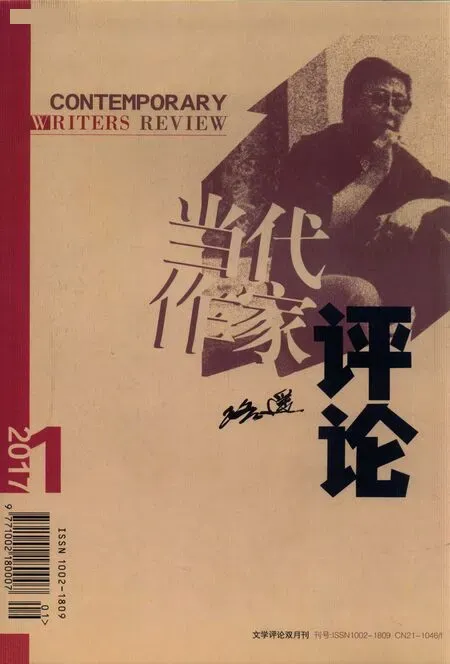现实与历史:非虚构文学的独特叙述
王 晖

现实与历史:非虚构文学的独特叙述
王 晖
一
文学以艺术的方式对现实和历史进行叙述。这种“艺术的方式”可以是虚构的,也可以是非虚构的。前者如小说和剧本,后者如传记、纪实(报告)文学等。
当然,“非虚构”概念是宽泛的。英语中的“Nonfiction”一词,直译是“非小说”,还可译为“非虚构文学”。在西方,非虚构不仅涉及文学,也包含新闻、历史、哲学、社会学(如被誉为“新闻界的诺贝尔奖”的普利策奖中的新闻类和历史、传记、非小说等艺术类)。上世纪60年代,诺曼·梅勒、汤姆·沃尔夫、杜鲁门·卡波特等人的“非虚构小说”和“新新闻报道”在美国盛极一时,成为文学领域非虚构创作比较早的典型代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学界开始引入“非虚构文学”概念,刘心武、蒋子龙、刘亚洲等作家曾写过“纪实小说”,《光明日报》等重要报刊还发表过有关这一写作现象的争鸣文章。上世纪90年代,江苏的《钟山》杂志开设“非虚构文本”栏目,近几年来,王树增等作家称自己的作品为“非虚构文学”。但至少在2010年《人民文学》提出“非虚构”写作之前,无论是创作还是理论,这一概念在中国大陆都仅仅只是一股“潜流”,并未获得更为广泛持久的呼应。《人民文学》对于“非虚构”写作的提出,某种程度上意味着“非虚构文学”进入主流文学媒体的视野,使有关“非虚构文学”的创作和研究成为一个热点。2015年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非虚构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又将这一文类写作和研究推向新的高峰。
相对于文学的“虚构”写作,“非虚构”并非某种具体文体的写作,它更多的是指一个大的文学类型的集合,譬如非虚构小说、新闻报道、报告文学、传记、文学回忆录、口述实录文学、纪实性散文、游记、纪实性影视剧本等等。我们可以按照文本所体现的作家的写真意识、文本再现的似真程度以及读者接受时的真实感效果等三个方面因素,将非虚构文学划分成“完全非虚构”和“不完全非虚构”两种主要类型。另外,还有一种“仿非虚构”,如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写实小说,它们基本属于虚构、但在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上具有“非虚构”元素。“非虚构性”或曰“写实性”是非虚构文学最重要的特性,这一特性告诉我们,文本所呈现的是经验世界中给定的现实,是一种不以主观想象为转移的、与特定历史或现实时空所发生的事实相符合的特性。以此为中心,田野调查、新闻真实、文献价值、跨文体呈现等成为构建非虚构文学的基本元素。在文学家族中,虚构与非虚构实际上是共存共荣的。
而无论虚构还是非虚构,文学家对现实与历史的叙述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譬如对于历史的叙述,即有所谓“宏大叙事”——通过记录重大历史性政治经济文化事件、领袖或精英人物的言行,以把握或反思历史。此犹如黑格尔所言:“所以一种民族精神的全部世界观和客观存在,经过由它本身所对象化成的具体形像,即实际发生的事迹,就形成了正式史诗的内容和形式。”也可以以一斑窥全豹,用草根、民间性世俗化事件和细节来演绎历史,显示出充满生活质感的“小历史”。就像阿列克谢耶维奇写二战时苏军女兵的故事时所说:“我是在写一部感情史和心灵故事……不是战争或国家的历史,也不是英雄人物的生平传记,而是小人物的故事,那些从平凡生活中被抛入史诗般深刻的宏大事件中的小人物的故事,他们被抛进了大历史。”如果说,历史有大历史和小历史之别,那么,在文学中,这种“大”、“小”历史应当是浑然一体的。这正如文学文本中“大环境”与“小环境”之间的关系。优秀的文学文本应当是将主要人物生存的具体生活环境即“小环境”(包括其周围的人,身边所发生的事情,以及与其发生各种联系的自然环境和物质生活条件等)与这种环境所折射出来的社会背景、历史趋势即“大环境”的高度统一。而非虚构文学对于这种“大”“小”融合的现实与历史的叙述有其独特性,它表现在,一方面,是要清晰地再现现实或还原历史的细节质感,创设最为基本的“非虚构性”;另一方面,是要超越细节质感,甚至超越时代、党派、国度、民族或意识形态,进入到对人性、人道和人类的思考,即人的终极关怀,回归到“文学是人学”的基本轨道。
二
在当下语境中,非虚构文学写作之于现实和历史的独特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新时期文学”之初,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文学大多呈现出历史意识的重新觉醒以及对“大历史”的直接表达。这在小说以及非虚构文学中表现明显,譬如发表于《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的刘心武小说《班主任》和发表于《人民文学》1978年第1期的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它们分别以受到心灵伤害的青少年和知识分子为表现对象,成为新时期文学对“文革”历史进行反思的先声。自此之后,在散文、诗歌、传记和影视戏剧等文艺样式中,作家艺术家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甚至于近百年中国历史的反思汇聚成气势恢宏的浪潮。上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改变,包括非虚构文学在内的许多作家热衷于“小现实”和“小历史”的展现,对于“大历史”的书写显得更加多元、甚至更加隐晦。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些非虚构文学作家对现实和历史叙述的诚意。他们真实地描述现实,但又不拘泥于对现实的表现,而是有所超越和提升,在由无数个日常生活细节、事件以及人物所组构的“小历史”的“以小见大”中,实现对人类过去、现实和未来命运的思考。我们当然可以开具一个可观的名单和书单来详述这样的中国作家和作品。然而,在此,我更愿意列举两位典型的外国作家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位是诺曼·梅勒。文风大胆、言辞犀利、反叛意识浓郁,是这位美国当代著名作家给予我们的强烈印记。作为以长篇小说《裸者与死者》成名的两届普利策奖得主,梅勒在其非虚构文学作品《夜晚的军队》(又译《黑夜军团》或《夜幕下的大军》,1968年获普利策非小说奖和美国国家文学奖)一书中显示出对现实和历史表现的独特性。这部作品主要描写的是1967年10月发生在美国华盛顿五角大楼前的民众大规模反对“越战”的游行示威活动。“在《夜晚的军队》中,梅勒把小说的虚构技巧应用于描写真实的事件,重新点燃了卡波特在《在冷血中》开始的关于‘高等新闻写作’的批评性辩论之火焰。梅勒的作品是他根据自己在五角大楼前的示威游行经历写成的‘真实历史’。和卡波特的作品一样,提出了关于新闻观念的演变和美国的写作方向等重要问题。”长达十余年的越南战争,是二战后全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阵营冷战对抗的一个突出象征。由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所带来的东西方冷战,使全球在上世纪60年代处于剧烈动荡之中。在美国国内,社会各阶层对“越战”的反应充分表现出某种反战和反叛精神。作为作家和记者的梅勒亲历了那场惊心动魄的游行示威活动,他以《夜晚的军队》对此作出近乎自然主义式的详尽记录,譬如自由派的晚宴、恩巴萨德影剧院的演讲、行进中的游行队伍、河边对抗、五角大楼前示威者与警察的对峙、主人公梅勒的被捕和审讯等等,逼真地还原了现实和历史。可贵的是,梅勒没有止步于此,而是力求通过小说与历史、现实和想像、写实与虚构交织一体的反“越战”游行的描述,以“作为小说的历史”和“作为历史的小说”为作品结构,在看似二元文本的叙述中,实现超越于现象、现场记录的隐喻象征意义。这就像海登·怀特所说“它利用真实事件和虚构中的常规结构之间的隐喻式的类似性来使过去的事件产生意义。历史学家把史料整理成可提供一个故事的形式,他往那些事件中充入一个综合情节结构的象征意义”。因此,我们通过作品可以看到,梅勒既对上世纪60年代美国“分崩离析”的社会政治现实做出尖锐批评、对美国历史做出深刻反思,又超越狭隘的党派归属、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传达出对人性、人道、人类文化生态和世界和平的热切关注,显示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人类关怀的气度。梅勒因此成为影响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重要作家,被美国社会文化批评家琼·迪迪恩誉为“美国伟大的良心”。
另一位是阿列克谢耶维奇,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为诺贝尔奖首次授予的非虚构文学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其实是一名生于乌克兰、毕业于白俄罗斯明斯克大学新闻系的记者。“她的复调式书写,是对我们时代苦难和勇气的纪念。”(另译“因为她丰富多元的写作,为我们时代的苦难和勇气树立了丰碑”)这是诺贝尔文学奖给予阿氏的授奖词。复调式书写原为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特征的评价和总结,此意似在强调阿氏写作的“多声部”,即作品中的人物不受作者意识的控制,都具有独立意识和独立话语,以致形成“众语喧哗”的广场效应,体现表达的自由和多元。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是新闻、文学和历史的复合体,契合非虚构文学所要求的非虚构性,在对现实和历史的反映上个性凸显。除二战外,阿氏作品所写的其他事件(如阿富汗战争、切尔诺贝利核爆炸、苏联解体等)均是作者参与其中、亲身经历、感同身受的。在叙事上,其作品大多以被采访者的第一人称口述为主,让人物自然呈现事实和倾诉情感,作者一般不做主观心理分析,以此显示客观性和原始叙述状态。在人物和结构设置方面,其作品基本无中心人物,一些没有严格的章节架构(如《我是女兵,也是女人》和《我还是想你,妈妈》),一些则有内容相对集中的章节划分(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分为三部——第一部“死亡之地”、第二部“活人的土地”和第三部“出人意料的哀伤”;《锌皮娃娃兵》分为“前言”、“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和“后记”)。其文学性的表现主要体现在:选择口述对象,整理口述材料,以或抒情或议论等非叙事性话语(如作者的手记)连缀章节、表达自身立场。这其中,叙述苏联参加二战的女兵口述《我是女兵,也是女人》(War’s Unwomanly Face),是比较早译介到中国的阿氏作品,1985年曾以《战争中没有女性》为书名出版中文译本。这部经2013年最新修订重版的作品告诉我们,战争由内到外——穿着、发型、行为、性格、脾气、生理、心理等,残酷地改变了女性。表现战争中的女兵,尤其能够表现战争本身的残酷和反人性。“人性能够击败非人性,仅仅就因为它是人性。”作者在该书“创作笔记”中说“我不是在写战争,而是在写战争中的人。我不是写战争的历史,而是写情感的历史”。不再重复过去宣扬的东西,而是去寻找心灵的记录,“人的心路历程比他们经历的事件更为重要”。“她实际上是开创了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政治音律的长篇忏悔录,小人物在其中亲身讲述自己的命运,从小历史中构建出大历史。”吕宁思在译后记中所说的这句话正是抓住了阿氏作品的基本写作指向。
以口述实录的方式再现现实、还原历史,无疑是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品的特出之处。它给予读者以淋漓尽致的真实。而更为重要的是,阿氏通过这些致力于揭示二战、阿富汗战争、切尔诺贝利核泄漏、苏联解体等影响人类历史进程大事件的作品,力图表现这些事件对普通人生存和生活的巨大影响。她有着鲜明的揭露真相、还原事实的立场,以及为当代书写、为当代立言的姿态,这就是关注“生物的人、时代的人、人类的人”,反思战争或社会巨变带给人类的灾难和人性扭曲,深刻表达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和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忧思。在作品中,作者多次带有批判性地写到有关前苏联的一些问题,但她并非单单剑指制度或政党行为,更多的是超越于一时一事,超越于国家、政党和地域,进入到对人、人性、人道和人类的思考。因此,授奖词称其作品是“对我们时代苦难和勇气的纪念”,其意思在于肯定其勇于直面、揭示、反思因为人为的原因所造成的时代和人类的苦难。从这个意义上说,阿氏的作品绝非廉价的颂歌和无节操的娱乐,而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写作,也是为人类的写作。在“娱乐至死”的文化环境和价值取向面前,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选择也许是孤独的,但对于人类的未来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三
在谈到非虚构文学对于现实和历史的独特叙述这一问题时,除了上述所言两位外国作家之外,我们还不能不关注从2010年第2期开始《人民文学》杂志开设的“非虚构”新专栏及其由此亮相的作家。这本曾发表过《哥德巴赫猜想》等一系列著名报告文学的中国旗帜性期刊,在2010年第9期上刊有编者的这样一个“留言”——“我们希望由此探索比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更为宽阔的写作,不是虚构的,但从个人到社会,从现实到历史,从微小到宏大,我们各种各样的关切和经验能在文学的书写中得到呈现。”这段话一方面点明新栏目开设的初衷,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一个不仅仅局限于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的十分宽泛的“非虚构”概念。在这“留言”当中,小与大、微与宏、经验与关切、现实与历史等元素尽在其中,最终落脚到“文学的书写”,与基希当年提出的“艺术的文告”异曲同工。“关注现实”、“文体宽阔”、“呈现生活原生态”是这一栏目最为醒目的三个关键词。而强调作者身份的个人性、写作的亲历性、文本的揭秘性、题材的猎奇性和叙述的故事性,又成为这一栏目刊登作品的基本风格。在个人、细节、亲历、现场等元素的作用下,实现对原生态现实和历史的再现,以此构筑非虚构文学有别于虚构文学的基本特性,其意义无疑是值得肯定的。这样的写作既是对文学观念进行的积极调整和拓展,也是对文学写作方向的重新定位,即将现实生活、经验的故事和田野写作视为文学对现实的参与和渗透的强大力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当印刷媒介面临融媒介时代受众收缩与流失困境之时,“非虚构”已然成为主动应对的写作形式,成为社会转型时期关注现实、融入现实、砥砺现实、反思现实的文学利器。
在《人民文学》所倡导的非虚构写作中,李娟、丁燕、乔叶、慕容雪村等作者脱颖而出,奉献了诸如《冬牧场》《工厂女孩》《拆楼记》和《中国,少了一味药》等作品。而学者兼作家的梁鸿则无疑是其中一个最明亮的存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人民文学》“非虚构”专栏成就了梁鸿。因为梁鸿的《梁庄》首发于此,并引起重要反响。在此之前,梁鸿给人们的印象仅仅是一位普通的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其实,相比较那些作品等身的非虚构作家而言,梁鸿的非虚构作品屈指可数,目前引起反响的仅为《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两部,但其所引发的“非虚构”现象却不容忽视。在这两部作品里,梁鸿不是以宏大叙事而是以“小叙事”折射大问题,以个人化视角诠释现实与历史、社会与人生。这里的“小叙事”所依据的是梁鸿写作的基本叙述策略,即舍弃“先验观念”和“主题先行”,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材料的重新“编码”,类似于“有我之境”。即“一种建立在基本事物之上的叙述,这就是非虚构文学的‘真实’。并不局限于物理真实本身,而试图去呈现真实里面更细微、更深远的东西(这是一个没有穷尽的空间)。在‘真实’的基础上,寻找一种叙事模式,并最终结构出关于事物本身的不同意义和空间”。这种“小叙事”的聚焦点不是社会精英和商界领袖,而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譬如留守老人、妇女、孩子和外出打工的中青年农民工等。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小历史”。作者通过密植在文本中的丰富细节来实现对“小历史”的叙述和呈现。即便是重新“编码”事实,梁鸿也仍然秉承做“展示者”而不做“启蒙者”的理念,在作品中融入大篇幅的被访人的口述,如阿列克谢耶维奇一样,力避以“启蒙者”的眼光去审视和反思这一切,做一种“平视”而非“俯视”的观察和描述。当然,梁鸿的“展示”并非“零度介入”或“有闻必录”,对事实的“编码”实际隐含着作家的主体因素在其中。因为在梁鸿看来,“梁庄”以及被遍及全国各地的梁庄打工者所延伸出来的乡村,“都不是与‘我’无关的事物”,“我们应该负担起这样一个共有的责任,以重建我们的伦理”。因此,作者并不只是简单地回到梁庄,记录“我的亲人”和“我的故乡”,而是“重回生命之初,重新感受大地”,并且清晰地揭示自己在亲历家乡巨大现实变迁时所表现出来的或惶惑或温情或伤感或欣喜等种种矛盾情感。
在回到“小村庄”、描述“小人物”、构筑“小历史”的同时,梁鸿还力求以更为深邃而广阔的视野,透视以“梁庄”为代表为象征的中国当代乡村现实与历史的变迁,显示出人在社会巨变面前的复杂心态——“当把一种正在生长、正在转型的文化看做现实,并从此出发去寻找新的出路的时候,我们忽略掉的是什么呢?是仍处于这一文化中的人们。他们的情感、思想,他们的生存方式并非全然跟随这一转型而变化,相反的是,他们可能仍然渴望回到那种传统的模式中。”这既是对人心的真实描摹,也是更高层面“以人为中心”社会发展理念的体现。在这一点上,梁鸿与阿列克谢耶维奇有着比较多的一致性。
“非虚构文学作品的激增,标志着人类写作活动的一重大转变,即从传统的艺术虚构写作转向现代的纪实写作。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写作方法已难反映当代这个繁杂快节奏的世界了。真实生活的生动性有时超过了虚构故事的魅力,人们变得越来越喜欢看杂志文章,喜欢看真实的故事。”这段话虽然是对美国上世纪60年代非虚构文学作品兴盛原因的总结,但它也再好不过地概括了非虚构文学绵延至今成为世界文学大潮的壮景。“喜欢看真实的故事”当然是其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由美国的诺曼·梅勒,到白俄的阿列克谢耶维奇,再到中国的梁鸿,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非虚构文学对于现实和历史叙述的独特性。是否也可以这样说,在再现现实真相和还原历史原貌方面,非虚构文学拥有极大的文体优势。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写作《我是女兵,也是女人》时曾做过这样的田野调查:“我走遍了全国各地,几十趟旅行,数百盒录音带,几千米长的磁带。采访了五百多次”,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作品不断修订完善。“它们在这里没遭遇任何加工处理,十足地原汁原味。”在此,仅仅是田野调查一项,强烈的现场感和原生态就足以给予读者以强烈的真切感受和情感冲击。然而,更为重要的是,非虚构文学在叙述现实和历史时候所应该具有的超越感,这是对具体细节、事件等等的超越,最终进入到人的终极关怀上,实现形而之下与形而之上的完美结合。这也许是非虚构文学与历史、新闻、社会学等相区别,使之成就为“文学”的一个根本所在。
(责任编辑 王 宁)
王晖,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