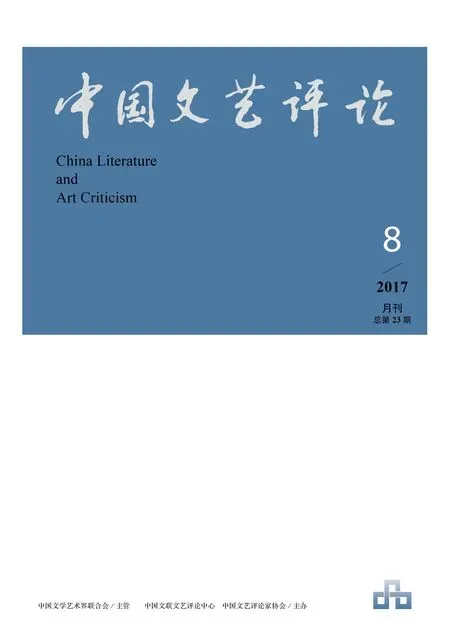香港和内地文论交流的回顾与思考
黄维樑
香港和内地文论交流的回顾与思考
黄维樑
本文结合作者的亲身经历,以比较文学和《文心雕龙》研究为中心,回顾了香港和内地文学理论学术界之间的交流互动,总结了香港和内地学者在实现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中西文论整合与建构,以及“龙学”研究等方面的历程及主要成就,指出应以内地学者为主力,发挥香港学者的优势,推动中国学派建设。
文论交流 《文心雕龙》 香港 比较文学
两地学者络绎交流
香港这小岛紧接内地,有祖国广大的腹地,与内地向来交流互动;19世纪中叶成为英国殖民地之后,情形不变。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文革”的政治动荡时期,与内地之间仍然联系着。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两地的交流互动,很快就从以前的细水长流,变得长川巨流起来:金融经济专家交流,文艺学术名家也交流。在动荡和封闭之后,国家改革开放了,开门向哪里,放眼看哪里?最近的地方是香港。面积1000平方公里的资本主义殖民地,有千新百奇值得内地同胞观摩的事物。很多香港人则想接触内地来港的人物,也想亲身到内地体验新发展、新景象。
笔者1976年夏天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随即返回母校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数年后内地改革开放,与内地交流的香港学术机构,中文大学大概是最积极的。1981年秋天,中大中文系举办现代文学研讨会,柯灵、王辛笛等先生应邀参加,余光中教授(1974-1985年在中大任教)发表讲话,题为《给辛笛看手相》(辛笛有诗集名为《手掌集》)。中大新亚书院邀请多位内地学者来校主持讲座:1981年有清华大学的钱伟长教授;1982年有北京大学的王利器教授;1983年有中国社科院的贺麟教授;同年还有美学家、北京大学的朱光潜教授,书院特别从台湾请来钱穆先生让两位老人家会面。1984年秋中文大学把荣誉文学博士学位颁予巴金先生,表扬秋收累累的文学家,并趁此举行会议,让巴老与香港文化界谈文说艺。另一方面,文学界、学术界人士赴内地开会、讲学或者拜访前辈的,这几年也络绎于途。
1984年4月,我第一次赴内地参加文学学术研讨会;同年夏天第一次到北京旅行,心血来潮要拜访钱锺书先生,且如愿拜会了。也就在这1980年代初,潘耀明在内地辛勤的采访之后,撰写和出版了他的《当代中国作家风貌》正续两编。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活动纷繁,难以备述。这几年的交流互动,我只就记忆和手边资料所及,略加举例如上,把焦点定于“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和“龙学”也就是《文心雕龙》研究展开记述。
香港的大学校园有“比较文学家之径”
比较文学研究的是不同语言、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传统的文学,剖析比较其异同,或追寻其相互影响的轨迹。比较文学兴起于19世纪的欧洲,美国在20世纪接其绪;而比较的兴趣和论述方法,则源远流长。20世纪比较文学作为学术专业进入中国之前,清末的知识分子接触西方文学时,就已一边阅读一边比较:中国小说和法国小说的起笔有何不同?狄更斯和司马迁的文笔,谁更超卓?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比较文学在中国兴起并发展;1950至1970年代,内地的比较文学变得消沉以至寂灭。
而1950年代开始,海峡对岸的台湾,学术文化受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影响越来越大;留美之风大炽,“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成为青年学子的口头禅。在台湾,比较文学在1960年代兴起,至七八十年代而大盛。香港是中西文化交汇之城,知识分子的言谈与书写,常常喜欢中文与外文(主要是英文)夹杂、中华事物与西方事物比较,文学学术界早有中西比较文学的土壤。1970年代中叶开始,一些具台湾背景和留美经历的文学学者,加上具香港背景和留美经历的文学学者,先后到香港的大学任教;天时(邻近的台湾此时比较文学大盛)、地利(香港有中西交汇、中西比较的土壤)加上人和(进来了具有留美经历的学者),于是在大学里特别是在香港中文大学里,比较文学赫然出现。
1970年代中叶开始,在香港中文大学,短期或较为长期,从事中西比较文学教学和(或)研究的华裔学者,包括余光中、梁锡华、笔者(以上属于中大中文系),袁鹤翔、周英雄、郑树森、王建元(以上属于中大英文系),另外有美国人李达三(John Deeney, 属于中大英文系,具台湾背景);在香港大学,则有锺玲和黄德伟。
1997年香港回归,首任特首董建华1999年的施政报告,表示把香港定位为“亞洲國際都會”;说在文化方面要见纽约、伦敦之贤而思齐。差不多与此同时,美国《时代》周刊有专辑论“九七”后的香港,封面的专辑标题是“自铸伟辞”(这四字出自《文心雕龙》)式的“New-Lon-Kong”,意思是香港很可发展成为纽约和伦敦一样的国际大都会。1960年代起香港经济快速发展,衣食足而后知文化,香港又长久以来中西文化交汇;因此,1980年代的香港,可说是迷你型的纽约、伦敦、巴黎,是个“小纽伦巴”(a mini-New-Lon-Pa)。香港的华裔学者与内地的学者同种同文,都是所谓“龙的传人”;内地学者尤其是年青的一代,要窥探、接触境外以西方为马首的文化学术新世界,香港地利人和,是经济便捷的首站。
1985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暨首次学术研讨会,在深圳大学召开。会议汇集了内地老中青不同年龄段的比较文学研究者,香港的一些同行则赴深圳参与盛会。就记忆所及,香港中文大学的袁鹤翔、李达三、周英雄和笔者都出席并做了演讲。我讲了一两场,内容是美国的新批评,以及加拿大佛莱(Northrop Frye)的原型论(archetypal criticism)。在1985年稍前和以后到中大访学的内地文学学者或比较文学学者,络绎于途。他们在中大一般居留一个月到三个月,与中大英文系、中文系和(基本上由中英文系讲师教授组成的)“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中心”成员交流,在中大图书馆阅读查看各种资料,与若干中大学者从事合作研究,参加学术研讨会或座谈会,或主持讲座。
上述中大中文系和英文系的学者,多少都参与接待和交流活动,我是较多参与者之一。所费心血、时间、精力最多的是李达三。他拟定计划、筹措经费、接待访客、安排活动、合作研究,日以继夜,工作繁重。1985年,当时40岁的刘介民到香港中文大学访学,以后多次到港,和李达三从事比较文学合作研究。二人多年多番互动,编印了多册资料集和文集。刘介民和李达三的关系亦师亦友,延续了30年,见证了港、陆两地交流互动的盛况。曹顺庆是当年另一位到中大访学的年轻学者,他曾与我合作编印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垦拓——台港学者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一书,我在此书的序言写道:
中文大学是香港以至台湾、大陆比较文学的重要基地。德国的海德堡和日本的京都,都有“哲学家之径”。在我看来,中文大学的山村路、中央道、士林路可连成一线,谓之“比较文学家之径”。香港的、台湾的、内地的、其他地方的比较文学学者,在这条路上行走,或上学,或回家,或前往参加研讨会,或回宾馆休息,他们在山径上沉思冥想,柳暗花明,涉及的常常是比较文学的问题。李达三、袁鹤翔、周英雄、朱立民、锺玲、乐黛云、刘介民、曹顺庆、张隆溪、雷文(Harry Levin)、奥椎基(A. Owen Aldridge)等等,都在这里留下了他们比较文学的足迹和思维。
20世纪西方的文学批评理论,有精神分析批评、英美新批评、现象学批评、神话与原型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结构主义批评、解释学批评、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批评、解构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等,可谓风起云涌,西风吹遍全球。求知若渴的内地年轻学者,在“小纽伦巴”取西经,往往大有收获。返回内地后,他们继续努力,不少人争取机会出国进修。凭着聪颖勤奋,加上运气,很多当年的萌芽学者(budding scholar)都已大有成就。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倡议
改革开放伊始,内地文学学术界即采用西方理论来研究中国古今文学;西风越吹越烈,以至几乎有全盘西化的态势。极为西化的现象,1970年代的台湾比较文学学术界已出现过。有识之士认为泱泱的中华古国,不能这样唯西方的马首是瞻,因此有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倡议。李达三、陈鹏翔、古添洪在1970年代下半叶,分别撰文阐释“中国学派”的研究取向,大意是在引用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文学之际(也因此“中国学派”曾被认为基本上就是“阐发派”),要对西方理论“加以考验、调整”,并从中西比较中,进一步“找出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法则来”。身为美国人而曾经在台湾教书、后来在香港教书的李达三,不同意一切以西方为中心。他倡议“中国学派”的一大目的,是希望“在自己本国(即中国)的文学中,无论是理论方面或实践方面,找出特具‘民族性’的东西,加以发扬光大,以充实世界文学”。李达三原为耶稣会教士,他提倡“中国学派”和促进相关学术活动,有近乎传教士的宗教情操;在从台湾转到香港任教后,经常赴大陆开会、讲学,其热心不变。
改革开放开始后数年,内地一些先知先觉者如季羡林、严绍璗、黄宝生、曹顺庆,反思西化的学术界状况,感叹中国没有自己的文论话语,没有在国际论坛发出中华的声音。台港那边有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呼声,内地听到了,于是也就此议题讨论起来。曹顺庆接过李达三“启蒙、催生的”学派旗帜,使之在神州的比较文学场域飘起来(王宁另外有创立“东方学派”的说法)。学术界一方面大用特用西方文论,一方面认为中国要重建文论话语,中国的古代文论要作现代转换,学者们要建立中国学派。
曹顺庆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做了说明。他从“跨文化研究”这一理论特征出发,指出其方法论有五:阐释法(或称阐发研究);异同比较法(简称异同法);文化模子寻根法(简称寻根法);对话研究;整合与建构研究。曹氏所论,企图涵括20世纪多位比较文学学者如朱光潜、钱锺书、乐黛云、钱中文、张隆溪、谢天振、王宁以至港台海外如刘若愚、叶维廉、袁鹤翔、李达三、陈鹏翔、古添洪的种种理论和观念,是一个深具雄心和融合性的体系。曹氏的“跨文化”说法引起若干争论,至于涉及的中西文化比较,二者是异是同,也众说纷纭。钱锺书有“东海西海心理攸同”说,张隆溪和笔者等都认同。不过,“核心”与“至理”虽同,中西文化毕竟千汇万状,从其异者而观之,则异者举不胜举。十多年来,谢天振在(与比较文学关系密切的)翻译研究提倡“译介学”,曹顺庆提倡“变异学”,都是关于“异”的理论。如此等等,内地最近二三十年来,比较文学的诸多理论,先后登场,蔚然大观。
两地“龙学”的交流互动
建立中国学派、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研究中西文论如何整合与建构——从这些话题,我们正好转到另一个:内地和香港对《文心雕龙》的研究及其学术互动。《文心雕龙》体大虑周,是公认的中国文论至尊经典。百年来的《文心雕龙》研究,号称“龙学”,是显学。20世纪的龙学家,从黄侃、刘永济、范文澜、杨明照、周振甫、王利器、詹锳、郭晋稀、王元化、牟世金等,只列述先贤,已经阵容庞大;加上内地学者,可编成一份如长龙的名单。1962年12月出版的《香港大学中文学会年刊》为《文心雕龙研究专号》,是香港早期龙学成果的一个展示。内地和香港,“文心”互通,活动起来,可以就是一条“龙”。改革开放以来,龙学的显学地位日升,1983年“中国文心雕龙学会”成立,此后经常举行龙学研讨会。就记忆与手边文献所及,1988年在广州举行的“《文心雕龙》1988国际研讨会”,香港的陈耀南和笔者应邀出席;其后近30年的龙学研讨会,笔者和其他香港学者每有出席者。参加研讨会是同行学者交流互动的好时机,切磋琢磨之外,还可为后续的互访争取机会。
龙学者一般是中国本位的文学研究者,很少涉及西方文学的,与比较文学学者的“一脚踏中西两文化”不同。内地如此,香港也差不多。百年来的龙学,在版本研究、篇章解释、全书结构、中心思想、作者生平等范畴,成果丰硕,自不待言。根据戚良德编著《文心雕龙分类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一书的统计,直至2005年的近百年来,学术界论述《文心雕龙》的单篇论文有6143条,专著有348条,西文论著有26条;虽然这个统计有不少遗珠,却足以证明龙学确实是显学。蒋述卓等著的《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与黄霖主编、黄念然著的《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文论卷》(上海的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两书中,《文心雕龙》都是最为重要的述评对象之一,所占篇幅极多,这也可说明其显赫的地位。
中国本位的龙学者之外,也有另类:少数兼涉中西文学的龙学者,则从比较诗学(comparative poetics;诗学的意义基本上等同文学理论)的角度,通过比较,阐释《文心雕龙》的义理。比较论述是自然不过的学术作为,前文提到中国比较文学的发轫,对此已有提示。鲁迅在《诗论题记》中早有比较诗学,他说:“篇章既富,评骘自生,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斯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 钱锺书、王元化、詹锳等的龙学论述已有比较诗学的元素,王毓红的《跨越话语的门槛:在〈文心雕龙〉与〈诗学〉之间》(学苑出版社,2002年)与汪洪章的《〈文心雕龙〉与20世纪西方文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一与古代比较,一与现代比较,是龙学的比较诗学专著。
笔者是龙学“少数派”的一员。1991年10月笔者应邀在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筹备处,以《〈文心雕龙〉与西方文学理论》为题,做了一个演讲,后来据演讲录音整理成文,分别在台北的《中国文哲研究通讯》和上海的《文艺理论研究》发表,时为1992年。在此之前九年,即1983年,笔者已发表论文,比较《文心雕龙》与“新批评家”的结构理论。同为1992年,笔者另外发表专文:用《文心雕龙》的六观法来评析白先勇的小说《骨灰》。可以说,笔者自此之后的龙学撰述方向——通过中西比较以彰显《文心雕龙》的理论特色,把其理论用于文学作品的实际批评——在这一年已决定了,这也是笔者为龙学新辟的蹊径。
笔者在研究、教学、撰述的兴趣,主要是20世纪汉语文学和中西文学理论,《文心雕龙》是个重点。1992年前后,我参加内地的文学理论或《文心雕龙》研讨会,发表论文,基本上都以《文心雕龙》为论题,相关论文都曾在内地、香港以至台湾刊布,并先后得到两岸三地同行的回馈,内地的尤其多。1995年,笔者在北京参加《文心雕龙》研讨会,在论文中发出慨叹:“在当今西方的文论(学术界),完全没有我们中国的声音。”
这与曹顺庆的“失语症”说可谓同声同气;希望藉着《文心雕龙》为中国发声的意图,这里颇为明显。比较文学如果要具备中国特色,甚至建立中国学派,其理论最宜由中华学者来建构。这样的建构不可能凭空而来,而极可能以至必须以传统的理论为厚实根基;建构起来的理论,必须通达,具有普遍性,且具备可施诸作品析评的实用性。内地有不少学者推崇王国维《人间词话》的“意境”说,且有用它来搭建具中国特色理论之意。笔者曾发表评论,表示“意境”说的内容单薄,可成为一间诗论的沙龙雅舍,而不可能成为文论的巨厦华楼。以言宏大以至伟大,非《文心雕龙》莫属。
二十多年来笔者陆续在内地刊布的龙学论文,获得很多内地比较文学或龙学学者的肯定;有学者甚至指导研究生,以笔者的《文心雕龙》六观法论述为对象,写成学位论文。受到种种鼓舞,笔者终于完成写作计划,出版了专著《文心雕龙:体系与应用》(香港的文思出版社,2016年),此书的重头篇章是《“情采通变”:以〈文心雕龙〉为基础建构中西合璧的文学理论体系》长文。如果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有中国学派的话,则《文心雕龙:体系与应用》应是这个学派的组成部分。笔者发表过这样的观点:中国学派这个标签,最好由其他国家的学者为我国贴上;我国学者应该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为目标,努力做出实绩;目前中国学派这名义,可作为同行的“内部参考”,可作为一种鞭策。无论如何,笔者由“龙弟”一步步成为“龙兄”,以至“龙叔”,以至可能升格为“龙伯”,其龙学成果,除了是来自个人的思维和修为,还与学术上香港、大陆两地的交流互动有很大的关系。
内地的学者应成为建构中国学派的主力
香港和内地在文论方面的交流互动还有很多,包括参加研讨会、出版文论专书、互访等,但也有交流中“流产”的项目。1990年代中叶的一个春天,李达三和笔者等到访北京大学中文系,与同行讨论合作出版一本用英文编写的中国文学理论术语手册。赴京前计划拟定了,在京时讨论了;后来由于港、台方面的原因,没有继续。
由这件事情,我们可以转而谈谈香港、内地学术文化发展的领先与滞后。“文革”期间万马齐喑,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等活动大多停顿。在此非常时期,香港正常发展;学术思想和研究实绩,在刚开始改革开放的内地学术界看来,这小岛在好些领域领先了大陆。但是,时代和形势会变化,领先可能变为滞后;反之亦然。
内地《文心雕龙》的学术活动,自从1983年“中国文心雕龙学会”成立之后,诸如举行研讨会、出版各种专著、专刊和工具书,一片欣荣。香港则从来没有举行过以《文心雕龙》为主题的研讨会;出版过的相关专著、发表过的相关论文疏落,龙学学者寥寥;据说某大学中文系的学生畏难,《文心雕龙》一科因选修者极少而开课不成。
比较文学方面,就在上面所说与北大合作出版英文编写中国文学理论术语手册会议那个春天,我们在开会期间,收到新近出版的《世界诗学大辞典》。这大开本的数百页巨册,由乐黛云、赵毅衡等主编,数十位内地学者撰稿,且由钱锺书题写书名。内地的比较文学学报,如《中国比较文学》《中外文化与文论》多年来持续出版;已面世的比较文学专著琳琅满书架满书室;比较文学在大学里成为重要的学术专业;不同性质和规模的比较文学研讨会,在国内不同地方经常召开,连全球性的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也定于2019年在国内举行了;内地背景的张隆溪且于2016年当选为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的会长。香港的比较文学呢?香港中文大学校园里的“比较文学家之径”呢?在20世纪末,郑树森、周英雄、袁鹤翔、李达三等都已先后离开中大,以后英文系和中文系的教授,或者由于学术经历不符合研究要求,或者由于学术兴趣不在此,就渐渐地少见与比较文学相关的活动了。香港的其他大学,就笔者见闻所及,似乎也少有把比较文学,特别是中西比较文学,当作一桩大事。不过,如果从上面提过的“阐发派”角度来看,香港的学者,引用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文学的大有人在,然则比较文学可说仍然生存。
内地的比较文学如日方中,声势浩大。下面再举一个实例:2012年曹顺庆主编《中外文论史》的出版。执笔者共有数十人;耗时前后二十多年;凡四卷共八编,连目录、前言、参考书目、后记,共约4180页;是皇皇巨著,是中国和外国迄今唯一一本广泛涵盖中国和外国文学理论的史书。主编者把世界的文学理论史从古希腊、中国、印度作为第一个阶段开始,共划分为七个阶段,每个阶段占一编的篇幅,一个阶段为时三数百年。七大编有如世界七大建筑;加上第一编(有如建筑群的中央大厦)“中外文论的纵向发展与横向比较”,全书共八编,八编之前还有主编者的《前言》和《导论》。此书涵盖的国家有中国、希腊、印度、罗马、埃及、阿拉伯、波斯、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朝鲜、越南、泰国、美国,跨越欧亚非美四洲,跨越不同的文明。在视野、规模方面,远非William Wimsatt和Cleanth Brooks的A Short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以及 Rene Wellek 的A Historyof Modern Criticism所能企及。此书的总体性、全面性、宏观性厘然可见。
笔者阅读这本巨著,深佩其内容扎实宏富。编著者在呈现中外文论的内容、在纵横通论中外文论之际,对《文心雕龙》作详尽述析,拿它和外国多部文论经典加以比较,彰显它的特殊贡献;这或可视作中国文论“发声”的先声。本书的内容不可能尽善尽美、无懈可击,尽管如此,这样的一本总体性《中外文论史》,诚为中外文论学术界的首先创制。如果目前汉语的国际性地位可与英语看齐,或者如果此书有英语等外文译本,那么,这部宏微并观、纵横比较、内容富赡、析评细致、彰显中国文论价值的《中外文论史》,是在国际文论学术界响亮“发声”了。
30年前,香港是“小纽伦巴”,后来虽然有发展,然而北京和上海已经和纽约、伦敦、巴黎直接来往,而且见她们之贤而思齐了,甚至将与贤齐了,香港的“借镜”价值大不如前。内地崇西之风仍盛,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意识的产生,却毕竟是一种反省,一种泱泱大国精神的兴起。香港的中国文学学者,当然具有中国意识,但这可能只是一种学术研究的中国意识,而不一定是国族心态。近年香港社会因为“政制改革”而论争不绝,持所谓“香港本土”观念者,态度狭隘,极少数极端者更对某些“去中国化”的做法东施效颦起来。一般大学里的中国文学教授,兼治西方文学者已少,即使有,也因为要保持“政治正确”,或因为不想被贴上莫名其妙的标签,而不愿明显表达自己的立场——譬如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相同或相通的看法。在香港,笔者是中国意识比较强的,因此才在文论界发出“让雕龙成飞龙”(这句话成为2000年4月5日内地一份报纸头版头条的大字标题)的呼声。在学术文化方面,就如其他很多方面一样,香港与内地相比,其明显的优势逐渐消失。香港从领先到滞后,内地从滞后到领先,正是“风水轮流转”。其实这是事理的必然:在学术文化条件相差不远的前提下,小岛与大陆的表现大有差别。情形如此,种种交流互动还是一定会继续的。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发达,社会日进,国力强大。内地学术人口众多,“势大”不必说,近年更颇为“财雄”。学术文化发展快速,人所共见;有时我们几乎可以联想到高速公路和高铁的气势。目前内地的学术文化,可以用非常兴旺来形容。学术界大幅度向西方开放,“海归”的留学生数目增多,中西的交流互动频繁,中西兼通的年轻一辈学者日增;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其发皇有了良好的条件。中国经济强大了,文化输出的呼声日高,建立中国学派(或建立具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理论)的意识日浓;有数十年来的学术积淀,成派的底子厚了。中国学派之学够强,则派可立。而建构中国学派的主力,无疑应该是内地的学者。
黄维樑: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
(责任编辑:胡一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