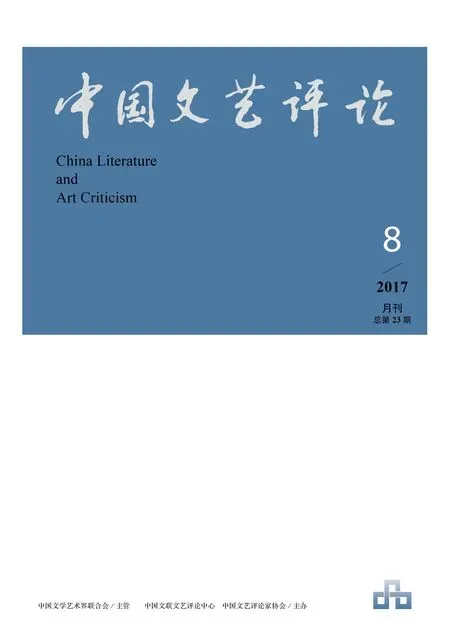生态话语与当代科幻电影的结构性困境
孙佳山
生态话语与当代科幻电影的结构性困境
孙佳山
二战后,当代科幻电影从最初的充满了科技性特征的乌托邦的先锋探索,一步步走向了后现代文化反思的梦魇呈现,而在这个过程中,生态话语起着至关重要的枢纽作用。深入解析当代科幻电影的历史沿革、来龙去脉,理清在当代科幻电影中已经事实上构成内在叙事动力的生态话语的发展线索,以及生态话语在当代科幻电影中所具体承载的审美表达和意识形态症候等不同结构性功能,就不仅仅关乎着对当代科幻电影流变的全面系统梳理,还将直接影响中国电影对于世界电影发展趋势的判断和认识。
科幻电影 生态话语 风景 乌托邦
二战之后,随着社会秩序的重建、影视技术的日渐成熟,在大众文化工业生产的逻辑下,科幻题材也在电影领域呈现出相对清晰的题材分类。尽管科幻电影在二战以来的发展历程中有着阶段性、周期性的回旋和曲折,但一个基本线索是当代科幻电影从最初的充满了科技性特征的乌托邦的先锋探索,一步步走向了后现代文化反思的梦魇呈现,而在这个过程中,生态话语起着至关重要的枢纽作用。因此,从生态话语切入,将是我们完整把握当代科幻电影全貌的强有力抓手。
尤其是近年来,以《2012》《阿凡达》《云图》《环太平洋》《雪国列车》《地心引力》《星际穿越》等为代表的,一系列被生态话语包裹的当代科幻电影在全球的热映并引发了持久的讨论和争议,足以说明这一话题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和热度,在这些影片中也充分地暴露出全球资本主义过度发展的深层次困境和当前全球中产阶级趣味自我想象的边界,同时也佐证了全球新自由主义背景下文化保守主义的价值取向。那么,能否深入解析当代科幻电影的历史沿革、来龙去脉,能否理清在当代科幻电影中已经事实上构成内在叙事动力的生态话语的发展线索?生态话语在当代科幻电影中具体承载着怎样的审美表达和意识形态症候等不同结构性功能?这些问题不仅仅关乎着对当代科幻电影流变的系统梳理,还将直接影响中国电影对于世界电影发展趋势的判断和认识。
一、最晚近的“发明”——生态话语在当代科幻电影中的源流
1963年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出版了标志着人类首次关注环境问题的《寂静的春天》。在此之前,征服大自然,重新确立人和自然的关系,作为打破中世纪宗教蒙昧的现代性启蒙理性,具有不言自明的正当合理性、合法性,不仅从未受到过任何质疑,甚至还有些神圣不可侵犯的味道,生态话语也从未出现在人类的任何辞典。在《寂静的春天》这部划时代的著作中,描述了人类可能将面临一个没有鸟、蜜蜂和蝴蝶的世界,以春天不再有鸟叫虫鸣为隐喻,在当时惊世骇俗地提出了农药将严重危害人类生存环境的旷世预言。这部著作自面世伊始,就强烈震撼了那个时代的广大社会民众,但也受到了美国麦卡锡主义与之利害攸关的垄断资本的猛烈抨击。因为在此前,生态问题从未进入到人类意识,卡森也因此遭受了空前的诋毁和攻击,而且持续了差不多十年光景,直到1972年联合国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人类需要有意识地保护环境才正式成为一个问题开始逐步浮出历史地表。此后,生态文学、生态电影、生态哲学等一系列新兴文化艺术现象和知识学派才得以蝴蝶效应般地陆续产生和发展,卡森的《寂静的春天》中关于昆虫抗药性的第十五章《大自然在反抗》和十六章《崩溃声隆隆》的部分内容,甚至构成了现在被奉为华语科幻经典的刘慈欣的《三体》中的一个核心元文本,是小说中情节演进的一个关键节点,足见其影响之深远。但这也绝非一日之功,这一过程也是足足煎熬了20年之久,1972年出版的对后世影响极大的《增长的极限》尽管在当时就某种程度的呼应了卡森的预言,但即便它是被国内阴谋论者所热衷的罗马俱乐部出品,在当时亦曾遭到讥讽和驳斥。一直等到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签署,世界各国才开始在政府层面围绕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进行了一系列谈判和磋商,生态话语才真正进入到全球性的公共文化领域,但也仅仅是登堂入室而已,形成今天这样的压倒性优势,还是从世纪之交才肇始。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在大众文化领域有着极高的曝光率。2000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保罗·克鲁岑,则提出了著名的地质学概念“人类世”。“人类世”指的是新生代第四纪以来继更新世、全新世之后的第三个地质时代,跨度则从1800年左右的工业化时期开始至今。在这个地质阶段,人类社会的种种活动已经取代了自然循环,成为塑造地球环境的最重要因素,而且人类如若继续肆意妄为,将很可能会引发第六次生物大灭绝。特别是近年来在哥本哈根、坎昆、德班等一系列联合国气候大会中,与会各国就全球生态保护问题的市景集市般的讨价还价后所产生的尖锐分歧,更是引发了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和焦虑。
当然,从科学界到文艺界,比如各类科幻题材作品,对“人类世”这个历史周期可能会引发第六次生物大灭绝的预期和恐惧,其实远远早于这个严谨概念的诞生,也早就有一大批科幻题材影片对此进行了几近全景式的想象和书写,甚至比这个概念走得更远。早在上世纪30年代,《洪水》就通过将自然灾害的发生地点放置在现代都市纽约,试图对现代化与自然的矛盾做朦胧地影射,而50年代的《世界末日》和70年代《惊恐万状》的科幻想象中尽管还带有某种“创世纪”式的宗教色彩,但生态话语的分量已经开始明显地提升。生态话语对当代科幻电影的逐步渗入和掌控,与全球范围内对生态问题的认识的逐步深入也几乎是同步的。在电影领域,尽管有着1982年捷克斯洛伐克的生态电影国际观摩、1984年的国际生态电影节,但是,生态话语开始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题材、类型,则是非常晚近的事情。当代科幻电影开始具有强烈的生态意识更已经是发生在1990年代,并且也是到了新世纪以后,生态话语才在不同题材的类型片中被赋予了普遍性价值,确实几乎所有近十余年来全球热映的影片,都多多少少地涉及到了生态题材。作为非常适应3D、IMAX,包括已经初露峥嵘的虚拟现实技术的当代科幻电影,在充分消化了当下最为时髦的生态话语后,也更为如鱼得水地讲述着现今时代的“主旋律”。
因此,作为在上世纪70年代前后才浮出历史地表,并且在世纪之交才开始进入到大众文化领域的生态话语,实际上是非常晚近的、晚生的产物,但在今天的社会现实生活中,俨然已经是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普遍”真理。尤其是在我国,美丽中国、节能减排等概念的提出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这也意味着下到娱乐文化消费,上到国家宏观政策,不同层次的审美诉求在这个领域都能愉快、顺畅地达成共识。也的确,生态话语,在今天的大众文化政治实践中,具有着“旗帜”性的号召力量,是大众文化的深层次审美需求的喷发焦点,任何需求和消费的呈现和表达,只要沾上生态话语,就能立即获得大众文化领域政治正确的“豁免权”。所以,生态话语、大众文化的生态政治,进入到电影领域,特别是以科幻题材电影的形态来呈现,不过是上述时代逻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必然结果。
二、最后的“历史终结”——生态话语在当代科幻电影中的功能
《2012》《阿凡达》作为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伊始的两部代表性作品,它们同时吹响了拉开中国电影百亿票房时代帷幕的号角。两部影片尽管各有侧重,但生态话语无一例外的在其中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两部影片也代表了受生态话语左右的当代科幻电影中的两条基本脉络:即《2012》所代表的灾难类科幻影片、《阿凡达》所代表的外星探索类科幻影片,这两种当代科幻电影的基本类型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延续,并承接和回应着这个时代的主题,或者毋宁说在映像着这个时代的焦虑和绝望。在两部影片中由生态话语所牵引的,与其说是生态灾难所导致的“逃亡”,不如说是在2008年之后,后全球经济危机时代,中产阶级所恐慌的,很有可能再也回不去的“日常生活”。
在“十部进口大片”时代的《未来水世界》就给中国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在1990年代中期,就把两极融化后,以人类对淡水、食物、资源的争夺等角度切入的可怕后果予以完整地视觉呈现,即便是对于当时的好莱坞观众而言,也实在是太过震撼和刺激,但如前文所述,这也不过是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签署所带来的蝴蝶效应之一,生态话语正是在那个阶段开始具有了不言自明的“先锋”性。因此,到了十年之后的2004年的《后天》,则是水到渠成,甚至已经不再具有太多原创性,从两级融化到两级冰封,仅仅是同一类型的反向呈现,门槛在逐渐降低,其寓言性也大打折扣。只是因为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同一导演操刀的同一风格的《2012》由于准确、及时地踩到了这一时代节点,视觉奇观意义的灾难类科幻影片才又在这个时代风靡一时,生态灾难于是成了市场上最“安全”的题材,因此也难免被这个时代所驾轻就熟。
而《阿凡达》所代表的外星探索类科幻影片,则接续了从1977年以来的《星球大战》系列,这一系列作品的影响力之大,几近当代科幻电影标杆的地位,也为《阿凡达》等作品做足了历史铺垫。尤其是当冷战谢幕之后,后冷战时代的《阿凡达》《云图》《星际穿越》所探索的外层空间,更是成为了新世纪版本的现代怀乡病的最佳载体,也全都被赋予了超越现代文明的意义,具有了审美上自明的绝对合法性,这一类作品自然也毫无例外地都体现出了强烈的史诗化风格。但以《阿凡达》为例,其实我们只要稍加聚焦,就不难发现:对《阿凡达》中潘朵拉星球的纳威族,和《与狼共舞》中的苏族印第安部落、《澳大利亚》中的黑人土著人相比,在形象刻画上实则并无二致;而《阿凡达》的灵魂树,和《与狼共舞》中的图腾崇拜、《澳大利亚》中的“奥兹国”,也太过异曲同工。这些外星探索类科幻影片中的星际空间,只不过是从《与狼共舞》到《澳大利亚》这一涉及少数族裔脉络的众多影片,所一直标榜的文化多样性的星际乌托邦版本——当地球已经在劫难逃的时候,还有优美的星空可以作为诗意的“远方”。
在上述两种非常主流类型的当代科幻电影中,自然以及被转喻为自然的宇宙与人类社会、人类活动都被放置在二元对立的结构中。自然和宇宙是有其自身规律的,能够完成自我调节的有机体系;而人类社会、人类活动则在很大程度上有了“原罪”色彩,之所以会出现生态危机,正是人类社会的过分发展干涉了、打破了原本均衡有序的、和谐稳定的自然、宇宙的法则与秩序。这几乎是当代科幻电影呈现生态话语的“标准格式”,当下大众文化领域的生态话语,几乎无一幸免地通过将自然、将宇宙予以诗意的符号化,将现代意义的人类社会、人类活动与自然、与宇宙的关系,以几近二元对立的结构安置在这个价值序列中,并在此基础上进而一步步完成对当下身份认同的重构,而人类“现代”的积极意义也因此被无视和遮蔽。所以,真正有价值之处在于,这种对“现代”的意义重构中所刻意遗漏的因素,这些当代科幻电影通过生态话语所呈现的想象性的“再现”关系,是如何被演绎成理应如是的“真实”关系的?也就是说,这种审美意识形态在竭力遏制哪些因素?这才是我们揭开生态话语在当代科幻电影中的功能和逻辑的秘密的关键所在。生态话语毫无疑问是这些科幻影片中,自然、宇宙与人类社会、人类活动相冲突、相矛盾时最为重要的“粘合剂”,但它所试图弥合的世界观、价值观困境,其实也恰恰是这些由生态话语所支配的当代科幻电影的最大症结所在。
无论是《未来水世界》《后天》《2012》,还是《阿凡达》《云图》《星际穿越》,贯穿于这些不同线索的当代科幻电影背后的,由生态话语驱动的自然、宇宙和人类社会、人类活动关系的二元对立式的二分法,其实只不过是在这个年代畅通无阻的全球新自由主义话语的文艺“变体”,活灵活现地展示了新自由主义话语的一体两面:在经济上,市场和自然、宇宙一样,都是均衡有序的、和谐稳定的有机体系,具有完善的、自律的自我调节机制;在政治上,国家只能做好“守夜人”的角色,丝毫不能干涉市场的环境和秩序,就像人类应该遵守自然和宇宙的规律和法则一样。市场、自然、宇宙,在这里具有相同的语义,具有着万法归宗的神谕式效应。
而且,新自由主义的功力还远不止于此,它还以当下的生态话语为节点,充分消化了在启蒙时代,就已经蕴藏的反现代的审美现代性因素,也就是与当代科幻电影差不多同时代诞生的,对自然的崇尚和对人类社会的工业化进程相抵制的浪漫主义文艺思潮(例如以在大众文化领域经久不衰的《瓦尔登湖》为代表),而且还完成了在浪漫主义的基础上的更进一步。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生态话语中,自然逐渐上升为具有“神性”的存在,人类在自然面前已经“沦为”只能听命于开始具有“神性”的自然法意义的“原初”生命。这的确颇有些颠覆性效果,毕竟在启蒙时代完成的由人取代上帝作为世界的中心,被自然作为世界的中心所替换——回到前现代的社会共同体之中,恢复传统的等级秩序,这不正是全球新自由主义格局下典型的政治上的文化保守主义观念吗?《云图》就是最为经典的例证,由六个彼此形成互文指涉关系的文本所构成的意义体系,在经历了煞有介事的九曲回肠之后,其所召唤和还原的,正是自然法意义上的“原初”自由。因此,在这个逻辑下,无论是过去政治意义上的征服大自然,还是后来经济意义上的资本扩张,都不可避免的带有了某种“原罪”式格调。那么在这些不同层次、角度的“原罪”之外,包括科幻电影在内的各门类文化艺术实践中,如何以“现代”的逻辑,而不是以前现代的逻辑——实质上是人为制造的看似“天然”的所谓的传统的逻辑——进一步深入到大众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内核展开批判,进而修正甚至引导大众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方向,最终进入到对现代性逻辑内部,对不同阶段的现代性的历史代价进行有效反思?而不是在表面上对以自然为喻体的星际空间进行诗意符号化,而实则以前现代价值作为这种生态话语的肌理。
因为如若以这个逻辑来演进,那么这些由当下生态话语所包裹的所谓的前现代“美丽”乡愁,恐怕只会让以“自然”为名的星际空间,再度被他者化,而且还将离我们越来越远;更进一步的艺术探索,也都只能停留在这“诗意”的抗争姿态中为止,我们还将再次深陷到大众文化的精神分裂之中。这也是这个时代受全球新自由主义的文化保守主义世界观、价值观支配的大众文化领域到目前为止,尚无法摆脱的时代痼疾。作为最晚近的“发明”的生态话语,在这里,却发挥着上一个年代都没做到的历史的“终结”作用。
三、最“清醒”的梦境——生态话语在当代科幻电影中的困境
如果我们想充分讨论生态话语在当代科幻电影中的起源、功能和困境,其实离不开对当下以全球新自由主义为表征的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认识和批判。如果仅就价值观角度而言,其实《雪国列车》无疑更具代表性。《雪国列车》中“破雪者号”环球列车封闭的列车环境,将各种矛盾集中起来形成了一个解不开的“死局”。这个“死局”正是理性被推向极致后的“疯狂”,而革命的意义则在这场极致理性的“疯狂”中,仅仅是理性的副产品——革命不再具有任何进步意义,仅仅是理性自我调整的“节拍器”——革命在最后和理性一起走向了绝境,或者说,革命成为了理性的殉葬品。那么超越性的意义由谁来赋予?毫无疑问,正如前文所述,无疑是生态话语所操控的“原初”自然,新自由主义正是藉此完成了“狗咬狗尾巴”式的循环论证——我们此刻正陷入在一种最为“清醒”的梦境中。
在《雪国列车》中,人类为了逆转温室效应而向大气层中散播制冷剂反而沦陷为“雪国”的境地,是这个时代由生态话语驱动的当代科幻电影的最为形象的隐喻。资本主义是一个巨大的现代性进步装置,这是现今的一般共识,正如本雅明所言,马克思说革命是世界历史的火车头,但在今天的情境下这一切可能恰好相反:也许,革命是火车上的乘客——即人类——去启动紧急刹车而所作出的努力。显然,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的不再是加速、不再是过去意义的“进步”,而是至少要给现代性的发展减减速、看看路,并以此寻找开启未来历史的真正有效节点。这也直接意味着我们该如何处置在这个资本主义式的现代性进步装置中的主体位置,也就是在当下的境况下到底需要一种怎样的主体性,才能让这个进步性装置放慢速度,乃至改变方向。然而遗憾的是,在《雪国列车》中,新自由主义生态话语所操控的自然,在取消了已经彻底走向疯狂的极致理性的合法性之后,也连带着取消了革命的意义。影片中柯蒂斯领导的底层挑战强权压迫的革命,最终只被赋予了技术性的价值,他们的反抗和牺牲不过是现代性进步装置中自我调节的“安全阀”和“刹车片”,也就是通过自然、宇宙和人类社会、人类活动的二元对立设置,取消了这个资本主义式的现代性进步装置中的主体位置。所以,在今天被新自由主义话语所包裹的中产阶级主体们,就只能被“拘禁”于这种生态话语的“穹顶”下,毕竟对当下的中产阶级趣味群体来说,想象地球的毁灭远比想象资本主义的终结要容易得多。由新自由主义生态话语所操持的科幻题材“艺术作品,或者直截了当地说,就是通过象征,将不断的变动固定化的同时又保持其变动性,进而解决了资本主义的动荡和资产阶级的稳定性之间的矛盾。一个事实上的矛盾被转化成了一种精神价值”,“这也是使形式合乎逻辑地诞生于其内容的运动,尽管在中产阶级社会的分裂世界当中,情形完全并非如此”。由新自由主义生态话语所把控的当代科幻电影,就是以这种方式和逻辑完成了在当下语境下进退有度的“障眼法”和“易容术”。就像吉登斯所说,“全球变暖带来的风险尽管看起来很可怕,但它们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可见的,因此许多人会袖手旁观,不会对它们有任何实际的举动。然而,坐等它们变得有形,变得严重,那时再去临时抱佛脚,定然是太迟了”。因此“吉登斯悖论”,对全球中产阶级来说还依然奏效,他们自我想象的边界在这种“精神价值”的指引下,被给予以了精耕细作地框定和标识。
以科幻题材影片为代表的文艺作品,无论是早期的以上世纪30年代的《未来的事物》为代表的,对科技改变未来的进化论式的科幻史观开始产生质疑的影像追问,还是二战后以《宇宙静悄悄》为代表的反思,它们始终都具备的一个基本特征,就在于其不可替代的前沿性和展望性。只不过这一切,在今天正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尴尬和困境,我们被完成循环论证的新自由主义生态话语牢牢地禁锢在“今天”,这恐怕是远比“囚徒困境”还要难堪的境地,因为我们即便完成《星际穿越》般的壮举,也依然是在“明天”回到“今天”,新自由主义话语的最精简训诫,也就是相信“今天”。所以,我们第一步要打破的枷锁,就是要打破将自然、宇宙和人类社会、人类活动的关系置于二元对立式结构的二分法。因为,尤其是在人类社会开启了现代性进程以来,自然就从来没有外在于人类社会;或者说,当资本主义进入到垄断阶段以来,人类活动对全球生态系统更是产生了根本性乃至毁灭性的影响:地球的几乎每一个角落,都已经被打上了人类的烙印,人类彻底以人类的方式改造了自然,也彻底地改变了地球的生态系统。这也构成了“人类世”概念的起点和结论。事实上,我们就是不在进化论的意义上进行讨论,均衡有序的、和谐稳定的,具有完善的、自律的自我调节机制的自然,也是很难客观存在的;充满了不可预知的突变、灾难等事件,才是真实的常态——这其实更接近“原初”意义的“崇高”概念,只不过这显然被选择性无视了。新自由主义的“审美话语的全部任务,就是弥合资产阶级秩序本身所特有的形式与内容之间的裂隙,这种裂隙在其他地方也体现为该阶级道德和文化领域的壅滞与它物质世界的变动之间的分裂”。今天新自由主义生态话语下所勾勒和描绘的自然,不过是在为全球新自由主义秩序提供“自然”的理由,使新自由主义国家的阶级、民族、性别关系也能披上“自然”的外衣,从而保证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空间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并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然法式的“原初”秩序权威,一切社会等级关系都因而被披上了生态话语的外衣,呈现出“自然而然”的样貌。这就是推动当代科幻电影演进的新自由主义生态话语的全部秘密,它在我们面前,以一种最为激进的“保守”形态出现,是这个时代挥之不去的梦魇和幽灵。
与国外特别是好莱坞科幻题材影片相比,我国的科幻题材影片的缺失还很突出,我们还缺乏真正内嵌于中国社会的科幻意识,本土科幻题材影片至少目前并未为当下中国提供新的文化认同,本土科幻题材影片也并未真正进入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随着刘慈欣的《三体》荣膺“雨果”奖,中国式科幻题材影片在如今如火如荼、已近疯狂的产业大潮中自然也不能免俗,势必将掀起一波不会短暂的中国式科幻题材影片浪潮。那么能否表达现代中国的经验与情感,能否为我们这个时代错综复杂的、难以名状的集体无意识化境、赋形?如何在当代世界电影的发展与当代文化的结构中把握中国科幻题材影片,它在未来会有怎样的走向和命运?这些都构成了在我国科幻题材影片发展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历史课题,与此同时,这也是当代中国文化应该密切关注的筋脉式问题。
结语:当代科幻电影——没有“明天”的未来?
综上所述,在今天,生态话语的的确确和我们几乎所有人的日常生活都息息相关,它也因此获得了接近垄断性的价值感召力,但在这种实则为循环论证式的新自由主义道德修辞背后,卡森的《寂静的春天》时代所开启的生态话语的前瞻性和建设性该怎样落地?生态话语该如何协调与人类“现代”的基本价值的关系?生态话语如何摆脱看似激进背后的文化保守主义形态?这些远未被触及的时代症结也为我们理解当代科幻电影提供着这样的历史启示:以当代科幻电影为历史标的,在对生态话语的探索和实践中,当代科幻电影能不能从前现代的“美丽”乡愁向“现代”风景再进一步深入迈进,在“现代”意义上正面、直面人类的“现代”的价值和种种“现代”的代价的考量和拷问?
那么,这就不仅仅是具有着世界电影史的意义,对于我们当前的整个文化艺术实践而言,都将是一道关乎着能否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挑战——在以生态话语为症候的这些看似最激进的“保守”形态所构筑的新自由主义“铁幕”下,这直接意味着我们到底能不能“看”得见我们的未来,甚至连科幻都很难想象出一个明确的未来,这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恐怕都将是一个叹为观止的“奇葩”历史周期。
孙佳山:中国艺术研究院当代文艺批评中心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杨静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