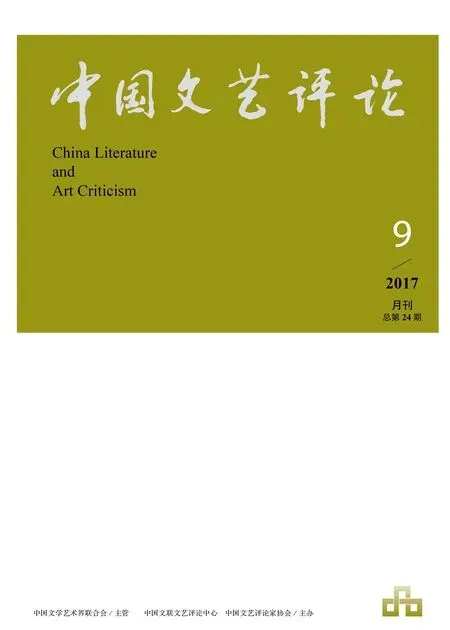延伸阅读
延伸阅读
“中和”的审美规范使得中华美学区别于西方美学
杨春时在《学术研究》2017年第7期撰文认为,中华美学的“中和之美”兼有“中和”的两种含义,既是外部和谐,也是内在和谐。中和观念在美学上的体现,形成了“中和之美”的概念。中和之美是判别美与非美的标准:符合中和则为美;偏离中和则非美。中和作为中华美学的审美规范,制约着中华美学的审美范畴。它既反对主体征服客体,也反对客体压迫主体,认为自由境界是主体与世界之间的互相尊重和亲和;它追求情理协调和内心的和谐,排斥任何极端、激烈的情感。近代以来的西方美学是主体性的,审美成为意志自由、自我实现的途径。而中华美学则具有主体间性,审美成为超越主客对立、实现天人合一的途径。此外,西方美学中感性与理性紧张对立,审美或者定位于超越感性、理性的神性(中世纪美学),或者定位于与理性冲突的感性(近代美学),或者定位于非理性的超验性(现代美学)。这种冲突使得西方美学产生了优美、崇高、荒诞、丑陋、悲剧、喜剧等审美范畴。而中华美学则围绕中和之美,产生了诸如秀美、壮美、哀怨、谐谑等审美范畴。中和之美塑造了中华美学的基本品格,如在“温柔敦厚”的规范之下,喜剧和悲剧都变得平和了,成为中华美学的哀怨和谐谑范畴;由于刚柔相济,中华美学的秀美范畴与壮美范畴之间也失去了对立性,彼此相容互补,从而区别于西方美学优美与崇高的对立。
庄子心性之学具有丰厚的美学意蕴
杨锋刚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 年8月8日撰文认为,庄子的心性之学所饱含并指向的那种对人性之“真”与“美”的理想和追求。对人性至真、至美的彰显和高扬,使庄子的心性之学具有丰厚浓郁的美学意蕴。人们往往把庄子的道当作某种外在的对象,习惯于以语言、文字、知识、思虑等方式去言道、思道、求道,并希望在此基础上拥有道,这使得我们非但不可能走向道、接近道,反而逐步地远离道、遮蔽道,从而造成人的现实生存的非本真状态。在庄子看来,只有从根本上断除关于道的种种认知、言说、思虑的意图、方式和手段,才可以无心而合道。为此,庄子特别强调“目击而道存”“以神遇而不以目视”“以心复心”等内在心性直觉对于体验道的意义。这就要求我们从外在对象性世界中转身,回到生命本身,通过“修心反真”“体性抱神”等心性修养的功夫,开启和守护内在生命的觉性和光明,让心灵回归精纯不杂、恬淡平易、虚寂专静的本然状态。
“身体美学”构建我国美学生态新景观
王亚芹在《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撰文表示,作为一种新兴的美学形态,身体美学跳出了后现代解构一切的思维方式,将“身体”翻新后重置入美学的核心,形成了对传统美学的拓展而非解构。身体美学“通过身体思考”激活了中西方文化中丰富多彩的“身体”资源,为重构美学谱系奠定了基础。中西方文化中都存在丰富繁杂的“身体”理论资源,但是,至今仍未有系统性的理论梳理与概括; 而且缺少一种实践性的东西,使这些理论能够平安“着陆”,接上地气。通过“身体美学”这种新名称,或许可以引起人们从更加多元化的角度去认知人类的“身体”问题。特别是我们传统的医学、武术、太极拳和禅定等身体训练方式与身体美学之间的相互阐释与相互支撑关系。中国传统哲学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实践品格,但由于近现代深受西学二元对立思维的影响,国内学界对这方面的关注很少。身体美学尽管是在西方文化的语境中孕育和成长起来的,但是在许多方面都与中国传统的身体观不谋而合,在中国找到了适合其成长的土壤,就我国学界而言,身体美学的出现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不但拓展了传统美学的研究空间,而且直接影响并建构着当前美学的生态景观。
书法审美需要文化的提升
向净卿在《中国书法》2017年第7期撰文称,个人审美习性或者个人审美偏好较多地源自于文化方面的修养,所有从古法帖而来的技术学习中伴随的审美素养的提高还不够,还需要文化修养的提高。这一点对于书法的学习非常重要,可惜在当代书坛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过度重视技术而忽略了个人审美偏好以及审美文化修养的提升,以至于其反而影响了个人后期技术的选择。许多书法家越到后期,技术越成熟,可是越来越单调或者越来越走向纯粹“技术癖”的路子,作品内涵越来越少,越走越板滞。究其原因,就是自认为掌握了完善的技术,选择自己喜欢的路子,殊不知,因为文化修养而导致审美偏好的偏离,从而对技术的选择造成偏执。个人审美偏好其实是一种心理活动,这种心理活动高度依赖于个人文化修养,趣味选择。从美学对于艺术主体的能力定义看,中国书法的想象力与灵感问题也不如其他艺术比如绘画、文学等那么突出,因为书法讲究的是日积月累,想象力与灵感在书法创作中的作用远不如绘画或者文学那么重要。相反,书法重视技术和修养的积累,重视情感的外化,或平心静气、或怡然自得、或狂狷不羁等等。
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味”
邹士方在《文艺报》2017年8月7 日撰文称,“味”是中国古典美学的特殊范畴,也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独有的概念。这与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的发达很有关系。刘勰、司空图对此都有很高的见解,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中,提出谈论诗首先要善于“辨于味”,诗歌的“味”,用譬喻来说,并非酸只是酸,咸只是咸,而要达到一种“咸酸之外”的“醇美”,或者说,是一种“味外之旨”。只有真正体会到“无味之味”,你才能在人生和文学艺术上达到崇高的境界。“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此之谓也。
家国情怀是中国美学的重要主题
张法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9月1日撰文指出,家国情怀是中国文化和中国美学中的非常重要又非常深厚的主题,然而现代以来,家和国的现实和观念都有了重大的变化。如何在美学和文化的结合上,合理吸收其文化和美学资源,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美学,尚是一个虽然一直在进行,却并未得到应有深入讨论的问题。家国情怀,用现代汉语来讲,可以说就是中国美学。这里的“可以说”意味着“不仅是”。“中国美学”是中国与西方在世界现代性进程中经过长期互动之后出现的语汇,其语词后面有着一种西方的方式,即要用一种与哲学—科学(知)和伦理—宗教(意)不同的美学—艺术(情)方式来看问题。而家国情怀,是建立在一种内在统一上而又具有很强的美学意味的古代汉语。中国文化从整体性来讲美,可以有很多角度,但以个人为基点,展开为两个方面,一是身—家—国—天下的向外扩展而来的整体,二是性—心—意—志—情的内在展开而来的整体。两者又如太极图般地相互关联着。从后者进入,一个由主体而来的中国美学特色就显示出来了,与西方由知情意划分而来的具有区分型特点的心理结构不同,中国的性—心—意—志—情呈现为关联型的心理结构。由性—心—意—志—情的主体,进一步进入身—家—国—天下结构,这一结构本有的美学性质就彰显出来了。家国情怀中的“家国”,内蕴的就是身—家—国—天下这一整体,家国情怀中的“情怀”,内蕴的就是性—心—意—志—情这一整体。在这整体中,性来自于天,是超时空的,性受时世的教化而成为心,有具体时空性质,意是性—心一体形成的具体思想或主意,志强调思想或主意的目标,情是内蕴着性—心的意—志的外在体现,情一方面体现性—心—意—志的具体性,另一方面又在主客互动中有喜—怒—哀—乐的类型特点,是二者的统一。从身—家—国—天下的整体性来看中国美学,可以将之分为两大基本类型,儒家的家国美学和道释的隐逸美学。这两大美学构成了中国美学的基本核心或曰场极。其他的各类美学都围绕着这两个场极,并在与之的关联中产生出自己的美学,如楚骚美学、玄学美学、都市美学、民间美学等。
⋆本刊转载部分文章的稿酬已按法律规定交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付,敬请作者与该协会联系领取。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120号太丰惠中大厦1027-1036室,邮编:100050,电话:010-65978917,传真:010-65978926,E-mail: wenzhuxie@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