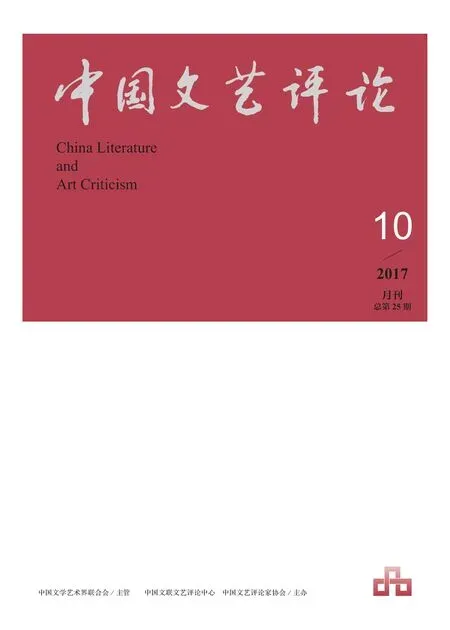传统“遗忘”理论对当代文艺创新的启示
高文强 王 婧
传统“遗忘”理论对当代文艺创新的启示
高文强 王 婧
创新是展现文艺时代精神的重要路径,但当前文艺领域所呈现出的面貌却是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因此,探索文艺的创新路径是十分必要的。在文艺创作过程中,“遗忘”现象的存在及发挥的积极作用给予我们非常有益的启示。“遗忘”机制的历史渊源与美学意蕴表明,创作主体的审美心理经历了从“去蔽与澄明”的审美心胸到“因忘而通”的审美境界这一过程,于“得意忘言”中,“遗忘”机制帮助主体摆脱创作的藩篱,走向文艺创新的自由之路。
“遗忘” 文艺创新 时代精神
创新是文艺的生命,也是文艺展现时代精神的重要途径。然而,当前文艺创新能力不足却是一种普遍现象,“模仿至死”甚至成为当前文艺创作追逐的一种潮流,这一状况值得我们深思。当然,造成当前文艺创作模拟成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在信息高度数字化的当代,曾经作为创作者优点的“知之甚多”正在从创新的动力转变为一股阻力,这一现象同样值得我们深思。面对当前文艺领域这一怪象,不仅令我们想起文艺发展历史中的“遗忘”现象。《庄子·德充符》云:“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谓诚忘”。在文艺创作中存在这样一种现象,面对理论与实践的长期积淀,优秀的创作者常常能“忘其所忘”,从而摆脱不必要的框架与束缚,进入一种自由自在的创作境地,从而创作出具有创新性的优秀作品,这一创作机制无疑为当前文艺创新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路径与方法。本文正是从这一思路出发,欲对“遗忘”机制在“模仿至死”的当下对文艺创新的意义作一理论分析。
一、当前文艺发展之痛与“遗忘”联想
在当前这样一个大众传媒时代,商品化的逻辑在社会中蔓延,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的距离被逐渐消解。我国的文艺在商品、文化、大众相互交错的时空中呈现出新的风貌与特质。以文学为例,其表现空间随着电子媒介与消费市场的发展得以拓宽。新的文学样式,如电影文学、电视文学和网络文学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文学与电影、电视走向联姻,众多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剧本,文学影视化趋势凸显。艺术的形态在趋向融合的过程中亦加速了文艺市场的兴盛与繁荣,但繁荣背后也滋生了诸多病痛与隐忧。其中,文学与影视方面所存在的抄袭乱象尤为刺目。
在2017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王兴东直言“网络小说已成为抄袭重灾区”。面对记者采访,他指出这一现象的症结所在:“部分网络小说作者往往注重字数更新量而非作品质量,为保持读者的关注度、活跃度,以及自身收益,网络小说作者力求每日更新作品章节,从5000字至上万字不等。此种荒唐的创作需求催生并助长了行业的歪风邪气,更导致‘黑色科技’在行业中大行其道。”因此,针对这种网络文学抄袭之风、“抄袭软件”泛滥的行为,王兴东建议,加大文学原创权保护,清除复制抄袭“毒瘤”。不独网络文学,影视剧方面的抄袭跟风现象也随处可见。正如一位学者所批评的,当前文艺领域是从“创意匮乏到模仿至死”,这种创新能力的不足将严重阻碍文艺的健康发展。
当前,国家已经深刻意识到当下文艺的发展之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在习总书记看来,创新是文艺的生命,文艺创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同创新能力不足有很大关系。他还强调“文艺创作是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合的深度创新,是各种艺术要素和技术要素的集成,是胸怀和创意的对接。要把创新精神贯穿文艺创作生产全过程,增强文艺原创能力。”此外,“希望大家勇于创新创造,用精湛的艺术推动文化创新发展”是习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所提出的第三点希望。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精神,恰逢这样一个生机勃勃、文化繁荣的时代,在国家层面已视创新为文艺的生命,强调将创新精神贯穿于文艺创作的全过程,这一理念高瞻远瞩,切中时弊。因此,我们更有必要响应时代的号召,直面文艺的时代精神,为文艺的创新路径作出一些有益的理论思考与探索。
回顾中国的文艺发展历史,从创作主体革故鼎新,跳出创作藩篱,在前人的基础上成功创新的案例中可以发现,“遗忘”机制对当前文艺创作中存在问题的解决无疑可以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帮助,因为这一机制在历史上曾经“帮助”许多作品流芳后世,成为经典。
文艺发展中所存在的“遗忘”机制是文艺在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基本规律之一,“遗忘”可以用来概括文艺发展机制的部分特性。“遗忘”机制中的“遗忘”迥异于其他学科里的“遗忘”概念。这种存在于文艺发展过程中的“遗忘”并不是说真正忘却了过去所发生的事件,而是在文艺创作方面,前代作品对主体创作的影响往往是潜移默化的。在创作主体构思与创作时,主观上并非有意模仿或联想到前人的成果,却创作出了与先前作品具有相似语词、体例或意境的文本,甚至还成为文艺史上的经典。而这种相似是作者当时浑然不觉的,并非故意而为之,且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艺术魅力与风格。比如,王勃《滕王阁序》中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与庾信《马射赋》中的“落花同芝盖同飞,杨柳共春旗一色”相较,两句在语词与语序方面的相似度极高。这一“遗忘”现象的心理过程就在于后人在阅读前人之作时,会对其中的点睛之句反复玩味,感触颇深,积累并消化进自己的语料库中。当情感一旦被外物感发,先前的积累就会在创作中不自觉地在主体的无意识里起到积极作用。
由此看来,在“遗忘”机制的影响下,文艺创作能够变得更加自由,从而使文学紧跟时代的步伐。重视文艺创作中的“遗忘”现象有助于将其区别于创作过程中的借鉴、模仿等形似而实不同的特殊文艺现象,也启发我们在文艺实践中要善于“遗忘”,从而突破传统思维与观念的藩篱,摆脱前人创作的消极影响与束缚,进而体验自由的创作与审美。
二、“遗忘”机制的历史渊源与美学意蕴
那么,这一机制有利创新的理论依据在哪里?事实上,出现于文艺创作中的“遗忘”现象自古有之。追根溯源,早在庄禅那里,便可窥见“遗忘”现象的历史与哲学依据。在艺术的领域里,庄禅思想常浑然一体,难分彼此,对后世的文艺思想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以庄禅思想中的审美遗忘性为历史依据,可以明晰“遗忘”机制所蕴含的美学思想,从而进一步探究“遗忘”现象的合理内核。
1.“去蔽与澄明”的审美心胸
审美心胸是主体进入审美活动的前提。在进入审美活动之前,只有将心理调整或历练至一个较为理想的状态,才能达到令人满意的审美之境。早在先秦的《老子》一书中就出现了“涤除玄鉴”这一命题,老子云:“涤除玄鉴,能无疵乎?”意思是洗掉尘垢,排除人们的主观欲念,使头脑像镜子一样纯净,有利于实现对道的观照。后来,庄子把老子“涤除玄鉴”的命题发展成为“心斋”“坐忘”的命题,建立了关于审美心胸的理论。与之相似的是,“遗忘”机制的发生也是主体在进入创作活动之前,心理主动“去蔽”的过程,这与庄禅所倡导的思想路径相吻合。
“吾犹守而告之,参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庄子·大宗师》)
程小青在翻译过程中并不是全盘的异化,应该归化的地方还是采取了归化的策略。若是一本小说,读者阅读过程中碰到的全是陌生的文化,读起来太生分,则会丧失阅读兴趣。柯南·道尔小说原文中的一些词,在目的语文化中是没有的,程小青则是采用归化的手法将其译出:
《庄子》中的这段话明确指出了人们可以通过遗忘来达到心灵“朝彻”的理想状态。“外”的含义即是“遗忘”。成玄英疏曰:“朝,旦也。彻,明也。死生一观,物我兼忘,惠照豁然,如朝阳初启,故谓之朝彻也。”其实质是一种“虚静而明”的审美心胸,遗忘又何尝不是一种虚静的状态。此外,《庄子·达生》云:“工倕旋而盖规矩,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灵台一而不桎。”工倕用手指旋转画圆圈等而能与用规和矩所画的相符合,他的手指所画之图妙若自然物象。正因其完全不依赖于心思的指示,摆脱了感性与知性的束缚,所以他的心灵才能专一而不窒塞。
禅宗亦有名异而实同的观念。如菩提达摩禅师曾倡导壁观,以壁观教人安心,去除妄想,从而回归真性,与外在的道体相契合。“达摩以壁观教人安心,外止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可以入道。”(《禅源诸诠集都序》卷二)这种“凝住壁观”的修心方式与庄子“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精神内核趋同,都有利于培养艺术创作或欣赏主体的虚静之心。洪州黄檗希运禅师的一段话也颇具启发性:
“凡人多为境碍心,事碍理。常欲逃境以安心,屏事以存理。不知乃是心碍境,理碍事。但令心空,境自空。但令理寂,事自寂,勿倒用心也。凡人多不肯空心,恐落于空,不知自心本空。愚人除事不除心,智者除心不除事。菩萨心如虚空,一切俱舍,所作福德皆不贪著。然舍有三等,内外身心一切俱舍。犹如虚空,无所取著,然后随方应物,能所皆忘,是为大舍。”(《指月录》卷十)
这可以视为对虚静之心以禅宗视角的另一种阐释,心能碍境,心空才能境空,智者重视心的作用,懂得除心之道,最后方能达到能所皆忘,随方应物之境。这便是去蔽后,澄明的审美心胸为文艺创作所能准备的最佳状态,为审美境界的获得作好铺垫。
另外,“遗忘”之所以能够塑造与培养主体的审美心胸,是因为这一审美心胸关联着超功利与任自然的审美心理,故这一机制能在文艺创作中发挥巨大作用。
《庄子·大宗师》云:“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不忘记生命之源,亦不寻求归宿;有了生命之后就常自得,一任复归自然而忘记是死。这是庄子对生死的理想概括与诗意总结。“遗忘”机制也是如此,它并不是完全的遗忘,作者创作能力的高下必然要受到先前知识积累与文化观念的影响,所以不能忘其所始,但创作的结果不应该是作者所刻意追求的,作品的好坏与影响也不应是亟待作者关心的。在纯任自然的过程中情动而辞发,享受自由的发挥与创作,才有可能取得较为理想的结果。此外,《庄子·达生》上说:“仲尼曰:‘善游者数能,忘水也……凡外重者内拙。’”擅长游泳的人在经过多次练习之后能学会驾船,是因为忘掉水能危害人的性命。凡是看重外物的人,其内在的心思就笨拙。因此,在文学创作与欣赏中,必须摆脱不必要的心理束缚,而“遗忘”恰能去除许多负累,使心灵变得圆融、畅达,“遗忘”机制能够将心理调适至自然与平衡的状态。
庄子对“忘”之境界的追求更加彻底,“故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庄子·让王》)不但要忘掉形体与利禄,还要连心神也忘掉,如此才能超越意志与形体,获得至道的境界。但正如“艺术要摆脱一切然后才能获得一切”,审美必须是超功利性的,而“遗忘”机制正具备了超功利、任自然的精神实质。遗忘是一种超越,作为创作主体和欣赏主体都会不约而同地在某种条件下产生超越对象的心理行为。这种遗忘的心理行为并非如同单纯的生理遗忘,而是在建构新的主体心态,它在从“忘”至“空”“无”“虚”的过程中解除纷扰,进入澄明的心境,无功利地、自由地与万物交融,从而实现心灵的高度自由,并由此导出诗意的人生态度。
2.“因忘而通”的审美境界
有学者认为,作为一种触及整个身心的活动,审美活动通过感物动情的诗意方式,体现了对象与主体身心的贯通——使全身心都获得愉快,并通过虚静的心灵,和特定的感悟方式使主体的生命进入崭新的境界。这一观点正好指出了“遗忘”机制运行过程的合理性,“遗忘”机制产生作用,其运行符合由虚静之心到生命进入崭新境界的过程。而这一境界,在庄子看来,则是“通”的审美之境。
《庄子·大宗师》云:“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庄子》解释了“坐忘”的内涵,可见,坐忘的结果是“同于大通”。郭象注曰:“夫坐忘者,奚所不忘哉!既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者,内不觉其一身,外不识有天地,然后旷然与变化为体而无不通也。”成玄英疏曰:“大通,犹大道也。道能通生万物,故谓道为大通也。”因此,“通”是与大道混同为一的无穷之境,指归于超越有限而把握无限的审美境界:
“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人相与友,曰:‘孰能相与于无相与,相为于无相为?孰能登天游雾,挠挑无极,相忘以生,无所终穷?’三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莫然。”(《庄子 ·大宗师》)
郭象注曰:“忘其生,则无不忘矣,故能随变任化,俱无所穷竟。”成玄英疏曰:“终穷,死也。相与忘生复忘死,死生混一,故顺化而无穷也。”由此可见,审美主体能够通过“忘”来达到无穷的境界,“无穷”则“通”。另外,《庄子·大宗师》曰:“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泉水干涸了,鱼儿共同困在陆地上,用湿气和吐沫相互滋润,还不如在江湖里彼此相忘而自在。与其称誉尧而非难桀,就不如善恶两忘而与大道化而为一。所以,“忘”的好处就在于它可以引领人们走向无穷、自由,与大道合为一体的审美之境。
“因忘而通”的审美境界还蕴含着对“无”与“有”之间辩证关系的正确把握。如《庄子·刻意》云:“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道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郭象的注清楚地指明了“无”与“有”之间所存在的辩证之理:“忘,故能有,若有之,则不能救其忘矣。故有者,非有之而有也,忘而有之也。”有一位禅师说过:“向东走一里就是向西走一里。” 日本曹洞宗禅师铃木俊隆认为这是真正的自由,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追寻的完全的自由。在他看来,要活在佛性之中,就必须让小我一刹那又一刹那地死去。失去平衡时,我们就会死去,但与此同时我们又会茁壮成长。我们看到的一切都是变动不居的,是正在失去平衡的。任何东西之所以看起来美,就是因为它失去了平衡,但其“背景”却总呈现完全的和谐。这也正是“遗忘”机制能起巨大作用的内在原理。文艺创作中,在“遗忘”机制的作用下,因“无”而生“有”。 “无”与“有”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辩证关系,“有”正是文学上的革新,革新可以使文艺跟上时代发展的意义。文艺革新与文艺继承相互依存,在文艺发展的进程中,与遗忘相悖的记忆也会产生作用。所以,体现着“无”与“有”辩证关系的“遗忘”机制可以督促文艺不断更新。
“因忘而通”的审美境界还表现在“忘”可以使主体的心性与自然合体,与变化为一。如《庄子·天地》云:“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成玄英疏曰:“入,会也。凡天下难忘者,己也,而己尚能忘,则天下有何物足存哉!是知物我兼忘者,故冥会自然之道也。”又如《庄子·天地》云:“汝方将忘汝神气,堕汝形骸,而庶几乎!”如果一个人能够去除机巧之心,遗弃形骸,就有希望接近于大道。所以,无论是与自然之道冥会还是接近大道,走向“通”的境界,必须有所遗忘和抛弃。又如“梓庆削木为鐻”的例子便与“遗忘”机制的心理路径相近:
梓庆削木为鐻,鐻成,见者惊犹鬼神。鲁侯见而问焉,曰:“子何术以为焉?”对曰:“臣工人,何术之有!虽然,有一焉。臣将为鐻,未尝敢以耗气也,必齐以静心。齐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齐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齐七日,辄然忘吾有四肢形体也。当是时也,无公朝,其巧专而外滑消;然后入山林,观天性;形躯至矣,然后成见鐻,然后加手焉。不然则已。则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与!”(《庄子·达生》)
梓庆在做鐻时首先用斋戒来使自己的内心清净下来,去除杂念,最后甚至忘却了自身的四肢形体,以人的自然本性与树木的自然本性相合,最终仿佛有完整的鐻呈现在眼前,然后着手取木,正如陆游所说的“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这些观念都可以视作对“遗忘”机制的诗意化诠释,也因此表明了这一机制饱含审美意蕴与诗性特质。
由此看来,“遗忘”机制的实质是一种审美的遗忘,它是审美主体渴望获得的一种妙不可言的心理感受,在审美的遗忘中,人们可以摆脱时间、空间和名物的束缚,最终实现心灵自由自在的超越之境。
三、“遗忘”作为文艺创新路径如何可能
学会“遗忘”,善于“遗忘”,不失为补救当下文艺创新能力不足的一种方法。但“遗忘”如何使文艺创新成为可能,首先要明确遗忘的主要特点以及与模仿、抄袭的区别。
《庄子·大宗师》中的“悗乎忘其言也”一语,可以作为对文学发展中“遗忘”机制之特点的恰当概括。成玄英疏曰:“悗,无心貌也。放任安排,无为虚淡,得玄珠于赤水,所以忘言。”这种经历“遗忘”后的相似性创作,确乎出于无心而忘却前人之言的缘由。有心与无心,是判断主体究竟是“遗忘”下的创新还是在借鉴、模仿前人的关键,这种无心而任自然的创作过程,更接近于庄子思想中所体现的审美态度。
其次,“遗忘”需要以继承为基础,继往才能开来。将“遗忘”作为文艺创新的路径,并非是无根之木,无水之源下的创作。以当下视角来观察,知识产权律师李田园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仅仅是模仿延续了文学作品的风格、意境、主题思想,但是在情节和语言表现上不相同不相似,我认为不构成侵犯著作权,仅仅是文学作品的借鉴;如果故事架构、情节设计、描写片段有大量的重合,我认为是侵犯了作者的著作权。”以这位律师的观点来看,“遗忘”的合理性在于要做到“得意忘言”。
“得意忘言”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关于艺术创作论的一个重要命题。庄子的“得意忘言”说阐明了言与意之间的辩证关系,其思想对后世影响巨大,且“得意忘言”说在魏晋以后被直接引入文学理论,开启了中国古代注重“意在言外”的传统,并奠定了意境说的理论基础,这是关于“得意忘言”说的最惯常的阐发。我们认为,“遗忘”机制的过程其实也是艺术创作过程中得其意而忘其言的过程。在创作中,作者显然已经遗忘了前人的表达,却能营造出与之相似的意境。如崔颢的《黄鹤楼》与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这两首格律诗都堪称经典,两者在意境方面较为相近。据说李白在登览黄鹤楼时本欲赋诗一首,但看到崔颢的《黄鹤楼》后,大为叹服,直言“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李白在创作《登金陵凤凰台》时显然是忘记了崔颢的诗作,正因前者对其有所震撼与触动,一旦遇到相似的环境与心境,以此为契机便会触发主体的灵感与诗情,不由自主地表达出相近的意境与格调,在遗忘中结诞出新的硕果。试想,如果主体将先前所阅读的材料统统记在脑海,下笔时便会觉得缚手缚脚,甚至无从谈起,这将不利于文学的创新与发展。所以“忘言”是继“无心”之后,“遗忘”机制内在理路的又一显著特点。《庄子·知北游》云:“狂屈曰:“唉!予知之,将语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成玄英疏曰:“初欲言语,中途忘之,斯忘之术,反照之道。”庄子借狂屈之口,告诉人们忘知、忘言而悟其真的道理,与“遗忘”机制的内涵有异曲同工之妙。
朱光潜认为可以将老子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应用到美感经验上去。学是经验知识,道是直觉形象本身的可能性。对于一件事物所知的愈多,愈不易专注在它的形象本身,愈难直觉它,愈难引起真正纯粹的美感。美感的态度就是损学而益道的态度。“遗忘”机制之所以具有重要的哲学与美学意义,就在于“遗忘”本身所具有的特性,无论是在心理学还是在文学发展中都起到一种调节平衡的作用。在心理学上,遗忘是保持的对立面,也是巩固记忆的一个条件。假如人们没有遗忘功能,不遗忘那些不必要的内容,要想记住和恢复一些必要的材料亦是困难的。在文艺发展中,如果没有“遗忘”的存在,人们也无法自由的创作,文艺便不可能具有长足的发展。所以,我们应该明晰“遗忘”机制的审美特质及其合理性,可以将其视作文艺发展中一项革故鼎新,看入审美本质的诗性理论,它指出了创作从枷锁到自由的道路。故而我们应自觉理解并遵循文学发展过程中的这一基本规律,忘其所忘,而不忘其所不忘。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审美文化产品的评价理论研究)(项目批准号:12AZD010)阶段性成果。
高文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王 婧: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陶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