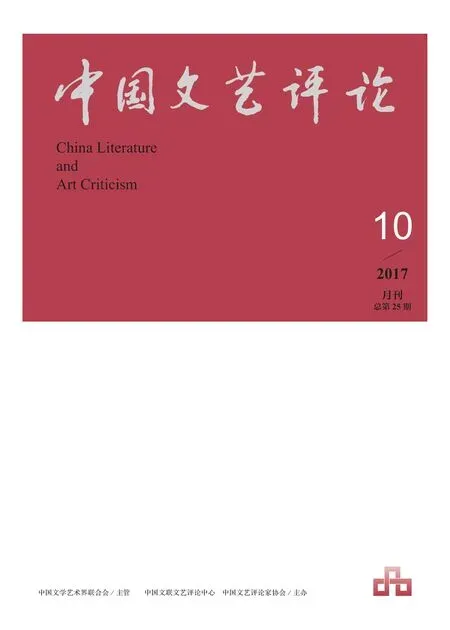文艺评论亟待开显汉语性
汪涌豪
文艺评论亟待开显汉语性
汪涌豪
当今中国的文艺评论要发展,要在全球化的众声喧哗中占得一席之地,必须坚持主体的自我主张,让自己的理论构造能接续上自来的传统,并在此基础上求得进一步的扩充与延展。中国人谈艺论文,从来以主客交感的形象为基础,以不脱经验的感性媒介传达超验的审美体验,既浓缩和凝练了一己对自然万物的深刻觉解,又充满着能动性与生命力,观照可谓周彻深刻,语体又备极灵警生动,自性活跃,自圆自足,有很强的抗异化能力,可成为人类艺术批评话语系统中独到的一极。故开显其特有的“汉语性”,不仅对当代中国人的文艺创造有根本性的规范意义,对人类整体性的艺术创造也能发挥极为有效的影响。
文艺评论 文化立场 汉语性
文艺评论当然要昭示批评主体的文化立场。当今中国的文艺评论要发展,要在全球化的众声喧哗中占得一席之地,没有自己原创性的发明与自洽性的体系建设,而一味张皇西方的理论,作移中就西式的论证肯定是不行的。相反,必须坚持主体的自我主张,让自己的理论构造能接续上自来的传统,并在此基础上求得进一步的扩充与延展。
其间,充分尊重并发扬传统资源,努力开显文艺评论的“汉语性”显得尤其重要。所谓“汉语性”不仅指传统文艺批评皆用汉语书写,故需符合汉语的逻辑与规范;乃至也不仅指基于这种逻辑与规范,今天的文艺批评应当在批评的用语与方式上更多顾及传统趣味,体现传统的格调与意境。而是想从根本上指出,中国人对于文艺的实验与知觉,从来都建基于主体活泼泼的生命体验,其目标既在明道与增德,也在养性与怡情,并且有时增广道艺与涵养德性两者很难分开。故其看取一切文学艺术,对其有所要求与批评,很大程度并不截然服从于纯粹的认知目的,而更广大为一种浮世劳生的情感寄托。
这造成了古人对艺事的体认与实践,当然也包括文艺思想的表达和文艺批评的展开,通常浑沦深在,关涉多多。既可以是实践性的,也可以是论理性的;既有名理上的辩难,也有经验论的展开,更多时候则体现为诸端的交互杂出,共同指向在天地大化的周流中安顿发扬个体生命这个目的。因为从根基上看,中国人的传统认知是认为一切艺事都从属于征象“天之文”的“人之文”,“人文”有着与“天文”一样的特性,都从属于德性熔炼与人生修养这个系统。这种基于价值论认同发展出的浓郁的人文气息,与西人基于认识论认同发展出的科学精神显然不同。因此,与将理论本身当作纯知探讨的西方文艺理论批评相比,中国人对文艺的要求和批评也与西方不同。
譬如,中国的传统文化多以人生与人心为观照重点,“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因此论道论学均少抽象的义理辨析,也少对象化的过细分析与名言的逻辑固定,而常以现实人生为依归,注重过程观照,体现修养目的。许多时候,为了尽其微妙,明其要约,常常取法自然,取象万物。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人的艺术创造提供一正确的参照,进而纠正各种末流的放失。故多直接从感性直觉中建立起观念体系,且凡所创设,少有联系的环节,也不一定非得仰赖中介。如果说西方常常将哲学科学化、美学哲学化,那么中国人则好将哲学美学化、美学伦理化;如果说西方的文艺批评与所论说的对象在文化时空中距离可以隔得很远,中国人则贴得很近,两者不仅视距不同,立足点也有所不同。后者更注意价值的选择,而非真伪的判断,更愿意从艺事的创造中见出一定的社会内容和一己的人生体验,故追求主体与客体、方法与本体融合的同时,对艺术与人生的融合投入了极大的关注。由于它重视规范人行为及价值的实用性分别,而轻视对观念系统本身的深刻厘析,既不愿对所讨论的对象作过多的结构性剖析,也无意接受逻辑与知性的检验,这使得它的许多论说在追求“无言而道合”的高境同时,其极灵动跳宕之能事的表层后面,有着强烈的实践性品格。
许多人觉得,今天中国画创作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它过于炫技,而且所炫之技非传统的笔墨之法与位置经营之法,而是过多地引入了西方抽象主义、表现主义等手法,有时甚至直线造型,平涂填色,一味追求装饰效果以博取俗好,丢失了中国人从来重视的“气韵生动”与“入神”之美。当此风愈烈,我想问,我们是不是该指出,这种丢失决不仅仅是技巧与画风选择的失误,毋宁说是文化选择的失误。由于很少读书甚至不读书,很少揣摩古人的作品甚至根本不揣摩古人的作品,更主要的是不再去深入、以至到后来也不再能深入到古人的创作语境,对其人特殊的心境、人格与风格成因,以及这种心境、人格和风格之与中国人人生理想和审美趣味的关系,自然就有了巨大的隔膜,从而也自然就没有可能从艺术机理上理解,受天地人合一相融的根本文化精神的规定,中国人是从来留心并努力地将大化周流的德性生命及其运动输入到静态的画迹中,从而实现“空间时间化”这种艺术理想与追求的。所以,并不是中国人从事的艺术创作就一定能结出中国的果。而当他自以为这就是中国的艺术并拿来四处招摇时,我们的批评是不是应该有所指正?但遗憾的是,我觉得眼下提出这种指正的批评并不多见,能从古人的论说中汲取智慧然后作针对性生发的批评更是缺乏。
再如,基于“惟人为天地之心”的观念,中国人从来重视人的主体本位,非常注意突出“心”的作用,由此强调“事为心本”“心为身本”,并重“意”胜过重“知”,重“情”胜过重“理”。认为人虽从属于天地,但终究为天地间最贵者,其心更截然居于主宰地位,故常讲“心知”与“意知”,以所谓“体知”代替一般的认知,即强调主体有把握客体的能力,客体意义的彰显离不开主体的观照,所谓“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人尽管不是造物者,却是一切物的意义的发现者。这个世界固然无需人确认而自圆自足,但它的意义却有待人的开显。没有人,它就不是一个有意义的世界。所以,结合切身的观察与体验,它的一切艺术创造都以能达致一种“默识心通”的境界为上。因此,有别于西方重“闻见之知”,它更重视“德性之知”,即重视经验中的情感体验的成分,以及这种情感体验的本真性,认为“情”是“性”之动,有天然的合理性,唯“情”真才能爱人,而爱人就是所谓“仁”了。这种先天道德情感在古人看来有时甚至重于客观真理。由此,当它对客体对象作主体化的形象呈现时,诚如宗白华《艺境》中所说,看似向外发现了客观的自然,其实不如说是向内发现了自己的真情。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从来不是“物本”的,而是“人本”与“心本”的。借此“人本”与“心本”,它从事艺术创造的目的,有时就不仅仅在艺术本身,还兼以求得对人生问题的解决,对现世苦难的解脱。总是在让自己达到一种充分的存在,一己的生命超越成为生活的目的,所以“我向性”很强,而“物向性”较弱。中国古代各门类艺术理论与批判于此多有阐发,它们与西方的理论批评构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
仍然对照当今各门类艺术创作,在传承开新这个问题上,我们常能见到许多无谓的争议。落实到艺术家的创作,更多谨小慎微的拘泥。其实,有鉴于传统艺术大多具有强烈的程式化倾向,如传统戏剧表现,生旦净末丑及其喜怒哀乐的表现均有一定之规;书法中指法讲厌押钩格抵,运法讲落起走住叠围回藏,结体则有欧阳询的“三十六法”与李淳进的“八十四法”,另还有“九宫格”与“变九宫格”的创制;绘画中有画谱画传,改把原本的登录为图示,如《芥子园画传》论画人,有“临流”“拂石”“卧读”与“寂坐”等六十四式,人物的情感表现似乎不在其考虑当中。至于诗歌创作是越往后越强调缀章、属对、调声与病累等程式讲究,此所谓“守法度曰诗”。尤其作律诗,整、俪、叶、韵、谐、度,哪一项都不能有所违碍。具体到状景述情,甚至也有“感今怀古”“抚景寓叹”等固定的格式。面对层层形式因构成的传统负累,今人的创作能否回到古人真正的初心,回到传统真正的根本?在我看是确保他的创作能否真正具有中国趣味与风格的重要前提。但现实是,我们尚没有走出呆板胶固的程式化讲究,有时候甚至忘记了盲目泥古不是尊崇传统,死抠“无一笔不见本原”不是雅人高致。对照古人的艺术理论,可以发现这些恰恰是汩没艺术生机的歧途。这些作品没有充沛的生命元气,没有灵动的情感宣泄,实际上也就没有了自我,故一旦抹去名字,就不知出于谁手,沦为典型的“大恶道”与“死板货”。但对这样的创作风气,我们的批评是不是提出过有针对性的匡救?即使有,似乎也很不够。
还有,中国人受天道人文相融合思想的影响,特别能兼顾伦理中心与入世关怀,由此尊重群体,热衷伦际,强调关系,希望通过推己及人的共性弘扬来达成社会的整体和谐,因此虽重吾省吾身,又重“慎独”,以为当处“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时,尤须从微处见,向静中讨,从而使“身心意知家国天下一齐俱到”。但实际上须臾离不开关系,更重视交往,乃至认为每个人都是所属社会关系的派生物。如果说他是有个性的,也只是道德伦序中的个性与人际互动中的有限个性,任何任意伸张独特个性的行为,都会冲冒干犯既有礼俗的风险,并很难得到社会人群的肯定。影响到谈文论艺,古人因此多重视审美关系而非审美理念。并且,相对于西人讨论关系时多依从“非此即彼”的形式逻辑,他们更多依从“亦此亦彼“的辩证逻辑,以致在绾聚和凝结这部分思想的名言,即那些批评概念与范畴中,“关系范畴”要远远多于“实体范畴”,从而使古代艺术理论批评在整体上一定程度显现出“关系美学”的征象,凡所指涉与概括,都围绕着文与质、道与艺、情与理、奇与正等对待关系展开。
以此对照今天各门类艺术创作,在美与丑的分疏、虚与实的拿捏、巧与拙的判断、浓与淡的选择、形与神的追求等方面,我们几乎仍存在着举止失措、把握失度的问题。譬如,不像西方人一味强调艺术须“尊美而避丑”,如克罗齐在《美学原理》中所说的那样,“丑是不成功的表现”,进而认为丑只有能显真、启善与衬美时才有意义。中国人认为丑本身就有独到的审美价值,所谓“陋劣之中有至好”“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宁丑毋媚”。一味求美反不得其美,求不丑则反得其丑这样的意思,是《淮南子》就已经提及的。倘再追溯至道家“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等论说,则其湛深的意味,可谓已奠定了中国人审美的重要基础。早些年,画坛出现了这样一群画家,画艺泯然众人,不见高明,大多用无笔触的薄画法,但所画人物形象却特别刺眼,无论大人还是小孩,单个还是成群,一例光头、板寸,穿中山装,着土布衫。最奇怪的是面部表情也一样,不是张嘴哈欠,就是呲齿傻笑,眼睛却经常是眯缝着的,如醉似睡,呆滞乏神,但居然被行内誉为“中国新艺术潮流的代表”“玩世现实主义”,有的画还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我们暂且不揣测其动机,说它是有意迎合近百年来西方人对“中国脸”的歪曲表达,仅就艺术创造角度着眼,其对美丑界限的分疏与拿捏显然是失当失准的。任何的艺术创造都必须明白,丑必须先被征服,才能收容于艺术,而放滥丑本身,甚至以丑为美,只能说是艺术的失格。但很遗憾,我们同样很难见到对这种创作倾向的批评。后来是市场做出了反应,这类作品已拍不出身价,为收藏家抛弃了。我想,以后当代艺术史同样会抛弃它们,或者将之作为艺术放滥的一个反例记录在案,因为它有悖艺术创造的原则,更大不符合中国人的艺术趣味与理想。
总之,中国人谈艺论文有基于自己深厚文化形成的特点,我们称之为汉语性。它从来以主客交感的形象为基础,以不脱经验的感性媒介传达超验的审美体验,既浓缩和凝练了一己对自然万物的深刻觉解,又充满着能动性与生命力,观照可谓周彻深刻,语体又备极灵警生动,自性活跃,自圆自足,有很强的抗异化能力,绝然可成为人类艺术批评话语系统中独到的一极。故开显其特有的“汉语性”,其实也就是它特有的“人文性”,是非常重要的。不仅对当代中国人的文艺创造有根本性的规范意义,对人类整体性的艺术创造也能发挥,实际上已经发挥过极为有效的影响。现在,人人都好讲全球化。其实全球化绝非单一社会模式的普及化,落实到学术层面,则绝非是某种特定理论的普及化,而是多元模式与理论的相互对待与作用。由于不同国家、民族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起点上面对全球化进程的,可以肯定,依据中国文艺创作与批评的实际情况,深入研究并积极传扬,是让传统文艺批评资源成为更多人共享的精神财富的唯一道路。
基于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批评的博大精深,我们完全有理由自信,一方面不拒斥吸收其他优秀的文明成果,积极汲取与自己文化构造相契合的养料,另一方面不忘传统的本位,不因现下西方艺术观念正占据主流而患得患失自轻自贱,我们一定能走出自己的路。而紧跟别人亦步亦趋不仅没有出息,也不足以造成文艺的繁荣发展。因为大量事实证明,一切以追赶为特征的发展都具有派生性,都注定不能持续。
汪涌豪: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责编:胡一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