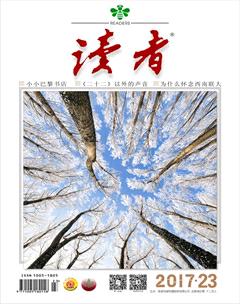空巢,还是空巢感
杨杰
在19世纪的美国,一大批作家都深受超验主义的影响。毕业于哈佛大学的亨利·戴维·梭罗决定返乡教书。过了3年,他觉得返乡还不够彻底,遂玩起了“独居”,成为老一辈的美国“空巢青年”。
1845年3月,梭罗向《小妇人》的作者奥尔科特借了一柄斧头,孤身一人跑进无人居住的瓦尔登湖边的山林中,自己砍树,建造了一座小木屋,并在小木屋里住了两年零两个月又两天。
他说自己就像住在大草原上一样遗世独立,拥有属于自己的太阳、月亮和星辰。不过他没有安安静静地独自欣赏美景,而是写了整整一本书来“炫耀”独居生活,这本书后来成为很多文青的朝圣指南。
他感受到“周遭自然环境带来的甜美与益处,人类邻里的种种虚无的益处变得一点都不重要了,我再也没有兴起过需要人类邻居来陪伴的念头”。但他同时也明白,“大多数人,在我看来,并不关爱自然。只要可以生存,他们会为了一杯朗姆酒出卖他们所享有的那一份自然之美”。
说得真是太好听了。就像身边那些忧郁的朋友,揣着几罐啤酒去海边,走偏僻的沙石路,两旁是低矮的树丛,里面藏着几株野麻。坐在僻静的野滩上,抽半盒烟,看没有生机的脏海,墨绿的藻类缠绕万物,四周天际一片灰色。在走之前除了留下烟蒂和酒瓶,还一定会拍一张虚头巴脑的照片,花半小时美图,再配一句“诗与远方”,然后默默等人点赞。
他们一边熬夜加班,吃臟外卖,悬浮在黏粥一样的雾霾里;一边还要听民谣,关心学区房政策,反思共享经济,供奉“男团”“女团”,给照片加滤镜。
他们的生活过得十分分裂,骑着ofo逃离北上广,灵魂随意安放,对明天抱有幻想,因为“仪式感”本身比仪式重要得多。
虽然造不起湖边小屋,但都市“空巢青年”每周订一次快凋谢的降价鲜花,摆在出租屋唯一朝阳的窗边。他们崇尚北欧的“安全距离”,热情转发“为了不与人交流,某人装了十几年盲人”的新闻。邻居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串铅牌上的数字。他们无法忍受半夜回家和不倒垃圾的室友,懒得进入一场真正严肃的关系。他们把独自生活看成一种更高级的生存状态并以此作为标榜,甚至连晒出来的“孤单寂寞冷”都是变相的“傲娇”。吃下的真正的苦,打碎了的牙,早就混着血默默咽进肚子。
这样的“隐居”充满悖论。生活在一个多世纪前的梭罗早就看透了这一切。
梭罗的小屋离公路只有260米,天气好的时候,他完全可以透过次生林看到汽车经过。小屋离康科德市中心也只有2.13公里,好朋友爱默生的住处也在散步的范围内,甚至去他父母的居所也只需步行10分钟便可到达。理查德·扎克斯在《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中描述,梭罗几乎每天都要去一次康科德,他的母亲和姐姐每周六会给他送食物,而他自己则时不时地回家去,“将家里装点心的坛子舔个干干净净”。
他的那些文艺圈朋友也频繁光顾他的小木屋,在湖畔举行聚会,甚至成立了名为“瓦尔登湖协会”的文人社团。天天派对,夜夜笙歌。
除了接待各种纷至沓来的参观人群外,梭罗还在小屋旁制造了一场森林大火。起因是煮鱼杂汤,火起后,这位大哥并没有着急灭火,而是爬到小山坡上观赏火景,事后还写道:“那真是十分壮观的一幕,而我是唯一欣赏到它的人。”这场大火烧毁了300英亩林地。
文艺青年玩起文艺来可真是勇猛精进。“隐士感”比做隐士本身更令人着迷,“空巢感”比空巢本身更具吸引力。房门一关,以为就疏离了人群。时常抱怨生活和爱情都欺骗了自己,起码要在精神上让人觉得孤立无援。
能够自由地选择独居,绝对是人类的进步。不过真正的隐士可不好当,开车半个小时到闹市享受烟火生活,通常是刻在人类基因里的交流需求。如果安静能给你力量,那你可以选择闭嘴;如果还需要繁华都市,那就尽情享乐,无须“外冷内热”地苦心营造一种“高级”的孤独感。“空巢青年”也不是一个时髦的标签,谁都能往自己身上贴。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的时候才吃饭,爱的时候不必撒谎。
(继续前进摘自《中国青年报》2017年9月20日,喻 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