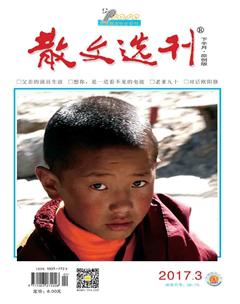我的一段学艺生涯
李寿祺

1970年,在“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季节,有人对我母亲说,这年头升学无望,就让孩子学门手艺吧,天干饿不死手艺人。母亲忙问他,学什么好呢?那人说,绒匠,灰大;漆匠,味大;泥瓦匠,室外作业,风吹雨淋;还是学个木匠吧,屋里干活,不伤身体。
我的师傅姓王叫有福。他身材高大,腰圆腿壮,一脸络腮胡子,一看就像个武人。他是到我家来把我领走的。我家离他家大约20里路程,分属两个不同的县。一路上,他和我讲了很多手艺界的规矩。比如,到主家上工,师傅走在前面,徒弟挑着木匠担走在后面;在主家干活,要舍得花气力,不能偷懒;要按主家意愿做事,三分匠人,七分主人;要尊重主家,哪怕他为人有些过分。吃饭也有讲究。农村人喜欢在堂屋摆四方桌吃饭,进门上方是上铺位,下方是下铺位,左右边是小大首,徒弟只能坐小大首;第一次吃饭坐定的位子,除开主家人坐去了外,一般不要变;吃饭时双手并拢,不能摊得太开,双腿不能叉着桌脚;吃饭不能发出声音,速度要快;添饭自己添,还要观察主家饭做得够不够,有没有添的。
第一次接触到斧、锯、刨、凿这行当的时候,我真有些茫然不知所措。师傅对我说,学木匠手艺第一招是基本功。用斧,要把树劈得直直的,光溜溜的,不能花花搭搭,像狗啃似的。用锯,要把树木锯成一条线,锯路不能弯弯曲曲,像蛇扭水似的;用刨,要把板子、档子刨出平面,不能走走停停,一路留痕;凿子是用来打眼的,眼有方眼、圆眼、斜眼,眼眼要凿得光洁成形,大小合分。
我学着师傅的样子,左手握着一段木料,右手抡起斧头,在树身突出的地方先剁它几下,然后从上至下像风卷残云般地剁下去,如果你怕木料剁坏了,不敢发力,用斧子在上面蹭,那蹭出来的平面就像鱼鳞一样不能见人。锯也是一样,我曾经观察我的师傅,右手握着锯,左手帮衬着,整个上身在摇动着,锯条也在摇动着,上身和锯条就像是循环着两个意念中的圆圈,这个过程实际是在发力;如果僵硬着身子,不会发力,硬推硬拽,不仅锯路歪斜,而且还把人累得够呛。刨木料也是个技术活,发力越猛,刨出来的平面越是有光泽;用力不够,刨出来的树色就发暗。锯过后的木料,如果不是很平展,就先在高出的地方用刨子铲它几下,把靠近怀里的木料也先铲出路径,然后风驰电挈般地一刨到底,那刨花嗖嗖地从刨眼里漏出,有像蛋卷那样卷着的,有像瀑布那样泄出带子的,刨花卷或不卷,这是因为材质不同而发生式样的不同。打眼和留榫是为把一块块木料连接成一个整体的需要。眼要打好,做出来的家具就结实。打眼有两种方法,先把木料放在板凳上,一是屁股斜坐在木料上,二是用左脚踩在木料上,左手握凿,右手抡斧,用斧脑击打凿枘,用力过猛,眼就打坏了;但发力还是要的,因为发力有一种快速穿透、眼壁齐整的效果。
一天,师傅对我说:“学木匠手艺的第二招是布局构图和批量生产。当第一天来到主家,你看到的是满堆的树木,听到的是主家要打哪些家具的吩咐。这时候,你就要成竹在胸,合理布局。比如,栗树可作脚(桌脚、柜脚等),松树可作档,杉树可作板,弯树可作椅翅等,这叫因材使用。另外,批量生产可以大大节约劳动时间,如下料,就一次性把主家所做家具的料全部下完;锯料,就一次性地按尺码锯开;用斧修正木料突出的部分,就一次性地斧劈;刨平木料,就一次性地用刨。之后就是一次性地画榫头、画榫眼。锯榫头是一次性的,打榫眼也是一次性的,这有点像工厂的流水线。最后一道工序是安装。安装动作要柔性,要有整体美感,安装好了才当屑榫、钉钉加固。当一切工序完毕,当一件件家具呈现在你眼前,崭新漂亮,琳琅满目。这时,你感到的不仅仅是家具,而是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令人赏心悦目了。”
我的师傅手艺好,他说所有的尺寸和比例,是木匠手艺的第三招,要等到第三年才传授。比如,那个时候农村盖房子做的是土砖山头墙,架桁条钉椽子,这是有比例的,陡了,瓦就掉下来了;平了,雨大就往屋里倒流;板凳眼也是斜眼,斜多少分也有规定。但我毕竟读了书,多少还能揣摩一些。记得有一次,师傅不在,主家木脚盆丢了两块幅子(那时候还没有塑料制品的出现),我居然把它补上了。后来师傅知道了大吃一惊,问我怎么计算,我说我学过圆,脚盆上面是一个大圆,下面是一个小圆,凭这两个圆我就知道幅子的宽度和斜面度。你还真不能说手艺人没有成就感,没有快乐。那年代粮食紧张,家家户户把手艺人看得还是比较重,一天三餐不说,早中饭后还要过午,通常是一碗面;一天一包烟,家庭困难一点是大公鸡(每包1角5分),富裕一点是圆球(每包2角)。每逢盖房子,出水的时候要办酒,砌匠木匠混在一起,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真有一种粗犷和豪爽的味道。更有很多趣事盈耳,什么张家长、李家短的,什么一生产队(现在叫组)故事,二生产队新闻,总引来一阵阵开怀大笑,仿佛吃四方饭的人就知道比别人多。每当此境徒弟一般不要插嘴,听听而已,因为毛嘴毛舌的不规矩。有时候到很远的地方上工,师傅晚上回家了,我不想走,就在主家歇宿。于是有的主家趁机叫你帮他做一个小凳子或是做一条树扁担什么的,我都有求必应,主家很是感激。一般要做个消夜,但我不吃,因为没有吃消夜的习惯。有一次,主家的孩子为做不到题而嚷嚷。我说,歇着也是歇着,我讲给你听。孩子懂了,主家也乐了。这事后来全垸人都知道了,凡是他们孩子有不懂的语文、数学题都来问我,称我是老师。我觉得有意思,乐此不疲。
当然,做手艺和学手艺也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开心,它有苦,甚至是苦不堪言,张家的活和李家的活不是对接得那么好,有时候做不完,有时无事做。有时主家的木材不是那么好那么多,你拼凑都很困难。有事做的日子,除开中饭后能休息20来分钟,一天到晚,做个不停。更多主家总有一位老人坐在你跟前,与其说是陪伴师傅,不如说是监工。即使收工要走了,主家可能还会拿一个破凳子让你修一修。一天下来,腰酸背痛,不想动弹。还有木匠的工具也不是好弄的,压着刨子的两个食指疼得钻心,锯有时也能伤到手的,起眼有时可能也打到手的。记得在黄石做工,主家要赶活儿,白天做了一天,晚上还要开夜工。12点以后,我实在太困,睁不开眼,就一斧头剁到手上,鲜血直流,主家和师傅立即将我送到黄石第一人民医院,缝了6针。
没有上工的日子,我就在师傅家干活,这一干断断续续达半年之久。那一年,师傅要盖房子,当然是土砖屋。一季稻割完以后,田就空出来了。先是把田里的小半截谷桩割掉,然后我和师傅抬来石磙,架上磙框用牛拉。一个石磙400多斤,我俩居然也抬到了田里。泼水、碾压一星期后,就开始人工划砖,接下来就是起砖,从田里起出来的土砖是侧着的,又过了一星期左右,砖干了一些,就可以码了,一块湿土砖有20多斤,码到半人高是很辛苦的。再过一两个月,土砖基本干定性,就召集很多民工挑到屋场码成大码。
在土砖晾晒的日子里,师傅又吩咐我去打柴,盖房子要请大工、小工,要起大灶做饭,需要很多柴火。当地打柴火有两种,一是拿柴刀在山边上、田埂上剖,田岸壁上劈,待有两捆之多,就用草绳捆紧,用冲担两端插进柴里挑回;另一种是到山上拔松针,那先要看松针是不是黄了,用拔柄在松枝上敲几下,然后用竹拔贴在山上拔,每當拔到一定数量就要打折子,打成一贴贴的松针,然后装进团兜,用扁担挑回家。
到了盖房子的日子,大小工请了30人之多。有和泥的,有挑泥的,有递砖的,有砌砖的。我的任务是为大工师傅挑泥,当我将一担泥送到了一人多高的山头墙边,刚离开时,“轰隆”一声闷响,发码的砖撞倒了山头墙,把两个大工师傅埋在土砖里,造成了严重的骨折,我幸而逃过这一劫,在场人都说我命大。
就在“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第三年春上,听说学校招考老师,我报了名,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被录取。细细算来,含头含尾,总共才一年零三个月。
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开展大规模“补偿性教育”,我这才考上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