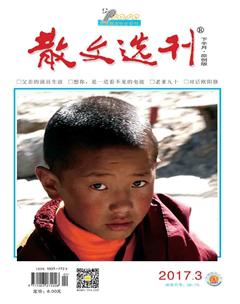癫痫娘
李玉胜
癫痫,精神病科疾病,又名羊角风,精神错乱时,瞬间口吐白沫,眼睛翻白,浑身抽搐,有知觉无反应。此病发病快,去病快,一分钟犯病,两分钟苏醒,抽完又恢复正常状态。发病后身体疲软,此病治愈难,发病率高,情绪是致病因。
娘患此病一生。
七十六年前,村里的一位拦羊大爷,急匆匆地从山上抱着一个不足月的女婴跑到了外婆家,大冬天自己穿着单衣,却用烂皮袄包着这个女婴送到外婆怀里说:“这娃还活着,差一步被狼叼走,我听见哭声,就往过跑,此时狼也跑到她跟前,我拼命地攥着羊铲赶走了狼,从干草上把这娃抱起,知道是你家前几天送的娃,看她还睁着眼睛,不停地哭,我就抱着她往回跑。”外婆赶快给喂奶,一会这娃好了起来,外婆惊喜,外爷生气……
这个弃儿就是我的娘,因为出天花昏迷,误认为死亡。由于受冷和惊吓,她得上了癫痫,大半生我听到的不是这个学名,而是羊角风。因为犯病,娘的童年遭遇到了太多的磨难,太多的不幸:上学不能正常,吃饭受姐妹们排挤,玩耍受玩伴欺负,娘一生天天哭的毛病可能由此而来。
苦难给了她坚强,不管别人怎样歧视,不管生存如何艰难,她始终不放弃活下去的勇气。
可能又是哭的原因,娘有一副好嗓子,十六岁时,娘唱的信天游《五哥放羊》《女孩担水》《卖菜》《南泥湾》、秧歌剧《兄妹开荒》红遍十里八乡,延安民众剧团将娘偷偷地招为演员带走,那时剧团都在庙里唱戏,一年四季赶场下乡,地主成分出身的外爷坚决不让娘唱戏,说唱戏是伤风败俗,丢贺家人的脸,娘的天赋被扼杀,又回到村子,这次娘又犯病了,外婆和外爷因为娘常常像仇人一样吵架和打架,最后外爷斗不过外婆,总是让步。
十八岁这年,由于村里的小伙伴长年地欺负娘,娘的病一犯再犯,让外婆伤透了心,无奈之下,外婆让已经当上地区卫生局局长的外爷的五弟,我的五外爷把娘带走。为了保娘的命,五外爷把娘带到城里一边给她看病,一边介绍给当时的县食品厂当临时工。一个月的工资仅有18元,对于娘来说,这既是活命的机会,又是改变命运的机会。娘是糕点工,拼命地干活。父亲也是临时工,和他同岁,从米脂县逃荒至此,处境比娘还差一倍。同命相连,患难携手。娘和父亲恋爱,娘的心全交给了父亲,父亲对娘感激万分,也不嫌弃娘的癫痫病,打算和娘白头偕老。
娘和父亲的婚礼很糟糕,婚礼戏剧般地差点成为“葬礼”。
外爷不同意这桩婚事,一听父亲是个米脂下来的穷小子,就火冒三丈,步行80多公里路从村里赶到城里,点着香,烧着纸钱来到娘的婚礼现场瞎闹。父亲有些动摇,娘抱着父亲,生怕外爷伤害父亲,并对外爷说:“你今天就是把我烧死,打死,我也不跟你回去,我要追求属于我的幸福。”娘跪到了外爷的脚下,父亲也跪下,这时,工友们也跪成一片。外爷无奈,生气地拍屁股走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四年没和娘来往。
此后,娘生了哥,遇上了“大跃进”时期。又一次为了活命,娘一手拖着四岁的大哥,挺着腹中的我回到了外婆家落户,村里的传统原则上是不让嫁出去的女儿回到娘家村落户的,在两个舅舅的求情下,外爷终于答应留下我们,但要在离村子很远的地方自己打土窑居住。眼不见,心不烦。父亲坚持不回农村,再难也要当工人,从食品厂调到了离家十多公里地的养路道班当养路工。虽然离家很近,但长年公路施工,长年不在家,娘扛起了一切……
娘很善良,生我时,正好二舅妈生下一对双胞胎表哥,舅妈奶水不够,娘只让我吃一只奶,把另一只奶留给了两个表哥,和舅妈轮着喂养。父亲看到这很生气,娘就劝他说:“都不容易,活命要紧。”父亲含泪为娘买了只奶山羊,让娘饲养好,用羊奶辅喂这些孩子们。
二爸去世,二爸唯一的儿子当时只有十五岁,可这时父亲已患上了严重的肺气肿病,娘背着父亲把二妈和二爸的儿子和小女儿雇车从几百里以外接到我们家,养了起来。后来又掏钱给我兄弟在城郊村落了户。看着弟弟成家,小妹出嫁。二妈去世后,娘又帮忙将老家埋葬的二爸和二妈葬在一起,搬坟花了不少的钱,娘说:“亲人是打断骨头连着筋。”
随父亲农转非回到城里之后,娘在高山头占了土窑洞和地盘,现变成了四合院;在街道工程队干了二十年拉扯大我们兄妹三人,都是中学毕业,并安排了工作;又伺候有病的父亲一生,受尽了罪。几次父亲因病受不了要轻生,娘劝父亲:“你是一家人的支柱,你就是瘫在炕上,也是我们的主心骨和灵魂,有你这个主心骨在,我们娘几个才能活下去,家就不會散。”
我们家现招租的许多邻居,都是70、80和90后的小夫妻组成的一家三口,娘成了她们生活中的大总管,问寒问暖,看家、看孩子,娘会用偏方看病,反正招数很多,只要靠自己的辛苦和智慧能帮助到别人,娘说她就幸福。
“房东娘”、“房东奶奶”、“房东老奶”是娘现在最新称呼,娘整天乐哈哈……
奇怪的是,娘的癫痫病后来再也没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