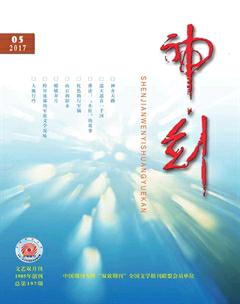脚下风景
秦延安
行走无定河
车出西安,经铜川,过延安,直奔榆林。越往北,路两边的植被越稀疏,绵延无际的黄土高原如张大嘴的老鹰,迅速将我们吞噬。车在黄土高原间左冲右突,却总是找不到突破口,即使冲天的刺槐、千年不倒的砍头柳,还有绵延无际的灌木丛,也未能将黄土高原装扮的俊俏些。就在那千沟万壑中,我搜寻着无定河的身影。
出发前,我曾在地图上观察过无定河的流向。它先北上再东南,如一把巨大的弓,迎着鄂尔多斯高原的寒风和毛乌素的风沙撑满身躯;又像一株成熟的稻穗,让荒凉的黄土高原顿时增色。作为黄河的一级支流,虽然无定河像它的名字一样,信马由缰、河床无定,在陕西十大水系中也并不起眼,但它却是一条多彩的河,对陕北的富饶起着关键性作用。
虽然已是人间四月天,但迟钝的陕北还处于春寒料峭之中。就在那漫无际野的荒芜中,却隐藏着万千草木,它们如潜伏的战士蠢蠢欲动。车过了镰刀弯,便进入毛乌素沙漠区。没有了黄土高原的阻隔,视线如脱缰的野马尽情驰骋。大漠的空旷荒凉了人的思维,也凝固了人的情感。就在一切都快要僵化时,突然从一道沟里挤出一潭溪水,便有了一缕水草、几棵砍头柳,虽然它们生长得异常艰难,却如夜空里的星星照亮了荒原。越接近白于山区,这样的情景越多,我知道,也许就在这渺无人烟的沙漠下,无定河正在悄无声息地前行着。
河流是大地的血脉。看似外表冷漠的黄土高原,用刀深深地切开肌体,用汩汩鲜血汇成无定河。虽然水量只有渭河的不到六分之一,但无定河的输沙量却有两亿多吨,仅次于前者。于是,在定边的许多河段,你看不到碧波荡漾,只是一股股细弱的水流在河床宽阔干涸的胸膛上左右摇摆,纠结徘徊着前行,水很浅,几乎一手就能探到河底。在降水少的年份,断流更是家常便饭。但就是这样一条濒临死亡的河流,却一次又一次地死里逃生,汇入黄河。
到靖边县时,已是黄昏,落日的余晖给蜿蜒的无定河镀上了一层橘红,非常壮观。从沙漠里闯出活路的无定河实属不易,但迎接它的却是坚硬的岩石。水似柔弱,又分外刚强。在天长日久的碰撞中,无定河竟然在坚硬的岩石中冲刷出一道道罕见的峡谷。这个峡谷群从靖边西北部起,至内蒙古乌审旗巴图湾水库的坝口止,全程约百里。这是用生命搏杀出的道路,以至两边的河谷也被染红了。深浅不一的红色砂岩在千百年来风与流水的侵蚀下,呈现出独特的美感。一路的搏杀,让无定河在此已所剩无几,但有水的地方就有绿色。闻讯而来的红柳站满了河两岸。红柳耐旱、耐热,尤对沙漠地区的干旱和高温有很强的适应力,所以此段无定河又被称作红柳河。虽然水量不大,但是水的清澈却可以与江南河水相媲美。毛细血管样的山涧涌泉,将众多细弱的汩汩水流汇入无定河。
坚硬的岩石挡不住,那就用万千沟壑颠覆吧!在横山、在米脂,我看到岸高谷深,河道曲折,多急流险滩。在黄土高原沟壑区的无定河,如同一道天河,让两岸的人们如牛郎织女般相见艰难。说话听不见,那就大声歌唱,于是便有了隔岸喊话式的信天游,那歌声如飞起的风筝窜得老远。随着无定河的蜿蜒,河畔也坐满了村庄,既有镶在黄土原上的窑洞,又有建在塬畔上的砖瓦房,还有川道里新砌的一栋栋小二楼,给孤寂的河流增添了几多光鲜。
凭借着坚强的意志,无定河冲破了重重阻隔,终于在清涧县投入黄河的怀抱。一路的厮杀,虽然让它已经没有了原先的清纯,但它前进的脚步却从未迟缓,就像这片土地上的人一样,从未放弃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建在地下的村庄
雨水之后的渭北大地,草木和着太阳一并开始生长,将荒芜一冬的黄土台原装扮得春意盎然。从三原县往北25公里到洪水镇,顺着七扭八拐的乡村公路一直爬上黄土台原区最高的山头,远远地就看到一棵棵楸树围绕的村落,那就是柏社村。
作为关中平原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风大、雨少、黄土深厚的特性,让柏社村民选择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居住方式——地窑。虽然时光的流沙,将昔日渭北的地窑村已经掩埋,但柏社村的地窑人家,却为我们揭开这种奇特的居住方式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
柏社村因为历史上广植柏树而得名,看似其貌不扬,却有着1600多年的历史,曾是关中通往陕北、甘肃、宁夏的重要通道,秦汉以后屡为兵家必争之地,近代革命时期是通往革命根据地“照金”“马栏”“延安”的咽喉要地,红军、八路军均在此设过秘密交通站。
进入村子,才发现,柏社村并不像其他地方的村庄一样紧凑。稀稀落落的房子前,有一些从地下冒出的树身,还有鸡鸣狗吠声,让人很是惊异。直到走近,才发现,那是一院院深潜地下的地窑。“见树不见村,见村不见房,闻声不见人”,让柏社村的地窑充满了神秘色彩。虽然村里许多人家已经搬离地窑,但那些曾经繁华的地窑并没有因为主人的离去而荒废。目前,村里还保留有窑洞780院,其中核心区集中分布有225院下沉式窑洞四合院,大多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地窑,部分老窑有上百年的历史。虽然现在仍居住的只有几十户人家,但他们却将曾经灰头灰脸的地窑装扮得分外光鲜,不仅砖砌了门面,瓦盖了窑顶,就连窑里也是窗明几净、粉饰一新。也许是物以稀为贵吧,有几户人家还将自家的地窑改成了农家乐,迎接着四方来客。老一辈革命家习仲勋曾在此居住过的地窑,现已辟成了纪念馆。
走近一户地窑。只见地面上围建着一个高约1米、长约10米的四方形青砖拦马墙,拦马墙里便是深8~9米的地坑。拦马墙既防止地面雨水灌入坑内,又保证了地面人畜特别是儿童的安全,在通往坑底的通道四周也同样建有这样的拦马墙,让整个地窑院落看起来既美观协调又古朴大方。马头墙旁立有太阳能热水器和水箱,让地窑的设施更加完善。沿着青砖铺就的十多米长的台阶式斜坡,穿过一个门洞,下入地坑。只见坑内四周分别建有窑洞。窑洞高约3米,深约10米,既有厨房、卧室,又有厕所、柴舍,还有鸡舍、畜圈,可谓一应俱全。地坑院中间,下挖了一口深约10米的渗井,专门用来聚集和渗进入坑的雨水,以便人畜饮用。旁边种植有花草树木,其中一棵柿树已将头探出了坑外。四合院式的地窯建设,蕴含着古老的人居文化基因,对昔日贫穷的渭北人民来说是再理想不过的了。站在地坑院落中抬头仰看,一方天地,日走云迁,岁月匆匆。一抹斜阳,投入院内,半屋敞亮。因为土层厚且坚硬,地坑院可谓是冬暖夏凉,就连外面轻狂的西北风,跌入院内也悄无声息了,储藏粮食更是三年五载不生虫。因为建筑奇特,设施完善,2011年,“地坑院营造技艺”已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endprint
作为生长在地下的村庄,柏社村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更为我们亲近泥土、触摸历史搭建起了一座桥梁,让我们轻而易举地窥探到乡村的纹路。
柳青故居
雨如断了线的珠子,在广袤的黄土高原上马不停蹄地奔跑。那蹄声惊醒了在黄土中埋头沉睡一冬的各种植被,它们纷纷探出绿色的脑袋,好奇地张望着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就连河畔的柳,也受到感染,扯出了嫩芽,鹅黄般地醉人眼。于是,原本荒芜得让人心痛的高原,顿时满是生机。这种生机,在雨的滋润下,如燎原之火般,在苍茫的高原上迅速蔓延,让人的思绪也如这满山的植被一样,意气风发。我们的车,就在这漫山遍野的绿色夹缝中,蜿蜒前进。那从窗玻璃上滑下的雨线,让我想起了梁生宝买稻种时遭遇的那场春雨,只不过那场雨下在关中的渭河岸,而这场雨却落在陕北的黄土地上。但不管下在哪里,都是春雨贵如油。梁生宝当年是怀着忐忑的心情去买稻种,而我则是抱着复杂的心情去探访柳青的故里。
柳青是先于路遥从陕北黄土地上走出来的著名作家,被喻为陕西文学的“教父”。很多人都知道他的《铜墙铁壁》,都读过他在长安县皇甫村写就的《创业史》,可是,知道柳青是吴堡县人的却并不多。因为柳青12岁就离开吴堡,因为写作需要,曾长期在长安县皇甫村蹲点,这让很多人误以为柳青就是长安人。
车在黄土高原上奔驰,见得最多的树木还是柳。不管是单棵,还是成林,这种坚忍不拔、久经考验的树木,就如柳青一样,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总是以顽强的生命力给人以惊喜,给人以希望。不知什么时候,雨已经停了,车也停到了距吴堡县城40公里的张家山乡寺沟村口。同许许多多的陕北农村一样,寺沟村的四周皆被群山围绕,纵横的沟壑呈丁字形,将一个偌大的村庄分隔成不规则的条块状。一条还算平坦的柏油路穿村而过,路边矗立的一块石碑上,由贺敬之书写的“柳青故里”4个大字,虽然布满了风雨的斑驳,但仍不失风骨。一户户人家如一把秕谷撒在沟沟岔岔,特有地域特色的窑洞,就顺着道路,前后左右地将陕北人家的风情,呈现在你的眼前。
沿着路碑右拐,走过一条200米长的土筑坡道,就看见上下两排各五孔窑洞。下面的五孔窑洞已经废弃,只有院里几棵吐芽的枣树,似乎还记录着昔日的辉煌。上面的五孔窑洞修葺一新,现在住着柳青的侄儿刘汉哲一家人。柳青于1916年就出生在这里。在正中的一孔窑洞里,陈列着柳青从小到大许多珍贵照片。那一张张稚嫩的、羞涩的、坚毅的、纯朴的、憨实的、苍老的脸,为我们勾勒出了柳青一生的轨迹。随着这些照片,我看到怀揣梦想的柳青,从寺沟村走进吴堡,走入榆林、走向延安、走到北京……为了理想,他又毅然走出京城就像他当年毅然走出寺沟村一样。在秦岭脚下的皇甫村,一待就是14年。14年,他像老农民一样活着,汲取大地的营养,提炼生活的精髓,把握时代的脉搏,终于写出了具有史诗品质的《创业史》。人们以为是皇甫村给了柳青的成功。其实不然,是故乡,是寺沟村的窑洞,是陕北的黄土地,是那年年青的柳,让柳青懂得,火热的生活就是文学艺术的源泉,人民就是写作的根本。只有坚定执着的创业,才会有美好未来。只不过,他的创业是用笔在纸张上耕耘。
雨后的陕北,如清洗过一样,纯净、明媚。站在柳青故居的窑洞前,极目远望,皆为皱纹密布的山。就在那山头上,我突然看到一棵棵柳,虽然它们生长得异常艰难,却依旧是柳叶青青,光耀着整个大地。
古村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那些原本看似稀松平常的村子,一个个如古稀老人似的,跌进了时间的深渊。和村子一并老去的,不仅是人,还有那些饱经风霜的房屋、积满岁月尘垢的老物件、印满足迹的街巷,以及那些枯藤老树。所有的一切繁华和喧嚷,都如远去的炊烟一样,消失在岁月的尽头。逝去的化作了一抔泥土,走的永远地走了。人稀了,村子也似乎荒了,一切都被隐在了岁月当中。
没有记忆,过去就死了,不得再生。没有记忆,历史就是一派胡言,毫厘不值。谁也没有想到,就在乡村一爿一爿地坍塌、兀自衰败,那些快被遗忘幸存下来的古村,却愈加弥足珍贵。原来它们是那样的有风韵有价值,就像一壶老酒一样,味道醇香、深厚、悠远。当然,相比于更多的村庄,古村是特色鲜明、历史记忆深厚、民俗和民间文化遗产丰富的。那些几百年的老房子积存了过往,老物件传承了记忆,老街巷写满了故事,老树记录了历史。古村,如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不仅拥有最初的原始性,而且还内涵深厚。
最引以为荣的当然是名士大儒。他们曾经一个个都像金黄的谷粒一般,饱满着生命的激情与荣耀,或为社稷江山尽忠,或为桑梓父老尽孝,成为古村的骄傲。不管他走得多远,也不管他有没有再回过村子。反正古村留下了他的印迹、记录了他的故事,于是便有了名人故居、便有了纪念馆。在作家的笔下,那些古村更是缤纷多彩,有滋有味。不管是魯迅的绍兴水乡里、沈从文的凤凰古城,还是陈忠实的白鹿原、阎连科的耙耧山……在无声的文字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作家们浓厚而复杂的乡情,更是窥探到了一座古村的曾经神秘。当然,还有许多没有被书写的古村,但它们却活跃在民间中,丰富在乡野里。
古村是在阳光、地势、岁月的滋养下,日益生长而成的。虽然没有设计师的设计,但却孕育了独一无二的风格与气质。不管是皖西南的宏村,还是川西的桃坪古寨,或是南疆喀什噶尔古城等,那些青砖灰瓦的房屋、山上的岩片石、盆地的木材,都被全新解读,成为打开“人、自然和建筑关系”的钥匙。这些积蓄了原生态、充满生存智慧的建筑,让古村风味独特,古色古香。
古村是诉说衷肠的地方。“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低头思故乡”的惆怅,都可以向古村述说。我的邻居张二杆,十八岁时便进了城,他如一只风筝越飘越远,就连父母留给他的房子最后也卖了。进城的张二杆,以为他与那个村子早没有了关系,可是,当他功成名就,进入知天命之年时,最想去的却是那个遥远的村子。但是,他再也回不去了。
其实,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座古村。无论他在城市里生活了多久,但若查他祖籍,总有一代是从村子里走出来的。古村承载着历史的基因,是中国文化的箱底儿和人类的父亲。据说,在这些古村里,保留着一千多项国家级“非遗”和七千多项省市县级“非遗”。它如一本厚厚的古书,内容纷繁复杂,磅礴大气。endprint
于是众多像张二杆一样的人,便喜欢在逢年过节时,去古村里转转。城市钢筋混凝土的封锁、脚不挨土的空虚、屋上无片瓦的忐忑,让他们总想在古村里住上一段日子。村里,青砖灰瓦、雕梁画栋、镂花窗棂,古雅凝重,气势不凡。村外,阡陌纵横,鸡鸣犬吠,生态园田掩映在绿树丛中。站在古村倒塌的豁口,习习天风拂来,有如一位没齿的老人在含混不清地絮叨着久远的往事,那是不能消失的根。
横渠书院
太阳把秋天的一切风物都揉碎在阳光里,让收获的气息跟着风一起奔跑。伴随着这丰收的气息,我们来到了眉县城东被田野包围着的横渠书院。
门前两棵郁郁葱葱的柏树像士兵一样守卫在门前,门楼上悬着“张载祠”鎏金黑漆大匾,两侧挂有“三代可期井田夙报经时略,二铭如揭俎豆能往闡道功”的木制黑漆金字对联,旁边挂有横渠书院的牌子。灰色的砖墙顶着灰色的瓦,让刻满岁月印痕的大门古朴典雅、庄严肃穆。大门两旁是横渠书院主人公张载的生平事迹,整个壁画线条流畅、笔墨简洁、色彩清丽,人物栩栩如生。
张载是北宋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关学”的创始人及领袖。横渠书院前身为崇寿院,张载年少时曾在此读书,晚年隐居后,一直在此兴馆设教。他去世后,为了纪念这位北宋大儒,人们将崇寿院改名为横渠书院。公元1295年,在原横渠书院旧址上修建了张载祠。公元1326年,在张载祠内恢复了横渠书院,形成了“后祠前书院”的格局,并成为关中十八景之一。从元、明、清至民国期间,先后历经14次修葺。现存建筑为清道光年间所建,主要有献殿、山门、学圣殿、学堂等建筑,祠内有明万历及清乾隆等重修及拜谒祠庙碑石八通,明清木刻《横渠志·卷之六》“第十八代裔哀祠”原版等。1985年眉县政府成立了张载祠文物管理所,并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横渠书院坐北向南,主体建筑以中轴线依次排列,附属建筑均以轴线为中心对称排列。跨过一道门槛,进入书院,左右两边分别是张载及关学思想文化展厅。关学强调“通经致用”,以“躬行礼教”。作为儒学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学派,从北宋到清末,延续了800余年,誉播华夏,影响深远。
沿着青石铺就的道路前行,两旁是古木森森,七棵千年古松,虽然饱经风霜,但依然苍劲有力。一株张载手植的柏树高达9.3米,树形奇特,枝干盘若蛟龙,两人不能合抱;枝叶繁茂,郁郁葱葱,荫翳了直径六七米的地面,被国家林业局列为“中华名树”。再往前不远,便是张载祠堂,正殿门楣上悬挂着康熙亲笔御题的“学达性天”匾额,里边供有张载彩塑坐像,墙壁上重彩工笔壁画。画面展现的是张载生平故事,如:求学悟道、奉母教弟、习练兵法……辞官归里等。壁画色彩鲜艳明丽、线条细腻流畅、形象生动饱满。
祠堂旁是横渠书院楼,为“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图书馆,也是关学学术交流之地。绕过书院楼,便是一条U形的纪念碑石长廊,廊内立有于右任等历代文人墨客留下的碑刻50余道,以及古今文化名流、政客题写的诗文对联。东院正中矗立着一尊香港孔教学院捐赠的高达3.3米的张载铜像。如今,横渠书院已经成为集学术研究、培训教学、宣传推广、文化旅游为一体的综合文化活动中心,吸引着四方来客。
虽然横渠书院历经千年,但依然如院中的那棵柏树一样,枝繁叶茂。那旺盛的岂止是外表,还有源远流长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关学思想。
白河
到白河似乎是一个遥远的路程。从旬阳下火车,再倒汽车,沿着山路,一路向东。绿绸似的汉江与我们捉着迷藏,一会在左一会在右一会又跑地没踪影,就留下那高高的大巴山与我们对峙。往上看不到山顶,往下看不到江底,我们的车就在狭窄山道里,时而上坡时而下坡,一路向前。就在感觉似乎快要下到江边时,那个古时叫钖穴的地方就到了。
这就是白河。虽然地方不大,人口也不多,却是秦头楚尾襟喉之地。山沟相间,山山相连,让白河连一处百亩平地都没有。西部从北向南有土地岭、太平山、五条岭、界岭;南部自西向东有马食坪、韩家山、圣母山、平顶山、野人山;中部从北向南,依次为天池岭、蒋家梁子、大山庙梁、韩家山。这么多的山,连接在一起,便呈现出一个向东倾斜的“山”字。
当两岸的山拉开了距离,就在狭小的汉江边上,白河县城择机而生。楼挨着楼,墙贴着山,依着高低不平的地势,整座县城就像搭积木似的环山而建,一层一层呈阶梯形,从山脚一直延伸到汉江边。远远望去,颇有几分悬崖峭壁立危楼的雄壮气势。看起来是够凶险的,有些楼就站在半崖上,像鹤立般眺望着。有些楼如老虎般卧在山脊上,一条蛇样的小路将它与城市衔接;有些楼半个身子悬在空中,那从沟里长出的水泥柱子,如举重的运动员稳稳地托着楼体,让人在担心之余更多的是惊叹。寸土寸金,不仅在这里被放大,还诠释得更加真切和形象。在这么复杂和险恶的环境里,竟能建起如此精致的山城,你不能不佩服白河人的智慧和坚毅。当然这只是白河精神的冰山一角。拥有“三苦”精神优良传统的白河人,凭着“愚公移山”的意志,开山、造地、改河,硬是在“山大、沟深、地无一平”的地方,建出了一座城、一片田,让自己的日子幸福的如花儿一样。
虽然没有一马平川的地理和四车齐驱的街道,但这并没有影响白河县城的功能。就在这密密匝匝的楼群中,白河县的党政机关、学校文化企事业单位齐聚于此。一条弯弯曲曲的街道,在高低错落的楼群间,像肠道般曲里拐弯,走进去,便湮没在楼群里。打开窗,半个县城都在眼底。喊一声,整条街巷都可以听到,但走起来,也许得花一些工夫。虽然县城很小,大半天工夫就可以转完,但却小得经典,小得雅致。该有的机关部门、该有的生活设施,都一应俱全。抬头看山,山,高峻连绵,巍峨入云;低头看水,水,空明澄寂,一派纯净与爽朗。在这里,你听不到轰轰的机鸣,也听不到嗡嗡的车鸣,有的只是青山绿水,有的只是花香鸟语。那种悠闲与散漫,安逸与祥和,岂能是在大城市里获得?
街上行人不多,来来去去的都是熟识的或是沾亲带故的,互相问候,或是招呼去家里品茶喝酒。在一座城市里,能与熟识的三五好友,经常相聚,互叙情感谈天说地,那又是怎样的一种恣意。因为地处秦楚边陲,时而属秦,时而为楚,所以,秦楚文化在这里得到了交相辉映。街两边的商铺里,既有从西安运来的商品,也有从下游十堰进来的货物,较为丰富。虽然店里的生意,像街上的人一样不紧不慢,但店主却一点不着急,好像他们开店并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享受这种生活一样。endprint
不经意间,便从城里走到了汉江边。自西向东的汉江,像这块土地上的人一样,终年四季日夜不停地奔忙着。新落成的堤防如巨龙般,守护着整个城池的安全。天很高,水很宽。对岸的青山,青山的丛林与藤蔓芳草,还有近岸的城市建筑,都齐刷刷地、一无例外地倒插在水里。这么幽深的水,竟能如此清澄、透明、一尘不染,让人不能不叹为观止。这水不仅喂养着白河人民,更是一路向东、向北,将白河与祖国首都紧密相连。面对这清纯真切的水,我们除了一种超然的享受外,就连五脏与六腑、心事与灵魂,都被洗得清亮清亮、干干净净。
行走白河,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白河的风貌,还有白河人的精神。正因为有着这种精神,白河的山才更清,水才更亮,日子才更红火。
五丈原
地域環境有时会左右一个人的命运,特别是在战争中。具有智慧之星的一代将相诸葛亮,便因为选错战场,不仅让自己功亏一篑,“出师未捷身先死”,更是让寂寂无闻的五丈原从此载入史册,名扬天下。
伴随着秋日的斜阳,我们去探访五丈原。从西安沿西宝高速西行,经咸阳,过杨陵,由岐山县蔡家坡下,向南,在渭河桥头向左前方看去,逶迤而下的秦岭将入川道时形成了一处缓坡,左右延展,成为琵琶状黄土台,这就是五丈原。南靠秦岭,北俯渭河,三面凌空,让五丈原扼东西交通,镇斜峪关口,守南北要冲,可谓是依山傍水,易守难攻之势。《地理通志》中记载:“五丈原高、平、旷、远,兵家必争之地也。”对于五丈原得名,说法有三:一说此原前阔后狭,最狭处仅五丈;二说秦二世西巡至此时,原头曾刮起五丈尘柱大风;三说原高五十余丈,原称五十丈原,口口相传,简成了五丈原。不管因何得名,反正让五丈原名扬天下的终是诸葛亮。
从河谷沿着盘旋的公路,一路蜿蜒而上,七绕八拐地便来到了原上。极目远望,渭水东流,如绸缎般在村舍楼宇间若隐若现。就在那葫芦口处,诸葛亮伏兵火烧司马懿。近前的高店镇,就是当年魏延的驻防之地魏延城。隔河相望,北岸的三刀岭,就是司马懿驻扎帅营之处。再往对面看,就是史书上屡屡提到的北原,隔川眺望,只觉得宽大、高远,没有想象的那种仄陡。
公元234年,诸葛亮改变了前4次伐魏的路线,率领10万大军从汉中出发,取褒斜道,穿秦岭,进驻五丈原。作为老对手,司马懿深知诸葛亮足智多谋,也知道诸葛亮前几次伐魏失败的主要原因还是军粮不济,所以他选择了深沟高垒,闭门不出。五丈原背靠秦岭,它的东边是武功县,西边是陈仓,北边是岐山。武功县距离西安只有区区一百四十里地。如果诸葛亮出斜谷后东进,兵锋直指长安,那么司马懿将被迫放弃死守策略,与诸葛亮决战。或是诸葛亮以五丈原为基地,北上攻取岐山占领北原,那么曹魏的西北防线将会被切成陇西、陈仓和关中东部三块,届时诸葛亮可以从容消化。但诸葛亮均没有这么做,百日对峙,没有拖垮司马懿,却让自己积劳成疾,鞠躬尽瘁,这让人不能不悲叹。
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忠贞不贰的蜀汉良相,于汉末晋初在地势平坦的五丈原北端,建庙筑祠,凭吊怀念,一直延续至今。在松柏掩映中,坐南朝北九脊歇山顶式的诸葛亮庙,古朴肃穆。大门上挂一竖匾,上书“五丈原诸葛亮庙”,门廊两侧镶有“一诗二表三分鼎,万古千秋五丈原”的对联,门厅东西两侧分别站立蜀国大将魏延和马岱雕像。穿过门厅进入中院,东西两侧耸立着钟、鼓楼,正中是书有“五丈秋风”牌匾的献殿。殿内牌匾盈门,雕像云集。左右墙壁上,以草船借箭、空城计等故事为主的清代彩色壁画,活灵活现。东墙壁下,镶嵌着岳飞手书的诸葛亮《前后出师表》的青石40块,表文语出肺腑,文笔出众;笔法奔放苍劲,流利酣畅;镌技高超,形同真迹,人称“三决”碑。石前还有明太祖朱元璋对诸葛亮“纯正不曲,文如其人”的评述石刻。殿中间安放着诸葛孔明的泥塑彩色坐像,虽脸色蜡黄有些病态,但仍是羽扇纶巾,一幅运筹帷幄之相。出得献店,便是直径达8米的八卦亭。绕过八卦亭,便是正殿。殿内塑有诸葛亮坐像,坐像前站立蜀国四员大将,东侧为关兴和王平,西侧为张苞和廖化。正殿西南侧有诸葛亮衣冠冢,南侧建有陨星亭,亭中立一块陨石,传说当年诸葛亮去世前,在五丈原南侧有陨石坠下。中院后墙上建有长廊,叫作将军廊,塑有蜀国晚期的将军像。东院有月英殿、八卦阵和书法展室,西院为诸葛亮生平展室。
出得诸葛亮庙,站在五丈原上,我思绪万千。虽然一千七百多年前的三国硝烟早已飘散,但是五丈原依在,它不仅是一个传奇人生的终结,也是一个史诗故事的悲壮结尾。
老房子
人越老越念旧,房子越老越金贵。也不知是因为念旧,还是物以稀为贵,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更喜欢游览、住宿、仿造老房子。于是,那些装满记忆、储有先祖气息和中国文化的乡村老房子,便如一件古董似的,越发弥足珍贵起来。
买房置地在古人看来是头等要事,这不仅是生活所需,也是身份象征。直到现在,盖房子依旧是乡村人家的头等大事,这便有了继承和传袭,有了老房子。中国现存最老的房子,是山东长清县孝堂山郭氏墓石祠。这座全部用20厘米厚青石板砌成的房子,建于公元一世纪的东汉早期,距今近1900年。石板房只是乡村老房子的一种,根据建设材质的不同,还有草房、木房、土房、瓦房、砖房等。不同的材质,让乡村房子有着不同的寿命。在风雨雷电、寒冬酷暑中,有的房子夭折坍塌了,有的房子凋敝消失了,还有一些房子却侥幸地保存了下来。这些经风沐雨的乡村老房子,如大浪淘沙般历久弥新,虽然垂垂老矣,却风姿犹存。
乡村老房子都十分考究,且非常智慧的。古人建房一般都有牌楼、华表、狮子、影壁、日晷、阙,殿堂、台榭、廊、亭、楼阁等等,这些建筑群落思想和形态及功能的丰富性,显而易见。即使普通人家,也有正堂、偏房之分。
乡村老房子是根的所在,那里曾飘起过袅袅炊烟,扯起母亲喊叫回家吃饭的嗓音,也寄托着父辈众多的期望。从乡村老房子走出了许多名人,虽然他们已远走他乡,但老房子却珍藏了他们的印迹,记录了他们的成长,于是那些寻常院落,便成了名人故居。我曾在水乡乌镇看过茅盾的故居,也曾去黄土高原的米脂探访过“明五暗四六厢窑”式的姜式庄园,还在阆中古城鳞次栉比的灰瓦下,寻访过旧日的寻常百姓。乌黑的瓦顶承载着天地精华,岁月斑斓的白墙上刻的是年迈的裂痕,雕栏花窗和深重的门后,隐的是寻常巷陌的烟火人家。在这些乡村老房子里,我看到了文化的厚重、思想的光芒,还有古风习习,仪礼淳淳。endprint
我喜欢这样的乡村老房子,它们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技艺的传承者。我曾一次又一次地去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仅为观赏那从各村整体移建而来的100所老房子。砖雕的屋脊、镂空木雕的床、几吨重的饮马槽、形态万变的拴马桩……让这里既是建筑艺术的宝库,又是民俗学的殿堂。我还探访过浙江泰顺县库村1200年前的鹅卵石房子。光滑的鹅卵石叠砌成一堵堵圆形的、方形的墙,重檐屋脊,瓦盖屋顶,驳风墙外有鱼龙图案花纹,让这些乡村老房子粗朴中透着幽雅。在不使用水泥灰浆的情况下,能让光滑的卵石站成一堵坚实的墙,你不能不惊叹库村古人手艺的高超。而这些老房子,不仅为一代又一代的库村人遮风挡雨,更是让耕读传家的祖训世代相传。沐浴着深厚的家族文化,库村后人带着满腹经纶走出了山林、登上仕途。
时光的狂沙让无人守护的乡村老房子日渐消亡,和老房子一同消失的还有那些精湛的技艺。当越来越多的摩天大楼和钢筋混凝土,日益迷离我们的视线时,我们更思念的是乡村。建筑永远是人类文明的记忆,乡村老房子便是这记忆的书写者和传承者,它不仅承接了我们的历史文化,还给我们现代的生活增添了文明。
终南山
如果说横亘在陕西关中南沿的秦岭山脉,是大自然雄奇险峻、气势磅礴的杰作,那么,处于秦岭中段的终南山,就是这一杰作中的精华。趁着人间四月芳菲天,我们去踏访《射雕英雄传》里赫赫有名的重阳宫。
车出西安沿着环山公路一路向西,终南山如骏马般与我们始终并驾齐驱。山峦重叠,逶迤峻峭,千峰碧屏,深谷幽雅,让人目不暇接。终南山,又称太乙山、仙都等。主脉为东西走向,支脉多呈南北走向,多达175道。著名诗人王维赞曰:“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人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正午的阳光洒下一缕缕金光,让终南山如穿了一件五彩衣般,分外耀眼。苍劲的青松、庄重的翠柏,还有不知名的各种花草树木,将终南山装扮的幽静爽馨。车经过一道峪口,便有一条溪水窜流而出。红墙黑瓦的村庄,“犹抱琵琶半遮面”地隐匿在树林中。大片的田野里,麦苗正在蹿个,金黄的油菜花开始衰败,而葡萄园里已是绿意融融。一条条山道曲径通幽,也许,其中有一条就是王重山上终南山所攀登过的。
车过户县,经祖庵镇南行不远,便到了道教全真派祖师王重阳早年修道和遗蜕之地。重阳宫,是我国道教全真派的三大祖庭之首,据记载,在最鼎盛的元代,重阳宫殿阁房舍达5048间,教徒上万人。虽然现在占地仅50多亩,但灰砖黑瓦的朱红大门,仍不失气场。经历近千年,悬挂在山门上方的元代皇帝御赐金匾,仍清晰可辨。进入山门后,就看见一块巨石,石上几个硕大的脚印和掌印为王重阳练功时所留。旁边不远处,有一颗粗壮的近千年银杏,为王重阳的大弟子马钰手植。苍劲的古银杏树腹中,滋生着一株翠柏,两树茂盛,相拥共生,犹如师徒之间的道义与友谊,情深似海。
重阳宫规模不大,但建设的却颇有味道,前殿巍耸,后院清幽。不管是清时的灵官殿、七真殿,还是后修的重阳宝殿、钟鼓楼等,均古朴典雅,风韵独特。而最大的看点还是祖庵碑林,现存石刻文物80余件,其中尤以31通巨型元碑最为著名。这些碑石记载着全真派的历史、教义、修炼要旨等,按内容可分为宗教历史类、书法名碑类、八思巴文类、内丹功法类四种。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碑文,我想从中寻到先天功、全真剑法、天罡北斗阵等秘籍的蛛丝马迹,但终是徒然。因为王重阳创造的道家武学,均是以炼气健身、修身养性为目的的。
出得重阳宫,往东走四五里地就到了位于成道宫中的活死人墓。《神雕侠侣》中,活死人墓不仅是一处世外桃源,还是王重阳、林朝英和杨过、小龙女爱情的见证地。其实,王重阳所建的活死人墓,为修道练功所需,只不过是一方带有墓冢的地穴,与《神雕侠侣》中描写的古墓派禁地有很大差别。如今,掩映在竹林下的活死人墓穴址依旧,地穴入口就在碑下,只是被封土堵起来。其实,活死人墓不仅是金庸小说里逃脱世俗的佳境,还是终南山隐逸文化的象征。
天下修行,终南为冠。行走于终南山,在满山黛色的森林中,散布着一株株山桃花,隐约可见一处处茅棚,那就是现今隐士的居所。据说,终南山里隐士约有五千人。其实,人生就是一场修炼,隐与不隐,都在于自己的内心是否能找到最本真的人生命题。而终南山也并没有超脱江湖,它只不过是隐士们一条通往俗世与江湖的捷径。
名州
“提起个家来家有名,家住在绥德三十里铺村……”一首陕北民歌,让远在深山的绥德,却声名在外。冲着这声名,我们的车从米脂沿着无定河去绥德。
夏日的盛情将贫瘠的黄土高原装扮得风流倜傥,伴随着一路青山绿水,我们的车渐进绥德名州古城。古城缘岩依阜而筑,背靠高峻的疏属山,无定河、大理河绕城交汇成一个“几”字,老城就处在几字中间。车进城区,只见密密麻麻的窑洞,如满天的星星洒落在路两边的梁峁沟壑间。地域的狭小,让这些窑洞前后衔接,一层又一层,从山道一直爬上半山腰。黄土挖成的靠山土窑、石砌的接口土窑,以及现代的石窑、砖窑,让形形色色的陕北窑洞在这里得到了集中展现。在大片的窑洞群中,不乏二三十层高的现代高楼夹杂其中。路两边,店铺林立,商贾往来,既有走街串巷的挑担货郎,又有开车吆喝的流动商贩;既有摩登女郎文艺青年,也有裹着羊毛头巾抽旱烟的老汉和挎着篮子顶着头帕的老妇,大城市的繁华与小城市的舒缓交相辉映,让名州老城风味独特。
作为石雕之乡,在名州,不管是住的窑、墙、门楼,还是戴的饰品、走的桥、用的碾等,都可寻到石雕的影子,这从石牌楼便可以窥见。乘着夏日的习习凉风,我们去看“天下第一楼”。老远地,就看见题有“天下名州”四个大字的石牌楼,矗立在学子大道与210国道的丁字交汇处。五门六柱十九楼的石牌楼,长36.9米,高16.9米,恢宏大气,庄严肃穆。牌楼上铭刻了虞姑、扶苏、蒙恬、李广、韩世忠等不凡事例,囊括了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中游的吉祥如意之物,可谓是一篇丰富的史书,其中尤以龙和凤最为传神。盘龙神角突兀,龙须根根似飘,凤尾开屏如天女散花,根根羽毛皆有神韵。整个石牌楼共由1168块雕石、66幅人物典故浮雕组成,总重量400余吨。这么多的雕石,竟能卯套契合,和谐统一,足可见工艺之精细、技术之高超。
看完牌楼,过龙凤桥,便是汇集黄土风情和狮文化的石魂广场。广场里引人夺目的便是石狮,其中又以入口处的一对石狮最为高大,达19.5米高,仅嘴就高2米,宽3米。“狮”也称为“狻猊”,是传说中龙生九子之一,为力量与正义的象征。广场入口右侧,为宽25米、高5米的九狮照壁石刻浮雕画,中间为34尊高6.6米的垒石底座式石狮群雕,其阵容严谨、错落有致。穿过石狮阵,沿着主干道上山,路两边葱郁的树木间,分列着108只形态各异的石雕狮。这些石狮造型各异,既有散落在黄土高坡田野里的灵物瑞兽,又有置于庙堂高山的镇山狮和珍藏炕头,还有扶正祛邪的炕头狮,有的刚健威严如勇士,有的活潑调皮像顽童,有的慈眉善目似母亲……神态生动,妙趣横生。
在名州,除了石雕外,还有石刻画廊、摩崖石刻、汉画像石馆等,这些雕琢自然、线条流畅、造型独特的石雕,不仅丰满了名州,更是让名州名满天下,吸引着四方来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