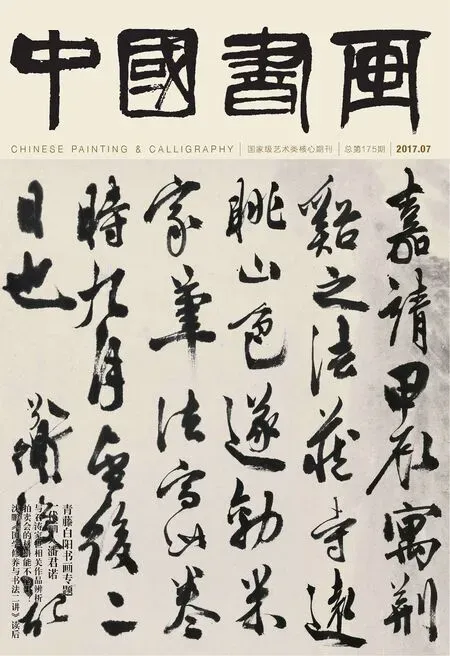此“水墨”非彼“水墨”
黄宗贤
四川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
此“水墨”非彼“水墨”
黄宗贤
四川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
水墨本是一种媒介、材质,但是很多时候人们往往将其视为一种画种。以媒介材质分画种,似乎也正常,比如油画、水彩画、丙烯画、版画、沙画、纸草画等等。随着媒介材质的变化,自然会出现一些新的画种,如瓷砖画、铝板画、综合材料艺术以及无所不包的“新媒体艺术”等等。
这些年来,“水墨”作为一个概念,其内涵远远超过了其作为材质的原本意义,也非附属于“中国画”这个概念的一种材质表述。“水墨”似乎有了一种自带的精神性、先锋性、时尚性,于是不同类型的画家,都在抢用这个概念,而不用或羞于用约定俗成的“中国画”这个概念。因而“现代水墨”“当代水墨”的感念与术语被广泛使用,以这类概念冠名的展览比比皆是。“当代水墨”在很多时候被视为等于“当代中国画”,只不过可能觉得“当代水墨”更洋派,故以之取代“中国画”,而在另一些场域,“当代水墨”的含义恰恰是对“中国画”概念的疏离甚至反叛。可以说,“当代水墨”是一个充满歧义的概念,这个概念又如一个香馍馍,大家都要去哄抢。
“前卫”艺术家往往用“当代水墨”这个概念来区隔与中国画或者说传统水墨的关系,隐含了“先锋”艺术家羞于与国画家为伍的态度。为了怕人误会,很多时候“前卫”艺术家干脆不用“当代水墨”这个概念,直接用“实验水墨”取而代之。处在当下的国画家用“当代水墨”来取代“中国画”概念,最多暗含着自认为具有承扬与创新品质之意的中国画,更主要还是看中这一概念的时尚感。在这里,先锋艺术家与通常意义的国画家所谓的“当代水墨”,内涵是完全不同的。在先锋水墨艺术家那里“当代”是一种观念、态度、立场,这种观念、立场、态度不仅与传统没有关联性,而且是对传统的疏离、反叛,在“前卫”“先锋”的名义下背离了中国画的基本传统,不断地付诸新的语言实验和价值重构。这里,水墨仅仅是一种纯粹的媒介而已。而另一部分源自传统中国画文脉走下来的国画家,之所以喜欢用“当代水墨”取代中国画概念,就如换了一件马甲,变得光鲜起来、时尚起来。就其内涵而言,“当代”在这里最多是一种时间意义的指代。
先锋水墨一派一开始就没有将自己纳入中国画范畴。传统中国画派自己添加了“马甲”,但是在先锋派眼里还是一个“过去式”。先锋水墨的先锋性表现在哪里?一是与中国传统水墨的笔墨技法彻底剥离,无论是骨法用笔或以书入画,或诗书画的结合,在他们以“观念”为主导的“实验”中已是荡然无存,更不必说传统中国画所蕴含的“淡然清远”“得意忘形”“氤氲雅致”一类的美学趣味了。水墨成为一种我行我素自由挥洒的材质。笔墨相随、相辅相成的关系被肢解为只有作为物性的墨。物性的墨在先锋艺术家们的挥洒中被赋予“观念性”“精神性”。其实在貌似深刻的视觉符号中,除了折射出一种对传统疏离态度外,未必有更多的“观念”与精神蕴含。就如一些当代书家,将行为+笔墨,其实与传统书法没有关系,最多是“当代”名目下并无新观念的哗众取宠的游戏而已。作为一种另一类“先锋”,多为借助水墨材质但并不按中国画的法理、程式涂鸦一些传统水墨(春宫画除外)所不涉及的题材,实质将水墨作为宣泄世俗感性欲望的媒介了。无能是哪一种“先锋”,未必是真正的“先锋”,因为真正的前卫艺术或先锋,依然是一种话语,一种表征。然而,今日之前卫与先锋,已然沦为一种资本的附庸,一种消费的物品,一种社会之附庸,甚至是一种哗众取宠的游戏。这也就是波德里亚所谓的“表征危机”。不消说,当下先锋水墨已经离中国画的人文传统越来越远,甚或说其已然断裂了人文传统,而常常试图以“怪异”之面目骗取“先锋”之名及其资本利益。“先锋”水墨或悄然无声或明目张胆地或与世俗感性欲望或与资本合谋。此类水墨,非国画,从事这类水墨的人也没有将自己视为国画家或水墨画家,他们只有一个称谓—“当代艺术家”。因而,此“水墨”非彼“水墨”,将先锋水墨与水墨的传统文脉区隔开来,从哪方来看都是合情合理的。
那些沿袭传统画法的国画家将自己的创作贴上现代或当代“水墨”的标签,也未必能够“当代”起来,是不会被先锋水墨艺术家们视为同盟或同道的。如果说不被当代艺术圈认同也罢,真的传承了文脉,有所拓展,也算是在艺术史上有或多或少的价值与意义。但是问题是,今天许多玩水墨的国画家,抽掉传统中国画的人文精神和价值取向,也已远离了中国画传统。对于中国画本身而言,重要的毕竟不仅只是笔墨,更是笔墨语言的表征中所渗透的氤氲气息和人文品格。

[清]石涛 赠刘石头山水册(之一) 美国纳尔逊艾金斯博物馆藏
众所周知,在传统中国社会的相当长时间里,主流艺术的话语权被文人所掌控。古代文人可以说是无人不能书,很多也能画,因此文人画成为中国艺术史上最重要的一种类型,也最能体现中国人的人生观与审美趣味。古代文人之所以钟情书画,不主要在于“格物”,而重在“言志”。在中国文人看来艺术并非是纯粹感官欲望的追求或发泄的手段,而是道德、情操、智慧的来源,是人格的象征,更是陶养完美人格的最佳途径。正是因为有艺术的滋养,许多文人才从欲望的重压和政体的桎梏中超脱出来,使自己的心灵升华到一种“逍遥”的境界,不至于在现实困境与理想追求的矛盾张力中,撕裂自身。“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是中国文人入世的行为准则,功名成就成为儒生们人生年少阶段或一生的外在追求,而“虚以待物”,“入山林观天性,以天合天”往往又是他们内在的精神诉求。入世与出世、外在功业追求与诗意化的精神栖息构成儒生的双重人格。文人们得意时志在仕途,失意时超然遁世。对于更多的文人士大夫而言,在险恶的仕途中难以得意一生,在追逐外在功业的崎岖路上散落着无数的失意者。一批批失意者或者对于现实的失望者,他们转向自然、转向艺术,寄情林泉与笔墨。在自然中他们能够体味到“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的审美境界,在墨色运化的天地中享受到“虚静而后能逍遥”的“至乐”“圣乐”。诗意的人生、艺术的人生往往是偶然的或一连串的现实的失意成就的。中国画的人文传统不仅为积极入世者提供了一种精神动力,也为超越者储备了一片自由的天空。尚文崇艺,对于是中国文人而言,绝不仅仅是才情彰显的需要,更不是自然的摹写与再现,也不是一种抽掉了人文精神的笔墨技巧的把玩。
而当下,不少水墨画者,仅仅把画画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或者附庸风雅的方式,学得几手传统水墨的程式套路,就可以走南闯北,游荡于江湖。于是“行头”不离身,走到那儿就笔会到那儿,表演到那儿。一招一式,招招试试,熟练无比,绝无废纸。就好比杂耍者,满街叫卖,出场见利。至于传统绘画所曰的“意在笔先”“画为心印”的内涵在功利化的表演中和永无止境的重复中被彻底消解。画画也好,其他艺术也好,本质上是心灵与内在情感的外化形式,就如米芾所曰:“意足自我足,放笔一戏空。”无“意”有笔,笔将空乏,画无意趣。也如弗莱贝尔所言:“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内在意味空疏,不管什么形式都是僵滞的形式。意生发于何处?在于胸次的高韬,学识的丰富以及对人世之流变、自然之运化、生命之节律、时空之转换的敏锐洞察与感悟。在真画者的行笔运墨中流溢出的是情感、灵性与深刻的体悟。当画者仅仅将画画看作是一种技术操练,一种程序控制,一种熟能生巧的语言游戏,那技术套路、程序编码、游戏规则当然就可以被无限复制,于是水墨画或者说中国画,就如被误解的书法一样,成为一种人人都敢问津、涉足、操控的“风雅”技术活,于是我们的确在千千万万的水墨大军中很难分得清“张家山水”和“李家花鸟”了。近百年前(1918年)陈独秀先生在《美术革命—答吕徴》一文中对中国画传承中的“恶”影响予以了猛烈的抨击,认为这种影响“具体表现为陈陈相因,用‘临摹抚仿’四大本领复写古画”。这种恶影响在今天的中国画界并未被完全消解,甚至在割裂了人文传统的现实境况中,在丢弃人文价值的消费文化语境之中,更是甚嚣尘上。
“先锋水墨”和沿袭性“水墨”表面上南辕北辙,格格不入,事实上,两者在内涵与价值支点颇有暗合之处。这种暗合就是都是去人文精神、去主体意志、去中国画内在品格的一种非常态的艺术表达范式。事实上,二者都已成为悬置了人文内涵的资本自觉的产物。实验水墨不同于一些自喻为“当代水墨”的中国画,两者也与中国画的传统精神相去甚远。中国画传统精神与人文品格在现当代的弱化与消解现象,以及我们应该在中国画的传统里承扬什么是 值得探讨的话题。
责任编辑:刘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