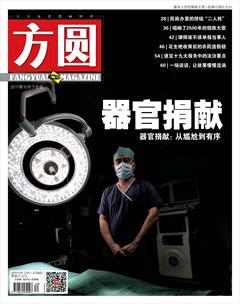器官捐献:从尴尬到有序
沈寅飞
许多国家的法律都认为,可移植的器官是稀缺的国家资源,也就是说在捐献者捐献某个器官之前,器官是属于捐献者的;接受者接受器官移植以后,器官是属于接受者的;而在分配系统没有确定它属于哪个人之前,它属于整个国家的资源
“娄滔与湖北省红十字会的器官捐献协议已经签好了,她目前正在接受医院的器官感染治疗,治疗可能有三种结果,一是娄滔康复,可能性非常小;二是娄滔病故,器官感染指数降低,可以捐献;三是娄滔病故,器官也因为感染指数过高不能捐献。娄滔的遗愿是将头部捐献给运动医学机构做研究,其他可用的器官移植给需要的人。我相信这也是一种生命的延续,长时间以来我们家庭受到社会的帮助与关心,更加坚定了我们要这样做。”10月16日,罹患渐冻症的北京大学历史系女博士娄滔的父亲娄功余接受《方圆》记者采访时表示。
2016年1月,娄滔被查出患有渐冻症之后,一年多来,疾病逐渐侵蚀她的运动神经,如今,娄滔躺在病床上,已经失去对自己身体的控制能力。
2016年下半年,娄滔将自己希望捐献器官的想法告诉娄功余和母亲汪艳梅时,父母非常不理解。娄滔一家是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土家族人,土家族一直以来都有全尸土葬的传统习俗,听说娄滔想去世后把头部捐献出去,汪艳梅哭了好几天。近一年来,经过娄滔的反复劝说,娄功余和汪艳梅才逐渐接受了器官捐献这件事。上个月,娄功余夫妇和另外两名亲戚还达成了一致意见:与娄滔一样,去世后也要捐献自己的器官,随时可以签协议。
器官捐献,曾是一个令人讳莫如深的名词,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许多人不愿意谈论器官捐献。而如今,人们逐渐意识到,对于不幸离世的器官捐献者来说,他们的生命可以换一种形式在世界上延续;对于接受捐献成功移植器官的人来说,他们重获新生。
过去十几年,从年均寥寥无几的自愿遗体捐献数量到现在高达四五千例一万多个器官捐献的数量;从一度停滞的器官移植困境到现在每年一万余例移植手术,中国的器官移植事业正悄然从备受诟病到有序发展,走向机制化、法制化。
中国器官移植的冬天与春天
十多年过去了,全国人大代表、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陈静瑜依然记得在2002年前他做国内第一例肺移植治疗肺气肿手术之前面对的谣言,当时就有人传言移植到人体的肺来自于猪,所以大家觉得做肺移植肯定不能成功。而且在此之前,我国的肺移植工作已经足足停滞了近5年时间,从1994年1月至1998年1月,我国只做了近20例肺移植,只有2例肺移植病人术后长期生存,余下病人均在术后短期内死亡,肺移植九死一生的黑色阴影一直笼罩着国人。
陈静瑜执刀的第一例手术成功了,后面又完成了上百例,而且移植受者的成活率几乎达到了国际水平。在此前后,国内其他各项人体器官移植技术和数量也不断快速发展,这让国人渐渐打消对器官移植的顾虑,但却始终没能得到世界移植界的肯定。在2015年以前,由于没有成熟的器官捐献体系,中国器官移植的两种来源,一是亲体捐献,二是尸体器官。因特殊原因,后者基本来自死刑犯,这一制度不符合世界卫生组织和全球移植界共同遵守的伦理准则。因此,世界器官移植界对中国实施“三不”政策:不承认临床移植成果;不允许在国际权威杂志发表临床器官移植文章;不同意中国移植专家加入世界移植组织。
2005年,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黄洁夫下决心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和伦理的器官移植体系。政府也高度重视器官捐献移植工作,出台一系列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推动器官捐献移植依法规范开展。2007年,国务院颁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明确规定器官捐献的来源和公民捐献器官的权利。2009年,原卫生部下发《关于境外人员申请人体器官移植有关问题的通知》,严格限制“移植旅游”。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施行,器官买卖和非自愿摘取器官“入刑”。2013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出台《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试行)》,形成部门法规,以确保器官捐献移植的透明、公正、可溯源性。
2014年12月,中国宣布将停止死囚器官的使用,公民捐献成为唯一合法来源。有人说,“中国器官移植的冬天到了”,因为他们认为没有老百姓愿意捐献。黄洁夫回应,“是春天到了”。
随后的2015年,中国器官捐献的事实证实了黄洁夫的话。这一年,中国公民器官捐献数量大幅提升,从2014年的1500例增长到2766例。国际移植界也宣告结束对中国的“三不”政策。这一年也被誉为中国器官捐献移植实现“里程碑式”转型的一年。
人们对器官捐献有了新的看法,黄洁夫讲述了一个让他备受感动的事例。2015年2月,一名法国青年在中国杭州旅游的时候意外坠亡,他的父母赶到中国,本来想将遗体转运到法国去再完成捐献,在得知中国已经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后决定在中国捐出孩子的器官,心、肝、肾、肺包括眼角膜都捐了。这件事被媒体报道后,安徽一位老人带着儿子、儿媳、孙子等一家七口到红十字会,要求捐献器官。老人的理由很简单,以前用死囚器官,我们不捐。现在连外国人都捐了,说明这个事情是阳光的,我们也要帮助别人。
打破程序和观念的障碍
“从2015年1月1日起,公民器官捐献成为唯一合法来源,我国的器官捐献数量不断創造历史新高,2016年公民完成捐献4080例,捐献大器官11296个,今年我们预计器官捐献会超过5000例,器官移植手术会达到1.5万-1.6万例。”黄洁夫说。
与此同时,必须清楚地看到,数字背后是中国年均约30万脏器衰竭患者有器官移植需求。有数据表明,2015年,中国成功完成肝脏移植2000多例、肾移植5367例,但2015年肝脏移植需求者新增4000多人,肾脏移植需求者新增了1万多人,供需差距进一步扩大,最长的等待名单肝脏移植就有500多人同时在同一家医院等,肾脏移植就有2000多人在同一个医院等待接受移植。endprint
“目前,我国器官捐献率只有百万分之2.98,而一些国家已经达到百万分之40。”陈静瑜认为,就移植手术本身而言,我国的移植技术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问题在于器官供体稀缺。
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民众对器官捐献的不了解、捐献程序的复杂也都是重要的干扰因素。《中国器官捐献公众意愿调查》显示,83%的参与调查者愿意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但其中56%的人不愿登记的原因是,“不知道在哪儿登记或手续太烦琐”。最初,做器官捐献登记的体系是红十字会,但手续非常烦琐,光填表就要填上足足三页。2014年,施与受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网站、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平台先后上线,但登记手续依然复杂。
2016年底,拥有4亿多用户的支付宝开通“器官捐赠”志愿登记,用户只需要十秒就能完成器官捐献登记,而且也可以随时撤回。短短几天之后,就有10万人参与了志愿登记。黄洁夫本想当第一个登记的人,结果却因为支付宝用户太踊跃而没能如愿,“我们做志愿登记是为了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这是一种爱心的表达,不意味着有任何捐献义务需要履行”。
除此之外,在传统思想方面,典型的就是孔夫子的思想,“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让不少国人认为死后应留有全尸,黄洁夫则做出了另一番解释,“我们还常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孔夫子指的是弃之不孝,而不是说救人不孝。孔夫子如果生活在今天,他应该会是第一个报名做器官移植的志愿者”。
“在器官捐献组织做好宣传教育、简化程序等工作之外,最重要的还是公民意识改变,这是器官捐献工作的突破口。”无锡市人民医院器官捐献与移植办公室副主任胡春晓认为,尽管这两年他感觉到器官捐献者的比例在不断升高,但总体而言,公民意识仍然不够,拒绝率仍然很高,几年的工作实践告诉他,器官捐献的成功率与捐献者的职业、性别、受教育程度、经济条件、家庭状况并没有多大关系,起到很大作用的是出发点,捐献的人和他们的家属具备大爱精神的同时,主导他们思想的通常都是,感觉亲人还“活着”,生命还在延续。
器官移植医生关心的法律问题
面对人体器官捐献的短缺,无论是黄洁夫、陈静瑜,还是很多一线的医务工作者,有一件事情他们尤为关心,就是为脑死亡立法。
我国传统以“心死亡”为判定标准。依据医学标准,即使医生宣布脑死亡者去世,如果家属不认为脑死亡者已故,也不能撤出治疗措施。结果,脑死亡后毫无意义的抢救和其他一切安慰性、仪式性的医疗活动给病人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财力负担。与此同时,等待捐献的器官也在逐渐受到感染,尤其是像肺脏这样与空气接触的开放型器官更为明显,这也是近年来陈静瑜团队多次无法成功获取捐献者肺脏的重要原因。
曾有实验者将实验用的小狗的头砍掉,然后在气管等器官上接上大大小小的管子。这条小狗没有当时死亡,而是抽搐了两天多才死去。这是陈静瑜从医学实验角度举出的一个例子,但它恰恰说明,“对于很多脑死亡者来说,维系生命而失去生活质量,可能出于子女的孝顺,但不一定是患者所期待的。”
陈静瑜认为,采用脑死亡作为死亡标准,有利于提高器官移植的数量和质量。因为脑死亡者仍有残余心跳,各脏器血液供应得以维持,所以在及时施行人工呼吸和给氧条件下,各脏器组织不会像心死者那样发生缺血、缺氧。作为供体,这些脏器组织有较强的活力,为移植成功提供了先决条件。可以预期,在脑死亡立法以后,更多需要器官移植的垂危病人能获得重生机会。
黄洁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脑死亡不同于植物人,更不同于安乐死,他是人体100%的死亡,只是用呼吸机可以继续维持很久,但事实上,生命从这一刻起已经没有了奇迹复活的可能,反而心跳呼吸停止死亡的患者,曾有复活的先例。脑死亡患者只是在呼吸机的帮助下,维持着看似活着的状态,这是对医疗资源的巨大浪费,同时,也是对死者的不尊重。”
为此,作为全国人大代表,陈静瑜已经连续两年提交脑死亡立法的提案。然而,相关部门回称,目前我国没有实施该法的群众基础。事实上,近年来每年数千例器官捐献者中大部分病人家属都认可了脑死亡,陈静瑜说:“这就是广泛的群众基础。”
据了解,目前全世界脑死亡立法的国家已有80多个,其中日本、美国、西班牙、英国、德国较为典型。我国司法实践中认定死亡的标准是:心脏、脉搏停止跳动,呼吸停止。脑死亡在司法实践中还没有被采纳。
事实上,为脑死亡立法不只关乎器官移植,在法律上也产生了诸多难题。如我国《刑法》许多条款都涉及死亡与重伤的问题,并明确规定了对故意及过失致人死亡或重伤的定罪和量刑。但是在法医学鉴定中,对于是否认定脑死亡者为死亡抑或重伤,直接影响对犯罪嫌疑人的判决。在民事法律关系中,死亡是公民民事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终止的原因之一。如果死亡的界限标准不统一,确定死亡的时间不一致,可引起遗嘱纠纷、保险索赔纠纷、职工抚恤金纠纷等法律问题,也直接影响到法律上的继承问题,婚姻家庭关系中抚养与被抚养、赡养与被赡养以及夫妻关系是否能够自动解除等问题。
不让穷人成为富人的器官库
人体器官属于稀缺资源,更是等待移植病人的无价之宝。去年北京一位老人捐献遗体事件中,一开始持反对意见的女儿担心的是器官不能帮助最应得到帮助的人。这一点也是很多器官捐献者和家属的顾虑。
“器官不是我们制造出来的,也不是生产出来的,是老百姓捐出来的。”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及机会副秘书长王海波说,任何捐献首先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用”,器官捐献中,如果讲不清这个问题,那就失去了社会的信任。
一位器官捐献者的家属曾这样说道,我们帮人,不论他是富的还是贫的,只要他需要,轮到他就可以用。说他穷他没钱,他就不能用,另外有钱的就可以用,这是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现象。
目前,在国际上伦理学的研究非常清晰,可移植的器官是稀缺的国家资源,也就是说在捐献者捐赠器官之前,器官是属于捐献者的;接受者接受器官移植以后,器官是属于接受者的;在分配系统没有确定它属于哪个人之前,它是属于整个国家的资源。所以器官分配应该比其他社会资源的分配更严肃、科学,更体现公平、公正、公开。
“整个中国公民都是器官捐献的一个潜在群体,但是如果只有支付得起费用的人才能接受器官移植服务,捐献的群体和接受的群体就会有差别。捐献群体的社会经济学状态会低于接受群体,就会被解读为穷人成为富人的器官库,这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和伦理法律都不可以接受的。”王海波说。
那么,面对目前登记在案的数万名等待者,如何分配那些稀缺的器官资源呢?
2013年8月,国家卫计委出台《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实行)》,首次明确严格使用COTRS系统实施器官分配。经过一套严密的评分系统测算,每一名在COTRS系统里排队等待移植的患者都会生成一个分数,而一旦发生器官捐献案例,经过区域优先原则筛选后,这个分数的排序将成為器官分配顺序的最重要依据。
如今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能让年均30万人的器官移植等待者人人都能拥有移植的机会,而不是因为高达几十万元的器官移植费用无奈等死。
目前,在广州, 肝移植术后抗排异药物治疗的费用已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在江苏,肺移植已列入二类医疗保险报销范围,患者个人仅需支付 40% 的费用,而且术后免疫抑制剂的费用个人仅需支付 10%,其余列入医疗保险报销范围,由国家补贴。但在全国范围内,器官移植仍未纳入医保。
近两年,陈静瑜、黄洁夫等在全国两会上不断呼吁将器官移植纳入大病医保当中,他们选择从肾移植纳入医保开始,一步步达到器官移植医保的全覆盖,他们希望更多的人有生的希望,因为器官捐献和移植必将发展得更加成熟完善。endprint
——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谈脑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