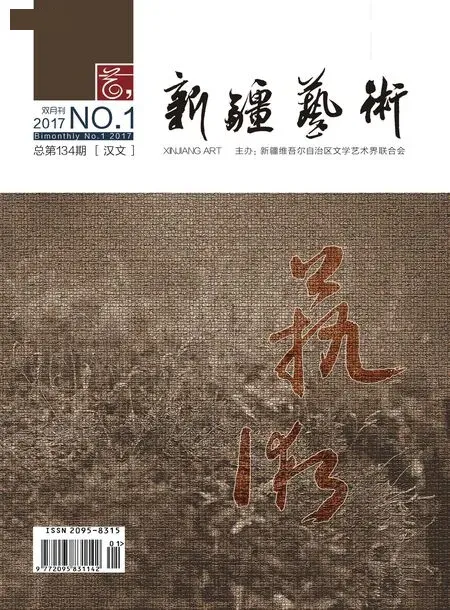“多元一体”视野下的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思考
□ 黄适远

大玛纳斯奇和年轻传承人
从2005年至2015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走过了十年。十年树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取得了重要的成果。特别是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终于落地实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准绳。在世界范围内,中国拥有的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世界最多的,共计29项,还不包括3项急需保护的名录。29项世界级名录涵盖了祖国的东南西北,呈现了中华文化的斑斓多彩,赢得了世界的高度瞩目,也表明了中国文化的薪火相传源远流长。
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起步与发展同样经历了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同呼吸共进步的十年。新疆文化具有多民族、多宗教、多种文化的色彩,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考察,其实也是天山南北多种文化的共生融合,具有鲜明的多样性。从历史上看,新疆文化用地域文化显然比用民族文化更合适这一描述和评价。毕竟,在广袤的新疆大地上,从史前文化到近代文化,新疆文化所呈现的文化交融和民族交融为世界罕见,四大文明长达几千年的交汇为新疆文化打下了深厚的文化积淀,这种文化积淀是一笔无比丰厚的遗产,也使新疆成为今天“一带一路”和世界对话的前沿和文化基地。因此,今天新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葆有的厚度、深度、广度在世界范围内都罕见。回顾十年保护,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取得了较好成绩,反映了新疆文化的底蕴和厚重,但同时,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依然面临着许多需要总结经验的方面,以为今后的“非遗”工作打好基础。

哈萨克族阿依特斯演唱
一、从国家到自治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法和路径
应该说,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国家和地方都相继出台了法律法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方法和路径。
(一)国家层面
1、2005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5】18号),首次提出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指导方针,并决定在全民中树立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借鉴法国等国家的做法,设立“文化遗产日”,于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举行宣传活动。2、2006年,文化部颁发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3、2008年,文化部发布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和管理办法》。4、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这是国家层面上文化遗产保护的第二部法律,在此之前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这两部有关文化遗产的法律成为保护和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有利武器。
(二)自治区层面
1、2008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把全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合理利用等工作纳入到法制化轨道。2、2009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出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3、201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保护条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是一个单行条例。它和上述法律法规成为一个有机整体,配套执行。
另外,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由自治区文化部门出台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也已经问世。为地州、县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依据和实施路径。
二、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结构:立体化与网格化
(一)立体化、网格化板块形成
机构队伍、名录体系、经费渠道呈现立体化和网格化。一是建立了从自治区、地州、县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和队伍。从2006年起,自治区各级文化部门纷纷争取各级党委政府支持,到2014年,全疆基本形成了自治区—地州—县市的三级非遗保护队伍体系,各地文化馆经当地编委批准均加挂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牌子(也有个别挂靠到博物馆或文物管理部门),初步形成了从上到下的三级工作链条。二是全疆各级非遗保护队伍均大规模开展普查工作,摸清家底。从2006年到2009年,全疆各级非遗队伍开展了大规模的普查,对民间文化艺术遗产进行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第二次摸底调查,挖掘和整理了大量的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线索,为建立基本名录打下了良好基础。此次普查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全疆历时最长、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覆盖范围最广的一次普查。全疆各地共召开普查座谈会573次,投入普查工作人员1896人次,社会参与普查人员9063人次,走访传承人19069人次,调查项目6109次,获得普查成果3772项。2009年以后,各级非遗保护队伍又相继自发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虽然没有统计具体数目,但可以肯定地讲,截至到2014年为止,取得的成绩绝不在2006年-2009年之下。三是建立了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四级名录包括了国家级-自治区级-地州级-县市级,初步建立了新疆名录包括文本、视频、音频在内的详细档案体系,夯实了基础性工程,为今后实施数据库管理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四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费基本得到落实。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4年,中央、自治区累计投入经费1.9亿元人民币,保证了普查和项目研究经费,推进了非遗工作开展。毋庸置疑,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明确规定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保护、保存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但从实际情况看,新疆各级政府大多数也都落实了此项要求,但仍然有个别地方没有落实,反而挪用上级文化部门拨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费。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建立长期的问责制、督查制,或建立一票否决制,才能使新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望得到更好开展。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形成网格化
1、木卡姆保护。《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于2005年11月25日成功申报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按照申报承诺,新疆有关部门做了大量后期工作。主要是三条腿走路:一是以研讨会形式开展。首先于2006年在乌鲁木齐召开了“第六届国际木卡姆研讨会”,就“中国新疆及境外木卡姆的历史现状”、“木卡姆在不同国家及地区的表现形式”、“木卡姆在21世纪的保护及传播”等进行了研讨。其次于2007年在新疆莎车县召开了“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学术研讨会”,围绕“各不同种类维吾尔木卡姆的保护传承现状及对策”、“关于不同版本维吾尔《十二木卡姆》的保护和传承”、“关于原生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区的建设问题”展开了研讨。二是建立各地木卡姆传承中心和传承人班社。目前,哈密、吐鲁番、莎车都已建成了木卡姆传承中心(以各地流传的木卡姆为演出对象),东疆和南疆由农民艺人自发组成的班社众多,以木卡姆传承中心为园地开展传承授徒和进行各种演出,活跃了当地文化生活。三是以新疆木卡姆艺术团为主由自治区财政扶持的公益二类事业单位,在国内外表演木卡姆。四是成立了中国维吾尔木卡姆和古典文学学会,作为国内研究和协调木卡姆的支持机构。
2、《玛纳斯》保护。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也于2009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当前,《玛纳斯》的保护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自治区文联民间文艺家协会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高度重视。建立了《玛纳斯》研究机构,出版了相关研究成果,同时在2012年成功举办了中国新疆克孜勒苏玛纳斯论坛国际学术会议。此外,出版了《玛纳斯》柯尔克孜文和汉文版1、2、3卷。只是非常可惜的是,被誉为“当代荷马”的“大玛纳斯奇”居素甫·玛玛依老人已去世。
其它:哈萨克族阿依特斯、蒙古族长调、新疆花儿、新疆小曲子、新疆社火等各民族非遗项目均得到了扶持发展。截至2014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共拥有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3667项,其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项目3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83项,自治区级293项,地州级1116项,县市(区)级项目1819项。认定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传承人4940位,其中,国家级传承人64人(已去世14人),自治区级521人,地州市级1286人,县市(区)级3069人。
传承机制。基本为五个方面,一是各地民间文化艺术的自然传承,遵从千百年来的规矩和传统,口口相传。二是各地政府的文化自觉,通过命名“民间大师”、举办各类演出活动极大调动了民间艺人的积极性,赢得了社会关注,为传承创造了良好条件。三是数字化记录传承。对濒临消失的某些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数字化工程等方式予以记录和保存。四是面向社会的多元渠道传承。包括《十二木卡姆》《玛纳斯》《江格尔》《格斯尔》、新疆花儿、新疆小曲子等许多项目通过进校园、进社区等形成不同传承链条。五是通过文化产业化实施传承。目前,自治区文化部门已经建立自治区级生产性保护基地28个,如疏附县乐器村、墨玉县桑皮纸制作公司、洛浦县时代地毯厂等,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为当地的文化产业化发展、就业与社会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
三、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地缘文化视角考量与定位
(一)多元一体
多元相对反映了新疆地域文化的厚重多样。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新疆这个祖国最西部的边疆地区,更多要弘扬和强调中华民族文化和中华共同体意识。多元文化不是相互独立毫无关联的文化,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共同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这个“一体”。因此,在新疆强调“一体”的意义在于“一体”中所包含的“多元与交融”,而不是“一体”与“多元”并列,更不是“多元”之间毫无交流交融,这是一个必须清晰的概念,这既是考量,更是定位。
(二)三个有利于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一章第四条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要遵循的原则:“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①在我们现在可以接触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个别地方或学者过多强调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性或不可替代性,实际上,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具有的独特性客观存在,在民间自然有序生长。因此,在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无须去刻意强调这种不同。从文化生态上观察,在现代生活和工业文明的今天,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文化多样性弥足珍贵。然而,对于新疆这样一个边疆地区来说,无论哪一个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可以游离在此之外的族群文化。所以,新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必须遵守三个有利于原则: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这是方向,更是原则。
(三)文化安全与跨界民族
新疆与中亚多个国家接壤,跨界民族较多,与接壤的多个国家在语言、习俗、历史、文化等方面既有认同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历史积淀、文化传统、生活生产方式、道德风尚等方面有相同点。特别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大同小异。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年的发展中,对于新疆跨界民族文化研究十分重视,起步较早。如对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格斯尔》、蒙古长调、哈萨克族阿依特斯等的保护,都走在了前面,确保了文化安全。当然,对于请求和我国共同申报跨界民族文化遗产的中亚国家,我国也站在跨界民族文化共享的原则立场上,遵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申报要求进行申报,做好周边文化交流。

英雄史诗《江格尔》演唱
(四)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
我国从2007年开始设立文化生态区如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等。文化生态区主要包括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产业的“三位一体”。新疆目前设立了自治区级的察布查尔锡伯文化生态保护区,尚未有国家级层面的文化生态保护区。从新疆的文化建设实际来说,保持文化多样性符合文化生态的目的,如果从提倡文化融合和包容不同的战略眼光看,特别是从保证新疆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的总目标考虑的话,假如要建立获得国家层面批准和扶持的文化生态区,关键问题可能在于不要以单一民族为主和架构的某项文化遗产为主,而要把视角放得更加开阔,重点和中心要放在能够体现新疆文化的整体感、厚重感和共存感上,特别是能够体现文化融合的综合性文化遗产上。比如把天池、喀纳斯建成文化生态保护区效果可能更好,这些地方生活着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等民族,已经形成了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共融的特色,充分体现了文化的“混成性”和“融合性”,是新疆地域文化的典型代表,这样的文化生态区保护意义非凡,在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方针下更能显出其和谐示范作用。
(五)文化产业化
文化产业化已经升级为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战略方针。在这个指导思想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要融入时代,融入生活。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传统手工、传统医药、传统美术,其审美和实用价值具有很强的融入性。在国家提倡文化复兴中具有卓越的实践意义。需要值得注意的是,不要在文化产业化的探索中,特别在提倡旅游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俗、节日的融入过程中,对于某些如“祭祀”、“婚礼”、“人生礼仪”这样具有神圣、庄严的文化遗产扭曲开发,应尊重其族群的民俗仪式的神圣庄重。在实际工作中,一定要按客观要求分类进行保护或开发利用,不宜一刀切。

(六)传承人队伍保护
传承人队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和主要载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特点是活态传承,口口相传为主要特征。十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建设中,最严酷的教训就是人亡艺绝,许多民间文化艺术的大师未及把全部所学留下就驾鹤西去,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永久之痛和深深的遗憾。目前,国家已经启动了传承人培训工程,新疆也已积极响应,已在新疆大学和石河子大学分别进行了传承人队伍培训。传承人队伍建设的好坏,直接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弘扬,他们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宝、省(区)宝、地县之宝,用好他们的作用,创造条件发挥好他们的作用,事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建设,一定要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
(七)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少数民族文化转型
现代生活方式和现代文化如何与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代表的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实行有机融合,进而实现少数民族文化在保持族群优秀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实现文化转型,对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具有重要的决定意义,这个命题现实而必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特点是既有独特性,又有活态流变性,没有任何一成不变的事物,文化更具有流动性。现代生活方式和现代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非绝对的矛盾,而是交融交织的,两者可以共融并共同获得发展,因此,少数民族文化转型也是大势所趋,是当今时代和文化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
(八)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全民共享
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源于大众,也应回归和反馈于大众,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义绝不是把传承人资料和遗产项目锁在电脑里、办公室里,而是要普及到大众文化生活里。特别是在当代社会中,这种惠及程度应该能做到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打开任意地方网络都可以欣赏到当地的遗产项目,了解当地的地域文化,和传承人对话、互动、交流。目前,各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络或数据库尚不能完全开放,随着大众文化生活欣赏和质量的不断提高,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和认知不断提升,目前已经形成了“倒逼机制”,要求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要“深藏不露”,而应不断走入大众生活,成为人们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而实现文化软实力从“飞入寻常百姓家”为始作俑者和出发点,最终实现全民所有全民共享。
(九)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
两者同为文化遗产,目前,实行的是物质文化遗产由文物局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由文化行政部门直接管理。而事实上,由于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都是前人创造流传下来的智慧结晶,只不过在属性的表现形式上物质文化遗产为“静”态,如壁画、文物、遗址,而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人的表达为“动态”,如歌舞、诗、民间文学,上述无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文化,都无一不是通过情感、思想、审美方式呈现给后人的,通常对于任何一项有关文化遗产的研究均需对两者进行详细的考察和了解。因此,实行合体统一管理(各地可以设立文化遗产局或文化遗产管理局),无论从理论还是实际操作层面上恐怕更有利于对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这也应该是今后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模式。
(十)非物质文化遗产“求大同存小异”
新疆少数民族众多,尊重差异,包容不同,相互欣赏是一个原则和认知平台,最重要的路径应该是“求大同存小异”。少数民族多,文化资源千姿百态,这是具体而客观的存在,必须尊重包容这种文化的多样性。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不要过于拔高或贬低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而是要积极寻找共同性。所谓“求大同”,最大的同就是对于伟大祖国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国家意识高于一切。小的认同则是寻求有共同性的方面。例如在新疆,每年3月21日的春分,是很多少数民族共同的节日,维吾尔族称为“努肉孜节”,哈萨克族称为“纳吾肉孜节”,塔吉克族称为“肖公巴哈尔节”(即引水节和播种节)。这种小的认同还可以延伸到互相欣赏,走进彼此的心灵,有助于消除隔膜,从而发挥文化向心力凝聚力的作用。至于“存小异”,无需赘言,就是保持各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的迷人魅力。但如果过于强调和凸显这种差异性,则可能消解文化向心力出现离心力,所以,“求大同存小异”,现实而必要,长久而必要。
四、结语
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千姿百态,对其进行文化梳理,融入现代生活,是其传承、弘扬、生存的根本要诀。保护中既不能有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心态,更不能有随意强制其变化的功利行为。尊重遗产,与时俱进,顺势而为,有序倡导,这是科学态度,也唯此,非物质文化遗产才会保持其户枢不蠹流水不腐的鲜活特色。后工业文明时期,善待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在这样的文化多样性中,我们的生活也才会色彩斑斓、生动有趣。
(本文图片由黄适远提供)
——围棋
——以新疆莎车县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