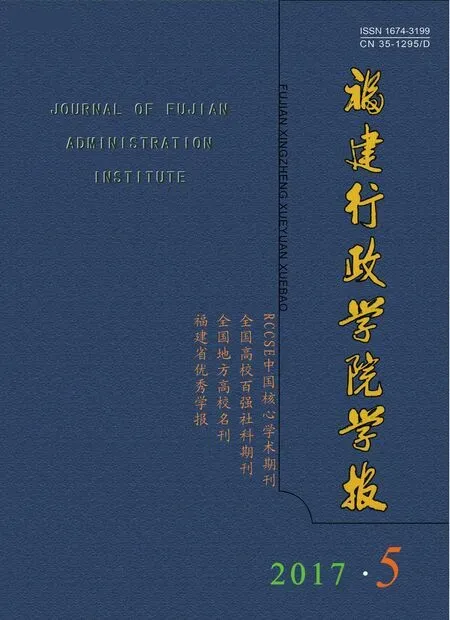社区治理中居委会话语权再造:一个理论性分析框架
单 鑫
(连云港市民政局 政治处,江苏 连云港 222006)
公共管理
社区治理中居委会话语权再造:一个理论性分析框架
单 鑫
(连云港市民政局 政治处,江苏 连云港 222006)
社区治理中的“话语权”是居委会自主性的重要体现,但是由于过度行政化、权力社会化和群体脱域化等原因,其话语权依然势弱,影响了基层社区治理能力的进一步提升。日益复杂的基层公共空间需要一个权威进行横向整合,居委会是社区整合的天然担当者,而增强居委会话语权又是居委会树立治理权威的合逻辑方式。为此,建议通过制度供给增强居委会的权利,通过秩序供给为居委会创造良好的治理环境,通过能力供给再造居委会,使其成为一个真正从事“社会工作”的组织。
社区治理;居委会;话语权
长期以来,国内政治学界、社会学界对“社区”投入了极大关注,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但是对于社区治理的主体力量——居委会这个“点”聚焦不多。尤其是对居委会在社区治理中应有的“话语权”缺乏足够的认知,鲜有这一问题的学术成果。对居委会话语权的忽视,不仅有违于社区治理的价值与内涵,而且也不利于激发改革创新活力,影响社区治理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国家的积极推动,社区建设在短时间内蓬勃兴起、成就斐然。但是,随着社区发展范式从“建设”走向“治理”,直接投入所产生的边际效应正在递减,要想可持续推进社区治理,还需要动更多的“脑筋”。为此,除了必不可少的投入之外,国家应更加着眼自治、民主等增量因素,既要实现政府的施政目标,又要推动社区治理发展;既要对社区给予必要支持,又不能干涉社区自治事务。于是,作为柔性权力的话语权也就应运而生了。通过供给话语权,以平等、尊重的态度来审视政府和社区的关系,立足于激发社区自身的治理动能,提升居委会的自主性和创造力。
本文通过对H区内多个社区居委会研究,尝试探索居委会话语权供给的理论性分析框架。H区地处沿海城市,在全国属于中等发达地区,下辖社区居委会近100个。近年来,该区不断创新基层管理服务体制机制,社区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随着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和政府职能的转变,该区的社区治理也存在着行政化倾向、“社会资本”流失和社区分化等共性问题。本文通过深入该区的多个社区,与社区干部、社会组织负责人以及居民进行深度访谈,透过一些比较典型的事例,探究居委会与政府、社会组织、居民之间话语互动的真实状况,在此基础上分析目前居委会话语权势弱的原因和增强居委会话语权的重要性,最后提出如何再造居委会话语权的一些思路,从而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
一、类型学的阐释:何谓居委会话语权
现代语言学中,“话语权”是人们为了充分表达思想、进行言语交际而获得和拥有说话机会的权利。“话语权”是语言权利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1]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学术语境中的话语权则蕴含着强制力量和支配力量。法国后结构主义哲学家福柯曾说过,在有话语的地方就有权力,权力是话语运作的、无所不在的支配力量,社会性和政治性的权力总是通过话语去运作的。话语和权力是相伴相生的,“话语的争夺实质上即权力的争夺,话语的拥有意味着对权力的实现。”[2]话语权是一种用话语和观念来影响他人的权力[3],而对方之所以被影响,抛开感性因素,必然源于某种现实权力的制衡才会就范。所以,话语权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它表面上体现为一种软权力或观念性权力,另一方面它又隐含着资源分配等物质性权力或硬权力。离开硬权力空谈话语权无异于缘木求鱼。
居委会的法定属性是基层自治组织,不是国家机关和行政机构,缺乏法定实在权力,它在现实的运作中常表现为一种话语性权力,即话语权。居委会话语权涉及多方面的权力关系,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系统,按内容和功能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见表1)。

表1 居委会话语权的类型[4]
(一)按内容,可分为政治性话语权、行政性话语权和社会性话语权
政治性话语权,即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指向社区居民和社会组织。坚持党在城乡社区的领导地位,这就必然要坚持社区党组织的核心领导地位不能动摇、战斗堡垒作用不能削弱。居委会的政治性话语权来自社区党组织,根源于国家体制。在社区干部配置中,有的是书记、主任一肩挑,有的是主任兼副书记,现实中居委会的政治性话语权常与社区党组织共同行使,其影响力是最强的。
行政性话语权,即居委会协助做好行政事务的自由裁量意思表达以及不同行动主体利益关系协调。*一般来说,利益关系调整处于政治的范畴,但是本文并没有将利益调整的内容归于政治性话语权,主要考虑到居委会所协调的利益关系大都是社区内利益纠纷,一般不涉及深层次利益格局调整,而且其利益关系调整能力远逊于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能力,所以将之归于行政性话语权更符合现实、更便于区分。198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居委会组织法》)明确规定,协助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做好与居民利益有关的公共卫生、计划生育、优抚救济、青少年教育等项工作是居民委员会的任务之一。这些内容主要指向有需要的社区居民。行政性话语权的背后其实是实质性的权力,带有为居委会“赋权”的意味,其影响力属中等,弱于政治性话语权,但强于社会性话语权。
社会性话语权,即居委会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和社会组织动员能力及其对政府、社会组织、居民的影响力。它源于居委会解决社区问题过程中积累的公信力,建立在无形而又复杂的关系网络基础上,表现为抽象的凝聚力、号召力。这一权力最能体现居委会的自治组织性质,但在现实中恰恰也是最弱的。
(二)按功能,可分为表达性话语权、协商性话语权、约束性话语权
表达性话语权,即居委会向上级政府部门陈述想法、提出意见的权力。《居委会组织法》明确规定,居民委员会应当向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反映居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现实中主要表现为通过工作汇报、座谈会等渠道反映问题,但作为事实上的下级,仅通过单纯的汇报,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问题并不取决于居委会。
协商性话语权,即居委会在社区协商中控制话语导向的能力。2015年,中央和中办、国办先后印发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社区层面普遍建立了居民、相关主体参加的协商议事会。但是,居委会和居民、其他主体是平等关系,特别是在涉及切身利益的议题时,居委会很难对协商结果施加影响。理论上讲,居委会与政府之间也应存在一定的协商关系。
约束性话语权,即居委会意思表达的变现和意愿诉求的实现。对居民来说,这种约束性仅对于那些需要办低保、帮扶的弱势群体有效,即“有求于居委会”的人。对政府来说,居委会毫无约束力可言,因为居委会的运作经费、办公用房等均来自于政府,现实中也缺乏“约束”政府的制度安排。
从对居委会话语权的分类与分析中可以看出,居委会的政治性、行政性话语权相对较强,社会性话语权最为薄弱,居委会的功能性话语权均比较弱。可以说,处于政府和居民、社会组织夹缝中的居委会是一个“弱势”群体。
二、居委会的治理:话语权何以势弱
作为制度设计,居委会深嵌于城市基层社会之中,是国家治理的微观主体。随着国家对社会治理的空间由“单位”向“社区”转换,居委会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重要性日益凸显。但与之不相称的是,其话语权依然势弱,影响了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进一步提升。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过度行政化的困境
居委会的行政化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和西方不同,我国的社区并不是一个自发形成的“生活共同体”,远未达到经典意义上的“社区”概念。我国的社区建设肇始于国家的主导,其取得的成就来自于国家的强势推动。从委托代理的视角看,居委会既有协助政府完成部分工作任务的义务,也应享受政府为其提供的工作经费、办公用房、成员的生活补贴费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居民委员会的工作经费和来源,居民委员会成员的生活补贴费的范围、标准和来源,由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人民政府规定并拨付。居民委员会的办公用房,由当地人民政府统筹解决。所以,对于居委会的行政支持具有合理性,对于居委会事实上带有的“行政性”痕迹不应受到过度指责,问题的症结在于其行政化。承认行政性并不意味纵容行政化。行政性不同于行政化,行政性是量的问题,居委会事实上的行政性并不必然改变居委会的自治属性;行政化是质的问题,侧重于居委会的功能运作、性质状态整体向行政组织转变,行政化倾向才是应该加以改正的。有学者经过深入研究发现,处于一线的社区居委会干部抱怨更多的是形式化、文牍化的迎检考核评比以及权责不匹配的管理类和执法类行政职能,而非对承担的行政职能全盘否定。[4]加之,政府职能“社区化”所带来的条线工作进社区的随意化,作为承载者的社区居委会被“行政套牢”了。[5]
A社区居委会主任曾经讲过两件事:
区某部门在力推一项业务工作进社区,发文要求我们统计相关信息,但是没有下达工作经费。我说,这不在社区工作范围,我不愿意做,而且我们就这几个人,根本忙不过来。但是,这个部门的领导跟“街道”进行了协商,“街道”打电话叫我们做,那我就没有办法了,“街道”管我们,我只能照办。
前几天老百姓给市里打电话,投诉小区一个违章建筑,城管叫居委会想办法拆掉,我们又没有执法权,也没有这方面的力量。我们向违章建筑者说了,这家违章的户主也不睬我们。规定时间拆不掉、投诉解决不了,“街道”年底对我们考核时,就要追究我们的责任。
透过这两件事,居委会的行政化倾向可见一斑。A社区主任的话语权表达,在强大的行政权力和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面前,显然缺乏效力。
(二)权力社会化的困局
权力社会化的实质是将国家权力还原为公民与社团的权利。[6]改革开放以来,底层社会结构内部发生了深刻变化,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专业服务组织、联谊性组织等各类经济社会组织相继进入社区,以事实上的行政关系为纽带的社区居委会,面临着以产权关系、利益关系以及交往需求关系等为纽带的其他组织的冲击。虽然有学者经过实证研究认为,居委会作为实质上的街道办事处下级组织仍然处于社区权力中心,相对于业委会、物业、社团等其他组织,居委会仍然具有核心影响力,即使对于高档社区来说,居委会也不一定就会被边缘化,但是随着受过传统教育的老人不再成为社区志愿者主力,居委会这种依靠积极分子构成社区管理网络的工作方式是否还会有效是值得观察的。[7]在权力社会化的格局下,当前社区成为“单一社区”“复杂社区”“流动社区”重叠交错的复合体,每个组织在实际运作中总会感到自身既定的功能是非自足的,因而在独自解决具体问题时也会感到自有资源的不足,就连社区党组织也不例外。[8]以下事例能鲜明说明这一问题。
B社区是当地一个规模较大的社区,有近万人居民,人员混杂,流动量大,出租房多,小商小贩多。由于物业管理不力,小区内失窃案件频发,环境卫生脏乱差问题严重,居民反映强烈。居委会多次与物业公司沟通,并且也建立了制度化沟通渠道:居委会召集物业公司负责人、业委会成员代表和居民代表,半个月开一次协商会,但是效果并不明显。B社区居委会主任说:“我们只能督促物业公司改进,听不听就不好说了,他们业务上归区里房管所管,也不归我们管,而且有的居民素质也不高,环境卫生确实很难管。”
有一次,B主任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他面对镜头侃侃而谈,可是不远处就有居民对他所谈的社区工作成绩很不以为然,大声喧哗,无所顾忌,出言不逊,场面十分尴尬。B主任对该居民也无可奈何。
上述事例可以看出,无论是居民,还是物业公司,对居委会都可以“不买账”。B主任的话语诉求不太容易实现。
(三)群体脱域化的困扰
所谓脱域,是指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9]社区居民关系网络也呈现脱域化特征:居民个人的社会关系从“社区”这一特定的地域情境中抽离出来,在地域范围之外建构了新的社会关系。因为社区主要成员(职业群体)的主要社会活动,是在社区之外的交易市场、机关单位、社会团体中展开的。[10]这使居民和社区之间,既无相关联的利益需求,又无社会交往的情感需求,“脱域”现象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社区参与问题。一定程度上,只有部分自身缺乏资源的特定弱势群体才会对社区邻里和居委会产生资源依赖性,从而积极参与社区事务。[11]那些数量庞大的青壮年、中产阶级,在不危及自身权利的前提下,对抽象的自治权并不感兴趣,对居委会持有或多或少的“无视”态度。一位居民的话就很有代表性:“社区老打电话叫我去开会,说搞什么活动,我去过一次后就没去,去的都是那些在家带孙子的老年人,我们不像他们那样没事做,我们还要赚钱养家,哪有时间跟他们搞活动?”
三、社区权力秩序变革中的居委会:权威何以必要
(一)日益复杂的基层公共空间需要一个权威进行横向整合
近年来,业委会、物业公司、各种社团志愿者组织等在社区内异军突起,这是基层社会呈现组织化的信号。这些组织虽然牵涉社区内全体成员利益,但是其所动员的人员有限、所聚拢的社会资本也相对缺乏。这些组织内部以及组织之间也或多或少存在不信任、内耗、排斥以及争夺活动,甚至是“共谋”“俘获”现象,这些负外部性给基层社会治理带来潜在的风险挑战。“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横向的,不存在谁是当然的指挥者,由此,这种横向关系在运作中碰到了如何协调的问题,这也是权力秩序建构所需要解决的问题。”[12]出于防范治理风险的考虑,这种组织化与碎片化、原子化多重特性叠加的城市底层社会需要有一个权威进行横向整合。如谈到广受诟病的物业管理问题时,B社区一个居民曾经抱怨说:“物业管得这么差,收费还那么贵,业主委员会那些人说要开会和他们协调,但是也没有什么用,都说业委会的那几个“头头”物业费有优惠,交的很少。”(追问:你怎么知道的?)该居民说:“这还用问嘛?百分之百少交了!而且还不是一个人,是业委会一帮人少交了。要不然他们削尖脑袋进业委会干什么?”
(二)居委会是社区整合的天然担当者
居委会是社区整合的天然担当者,有着其它社会组织无可比拟的特点优势:一是法定性,它是国家法律认可的社区内具有唯一性的权威组织,这在《居委会组织法》中得到了明确规定;二是公共性,居委会具有代表社区公共利益的资格,这与业委会某一方面权益的代表性、其他社会组织某一类群体的代表性具有质的不同,物业公司等经济组织更是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三是群众性,在底层社会多年的制度运作中,居委会积淀了较好的群众基础和内心认同感,特别是在一些弱势群体中更是一种“依靠”。以上三个方面的特质,社区内其他任何组织不可能同时具备,因此居委会是社区整合的天然担当者。目前,虽然居委会合法性有所流失,但是“相比其他新兴社区组织,居委会有明显的执掌社区的经验和不算低的社区声望。”[13]以下案例就能说明这一问题:
B社区两个舞蹈队都看中了一块跳广场舞的场地,都声称应该归“我”所用,为此曾多次发生争执。后来经过居委会与物业公司协调,清理出两块场地,其中一块还设置石墩防止停车占用,对音响免费供电,最终两个队各得其所。当然,居委会主办的社区文体活动和公益活动,舞蹈队的成员随叫随到,并且是无偿付出。
通过居委会斡旋,两个有矛盾的舞蹈队最终各得其所,促进了资源共享和社区融合,增进了社区和谐。
(三)增强居委会话语权是树立其治理权威的合逻辑方式
治理是当代民主的一种新的现实形式。[14]14-15表面上看,权威和民主是一对矛盾体,在推进治理中树立一个权威似乎不合逻辑,其实不然。合理的选择是,尽量依靠现有的民主秩序,并在建立新权力结构的过程中充分推进民主化,同时控制实际运转的体制,使其发挥合目的性的功效。[15]所以,树立居委会的权威合乎治理的内在逻辑,关键在于以何种方式做到。建议的基本思路是:采用间接、柔性的方式激发居委会的活力,尊重其平等地位,提升其治理能力,进而增强其自主性,使其以更加富有社会性的方式运转。故而,话语权就成为当仁不让的选择。
四、居委会话语权再造:供给何以可能
(一)制度供给:以权力输出赋权居委会
面对社区正式和非正式权力博弈,居委会能否在新的形势下实现其功能定位、保持其存量的治理权威?沉重的历史包袱、根深蒂固的体制困境,以及居委会成员自身的观念、领导力和执行力等都可能成为居委会参与新一轮社区权力角逐的不利因素。因此,无论是对社区的可持续发展,还是对社区各组织的良性互动而言,居委会都有必要增补新的权力和声望来源。[14]36在与政府和社会组织对话中,通过权力输出,建构新的权力体系,增强居委会的协商性话语权和约束性话语权,特别是约束性话语权。
对于物业公司、业委会等涉及公共权益的社会组织来说,要继续发挥居委会的指导、协调、监督作用,更重要的是将这些抽象的权力“变现”。目前,居委会对物业公司的“约束”仅停留在协商、督促等方面,缺乏有效的手段。为此建议在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对物业公司的诚信评价、检查考核评优、资质审核管理、业务监督等方面,设计具体的可操作性的制度,将居委会的意见明确为刚性约束机制。
对政府部门来说,要进一步落实好《居委会组织法》关于居委会“向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反映居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的规定,要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倒逼政府重视居委会的“声音”,建立“约束”政府的机制,赋予居委会一定的约束性话语权。为此建议设计一套科学的评价体系,由民政部门牵头,每年组织居委会对政府工作进行量化打分,将得分情况纳入各部门年终考核。另外,要落实好《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等文件精神,激活“协商”的制度,让社区协商以不同形式普遍开展起来。
(二)秩序供给:以治理环境护航居委会
有学者在论及话语秩序时指出,在每个社会,话语的制造是同时受一定数量程序的控制、选择、组织和重新分配的,这些程序的作用在于消除话语的力量和危险,控制其偶发事件,避开其沉重而可怕的物质性。对于居委会来说,制造其话语权“程序”的最大决定因素就是治理环境,即行政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经济环境与社区所处的市场经济的发育情况相关,不是本文所讨论的主题,本文主要讨论行政环境和社会环境。居委会话语权的背后是社区治理中不同程度存在的“乱序”现象,这表现在两方面:一就行政秩序而言,政府与社区的权责存在一定的失范和倒置,有的政府部门工作让社区承担,又不给予相应的经费,对于这些不按常理出牌的部门来说,居委会要么是“说不上话”,要么是“说了跟没说一样”,“敢怒不敢言”;二就社会秩序而言,“社区权力分化带来了权力失衡,引起了社区冲突与失序”[16],面对社区内的居民和其他主体,居委会有时“说了也没人听”。
政府在进行秩序供给时,最基本的思路就是法治化,为居委会话语权创造有序的治理环境。一方面,政府职能要法治化,政府需要居委会协助的职能事务要细化项目规定,建立社区事务清单,让多年努力的社区减负真正落地落实;另一方面,社区治理要法治化,要健全社区工作的法律制度,对社区内各社会组织的活动进行规范、监督,明确居委会的职能作用,发挥其话语主导作用。
(三)能力供给:以社会工作再造居委会
政府的主动赋权仅是外在条件,居委会的话语权是建立在自身治理能力增强的基础上的,这来源于社区居民的认同,来源于对国家治理的成功补位和基层自治功能的有效实现,“有为才有位”,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居委会话语权。形象地说,居委会不仅要和居民、社区内社会组织打成一片,还要凝聚一片、带动一片。从这一点来说,能力供给主要是增强居委会的社会性话语权。
近年来迅速发展的“社会工作”为我们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有益思路。关于社会工作,比较权威的看法是:政府和社会工作组织为舒缓和解决个体、家庭、群体、社区的组织在与社会环境互动中出现的问题与矛盾而建构的专业化、职业化的社会服务制度。[17]社会工作与社会治理具有同构性,与居委会的角色功能具有契合性,社区社会工作更是社会工作的三大方法之一。除去行政性事务以外,居委会的一切工作都是在做社会工作。建议从组织定位和具体运作两方面入手,对居委会进行社会工作的改造。
在组织定位上,要用社会工作的理念改造居委会。社会工作的“社会”导向是值得正视的现实品性,其伦理强调社会关怀和社会意识,呈现出一种社会意境。[18]这与居委会努力摆脱行政化困境、增强社会性的内在要求不谋而合。在日常工作中,居委会可以协助做好部分行政事务,但是在组织定位方面,不能成为行政组织,居委会干部的潜意识里不能以管理者的身份自居,政府机关也不能将居委会作为自己伸入基层的一条“腿”而恣意使用。在破除这一理念的基础上,居委会应该更加注重回应性,回应居民诉求和社会组织需求,谋求解决治理难题,提升社区的凝聚力。
在具体运作中,要用社会工作的方法改造居委会。社会工作堪为社会治理的操作方法,更强调问题的个体化。[19]社会工作是一种专业性的工作,是一门学科和科学,现代社会工作包括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社会行政,这是一系列以社会福利制度为依托的社会服务。居委会工作人员,应该人人都成为社会工作师,领办社工机构,承接社工项目,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知识,在社会救助、纠纷调解、婚姻家庭、精神卫生、社区矫正等方面,成为解决具体问题的专家能手,在社区治理中产生带动和示范效应。这是居委会回归群众组织属性的题中之意。
[1] 冯广艺.论话语权[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54.
[2] 李平.试论中国管理研究的话语权问题[J].管理学报,2010(3):321.
[3] 高奇琦.制度性话语权与指数评估学[J].探索,2016(1):145.
[4] 张雪霖,王德福.社区居委会去行政化改革的悖论及其原因探析[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6(1):35.
[5] 孔娜娜.“共同体”到“联合体”:社区居委会面临的组织化风险与功能转型[J].社会主义研究,2013(3):106.
[6] 陈醇,李爱平.论权力社会化[J].甘肃社会科学,2014(6):166.
[7] 郭圣莉.国家的社区权力结构:基于案例的比较分析[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3(6):90-91.
[8] 李友梅.城市基层社会的深层次权力秩序[J].江苏社会科学,2003(6):64.
[9]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18-19.
[10] 兰亚春.居民关系网络脱域与城市社区共同体培育[D].长春:吉林大学,2012:28
[11] 张雪霖,王德福.社区居委会去行政化改革的悖论及其原因探析[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6(1):36.
[12] 李友梅.城市基层社会的深层次权力秩序[J].江苏社会科学,2003(6):63.
[13] 闵学勤.转型时期居委会的社区权力及声望研究[J].社会,2009(6):36.
[14] 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15] 王沪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要求:新权力结构[J].社会科学,1993(2):6.
[16] 张广利,徐丙奎.权力、治理与秩序:一个可能的社区分析框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10):209.
[17] 宫蒲光.社会工作: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制度安排[J].中国民政,2014(7):9-11.
[18] 顾东辉.治理、社会治理与社会工作[J].中国社会工作.2015(19):32-33.
[19] 焦若水.社区社会工作本土化与社区综合发展模式探索[J].探索,2014(4):140.
Abstract:“The discourse right”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embodiment of the autonomy of the neighbourhood committee. However, due to the excessive administration, the socialization of power and the decentralization of the group, the discourse power of the neighborhood committee is still weak, which affects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of the basic social governance ability. The increasingly complicated grassroots public space needs an authority to make horizontal integration. The neighborhood committee is the natural undertaker of the community integration,and enhancing the discourse right of the neighborhood committee is the logical way for the neighborhood committees to set up governance authority. Therefore, it’s suggested to enhance the neighborhood right through the supply system, to create a good governance environment for neighborhood committee through order supply, to rebuild the neighborhood committee through the supply of capacity to make it an organization that really engages in social work.
Keywords:community governance; neighbourhood committee;discourse right
[责任编辑:林丽芳]
ReconstructionofNeighborhoodCommittee’sDiscourseRightinCommunityGovernance:TheoreticalAnalysisFramework
SHAN Xin
(Political Section, Lianyungang Bureau of Civil Affairs, Lianyungang 222006, Jiangsu, China)
D669.3
A
1674-3199(2017)05-0001-08
2017-08-12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09&ZD063);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3CZZ038)
单 鑫(1983—),男,江苏连云港人,连云港市民政局政治处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