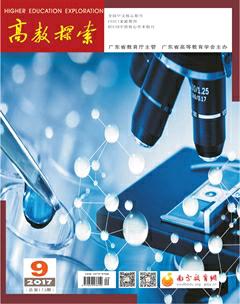民国时期大学女教师群体形成及其特征
项建英
摘要:民国时期大学女教师群体形成是由主客观因素共同促成的。教会女子大学的示范、中国自办女子高等教育发展、大学男女同校和女子留学教育等客观因素为女性成为大学教师提供了可能;而女性炽热的求知欲望、刚强不屈的个性、独立的自主意识和融汇中西的文化素养和能力等主观因素使可能变成了现实。这一知识精英群体形成后,在人员结构、地缘结构、专业结构和职称职务结构等方面逐渐呈现出鲜明特征。
关键词:民国时期;大学女教师;群体;特征
在封建社会,女子被禁锢在闺阁,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女性连受教育的基本权利都没有,更别说教书育人了。19世纪末,在大学中任教的女性基本是外籍教师。到20世纪初期,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长期以来形成的男尊女卑的社会心理开始出现裂痕,具有留学背景的中国籍大学女教师开始零星出现。而到1931年时,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有教员共7234人,女教员已达407人,占全体教员的5.6%。职员4234人,女职员没统计,若按5.6%的比率折算,女职员为237人。这样,女教员和女职员总数已达约644人。[1]到了1947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有职员13363人,女职员3060 人,女职员占职员总数的22.9%。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有教员20133人,女教员没有统计,若也按职员的比率折算,则女教员人数约为4610人。这样,高校女职员和女教员共计人数约7670人。[2]这说明大学女教师群体已然形成。大学女教师温柔而坚强,执着而奋进,她们渴望着自己的渴望,追求着自己的追求。这一群体形成后,迅速成为一个倍受关注的新知识精英群体,并呈现出鲜明特征。
一、民国时期大学女教师群体的形成
近代中国大学刚成立之时,坐在教室里读书的是男性,从事学术职业的也都是男性,女性是学術职业的“缺席者”。随着外部客观环境的变化和女性本人的主观诉求,大学女教师群体才逐渐形成。
(一)民国时期大学女教师群体形成的外部因素
自晚清以来,随着西学东渐,中国社会加速了新陈代谢的进程。“女子无才便是德”、“男主外女主内”等封建陈腐观念受到很大抨击,女子高等教育快速崛起,外部大环境开始有利于大学女教师群体的形成。
首先,教会女子大学女教师群体提供了示范。早在中国大学女教师出现之前,教会大学已出现了女教师,尤其在教会女子大学,从校长到普通教职员工,基本上都是女教师。最早建立的是1905年创办的华北协和女子大学,校长是麦美德女士。1920年并入燕京大学,称燕京女大,女校师资队伍也迅速扩大,当时任教的主要人员是“美国公理会的麦美德女士、费宾闺臣夫人(Mrs.Murray S.Frame)、斐恩(Jessie Payne)女士、拉拇(Maryette Lum)女士、包贵思(Grace Boynton)女士和莱恩(Anna Lane)女士;长老会的霍尔夫人(Mrs.Hall);美以美会的苏路得(Ruth Stahl)女士”[3]。华南女子大学于1907年创立,第一任校长是美国传教士程吕底亚女士(Trimble Lydia)。其师资也以外籍女传教士为主体,如华惠德(Wallace)、明茂利(Mary Mann)、康师姑(Elsie G.Clark)、和爱德(Katherine Willis)、罗黎晞(Roxy Lefforge)等。1915年,金陵女子大学于1915年创办,校长由德本康夫人(Thurston.Lawrence)担任,德本康夫人的治校理念是尽量聘用女教师从事女子教育。在金陵女大开学之初,教师全部为女性,其中包括美籍女教师4人,华籍女教师2人。此外,北京协和女子医校、广州夏葛医科女子大学等教会女子大学都以女教师为主体。教会女子大学大量女教师的出现,为中国广大知识女性提供了新的职业榜样,为中国大学女教师队伍的形成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其次,中国自办女子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职业舞台。随着教会女子大学的发展,国人自办的女子高等教育亦渐萌生。1919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得以创立,随之女教师已然成为迫切需要。据1924年统计,当时全校教职员124人中,已有女性教师10人,虽然女教师人数不多,但已初成规模,杨荫瑜、袁昌英、吴贻芳等人都曾任教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紧接着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也成立,1934年时已有19名女性教职员工,具体名单:孙家玉、杜隆元、曹棣生、柴岫茞、董家政、张玉华、冯启亚、朱高清兰、步毓芝、孙家玉、程之淑、王非曼、杜隆元、余淑琴、严琼圃、梁秀萱、贺升息、谈新铭、夏志珍。而后女子高等教育专门机构在各地陆续出现,如首都女子法政学院、成都女子法政学院、国立四川女子师范学院、重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等。在这些女子高等教育机构中,虽然还是以男教师为主,但独立高等女子教育已经呼唤女教师的出现,具有丰富知识和管理经验的女教师已成为急需,这给女教师登上大学讲坛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职业舞台。
第三,大学男女同校拓宽了就职空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男女平等的思想不断深入民心,人们对当时大学的现状极为不满,男女大学同校已成为时代呼声。国立大学中最早开女禁的是北京大学。同年夏,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始正式招收女生。这样,北京大学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为国立大学中最早实现男女同校的学校。1922年,《壬戌学制》颁布,女学不再另设系统,女子和男子一样接受同等教育,这是我国第一个不分性别的单轨学制,也是从法律上认可了大学开女禁。此后,各大学纷纷招收女生。大学校园女生人数不断增加,但“男女有别”的封建文化传统依然在社会中有着强大的根基。因此,为吸引生源,并让女学生家长放心,聘请大学女教师已成为急需,正如当年胡适所说:“大学当延聘有学问的女教授,不论是中国女子还是外国女子。”[4]这样,大学女教师不仅任教于教会大学、女子高等师范,国立大学的教职也开始向女性开放。1931年时,国立大学女教师已达122人,其中北平大学有53人,中央大学有16人,中山大学有5人,北京大学有8人,北平师范大学有15人,浙江大学有3人,清华大学有2人,暨南大学有7人,四川大学有8人,武汉大学有3人,山东大学有2人。[5]因此,大学男女同校极大地拓宽了大学女教师群体就职发展空间,女教师队伍逐渐壮大。endprint
第四,女子留学教育提供了一种可能。当时大学需要女教师,但为规范大学教师的资格,国民政府对大学教师制订了一系列的规格和要求。如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专门规定:大学教员分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副教授要求:“外国大学研究院研究若干年,得有博士学位,而有相当成绩者;讲师满一年以上之教务,而有特别成绩者;于国学上有特殊之贡献者。”而教授要求:“副教授完满二年以上之教务,而有特别成绩者。”[6]说明国民政府非常看重留学经历,留学成为担任大学教师的一项主要依据。而这些规定和要求,为留学归国女性担任大学教师提供了一种可能。因此,留学归国女性担任大学女教师的人数越来越多,如陈衡哲1920年留美回国后任教北京大学历史系;司徒月兰1922年留美回国先后任教南开大学、燕京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等;谢婉莹1926年留美回国后相继任教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劳君展1927年留法回国后任教武汉大学数学系;林徽因1928年留美后任教东北大学建筑系。
(二)民国时期大学女教师群体形成的主观因素
民国时期,女性要突破传统教育的束缚,真正从“社会需要大学女教师”到“我要成为大学女教师”,这个过程中还需女性自己本人的努力。而审查民国时期这些女性,她们在走上大学讲坛前,都具有强烈的主观诉求。
第一,炽热的求知欲望。民国初期,社会的风气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女性可以走出家门接受学校教育。但当时除一些比较开明的家长,顺应时代潮流,除了送女孩子上学外,整体社会还是非常保守,“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还是根深蒂固,一般家庭对女孩子读书并不重视,认为培养女孩子读书等于为他人投资,因此,若想接受学校教育,女性本人必须要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否则即使生在富裕的家庭,也未必能为自己争取到读书的机会和权利。如苏雪林为能上学,曾“哭泣、吵闹,总无结果”,最后她“走到附近一个地点,名为松川者,涧水渟滀深约丈许,我想不自由,毋宁死,不如跳下去求解脱”[7]。当时苏雪林以死相要挟,母亲真怕女儿会做出什么事,再三向祖母求情,祖母才勉强同意。这些大学女教师在整体不利的大环境下,想要和男孩子一样赢得读书的机会和权利,非常不容易,她们从小就有一股强烈求知欲望,特别珍惜读书的机会,这为日后成为大学女教师打下了知识底色。
第二,刚强不屈的个性。审察民国时期大学女教师,她们从小就生性要强,没有传统女子的低眉顺从、忍辱负重的性格,而是刚强不屈,坚定执着,不断地丰满自己的羽翼,努力做最好的自己。正是这种坚强的个性,使她们在外部环境不利的条件下,依然能与男教师一竞高低,自由地驰骋于大学讲台,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如吴贻芳,父亲在官场被人陷害,背上亏空公款的罪名,跳江轻生;哥哥不小心弄丢了筹集的学费,竟纵身跳入黄浦江消失在茫茫大海中;母亲因接受不了儿子的离去上吊自缢,姐姐在母亲出殡前一晚也随母亲而去。身边至亲一个接一个离她而去,只留下七旬祖母和九岁妹妹。面对冷酷的现实,吴贻芳并没有就此倒下,历经磨难的她,暗下决定一定要支撑起这个破碎的家,照顾好祖母和妹妹,成为这个家的顶梁柱,在性格上变得更加沉寂,更加坚韧。冯沅君小时候跟着教书先生学习,“沅君写大字,不知道先生说一句什么批评的话,沅君生气了,第二天就不去上学。母亲生气地说,不上学,就要把她送到上房后边的一间黑屋里。她宁愿上小黑屋,也不去上学。母亲劝说解释,亲自把她送到书房门口,先生也出来接她,她无论如何也不进门槛”。[8]这是哥哥冯友兰讲述的一段幼年轶事,但冯沅君倔强的个性可出一斑。从小就表现出争强好胜的个性和不屈不挠的韧劲,这些为她们日后成为大学教师打下了良好的个性基础。
第三,独立的自主意识。民国时期大学女教师从小就有强烈的自主意识。陈衡哲在自己的人生中,一直在为自己“造命”。从十三岁起,她就一个人南北奔走。曾有一次,从成都到上海的船上,她一路独行,并不感到寂寞,反而感到独处具有相当诱惑力。甚至考上了清华大学留美奖学金出国时,陈衡哲也不要家人为她送别,她说:“我已经习惯于各种各样的独处。”[9]林徽因从小就知道父亲不喜欢母亲,对她母亲非常冷淡。她父亲善诗文、工书法,是一个儒雅风流的新派人物,而她母亲则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旧式女子。所以“她爱父亲,却恨他对自己母亲的无情;她爱自己的母亲,却又恨她不争气;她以长姊真挚的感情,爱着几个异母的弟妹,然而那个半封建家庭中扭曲的人际关系却在精神上深深地伤害过她。可能是由于这一切,她后来的一生中很少表现出三从四德式的温顺,却不断地追求人格上的独立与自由。”[10]她跟随父亲游历欧洲时,就立志学建筑,做一名优秀的建筑师。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时,建筑系只收男生,不收女生,因为建筑系的学生常常要彻夜赶图,女生不是很方便,虽然林徽因在美术系注册上学,但第二年春季班开始,林徽因就成了建筑系设计教授的助理,过了一个学期,已成为建筑设计课的辅导员。虽然我们不知道林徽因是怎样成为建筑系设计教授的助理和建筑设计课的辅导员的,但有一点非常明确,她有她自己的执着追求,她不想步她母亲的后尘,她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想学什么,她想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正是这种独立的自主意识,使得她们敢于同传统守旧势力作斗争,实现人生的真正独立。也正是这种独立自主意识,使得她们非常自信,为她们以后走上大学讲台奠定了基础。
第四,融汇中西的文化素养。民国女性之所以能成为大学女教师,是因为她们敢闯敢拼,具有融汇中西的文化素养和能力。如武汉大学袁昌英教授,小时候就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上海中西女塾毕业后又自费去英国爱丁保大学深造,毕业后获英国文学硕士学位。之后,她又只身赴法,在巴黎大学攻读法国文学和近代欧美戏剧,获硕士学位。这种融汇中西的文化积淀,使得“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西方文化的接受時,袁昌英也并非盲目照搬,而是以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和自身的好恶,有选择地吸纳与接受,形成了她兼具知识分子的雍容气度、传统女性的兰心蕙质和西方人文精神的独立意识,表现出女作家中少见的才、学、识、德的水乳交融,这些正是袁昌英散发出的独特魅力所在”[11]。民国时期大学女教师大多兼融中西,视野开阔,为她们走上大学讲台打下了扎实的知识基础。endprint
二、民国时期大学女教师的基本特征
作为知识精英,这一群体一经形成就引人注目,因为每个女教师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和风采,但纵观大学女教师群体,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她们中有许多共同的基本特征。
(一)大学女教师的人员结构
民国时期大学女教师队伍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外籍女教师、留学归国的学生和本国自己培养的学生,这三部分人员共同组成了民国时期大学女教师队伍。不同时代,女教师队伍的组成结构不一样。
首先,外籍女教师是我国大学女教师队伍的有机组成部分。外籍女教师主要分布在教会女子大学。如华南女子大学的外籍女教师主要有华惠德、和爱德、琴陶世、刘玛利、邓惠贞、巴美德、康慎德、施曼姿等;金陵女子大学的外籍女教师有戴蔼士、克馥兰、余朴、穆思曼、苏爱兰、郭星丽、芮特夫人、海怡迪、师以法、黎富思、蔡路得、华群等。此外,一些外籍女教师还在其他综合性大学工作,如柯安喜女士在燕京大学英文系任教、赛珍珠则在金陵大学外语系任教、法国的季亚德夫人在东南大学任教等等。
其次,留学归国成员是女教师队伍的主体。清末主要留学日本,留日女性学成归国后,她们中很多从事大学教育工作,如担任校长的有杨荫榆、陶慰孙、钱青、程国敭等。到民国,大批留美女性学成归国,如陈衡哲、余矩英、俞庆棠、朱兰贞、张汇兰、陈淑圭、吴贻芳、王世静、冰心、方令孺、顾静徽、张蕙生、雷洁琼、林徽因等等。此外,还有一批留学加拿大、英、法、德、前苏联等国的留学女生也纷纷回国担任大学教职,如袁昌英、苏雪林、劳君展、魏璧、冯沅君等等。这些留学女生,经过几年的苦学,学有所长,逐渐成为女教师队伍的主力军。
第三,中国高校自己培养的学生也是女教师队伍的重要来源。各个高校自己培养的学生,不断地充实大学女教师队伍,如冯沅君在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深造之后,曾在燕京大学做执教;吴贻芳在金陵女大毕业之后,曾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执教;洗玉清岭南大学毕业后在岭南大学任教。到民国后期,随着女性接受高等教育人数的增多,这些女学生各方面表现突出,毕业后留在学校担任助教的人数越来越多。
大学女教师人员构成在不断流变。早期外籍女教师占有很大比率,但随着教会大学立案,外籍女教师所占比率逐渐减少。而与此同时,随着留学归国女生的增加,中国留学生逐渐成为大学女教师队伍的重要生力军。到民国后期,随着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高校自己培养的学生人数也不断增加,成为女教师队伍的重要来源。
(二)大学女教师的地缘结构
早在清末民初,中国还没有自己的女子高等教育,女子高等教育主要集中在教会女子大学,师资也以外籍女性为主。随着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中国籍女教师逐渐增多,而这些女教师群体的地缘结构有着显著特征,我们发现她们大多来自江、浙、闽、粤等东南沿海一带。
女教师主要集中在女子高等学校。如20年代的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当时女教师主要有杨荫榆(江苏无锡)、吴贻芳(江苏泰兴)、袁昌英(湖南醴陵)、廖翠凤(福建厦门)、刘吴卓生(浙江温州)等[12],她们主要来自江苏、浙江、福建东南沿海一带。教会女子大学也是女教师聚集之地,1931年华南女大教员履历表中,中国籍女教师8人全部来自福建。1936年金陵女子大学中国籍教师,来自浙江的有6人,江苏5人,广东4人,上海2人,福建2人,湖北3人,山东2人,北平1人,广西1人,湖南1人,共27人。其中,浙江、江苏、广东、上海、福建、广西等东南沿海一带,就占了75%。[13]即使在综合性大学,如1942年国立西南联大女教师名册,共25个女教师,其中来自江苏的有8人,浙江、福建、山东、湖南各3人,湖北、安徽、山西、四川、湖南各1人,江苏、浙江、福建三省占了56%。[14]
从上我们可以基本断定,女教师主要来自江苏、浙江、广东、福建等东南沿海一带,地域色彩浓厚。这一方面由于宋以后,江浙一带一直是中国文化重镇,经几百年的积淀,文化底蕴深厚,成为人才汇聚之地;另一方面,鸦片战争后,东南沿海一带最早受到欧风美雨的浸润,思想相对开放,较早吸纳了女子教育和男女平等思想,这也是江、浙、闽、粤等东南沿海一带女教师较多的原因。
(三)大学女教师的专业结构
近代大学学科专业的性别隔离现象非常显著,女教师大多聚集在人文社会学科。但大学女教师的专业结构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從最初的人文社科逐渐走向多样化。
最初,女性教师在大学的学科专业以文学、医科、教育、音乐居多,如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中的女教师,杨荫榆所学专业为教育,袁昌英所学外国文学,廖翠凤、张祥麟夫人、刘吴卓生3人都教英文,5位女教师所学全部是文科。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尤其到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规定大学及专门教育应遵守:“注重实用科学,充实科学内容,养成专门知识技能。”[15]同时颁布的《大学组织法》和《大学规程》都强调实科教育。在国民政府的倡导下,就读实科的大学女生越来越多,这些女生毕业后很多走上教师岗位,她们的专业也开始多样化,出现了航空工程、地质、经济学、土木工程等专业。如1942年,西南联合大女教师中李敏华所学为专业航空工程,汪静所学专业为土木工程,池际尚所学专业为地质学,陈丽妫和姚哲明学习的是电机工程等等。这些女性不畏艰辛,力图突破传统思维禁区,勇敢地闯入男性的知识和职业领域,开始自主地追求平等的发展机会。
当然,大学女教师专业选择虽然走向多样化,但整体还是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因为人文社会学科相对而言偏向感性、具体、情感等,学科特征正好与女性的母爱、善感多情等特质比较符合;而理工科类以理性、抽象、概括等为主要特征。随着科学的发展,理工科知识的重要性越来越突显,在学术系统中逐渐占据权威地位,而人文社科类地位日趋低下。在男权社会中,女性选择人文社科作为栖身之地也成为必然。
(四)大学女教师职称职务结构endprint
近代女教师跻身大学讲坛已属不易,要与男教师一竞职称职务更是难上加难。整体来说,相较于男教师的职称职务,女教师的职称职务是偏低的,处于金字塔图形的中下层。
在职称上,女性在大学的职称多处于中低层次。从1934年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教师一览表中可知,20名教授,其中男性教授18名,女性只有2名,女性占教授总数的10%;男性讲师22名,占男教师总数的55%,而女性讲师10名,占女教师总数的83%,女性教师高职称比例大大低于男性教师。再如40年代国立综合大学西南联大共有教授163名,教师总数为392名,教授占了教师总数的41.6%,女教授1名,占教授总数的0.6%;副教授共14名,占教师总数的3.6%,女教师副教授1名,占副教授总数的7.1%;专任讲师25人,女性1人,占4%;教员共29名,女教员2名,占6.9%;助教、半助教共144名,女助教和半时助教20人,占13.9%。[16]另从民国教育部1941-1942年编制的2册《专科以上学校教员名册》来看,在全国范围内上交资格证明材料并审核通过授予聘用证书的专科以上学校教师共4544人,分别为教授1829人、副教授656人、讲师1079人、助教980人。而其中女教授54人,占教授比率的3.0%;女性副教授38人,占副教授比率的5.8%;女性讲师80人,占讲师比率的7.4%;女性助教180人,占助教比率的18.4%。①可知,女性教师本来在大学就不多,而且称职越高,女性占的比例越小,这点在综合性大学更是突出。
在职位上,女性担任校长的人数很少。教会女子大学中曾有吴贻芳担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王世静担任华南女子大学大学校长。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教会大学的立案规定,教会大学必须由中国人担任校长或院长。当然,吴贻芳和王世静本人的才干也不容忽视。在国立的一般大学,女性担任校长职务的非常少,如杨荫榆曾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担任校长,俞庆棠曾担任江苏教育学院的院长,劳君展和张邦珍曾在国立四川女子师范学院担任院长等,但时间都不是很长。
大学女教师职称职务偏低与民国时期女性地位低下有必然联系。此外,我国女子高等教育起步晚,有机会获得大学教师职位的女性本来就不多,而一部分获得职位的女性,由于受到婚姻,家庭等各方面因素影响,很难全身心投入事业,从而影响职称职位的评定和提升。
综而言之,在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下,民国时期大学女教师群体形成。随着这一群体的产生和发展,在人员结构、地缘结构、专业结构和职称职务结构等方面逐渐呈现出鲜明特征。而透过大学女教师群体的形成与特征分析,我们也触摸到这一群体内心的挣扎和艰辛,但她们仍毅然决然地立于潮头,开风气之先,不仅演绎着自己的精彩人生,更为近代中国女性写下了亮丽一笔,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女子教育近代化进程。
注释:
①数据是根据1942年和1944年教育部编的《专科以上学校教员名册》(共2册)统计而成,名册中统计的教师人数和教师职称并不完整,审核没通过的教师没有记录,也不排除部分教师未上交审核材料等特殊情况。
参考文献:
[1]民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编.二十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Z].教育部自刊,1933:5-18.
[2]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Z].北京:商务印书馆,1948:1404-1405.
[3][美]艾德敷.燕京大学[M].刘天路,译.珠海:珠海出版社,2005:65.
[4]胡适.大学开女禁的问题[N].北京大学日刊,1919-10-22(3).
[5]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编.二十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Z].上海:商务出版社,1933:50-51.
[6][15]宋恩荣,章咸.中国民国教育法规选编[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636-637,36.
[7]苏雪林.苏雪林自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128.
[8]严蓉仙.冯沅君传[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1-2.
[9]陈衡哲.陈衡哲早年自传[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174.
[10]梁从诫编选.新火四代(下)[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170.
[11]刘馨.袁昌英对中西文化的选择与接受[J].安顺学院学报,2009(8):23-25.
[12]周一川.近代中國女性日本留学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287.
[13]朱峰.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M].福州:福建出版社,1992:260-263.
[14][16]王文俊主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四)(教职员卷)[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118-129.
(责任编辑钟嘉仪)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