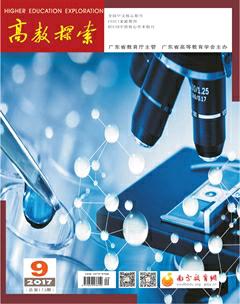知识生产模式转型与美国公立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
王聪
摘要:知识生产模式转型与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存在相互作用的关联机制。表层治理权力分配的变化内隐了大学知识生产由学科知识逻辑(知识生产模式Ⅰ)向应用知识逻辑(知识生产模式Ⅱ)的转变。伯克利加州大学是加州地区第一所开展跨学科研究并最先形成共同治理模式的公立研究型大学,基于知识权力格局的分析视角,其内部治理结构由知识生产模式Ⅰ重视学术权力的共同治理向知识生产模式Ⅱ强调技术理性的公司化治理模式发展。但由于大学的本质属性和不同权力间的博弈,两种治理模式在学术副校长和学术评议会的调节与秉持中努力走向共生、理解、信任合作的新格局。
关键词:知识生产模式;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伯克利加州大学
高深知识是高等教育的逻辑起点,学术性是大学存在的合法性基础,知识逻辑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指导大学运作的内部逻辑。随着社会的转型和知识经济的到来,知识逻辑与应用逻辑紧密相连,知识生产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影响了大学内部权力的重组,改变着大学内部的治理结构。伯克利加州大学是美国加州大学系统中的一所公立研究型大学,无论是在知识转型的应用中还是在共同治理的建构中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世界一流大学。知识生产与治理结构之间的关联机制在我们反观二十世纪以来伯克利加州大学的发展脉络中就可从中洞悉。
一、知识生产模式与大学治理结构的框架解析
(一)知识——权力——大学治理
知识的探索、发展、分析、阐述、传承和传播都是高等教育活动的主题。[1]知识与大学治理之间的作用机制是通过权力产生的。知识与权力的传统观点认为两者存在外在甚至对立关联,而随着新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在科学哲学中的发展,传统观点显然有失偏颇。权力对科学知识的影响不仅限于外部性,它会渗入到科学研究活动中,并且成为科学知识的起源,即知识就是权力,权力就是知识。[2]从微观角度看,抗衡性不是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属性,权力也并非通过信念遏制性的影响知识,正如米歇尔·福柯在《权力的眼睛》中所言,权力的实质要比20世纪60年代前的这些观点复杂得多。福柯运用政治解剖学的方法论述知识与权力一体化的连带关系。其后,霍斯金超越了福柯的知识与权力关系学说,明确指出是教育实践即书写、考试和评分构成了连接知识与权力的第三方,并且知识通过教育实践的规训不断创造新的权力形态以为自身增加价值[3],从而把知识与权力的关系集中于学校建制的话语体系中。新教育社会学的代表者麦克·扬将知识视为社会的建构,知识分层与权力分配和社会结构相关,并通过正规教育机构而将以制度化。[4]同样,罗蒂这位新实用主义哲学主要代表者终结了传统的个体知识论和形而上学知识观,从社会知识论的角度论述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指出知识和真理与历史语境和权力斗争紧密相关,知识不可能免于权力的干预。[5]可见知识与权力紧密联结,相互创生,权力规范知识中的话语体系,知识重构组织中的权力结构。从中世纪大学追求闲逸好奇的学者行会到柏林大学处于政治权威下从事纯粹科学研究的教授治校,再到美国大学实用主义驱使下大学服务社会功能的凸显,几个世纪的渤澥桑田中蕴含着知识与权力的互动与变革。
知识——权力构成了大学治理的根基。知识通过其权力属性在大学各个部门中发挥作用,形成了不同知识生产模式下相应的大学治理结构,其实质是不同的权力配置格局。那么权力是如何作用于大学之中又是怎样影响大学治理的呢?福柯认为“规训”是权力发生作用的轨道。规训包括一系列手段、技术、程序、应用层次、目标,它是一种权力“物理学”或权力“解剖学”,一种技术学。[6]规训是通过监视、纪律、规范化训练来使权力发生作用。而大学治理正是在治理制度中运用权力来协调各利益相关者相互之间的关系,因此表层的规范化活动内隐了不同利益主体权力力量对比的变化,这也是大学治理进行权力分配和重组的过程。知识——权力——大学治理之间的作用关系是双向的,大学之所以能够由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轴心,主要由于判断知识是否有价值的标准除遵循知识逻辑外,还在于各种政治、经济及文化资本的诉求。这些诉求隐含的是权力的作用机制,而权力身后则是占有资源的差异,大学资源依赖的属性使这些资源作用于大学内部治理之中,从而通过权力又影响着知识的选择、生产、传播方式。
·比较教育·知识生产模式转型与美国公立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
(二)知识生产模式转型——大学治理结构变革
20世纪末迈克尔·吉本斯等人提出了知识生产由模式Ⅰ向模式Ⅱ转型的理论。知识生产模式Ⅰ以学科知识为特征,以学术共同体的学术兴趣为主导,以同行评议为评价方式。知识生产模式Ⅱ则是问题为导向的在应用情境中进行的,以跨学科、异质性、社会问责的广泛性和质量控制的多维度为特征的新型知识生产模式。这种知识生产模式使学科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更多考虑的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求,而且通常是为了解决某一特定问题而迅速组成跨学科的研究团队,成果的考核也更倾向评议体系社会构成的广泛性。大学是高深知识生产和传播的主要场所,知识生产除遵循其内在的知识逻辑外,如今更多的映射出政治、经济等相关权力主体的利益驱动,从而出现了模式Ⅰ向模式Ⅱ的转变,并且这种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与大学治理结构的变革形成了互动关系。
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推动着大学治理结构的变革。在知识生产模式已然发生转型之时,大学的各权力主体如果被动甚至拒绝改变其治理结构,则很容易导致大学地位的衰落。大学为规避这种生存危机,保卫对知识的统治权,会在一定程度上调整治理结构以迎合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17世纪知识生产模式由思辨式向观察和实验式转变,但欧洲近代早期大学深受经院哲学的影响,对自然科学的发展反应迟缓,甚至出现政权和教会势力阻碍自然科学发展的声音。然而这为大学之外科学院的发展提供了空间,新的知识生产方式转移到独立于大学之外的其他科研院所。学术性是大学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大学的发展开始滞后于知识的更新与进步,大学知识中心地位因此受到了动摇。知识与社会需求的相连直接影响大学的资源配置方式。作为外部资源依赖型组织,寻求资源和经费支持是大學得以更好生存的永恒主题。由单一学科模式向应用情境的跨学科模式发展是当今高等教育学科组织化的发展趋势。当知识生产方式由模式Ⅰ转变为模式Ⅱ会使资源配置由官僚控制模式向市场主导模式过渡,外部力量进入到大学决策层之中,从而推动大学内部权力的重组和治理结构的变革。endprint
同时,大学治理结构的变革为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提供了空间和可能。产学研合作、跨学科组织的兴起和大学科技园的组建都促进了知识生产模式Ⅱ的发展。这些社会弥散性的知识生产组织的产生一方面归因于社会经济的需求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外部力量开始在大学治理中逐渐发挥作用。政府的宏观调控、市场的适度调节、社会多主体的广泛参与,使得大学治理走向多元主体共治,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推动了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机构的出现,从而推动着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
二、知识生产模式Ⅰ下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
知识生产成为大学职能之一要追溯到德国洪堡时期,洪堡第一次把科学研究纳入大学工作当中,通過科研追求纯粹的知识。那时的知识生产是依托于学院组织并具有学科性的知识生产模式Ⅰ,由于其学科分化细、专业化程度高,外行人员难以参与,所以在知识生产模式Ⅰ下的大学内部治理主要体现的是学术权力和学者自治模式。
(一)教师权力提升期
美国大学在建立及发展过程中吸收了英国大学的治理模式和德国大学的学术自由传统,构建了法人——董事会制度。董事会在大学内部拥有绝对权威,教师参与大学治理的权力是随着教师在学科知识领域中地位和作用的提升而逐渐加强的,可以说在二十世纪中后期之前是教师权力由无到有、由弱到强的抗争史。
19世纪中期,美国高校教师仅作为传播一般知识和塑造德行的主体,以通才教师的职业特征存在,不具有某一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科研和知识生产未纳入其工作职责中,这也使得他们对自身职业的社会地位和自治权都没有过多要求。南北战争后,工业化和城市化成为社会的主旋律,新知识和人才专业化是当时社会对大学的诉求,使教师地位大幅提升,从知识的传递者过渡为新知识的生产传播者。创办于1868年的伯克利加州大学由校外人士构成的加州大学董事会掌管,在董事会下设校长和学术评议会,学术评议会的权力有限,大部分学术事务的决策权仍掌握在董事会手中。尽管州立大学在建校之初受功利主义哲学的影响,但当时仅限于大学摆脱宗教束缚和满足高等教育民主化的需求。为国家服务是西进运动和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推动所赋予州立大学的基调。[7]所以,19世纪末期伯克利加州大学的知识生产仍主要遵循学科逻辑,教师基于在专业知识上的垄断权,开始关注公共决策、大学治理和学术自由,教师对学术治理权的争夺与董事会的强权控制使得大学内部治理格局越发紧张。
伯克利加州大学教师在大学治理中地位的提升始于1899年校长惠勒时期,而真正走上大学治理舞台始于1919年至1920年的“教工革命”。在惠勒任职期间董事会让渡了部分权力,校长在学术事务上享有绝对权力。同时惠勒意识到教师有责任参与教育政策的制定,教师在大学管理中的作用开始显现。但由于教师参与管理的权限有限并且其参管意愿越发强烈,惠勒对于教师的管理方式过于专断压制,最终于1919年爆发了“教工革命”。此次革命使学术评议会获得了在大学治理方面的部分实权,形成了共同治理的雏形。正如伯克利高等教育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简称CSHE)的高级研究员约翰·奥伯利·道格拉斯所言,“共同治理的最大意义不是处理好教师与董事会的关系,而是协调好教师与校长及其行政机构的关系”。[8]尽管之后的伯克利加州大学校长在确保自身权威的前提下广泛征询教师意见,但学术评议会曾一度处于校长的控制之下。这一时期不仅是伯克利加州大学的教师与校长及行政机构关系紧张,在其他公立大学也发生了冲突事件,犹他大学的行政部门在无正当理由和同行评议的条件下解雇了两名长期任职的副教授,这一事件引发了17名教师集体辞职,以抗议行政部门的不当行为。[9]随后20世纪中期的“忠诚宣誓”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学术评议会参与大学共同治理产生冲击,但教师的权力依旧在不同利益团体的博弈中缓慢曲折的增长。
(二)共同治理框架形成期
克拉克·克尔于20世纪50年代出任伯克利分校第一任校长。在克尔任职期间伯克利加州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不断趋于完善,构建了大学共同治理的基本组织框架。始终拥护学术自由的克尔由于多年受加州大学总校校长罗伯特·斯普劳尔的强权束缚,使他更加认识到应对大学内部的决策过程进行分权。[10]随后,他推行了学术评议会的组织变革,在加州大学系统成立学术评议会代表大会,在每个分校建立了学术评议会分部,教师与行政人员的权力开始趋于平衡。在克尔治理期间,不仅伯克利分校发展迅速,整个加州大学系统由于克尔的1960年总体规划而更加有序。此后,伯克利加州大学治理的基本结构是在董事会下设学术评议会和以校长为代表的总校及分校行政。[11]
伯克利加州大学共同治理的初步框架是全美高校治理变革的开端。真正使共同治理制度走向合法化地位始于1966年由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简称AAUP)、美国教育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简称ACE)和大学与学院董事会协会(Association of Governing Boards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简称AGB)联合颁布的《学院与大学治理联合声明》。声明中指出美国大学和学院已经到了由董事会成员、行政管理人员、教师、学生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在大学各机构间共同承担责任、共同合作的阶段了。[12]《联合声明》不仅确保了教师在大学中的地位而且也扩大了教师参与治理的权力范围。从此,维护学术自由、重视学者权力的共同治理制度在美国高校推行开来,形成了内部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
伯克利加州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从建校到20世纪60年代是教师治理权力由无到有,范围由小到大的艰难博弈过程。基于知识权力格局视角,教师权力得到增长是由于这一时期的知识生产主要以学科为基础并且局限于大学之内具有非社会弥散性的特征,董事会外行人员和校长及其行政机构无法踏入这种专业化极高的学科知识领域,而深谙学科逻辑的教师是知识生产模式Ⅰ的权威人士,鉴于教师的专业知识,教师应对学术事务的决策负主要责任。因此独具的学科专业知识是教师在大学治理中权力扩大的依托,迫使董事会和行政机构让渡部分治理权。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