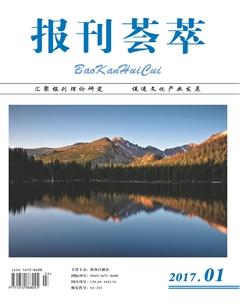《伤逝》是无爱的悲剧
摘 要:《伤逝》被认为是鲁迅小说中最复杂,最难解的一篇。研究者多从人物意蕴角度、文化角度(家庭文化、男性中心主义文化和两性文化等)、时代意义或叙事结构等角度对《伤逝》展开深入解读。其中对涓生和子君的爱情解读多也依附于“爱情与婚姻”的主题之上,基于对文本的细读,本文认为《伤逝》不是一场爱情的悲剧,更多的是一场无爱的悲剧。
关键词:《伤逝》;无爱;悲剧
幸福的恋情是相似的,不幸的恋情各有各的不幸。作为大胆追求自由解放的热血青年,涓生和子君的恋情是不幸且失败的。抛开外在和内在的压力,单从文本看起,单从涓生和子君看起,不难发现两人爱情从始至终都存在的虚无和空洞。
一、自私自利的涓生
《伤逝》写于1925年。其时天安门前轰轰烈烈的“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已六年,青年男女追求个性解放的步履终于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恋爱自由、婚姻自主被大众认可并蔚为一时风尚,自主选择的爱情被视为个性主义的表现和象征。
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不禁引人发问,涓生与子君的结合,究竟是源于真爱的吸引还是社会的召唤?正如涓生所言:“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涓生内心的苦闷加之外界的鼓动,便滋生了追求子君的冲动和寻找新生活的勇气。庄严的时代话题进入私密的谈情说爱中,一方面可以表现出两人的志同道合,另一方面却也埋下了危机的伏笔。涓生不清楚爱与欣赏的差别,他感到欣喜的事物他便要索取和占有。于是,涓生对子君的情感捕捉便是:“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誰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几句话很震动了我的灵魂……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读者看到涓生的狂喜想必会觉心寒,他的狂喜不是为子君本人或者子君的“情语”,而是为了一句追求个性解放的自我宣言。愛的注意力一开始就为“反抗”所转移,为维护自我选择的行为所遮蔽,而忽略了对选择的结果——爱的本身作更为切题的关注。当个体误把社会理想当作个人理想的时候,抽象的信念也就抽空了“爱”的具体内容。何况,子君只相信自己,而“自己”又是什么呢?一个潜在的事实是,“自己”的选择可能只是社会流行风气的一种反映而已。
“不但我自己的,便是子君的言语举动,我那时就没有看得分明;仅知道她已经允许我了……然而我知道她已经允许我了,没有知道她怎样说或是没有说。”涓生的自私可见一斑,他想要的是像电影中那样的求婚刺激,子君的存在只是为了填补他的需求黑洞。甚至“子君还卖掉了她唯一的金戒指和耳环。”即使这样,涓生仍然没有忘记为自己的贫穷和无能开脱,“我拦阻她,还是定要卖……”“五四”时期的独立自主精神充斥着涓生的脑海,他眼中的一切和心里的一切也便都是它。
所谓夫妻,便是要同甘共苦。涓生显然没有做到这点,他之于子君,更多的是索取,索取不到则是埋怨和冷漠。“尤其使我不乐的是她要装作勉强的笑容……但又何必硬不告诉我呢?”可是即便告诉了,涓生是否可以像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一样去保护自己的女人呢?现实是,他面对困难只会选择逃避,甚至在得知子君离世的消息之后,依旧在自欺欺人。“我不应该将真实说给子君……”显然,在涓生眼里,真正错的还在子君,因为子君居然承担不了一个“真实”的事实,宁愿生活在一个无所“真爱”的虚空中。那么,“真实”的含义究竟是什么?显然,真实的意义不在于涓生到底爱子君还是不爱子君,而在于涓生根本就没有正视自己罪孽的勇气,于是涓生便逃遁在“不爱”的自我欺瞒中。
二、自作自受的子君
《伤逝》前后唯有三处引述了子君的言语,三处均是情节转折的关键时刻,它成了叙事人极为节制地有所选择地展露人物内心世界的三个别有意昧的细节。
第一处是恋爱进行了半年,子君说出了“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乍一看去,这句话似乎是为了承载“五四”个人主义理念而出现的。仔细推敲,其实这句话可以表明子君在这场恋爱中的主动姿态,并为日后情节的逆向发展埋下了伏笔。并且这也可以和涓生的“其时是我已经说尽了我的意见,我的身世,我的缺点,很少隐瞒,她也完全了解的了。”这句话形成鲜明对比。这一欲抑故扬的态度与日后爱情悲剧的后果相呼应,并为涓生的责任承担作了开脱。但子君并不是真正了解自己,所谓“我是我自己的”也只不过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第二处是同居生活进入庸常阶段,情感贫乏的危机日渐暴露之际,涓生接到了局里的辞退函件,失业的厄运令“一个无畏的子君也变了色”,于是,她说了第二句话:“那算什么。哼,我们干新的。我们……”句末的省略号透示了人物的犹豫、茫然和对未来的恐慌。涓生感觉“不知怎地,那声音在我听去只是浮浮的。”其实按照叙事疗法,一个人所看的或所说的事物不一定真实,但是却一定是他内心想要看到或想要说出的事物。子君的话语也只是为了表现涓生的态度。简约的言辞有意无意地透露了她内在世界的苍白、贫弱和空洞。正如涓生所说“她所磨练的思想和豁达无畏的言论,到底也还是一个空虚”。这种弱点注定她没能力成为新式爱情的建构者。
第三处是当无爱已成为事实,涓生只是徘徊于说与不说之间的时候,子君开口了:“但是,涓生,我觉得你近来很两样了,可是的?你,——你老实告诉我。”不管涓生事后怎样为自己的说出实情而悔恨,直接促使他出“我已经不爱你了”的,其实是子君的这句话。它给涓生的逃离设了一个台阶,并促成了后面事态的发展。但是,这句话对于子君心理境况的透露,却十分有限。它除了暗示说话人对异性伴侣感情的变化有所察觉外,看不到有更多的内容。当涓生说“我已经不爱你了”,子君的反应是选择自动离开而保全涓生。看似洒脱的举止其实是对恋情的不负责任,作为始终默默付出的一方,因为一句话就不明不白地退出,稍显鲁莽和冲动。虽然无爱的恋情无法持久,但是也需要骄傲地离开。子君最终不幸离世,虽然死因不详,但读者大多猜测是因为无爱的悲剧。
参考文献:
[1]鲁迅.《伤逝》,《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12—113页.
作者简介:
李长培(1993—),女,聊城大学文学院2015级研究生,专业为现当代文学,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语言与文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