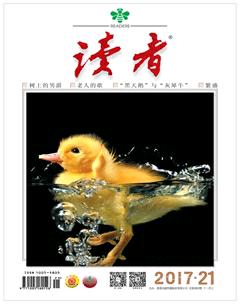课本里的食物
赵涛
每次吃豆腐炒肉都想笑。我想起小学课堂上,胖胖的徐老师给我们讲解“腐”字。他说:“你们看这个‘腐字,里头有个‘寸,还有个‘肉,把豆腐切成一寸一寸的,再放点肉,好吃得不得了!”然后全班同学都跟着流口水。
我上小学那会儿应该不存在吃不上饭的情况了,但童年时的我一直觉得饿。《武松打虎》那篇课文,最令人心旌摇曳的不是老虎出现之时,而是武松点菜那一段。我越朗读越坐不住,脑海里出现了一个盘子,盘子里铺着两三斤熟牛肉。我不爱吃肥肉,但牛羊肉必是有肥的才好。“小二,筛酒!”我心里暗暗嚷了一声。至今思来,这个“筛”字真妙,不光因为老家话也是这般说。如说“倒酒”,引不起人的遐想,至少对我而言是如此。“斟酒”是小心翼翼的,不自然。筛酒则足够活泼,似乎多了略微上提的动作,酒弧形注入杯中,沫子且激且泛,末了還要收一收。杯中酒真是热闹而又寂静。下课后,同学们争说熟牛肉,而我则独思这“透瓶香”。
讲《杨梅》那一课,也正当时令,杨梅下来,满街满巷都是。再好的杨梅,也只能骗骗舌头,吃多了真会连豆腐都咬不动。前一阵樱桃下来,老婆买了两斤,浸在盐水里。我问为何,说是樱桃招虫,盐水能把虫子泡出来。其实大可不必。就她的胃口,没泡出虫子还好,真泡出虫子,樱桃还吃不吃了?论招虫,杨梅可比樱桃要厉害,放盐水里泡,白花花一层。这是可以料想的。我家吃杨梅从来不泡,只过一遍水,只当虫子不存在。听同事说万物皆虫:山中虎豹,是谓毛虫;天上飞鸟,可称羽虫;水里鱼类,即是鳞虫;通常说的昆虫,以及虾蟹带壳之类,则另是一类虫。人也不是万物之灵长,不过一裸虫耳,与青蛙、蚯蚓同属。听了同事的“虫论”,我现在啥虫都不怕了,食堂菜里的大青虫都能淡然处之,搛至餐盘一旁,拨其身,数其节,定纲目科属,吃饭亦不忘格物致知。
《画杨桃》,让人觉得杨桃真别致,从那个切面角度看,的确是五角星。小时没吃过,长大也不是特别想吃,超市里有,从来没买过。一次女儿过生日,吃蛋糕时我吃到一片水果。老婆说,那就是杨桃。
《初冬》一课提到柿子。我至今不爱吃柿子,是因为不喜欢冬天的早晨。柿饼尚可接受,起的霜很有情意,不比天地间霜打草木的冷酷与冷漠。也是从同事处听闻,做柿饼,只有霜打过的柿子,才会起霜。我没办法求证,但对深秋的霜,也不再那么怨恨了。
(秋 伟摘自《品读》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