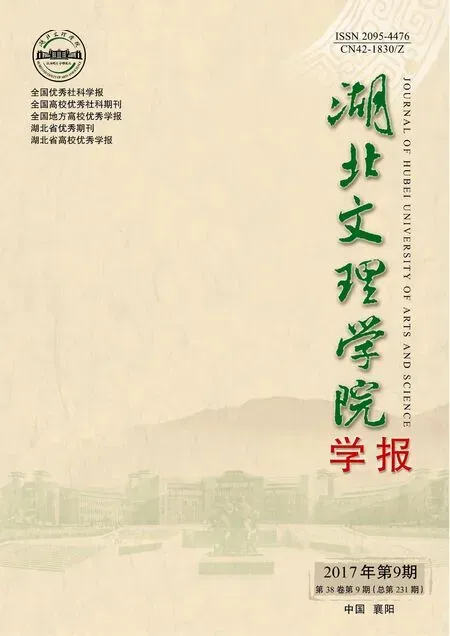《楚辞·招魂》“庐江”地望田野调查与研究
王芸辉,刘 刚,王 梦
(1.湖北文理学院 美术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2.湖北文理学院 宋玉研究中心,湖北 襄阳 441053;3.首都师范大学 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北京 100048)
《楚辞·招魂》“庐江”地望田野调查与研究
王芸辉1,刘 刚2,王 梦3
(1.湖北文理学院 美术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2.湖北文理学院 宋玉研究中心,湖北 襄阳 441053;3.首都师范大学 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北京 100048)
关于《楚辞·招魂》的庐江地望,历来多存歧说,莫衷一是,然均难与文本契合。通过对各家“庐江说”的评述与重要“庐江说”所关涉的青弋江、古潼水、古龙舒水故道的实地考察,并据《鄂君启节》所记泸江与《招魂》之庐江相参互证,经过深入地辨析,认为旧说舟节泸江为今安徽芜湖之青弋江或小淮水,既不合于《鄂君启节》铸制年代的时代背景,也不合于节文商路关卡标示的体例,疑点多多,难以成立;至于《招魂》庐江为襄汉间潼水说,其所言之“中庐水”,史无此水名称谓,而所指认的潼水又不曾通航,既不符合舟节航运的史实,也不符合《招魂》文本语境。因此可认定今安徽舒城县古龙舒水为庐江,龙舒水不仅符合舟节标示的地理条件与行文体例,而且符合《招魂》的文本语境与内在逻辑,当为《鄂君启节》与《招魂》共同记载的战国时代的庐江。
《楚辞·招魂》;庐江;《鄂君启节》;龙舒水
“路贯庐江兮左长薄”,这是《楚辞·招魂》乱辞中的一句话,意在描写作者与楚王曾经田猎的路向,其中“庐江”一词是研究作品写作时地与背景的一个“关键词”,历来倍受研究者所重视。值得注意的是,古往今来对庐江的注释一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至今还没有一个能赢得学界共识的说法。
一、古今“庐江”释说
最早为“庐江”作注的是东汉王逸,他在《楚辞章句》中说:“庐江、长薄,地名也。言屈原行,先出庐江,过历长薄。长薄在江北,时东行,故言左也。”南宋洪兴祖《楚辞补注》说,“补曰:《前汉·地理志》,庐江出陵阳东南,北入江。”[1]212
清洪亮吉等《嘉庆泾县志》卷二十八《辩证·论泾县水道第三书》则进一步考辨说:“总之,以桑钦、班固、许慎、韦昭等记载考道元之注,亦多有可印合者。桑钦云,陵阳县淮水出东南,北入大江;而班固庐江下注云,庐江出陵阳东南,北入江。所出同,所入同,道里又同,是淮水即庐江水也。”[2]12
《山海经·海内东经》说:“庐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泽西。”[3]332
关于《山海经》所记庐江,看似水流的发源、流经参照非常明确,但由于古今地名所指的变异和研究者认知的不同,却存在着诸多不同的说法:一、晋郭璞《山海经》注说:“彭泽,今彭蠡也,在寻阳彭泽县。”又于上条“浙江”注说:“按《地理志》,浙江出新安黟县南蛮中,东入海,今钱塘浙江是也。黟即歙也。”[3]333二、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与郭璞注不同,认为三天子都即为今之江西庐山,“庐江之名,山水相依,互举殊称。”[4]924三、清朱珔《文选集释·楚辞》说:“钱氏坫曰,庐江即今清弋江也。《海内东经》‘庐江出三天子都,入江。’下释云,‘彭泽西。’此彭泽非九江郡彭泽县也。丹阳郡宛陵县有彭泽聚,乃此彭泽耳。”[5]193这是据《山海经》衍生出的三个说法。
此外,关于庐江的地望还有清徐文靖的说法,其据《隋书·地理志》以为庐江指桂阳南平县之卢水,今人姜亮夫从其说[6]371。而此说仅据与庐江名称相近为说,而与《汉书》和《山海经》所记庐江发源皆有出入,且其水名晚出,更难以让人认同。
纵观上述诸种说法,均有着一个共同的疑点,即所指庐江均在长江以南,既不能与汉初庐江国(郡)辖域在长江以北相印证,又不能与《招魂》文本语境相吻合,因而清代一批楚辞学者便另辟蹊径,去寻找新的线索。如,李陈玉《楚词笺注》说:“庐江、长薄,皆近郢地。”[7]272贺宽《山响斋别集饮骚》说:“庐江、长薄,南征所经,纪其地也。”[8]583清王夫之《楚辞通释》则明言,“庐江,旧以为出陵阳者非是,襄汉之间有中庐水,疑即此水。长薄,山林互望皆丛薄也。右江左林,盖沿汉南江北而东游云梦之薮也。”[9]149其说源于《汉书·地理志》关于古卢戎国的记述。这一推测得到了今人谭其骧、陈子展的认同,并据《水经注》指实为古之维水,后世之潼水,且标注于谭氏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中。刘刚教授在认为《招魂》所招为楚考烈王之生魂的前提下,从而认为“庐江”不当在当时已被秦国占领的“襄汉之间”,因此据《汉书》所注卢子国的地望与此地古之“龙舒水”急言之可称“庐水”,认为“庐江”即为今安徽舒城县境内的古之龙舒水今之杭埠河[10]3-13,268-279。
二、相关“庐江”地望的田野调查
为了进一步了解庐江的地望,我们在以上说法中,选择出两种最流行的说法和一种最新的说法进行了实地考察,即对青弋江说(包括小淮水,因二水古时在入江处合流)、潼水说与龙舒水说的所指进行了考察,兹将调查印象报告如下:
(一)青弋江入江口鲁港调查
调查小组到达安徽省芜湖市后,对青弋江入江口与鲁港进行了重点调查。今青弋江入江口与鲁港并不在一处,青弋江入江口一段水域是镜湖区与弋江区的行政区分界线,而入江处是长江中路与长江南路的分界点,北临中西友好花园,南临长江长现代城,标志性建筑有临江大桥和中江塔。考察时,我们在临江大桥下滨江公园的观景平台上,时时可见有货运船只往来于临江大桥之下,或顺流驶入长江,或逆水驶入青弋江。桥上车水马龙,桥下航船穿梭,岸上游人如织,水中渔人撒网,好一派江滨城市的别一番景象。而鲁港在青弋江入江口南,沿长江南路里程计算约七、八公里。鲁港属于三山区,而临近于新设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处于长江南路的中段,在高新区管委会之西而偏南,标志性建筑就是鲁港大桥。考察时,桥下水已被截流,成了建筑工地,我们驱车从大桥下穿过,沿河堤路逆河道而上行,约四、五分钟,即看到截流河水的两道水坝,坝中水波不惊,有些许渔船停泊在岸边。我们在堤坝上树立的《芜湖市三山区防汛抗旱指挥部通知》中获悉,澛港大桥下正在施工的是“青弋江分洪道工程”。从鲁港流入长江的河今称漳河旧称鲁港河,与青弋江呈喇叭口状分布,也就是说二水在各自的入江处距离较近,直线距离约六公里,而逆追二水的流经则越来距离越大,最大距离约二十公里。这条漳河怎么为青弋江分洪呢?查看了芜湖市地图,我们发现青弋江与漳河两条河流之间,在三山区内,有星罗棋布、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河道、湖泊、堰塘,分布其间,有连接青弋江与漳河之势,如果将其连通,的确可以为青弋江分洪,保护芜湖市城区。这种连通之势,让我们想到,在古代青弋江是不是在鲁港汇合漳河而入江呢?后来青弋江改道才形成如今青弋江与漳河分流各自形成了各自的入江口呢?为此,我们查阅了《乾隆太平府志》,该书卷三《地理志·山川·繁昌县》说,“鲁港河(即今漳河),即鲁明江(即青弋江别名)穿港酾、丹阳余水入江处。”[11]25《太平府志》的记载证明,青弋江在清乾隆时原本是汇合鲁港河而入江的,今二水分流而形成各自入江之河口,理当为青弋江改道所致。《乾隆太平府志》“鲁港河”条下亦有“苦闭塞”的记载,证明鲁港河经常淤塞,这大概是青弋江改道的原因。
(二)古之潼水今之渭水调查
潼水,今称渭水。为湖北省襄阳地区的一条界河,在九集镇丁兰桥以东为襄阳与宜城之界,在丁兰桥以西为襄阳与南漳县之界。调查小组在古潼水今渭水流经中,选择了四个考察点,1、渭水入汉水处,其地古名潼口,今名小河口镇;2、建国后在渭水下游修建的渭水水库;3、渭水流域的卢戎国遗址;4、渭水中游的吴家集河道。渭水汇入汉水的河口处,河道不宽,约15米左右,水量亦不大,不见有船舶航行,唯有舢板类的小渔船停泊于渭水与汉水交汇处的汉水岸边。大概由于渭水水流过于细小,其与汉水交汇处的村镇才名之为“小河口”。位于襄阳市襄州区欧庙镇境内的渭水水库亦是个小型水库,蓄水量也有限,仅为农田灌溉而修建。拦河坝长不足百米,库区水面最大宽度在三、四百米左右,库区水面的延长距离也不过三、四公里。南漳县吴家集的渭水河道更窄,仅十米左右,水很浅,量很小,其流动也不明显。总之,从今之河道和流量来看,古之潼水今之渭水是决然不能通航的,邻近汉水、蛮河的当地人并不将其视之为名副其实的河,故以“小河”称之,甚至有的当地村民戏称为“小水沟”。即便在古文献中,我们也没有发现潼水通航的记录。春秋时的卢戎国都城遗址位于南漳县九集镇旧县铺村,渭水水库南支三八水库末端的西南岸,当地村民称之为“叶家土城”。据年长的村民介绍,“土城”原有夯土城墙,南北长约150米,东西宽约100米,早年由于平整土地取土的需要而被夷为平地。如今所能看到的“土城”遗迹仅有一段长约100米、宽约3米最宽处5米的城濠。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卢戎国都城遗址的遗存说明清王夫之关于潼水为庐江的推测有着一个方面的根据,然而在另一个方面,就潼水如今的河道现状分析,与襄阳附近的汉水支流清河、唐白河、蛮河(古夷水)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很难被古楚人称之为“江”。可见此水称“庐”尚可,称“江”则难以让人信服。更何况传世的文献中只有“卢戎”、“中庐”之地名,并没有王夫之、谭其骧所谓的“中庐水”。
(三)古龙舒水故道调查
据《光绪续修庐州府志》记载,今舒城县是庐江国或庐江郡的所在地,沿着龙舒水古河道留下了一些与古河道有关的遗迹,因此调查小组就选定了古河道沿岸的古代遗址“七门三堰:即七门堰、乌羊堰、槽堰”、“周瑜城”、“龙津桥”为考察重点。七门堰,位于干汊河镇七门堰村,东距舒城县城约15公里,遗址在古龙舒水今杭埠河的北岸,遗址处立有“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还树有汉羹颉侯刘信的半身大理石雕像并镌刻着他兴修水利的事迹,北侧有一石砌的水闸,当是七门堰从龙舒水引水的水闸。据宋代以来的地理类文献与地方志,刘信除修筑七门堰而外,还修筑有位于干汊河镇乌羊村的乌羊堰、位于城关镇西南郊金鸡墩的槽堰,然而由于古龙舒水改道两堰失去了水利灌溉的作用而早被废弃,因而遗迹无存。据李晖[12]考证,乌羊堰,“明万历年间龙口河(今名杭埠河)水南徙方家岗,以致堰口淤成陆地。”槽堰,“亦因明万历年间龙舒河水的南徙方家岗,而堰淤毁。”又据在七门堰挖堰渠的农民工介绍,乌羊堰就在瑜城村东北,已没有遗迹可寻了。于是我们便驱车到周瑜城进行实地考察。
周瑜城,位于干汊河镇瑜城村,东北距舒城县城约10公里。据考古调查,城平面近似圆角方形,长宽各近300米,面积约6万平方米,四围为夯土城垣,四周对称有四个缺口,疑似城门处。当地人称之为“周瑜城”,认为是三国东吴名将周瑜的故里,即周瑜24岁以前居住的地方。然而目前关于周瑜故里问题,尚存有很大的争议。不过据2012年的考古调查,在遗址内采集到周代陶片18件,于北缘水沟内采集到汉代的板瓦和筒瓦,看来这里为先秦两汉时的古城堡是可以肯定的。周瑜城南临古龙舒水,若以古河道论,当在岸边,如今距离稍远,计有千米左右。
根据遗址东北约2公里处的乌羊堰因河水改道而被废弃的情况分析,万历间龙舒水很可能就是从这里开始改道向南的,所谓“方家岗”即在周瑜城的东方。至于“七门三堰”的乌羊堰与槽堰,考虑到二堰已无遗迹可考,又据今本《舒城县志》已知乌羊堰位于干汊河镇乌羊村、槽堰位于城关镇金鸡墩,且获知金鸡墩所在地为南溪上游,我们路过二堰时便没有下车去漫无目标地寻觅,而直奔龙津桥去了。龙津桥,位于舒城县城关镇南门外的南溪上。据载,此桥最初为明嘉靖年间所建,后倾圮,万历间重建,清初毁于战火。今所见之桥,建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所建仿明代石桥旧制,而比明桥要短许多,为一座花岗岩平铺石板桥。长40米,宽3米,六垛五孔,垛高8米。桥头有碑,正面声明其为“全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背面镌刻着此桥的历史简介。其桥经建国后当地政府的多次维修,完好如初,仍然正常使用。一路考察而后,古龙舒水故道的流经在我们的头脑中逐渐清晰,古之龙舒水,至瑜城村周瑜城遗址起,不是像今天的杭埠河一样向方家岗方向流去,而流向东北的乌羊村(乌羊堰),而后又流向东北的金鸡墩(槽堰),最后流向金鸡墩东南的龙津桥,然后流入巢湖。考察记述到这里,我们还要申明的是,据古代地理文献和县志记载,龙津桥所在之处,至少在宋代就建有渡口,供往来船只停泊,且航运发达,历来有“龙眠古渡”之称,被古人誉为“舒城八景”之一。据悉,现今六安市交通部门亦有疏通杭埠河而恢复航运的规划。
三、《鄂君启节》与《招魂》“庐江”的考辩
1957年,安徽寿县发现了战国楚怀王六年(前323年)所制的“鄂君启节”四件,其中“舟节”铭文记有“泸江”,有力地证明了庐江地名在战国时期的实在。对于我们讨论《招魂》“庐江”问题大有帮助。谭其骧最初认为舟节“泸江当即庐江”[13]199。一年后,他又修正了自己的看法,以为铭文不当从商承祚释作“泸”,而应从郭沫若释作“浍”。在《再论鄂君启节地理答黄盛璋同志》一文中说:“‘淮’与‘浍’不仅声同,并且韵近,浍江当即桑钦所谓淮水,即今青弋江。”[13]220然商承祚所据为1960年新发现的一枚舟节,铭文清晰,释文不误,就是黄盛璋也纠正了释“浍”之误而改释为“泸”,并参考谭说,以为庐江指入江处与青弋江合流的小淮水。这为《招魂》庐江之研究又提供了新的线索。虽然谭其骧明确说舟节中的泸江与《招魂》之庐江无关,那是他在释舟节泸江前就认为《招魂》庐江指的是“湖北宜城、襄阳界上的潼水”,而不愿改变初衷。上文已经言及,今之渭水,古之潼水、维水或淮水,在《水经注》记载其水名之前是否有庐江或中庐水之名并无实证,只是研究者的推测而已。因而不能否定舟节泸江可以佐证《招魂》庐江的客观价值。
舟节研究者认为泸江是青弋江或在入江处与之合流的小淮水,并不符合舟节制于楚怀王六年的历史背景。青弋江或小淮水在今安徽芜湖一带,本属吴国,吴亡后属越。《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于是越遂释齐而伐楚。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彊,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集解》徐广曰楚灭越之时为“周显王之四十六年”[14]。按《史记·六国年表》,周显王四十六年(前323年),恰是楚怀王六年,其时舟节研究者指定的泸江所在刚刚被楚国攻占,楚国是否实际控制了该地区,并立即在那里设置通商口岸,即所谓“庚爰陵”,尚有待深考。又《资治通鉴》[15]65记楚威王杀越王无彊在周显王三十五年(前334年),其纪年为楚威王六年,早于楚怀王制舟节时十年,似乎有在泸江即今芜湖一带设置通商口岸的条件。但这个时间当是“杀王无彊”的纪年,而不是楚最终灭越的纪年。这里且先不计较《集解》说与《通鉴》说孰是孰非,即便以《通鉴》纪年为准,从楚威王六年到楚怀王六年这十年间,其地政局尚未稳定,或仍属越国自治。《水经注·河水》引《纪年》说,“魏襄王七年……四月,越王使公师隅来献乘舟始罔及舟三百、箭五百万、犀角、象齿焉。”[4]106魏襄王七年(前328年),为楚怀王元年。越有献于魏,且所献为大量舟战物资,说明越国尚有相当的军事实力,并未甘心臣服于楚,仍在联络魏国钳制楚国,别有它图。又《绎史》引《越绝书》说,“越王夫镡以上至无余久远,世不可纪也。夫镡子允常,允常子勾践,大霸称王,徙琅琊都也。勾践子与夷时霸,与夷子子翁时霸,子翁子不扬时霸,不扬子无疆时霸。伐楚,威王灭无疆。无疆子之侯窃自立为君长。之侯子尊时君长。尊子亲失众,楚伐之,走南山。亲以上至勾践凡八君,都琅琊,二百二十四岁。无疆以上霸,称王。之侯以下微弱,称君长。”[16]2996这是说,楚威王杀越王无疆后,越又传三世。在此三世间,越虽臣服于楚,但仍怀“卧薪尝胆”之异志,所以楚人不得不再次举兵征伐。而这次征伐,按时间推算当在楚怀王之时了。《越绝书》的记载还可以证明,《越王勾践世家》所记,并非仅限于“杀王无彊”一年之事,而是概括了从“杀王无彊”直至越最终被灭的全过程,这个过程当经历了较长一段时间。因此《集解》徐广说楚灭越在周显王四十六年,绝非无根之谈甚或误记,当是楚人最终灭亡越国的时间。《汉书·地理志》说:“粤(越)既并吴,后六世为楚所灭。”[17]1668也证实了这一点。既然如此,那么楚怀王六年灭越后是否立即在那里设置了通商口岸或商检关卡,并立即派遣商船到那个刚刚平定的地方进行贸易,就不能不让人生疑了。
据现代古城址考古,今安徽芜湖市东21千米芜湖县黄池乡(旧属宣城)有楚王城遗址,当地俗称土王城或土皇城。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部门曾对遗址进行了多次调查,从城址南垣采集的绳纹板瓦等遗物分析,这座古城应建于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18]319-320。这便印证了楚怀王时代楚国方占有芜湖一带的史实。
此外,舟节研究者认定的泸江通商口岸或商检关卡“爰陵”是古之宛陵,今之宣城,并不像舟节所记其他的通商口岸或商检关卡均在其水道附近,而在今水阳江(古称清水)边,距青弋江还有一定的距离,距小淮水就更远了。这里有个问题须要说明,《光绪宣城县志》[19]卷四《山川》载,“城西六十里曰清弋江,源出石埭,泾、太及宣之西南诸水皆入焉。”原注:“宣城旧治于此。”又卷三十七《古迹》载,“宣城旧城,在城西青弋江。”这很容易让人误会“爰陵”在青弋江边,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该志《古迹》又载,“汉宛陵故城,即今(指清光绪时期)县治,汉初置丹阳郡治,晋改为宣城郡治。”据此分析,其地改称宣城后治所始在汉宛陵故地,即今宣城城区,其后曾经一度迁至青弋江边,后又迁回爰陵,所以《志》称“宣城旧城”。由此可知,今之宣城市所在地才是古宛陵。既然宛陵距青弋江有六十里的距离,那么泸江为青弋江或小淮水之论,就难以自圆其说了。我们在考查安徽芜湖时了解到,今天的青弋江与水阳江在芜湖市与芜湖县交界处汇流,同在临江大桥处流入长江。这是青弋江改道后的情况,青弋江改道前是与漳河汇流在鲁港入江的。清代以前青弋江与水阳江并不相通,因此若认为舟节之“爰陵”是古之宛陵今之宣城,那么鄂君商船所到就不是舟节之“泸江”今之青弋江,而是水阳江了。
以舟节与车节所通关卡均设在楚国实际控制且相对安全的范围内这一事实来看,考证舟节泸江的地望还当立足于楚国既定的实际控制区内。因此谭其骧最初关于舟节泸江的释说还是有可以借鉴之处的,他说“有见于《山海经·海内东经》、《汉书·地理志》庐江郡下、《水经·庐江水篇》的庐江”,“是在长江南岸,而铭文中的‘泸江’,却显然应在北岸。那么这条‘泸江’究应何所指?我以为指的是汉代庐江郡得名所自的那条庐江”,“应在长江北岸今枞阳县附近。”[13]199-200我们同意舟节泸江在长江北岸,是汉代庐江郡得名所自的那条庐江,但对他推测的庐江“即今安徽庐江、桐城、枞阳三县境内的白兔河”,则存怀疑。舟节泸江可资参照的地名有松阳、爰陵,谭说松阳“当即今安徽枞阳县”[13]199,正确,可从,是鄂君商船沿长江行进的必经之地,经过此地方可进入泸江。谭氏据此推测舟节泸江即是在枞阳入江的白兔河,思路是对的,但白兔河古既无庐江之名,也无与庐江有通假关系的名称,指认白兔河为庐江,仅仅是因为其河流经汉庐江郡旧治舒城县故城,这便犯了他据古卢戎国指认古潼水今之渭水为《招魂》庐江相同的错误,未免有主观臆测、举证不足之嫌。谭氏以通假的方法指认《名胜志》引《水经注》提及的今桐城东六十里的团亭为舟节中鄂君商船沿泸江抵达的“爰陵”,也显得牵强,并无佐证的支持。因而对于舟节泸江,还需按照谭氏的庐江在江北的思路继续考索。
其实,在长江枞阳段以北有今之杭埠河,古之龙舒水,值得注意。《光绪续修庐州府志》[20]卷七《山川下》载:“龙舒水,《左传》杜预注曰,庐江西有龙舒,即此水也(《舆地纪胜》)。按龙舒河淤塞已久,后徙县治南,距城七里,今所谓前河是也。”又引《采访记》说:“前河,发源枯井源,东流至多智山,三入河南合平田水、屏风山水,又东过晓天镇北折,至大河口合阳山寨水东北流,至巴洋河合西山毛坦厂、毛竹园水东流,过梅山麓合南山庐镇关乌沙水,北至龙河口过九井,至小河口合南山汤池水东经七门山,至新河口由周瑜城南过七里河,至白毛荡合东西二谼孔家河水东流,至三河合后河水由庐江界之迎水庵入巢湖。河自源迄三河,行舒城者二百余里。此邑之经流所谓前河也。”“此据现在河道言之,古河道则前河自七门山北折东流,至县城南溪入巢湖。今所谓县河是也。久已淤废,惟巨涨乃通。”又于“南溪”条说明,“南溪,在南门外,发源孤井(即上文枯井源)去县西百五十里,东南流经七门堰归巢湖。龙舒水在城南三里,即南溪也(《名胜志》)。”以此知,古龙舒水虽曾改道,但流向没有太大的变化,又据我们的考察,当指周瑜城至乌羊堰、又至槽堰,再至龙津桥,最后抵达巢湖的一段。我们说龙舒水值得注意,主要因为:一是此水古称龙舒水,“龙舒”二字急言之,即将“龙”古来纽与“舒”古鱼韵平声相拼,正是来纽鱼韵平声的“庐”字。此水似可称“庐水”。二是龙舒水流域在春秋群舒境内,又邻近汉庐江国(郡)之治所所在地,而群舒之地即为汉应劭《汉书·地理志》[17]1569“庐江郡”下所注的“故庐子国”。清人多认为应注将地处宜城襄阳间的卢戎国误置于此,故考辨庐江时置其说于不顾。按学理,应劭当有所据,只不过其据亡佚,后人无从考索而已,因而应注不可轻疑。此可为龙舒水似曾称“庐水”之佐证。三是古龙舒水近处有团箕城。《光绪续修舒城县志》[21]之《古迹》载,“团箕城,《隆庆志》县西十里。”并作按语说:“按诸书所载古城十余所,大半淹没,今可考者亚夫、周瑜、霍湖三城而外有韩塘城、花园城、余家城、石家城,皆距县治西北十余里,土垣周遭,中平旷,有井泉,下多瓦砾,其为戍守之地,抑即古舒故城,皆未可决。”此团箕城若简称为“团城”,即可与舟节“爰陵”通假。此团箕城,“团箕”二字当就城之形状而言,我们所考察的周瑜城正是“圆角方形”,与“团箕”正相符合,距县城距离也比较接近,且临于龙舒水古河道北侧,故疑周瑜城遗址有可能即为《光绪续修舒城县志》失考的团箕城遗址,或为团箕城遗址同类的古城堡遗址,有助于对团箕城遗址的认知。此说若可成立,亦可作为指认舟节泸江之证。四是舒城县境内亦有称“三天子都”之山者。《光绪续修舒城县志》载,“洪涛山,县东南六十里,峡石关东,跨舒、桐、庐三县界。亦名三天子都。(原注:一曰金字寨,俗呼天子寨。)山势极峻,曹操曾屯此。此山发源之水,经界牌山后称新店河,为龙舒水支流中最大者。其山名是因《山海经》所记庐江发源而附会,还是本有其名,不敢妄断,即便是附会,也至少说明古代早已有人认定龙舒水是为庐江了。五是龙舒水上游支流有源出庐镇关者,即今龙河口水库的主要水源之一乌沙河。此庐镇关当为应劭所谓庐子国之名的孑遗。六是经龙舒水入巢湖,船只可由巢湖东界经濡须水(又名运漕河,今名裕溪河)入长江。也就是说,鄂君商船过松阳后沿江而下至濡须口西转驶过濡须水可横穿巢湖入龙舒水。龙舒水虽然不直接入长江,但也符合舟节记水的体例,如舟节所记经由长江进入湘、、资、沅、澧、油诸水,都要穿过今称洞庭湖的战国时之大泽(屈原《九歌》已有洞庭之称谓),但均省而不记。因而符合舟节“逾江,庚彭,庚松阳,内泸江,庚爰陵”的记述。七是舟节最后抵达的地方是郢,车节最后抵达的地方也是郢,不过舟节以所“庚”之地交待了去郢的通关路线,而车节没有以所“庚”之地交待去郢的路线,“庚居鄵(居巢)”后,便直接交待千里以外的终点“郢(楚都纪郢)”。分析其中原因是因为车节与舟节本是一体的通关节符,通关所经可以按需使用,有着“接力”的关系,如车节起始“自鄂往,庚阳丘”,即是“取道水路中的西北路至今南阳盆地,然后舍舟乘车,取道‘夏路’,东抵阳丘”[13]203-204,走了相当长的一段水路。以此推知,车节终点“庚居鄵,庚郢”,其间也当走相当长的一段水路,而这条水路非紧邻“居鄵”的庐江而莫属,即由庐江入长江,然后溯江经“松阳”、“彭”而抵达郢。如果将由“居鄵”至“郢”的通关路线理解为原路返回,再由“阳丘”经水路去“郢”,那么则未免重复记述通关关卡,既失去了节符标示商路所经关卡的意义,也不符合舟节和车节只标示去路关卡而隐含回路关卡的体例;如果指认江南青弋江等为庐江,那么车节去郢的通关路线“庚居鄵”后,就被留下了一大段难以合乎商运通关规制的空白。八是从舟节和车节的通关所经看,可以说基本上覆盖了当时楚国实际控制的东、南、西、北各个地区。车节所经是连接舟船难通的楚西北部至东部之水上商路,西北物产可经车路运至东部(居鄵),再经庐江等东部水路运抵郢;东部物产亦可经车路返回运至西北部(阳丘),再经汉江等西北部水路运抵郢。可见,舟节和车节所通商路的设计是非常科学的,是按照当时商路地理的客观实际情况设定的,切不可凭主观的以文献地理简单对接的方法去解读。综上所述,龙舒水当为舟节所记之泸江。若将龙舒水指认为舟节泸江,要比指为青弋江或小淮水更具理据。

[1] 洪兴祖.楚辞补注[M].白化文,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
[2] 洪亮吉.中国地方志集成·嘉庆泾县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3] 袁 珂.山海经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4] 郦道元.水经注校证[M].陈桥驿,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
[5] 朱 珔.文选集释·楚辞[M]//楚辞文献丛刊:第21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
[6] 姜亮夫.楚辞通故:第一辑[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7] 李陈玉.楚词笺注[M]//楚辞文献丛刊:第39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
[8] 贺 宽.山响斋别集饮骚[M]//楚辞文献丛刊:第46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
[9] 王夫之.楚辞通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10] 刘 刚.宋玉辞赋考论[M].沈阳:辽海出版社,2006.
[11] 朱肇基,鹿园甫.中国地方志集成·乾隆太平府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12] 李 晖.万古恩同万古流——论“七门三堰”及“三堰余泽”[J].合肥学院学报,2007(6):122-126.
[13] 谭其骧.长水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4]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5] 司马光.资治通鉴[M].胡三省,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
[16] 马 骕.绎史[M].王利器,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2.
[17] 班 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8] 曲英杰.长江古城址[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19] 李应泰.中国地方志集成·光绪宣城县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20] 黄 云.中国地方志集成·光绪续修庐州府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21] 彭鸿年.中国地方志集成·光绪续修舒城县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22] 石 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
[23] 陈 伟.楚东国地理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陈道斌)
I207.223
A
2095-4476(2017)09-0021-06
2017-09-04;
2017-09-14
王芸辉(1976— ),男,湖北襄阳人,湖北文理学院美术学院讲师; 刘 刚(1951— ),男,黑龙江哈尔滨人,湖北文理学院宋玉研究中心教授; 王 梦(1991— ),女,湖北丹江口人,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