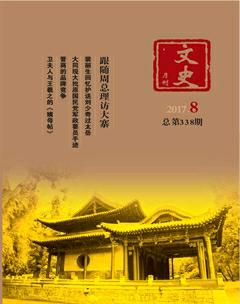从皇华馆到东缉虎营
九、从全面“清队”到局部“平反”
1968年夏天,根据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全国上下开始“清理阶级队伍”,从而把文化大革命运动再次推向高潮。我父亲是统战人员,不在清理范围之内,所以没有受到太大冲击,但是母亲却在这场运动中吃尽了苦头。
“文革”开始后,母亲也受到冲击,但总的来说问题不大。比如有人批判她嫁给一个高级官僚,她立刻反驳说:“我出嫁的时候,他还是个学生!”后来学校里停课闹革命,成立造反派组织,只有她和另一位“有历史问题”的女老师未被接纳,于是两个人便成了無所事事的逍遥派。
清队运动开始以后,全区的小学教师被集中到五一路小学封闭起来,不准与任何人见面。母亲在1949年以前一直是家庭主妇,唯一担心的是她是否参加过“反动组织”同志会。
对于这个问题,母亲自己也不大清楚。因为父亲是同志会太原市分会主任,所以她多次询问父亲,是不是也把自己拿去充数。父亲苦思冥想,好像也不能给出一个准确答案。现在看来这事很容易理解,因为许多人参加同志会就是填写一张表格,有时候还是别人代填,本人根本不知道。但是“清队”的时候人家却不这样理解,以为加入同志会就和加入共产党一样,不仅要宣誓,还要交纳党费。
清队运动结束以后,母亲告诉我,在北城区小学教师的清队运动中,问题最大的是她和富英。母亲的问题在父亲身上,所以她被逼急了还可以往父亲身上推,富英是五一路小学的老师,一直是全国劳动模范、全市教师学习的典型。所以她的罪名是资产阶级教育反动路线的代表,要她交待与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关系。
这次运动的高潮是在杏花岭体育场召开大会,富英和母亲被押上主席台,以“喷气式”姿势接受群众批判。
清队运动之后,母亲与富英结下了患难之谊。我结婚以后才知道,富老师的爱人叫常春厚,也是榆次常家的后代。他一直在山西省公路局工作,与我爱人是同事,退休前是局里的总会计师。 时隔不久,为了贯彻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先是知识青年下乡插队,后是机关干部下放劳动。想当初“地富反坏”“牛鬼蛇神”被赶出城市,如今赶他们的人也遭遇同样命运,仿佛是老天和大家开了个巨大的玩笑。
有意思的是,因为父亲不属于革命干部,居然躲过了这次劫难。大家走了之后,机关对我父亲的控制也形同虚设。在此之前我就隐隐约约地感到,父亲迟早会有平反的一天。有一次闲聊,我半开玩笑地对父亲说:“等到政策落实的时候,也许会给你补发那被扣的工资。”父亲觉得我在说疯话,便制止道:“不要胡说八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却不肯罢休,还为此算了一笔账,看看能补发多少钱。
大约在1970年春节之前,由于形势有所松动,父亲被扣的工资居然全部发还,总数在5000元以上,这在当时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后来我才知道,“文革”时扣发工资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被遣送回家者,他们的工资已经被财政厅扣发上交国库;另一种是没有被遣送回家的,他们的工资仍然由财政厅按月发放到所在单位。父亲属于后者,所以省政协只好把扣发的工资存入银行。时间一长,他们觉得这也不是办法,所以乘着形势松动,就把这些钱还给我父亲。
这笔钱到手的时候,正好是冬天来临,母亲根据我的提议,先给二哥买了一件人造毛皮大衣。当时人造毛皮刚刚问世,外表看上去非常漂亮,所以她又去华泰厚为我和妹妹各做一件,并把她和父亲的狐皮大衣换了面子。华泰厚是位于柳巷的一个老字号服装店,在老太原人心目中享有盛誉。没想到衣服做回来以后,却拙劣不堪,极为失望。这才让我认识到自从公私合营以后,老字号早已是徒有虚名,而我们在“文革”中还慕名而至,真是愚不可及。因此,我那件花了高价定做的人造毛皮大衣,只能长期压在箱底,最后卖给收破烂的了事。
此外,母亲还为我买了一辆自行车。当时我还在农村插队,每天下地干活,农民都骑着自行车,只有我安步当车,其实是苦不堪言。不久大妹参加工作,母亲为她也买了一辆。
十、从下乡安置到回乡探亲
机关干部下放以后,父亲也被安置到山西稷山,住在县城里的一个大院。当地还专门给这个大院取名为“团结大院”。同时被安置的还有省市统战系统的许多老人,大概有二三十户。
父亲平时工作繁忙,很少与别人交往。这次下去有了闲暇,所以交了许多朋友。别人大多是全家安置,我家只有父亲一个人下去,所以吃饭就成了问题。好在父亲平时在家做饭时经常给母亲打下手,做点简单的饭菜也还可以。因为是安置,没有什么事情,所以父亲经常回太原探亲。那年秋天,他带回来许多稷山枣,说是专门跑到正宗产地买的。所谓稷山枣,严格地讲也就是一个村子里的那几十棵枣树。这些稷山枣皮薄核小,糖分很高,是我吃过的最好的枣子。
就在这时,两个远房叔伯兄弟为争房产的事让父亲产生了回去一趟的想法。我的曾祖父是清代举人,曾在县书院担任山长(书院院长)。他在村里盖了一个高大的院子,听奶奶说门口还有旗杆,既威风又阔绰。曾祖父有五个儿子,我爷爷是最小的一个。他去世以后,兄弟们分家,爷爷也得到一份,我父母是抗战前夕结婚的,为此奶奶还做了精心的准备,其中包括两大箱全新的衣服被褥。抗战开始后,爷爷奶奶扔下所有东西带着母亲逃难,从此就再也没有回去。为此,奶奶在世时经常唠叨说贵庭把她的东西都变卖了。
这个贵庭是长门长孙,他的年龄与父亲不相上下,却与我是同辈,所以称我父亲为叔叔。他还有一个弟弟,名叫贵如,他们一直住在那个大院。对于祖上的遗产,我们从来没有放在眼里。如果他们能够和睦相处,当初爷爷分到的那几间房子也就归他们了。可能是因为当哥哥的比较强势吧,所以二人总是因房产发生纠纷,并多次找到了我的父亲。
父亲无奈,只好专门回乡一趟。回乡之前,他与奶奶的三弟即自己的三舅通信,询问对方需要什么。对方说想要一台三五牌座钟。于是我去解放路百货大楼买了一台,父亲便带了回去。这些年有人根据谐音说给人送钟就是送终,但当时人们并没有那么多忌讳。endprint
父亲回去以后,本来要把我家的房产分给他们,但他们还是闹得不可开交。无奈之下,父亲只好把房子捐献给生产大队。为此,他还以大字报的形式发表了一个声明。村里从来没有遇过这类事情,但又不好拒绝,只好接受。
前两年我从北京开车回太原,还专门下了高速去老家一趟。太原到定襄虽然很近,但我只是在很小的时候跟奶奶去过三老舅舅家一次。至于自己的老家南西力村是什么样子,我从来不知道。那次一进村子,正好遇到支书和村长,他们为了续修家谱,正在打听我们一家人的下落。我想看看当年的老房子,他们说早就拆了,拆下來的材料盖了村里的学校。
父亲那次回乡,还落实了我们的家庭成分。因为我们家没有参加过土改,所以我从小就不知道应该如何填写家庭成分。基于诚实,我一直在家庭成分一栏填写“旧职员”,并因此深受其害。直到家庭成分不重要了,我才变成了“中农”的后代。这种情况,回想起来特别好笑。
十一、林彪事件引发的灾难
1971年4月,我结束插队回到太原当了一名小学老师。回城之前,父亲问我:“你不是不愿意当小学老师吗?”我回答说:“插队以后,我才明白城市户口意味着什么。为了恢复城市户口,就是回城掏大粪我也愿意。”我还说:“今天我能当小学老师,明天就能当中学老师,后天就能当大学老师。”
对于儿子口出狂言,父亲什么话也没说。但我心里明白,这次回城当小学老师,与师范学校停办多年有关。既然如此,中学老师荒和大学老师荒就会接踵而至。
当了小学老师之后,学校里虽然实现了“大联合”,但是派性还很严重。因为女老师占大多数,所以两派对我都很好,但我心知肚明,始终保持中立。
学校里有个男老师,比我略小几岁。1971年国庆节刚过,他悄悄对我说:“大智,告你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林彪逃跑了!”这话让我大吃一惊,但是却不敢相信。当时我发自本能地感到,如果真是这样,那可是一件天翻地覆的大事。我问他消息来源,他说是听一个家在省革委的同学说的,绝对可靠。
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首先翻阅国庆节的报纸,仍然是毛主席和和林彪的巨幅照片;又查看《参考消息》,也没有任何蛛丝马迹。下班以后,我先到五一广场察看动静,当时广场主席台上依然挂着两人的巨幅画像。又跑到五一路新华书店,林副主席的画像也赫然在目。这时我才发现自己有些愚蠢:如此重大的事件,还没有逐级传达,怎能在公众场合有所反应?
回家以后,我模仿那位老师的口吻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全家。没想到“骇人听闻”四个字,对大妹妹刺激巨大,以至于患上了精神性疾病。
我这个妹妹小时候就因感冒而导致惊厥,后来早已痊愈。1966年初中毕业后,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一直找不到工作,所以她把家务活全都包揽在自己身上。直到1970年以后,她才在街道居委会的帮助下去了房地局修缮公司下属带锯厂当了一名工人。进了工厂以后,正遇上批林批孔运动开始,有一天师傅让她早点下班,路过五一广场时顺便抄抄大字报,为大家提供些学习材料。那天回家以后,她好像有点恐惧的样子,并对我说她有点害怕。我问她害怕什么,她也说不清楚,只是说除了心慌就是害怕。当时我们根本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所以也就没当回事。
第二天下午,她被师傅送了回来,说可能是劳累过度,需要好好休息一下。这时她的恐惧心理明显加大,就连拉电灯开关的声音也感到害怕。父亲闻讯后马上返回太原,带她到处看病。当时太原市已经有专门的精神病医院,但我们特别不愿意把她送到那里,觉得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那是个可怕的地方。
病情稍稍稳定之后,父亲带她到稷山疗养。在父亲的精心照料下病情明显好转。第二年夏天,她返回太原重新到单位上了班。没想到过了一个月左右,她的病又犯了。这次犯病以后,她开始狂燥不安,与家里人吵闹,甚至到处乱跑。父亲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来信说,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女儿会是这样,由此可见他内心的痛苦和煎熬。
为了照顾病人,父亲立刻返回太原。由于害怕她在外面出事,每逢她要出门,我总是暗暗跟在她后面。后来我身上长了个浓疮疼得要病,这事就落在父亲头上。有一次父亲气喘吁吁地回来说,妹妹跑得太快,把他甩了。这时我才发现父亲已经年过花甲,如此残酷的事实早已让他心力交瘁。
由于妹妹的病情越来越重,再加上害怕父亲难以承受,我力主把妹妹送往专门医院治疗。但是要送她到医院也不是容易的事。我试图带她乘公交车前往,但下车以后她就不干了。无奈之下,父亲只好向省革委统战办公室求救。那里派了一辆大卡车,我们费了很大力气才把妹妹劝进驾驶室。为了能够制服她,父亲让我也坐在里面,自己爬到后面的马槽(货厢)里。到了医院之后,我想先下车扶父亲一把,没想到车刚停稳,他就跳了下来,让我特别心痛。
妹妹住院之后,家里安静许多。但父亲由于操劳过度,患了感冒。到附近的太原市中心医院看病,说是胸膜炎。又过几天,发现痰里有点血丝。经过透视,医生建议去山医三院做进一步检查。
在这种情况下,母亲找统战办公室要了一部212吉普,和我一同把父亲送到三院门诊部。医生给父亲拍了X光片,看完片子之后,他让我们去住院部找内科的段大夫。段大夫摸了一下父亲的锁骨,立刻决定让父亲住院。等到我们把父亲安顿好以后,段大夫把我们叫到办公室,沉下脸来说:“病人情况不好,你们准备后事吧。”
十二、最后的100天
这简直是晴天霹雳!一个活蹦乱跳的人,怎么刚进医院,就让我们准备后事呢?当时我哀求她,能不能想想办法,她义正词严地拒绝了我,说这是绝症,死亡是迟早的事。在这位大义凛然的医生面前,我特别渺小,特别无奈。与此同时,她那瘦长的脸就像恶狼似的;身上的那件白衣,却好像长满一卷一卷的毛一样。
父亲住院以后,主要是通过静脉注射使用一种名为环磷酰胺的药品。这种药品副作用极大,父亲使用一周以后,食欲明显下降,两周以后出现恶心、呕吐等症状,为此我和母亲想尽一切办法也无济于事。endprint
病床旁边靠窗户的一侧,住着一位工人师傅。也不知什么原因,他与段大夫的关系特别好。段大夫每天查房,对别的病人总是凶相毕露,但是到了师傅床前却满脸堆笑。有一次这位师傅当着大家对段大夫说:“我儿子给你带来一把火钳子,放在你的办公室了。”段大夫更是笑得大嘴难合,乐得满脸开花。
这种火钳子是夹蜂窝煤用的,当时普通工人对领导文化大革命早已失去兴趣,而是利用工厂的设备和材料做些日常生活用品,既不用花钱,又可以送礼,可谓一举两得。
但是,段大夫的笑脸并不能挽救师傅的生命。师傅患的是肝癌,但他和大夫都说是肝腹水,小肚子鼓得气球一样。每天晚上,他都疼得直叫,那声音撕心裂肺,特别恐怖。父亲本来就神经衰弱,病房里六个病床,加上陪侍的家属,白天至少有十几个人,根本无法入睡。好不容易熬到黑夜,又遇上这么一个肆无忌惮、拼命喊叫的病人,真是苦不堪言。为此母亲曾找过省革委统战办公室,希望他们能够出面,让医院给父亲安排一个单间。据说办公室也派人前来联系,但被院方拒绝。
没过多久,这位师傅就因为病情恶化转移到急救室。说是急救,其实是怕死在病房,所以那个地方就成了医院的鬼门关,只要进去就别想回来。这时恰逢清明前后,病人们陆续被转移出去,一个急救室不够用,只好再加一个。工人师傅走后,又住进来一位瘦弱的老人,好像也是肝癌。他走的时候,都没有来得及往急救室送。自从那个师傅走了以后,段大夫就回老家探亲去了。听说她是清徐县王答公社人,离我插队的地方很近。
父亲住院期间,我正好在太原市教育干部进修学校参加为期一年进修。春季开学以后,为了侍候父亲,我几乎没有去过一次。当时母亲在家做饭,我一刻不离地陪在父亲身边。病人长期卧床不起,很容易患上褥疮。后来我发现父亲背部皮肤破裂,可能是褥疮前兆。为不让这个疮面恶化,我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个大车内胎,给他垫在身下,尽量避免与褥子接触,效果特别好。父亲躺得时间太长,感觉浑身发痒。也许是父子之间心有灵犀吧,我在为他搔痒时,总能搔到他最需要的地方。
在此期间,省民革主委、民政厅厅长杨自秀来信慰问,说他不能親自来医院看望,希望父亲好好养病。杨先生当时已届古稀之年,他虽然一笔一划都是弯弯曲曲的,但却写得非常认真、遒劲有力。
为了陪侍父亲,我晚上睡在一个能够折叠的担架上。起初还觉得不错,但时间一长就浑身酸困,有种休息不过来的感觉。这时二哥也回来了,我想让他在夜里替我几天,让我晚上好好休息一下。但是父亲却不愿意让我晚上离开。理由是如果晚上难受起来,怕影响别人休息。
也不知道是环磷酰胺的破坏还是癌细胞的攻击发生了作用,父亲在顽强地抵抗了整整三个月之后,终于败下阵来。4月中旬的一天,面容消瘦的父亲被转移到急救室,这等于是宣布抢救无效放弃治疗。
进了急救室以后,父亲呼吸受阻,我们借来了吸痰器为他吸痰。据大夫和护士说,吸痰器不能吸痰,所以他们都不使用。我不相信他们的说法,结果发现问题在于使用者的态度。通过试验我发现吸痰的软管只有一个小孔,如果你只是简单地把它从气管里插进去,就只能吸到对着小孔的痰液。于是我先是转动软管,后来又在小孔的对面剪了一个孔,这样一来,痰就基本上被吸光了。
我讲这些故事是想告诉大家人的潜能是无穷的,做任何事情只要肯动脑子,外行也可能超过内行。
有一天上午,父亲突然要说什么,但是却说不清楚。二哥听了半天,根据他的口形和声音,估计他是想见有关领导一面。于是我回去找统战办公室,二哥继续留在父亲身边。统战办公室来人之后,二哥已经把父亲的遗嘱记录下来。遗嘱很简单:一是把自己的病体捐献出来,供医学研究使用;二是葬礼从简,遗体火葬。
1973年4月26日下午,我在中午的时候回家休息,顺便给母亲做点晚饭。因为过于疲劳睡到3点半左右,醒来随便做了点汤面匆忙赶往医院。进入急救室以后,二哥急着说你可来了,爸爸的脉博停止跳动已经十几分钟了,之前他一直合不上眼,显然是想见你一面。见此情景,我扑在父亲身上边哭边喊,没想到父亲居然又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从来不相信所谓迷信。但是这一次我还是信了,我觉得父亲在半路上显然是听到我的呼喊,向我有所回应……
三天以后,当我们来到太平间准备送父亲去火葬场的时候,父亲的遗容已完全变样。我意识到这是捐献病体所致。
父亲是在龙山火葬场火化的,当时这个火葬场非常冷清,几乎没有什么人。从此以后,一个山医三院,一个龙山火葬场,都给我留下最伤心的痛。
2015年清明前夕,写于北京昌平。
(六)endprint